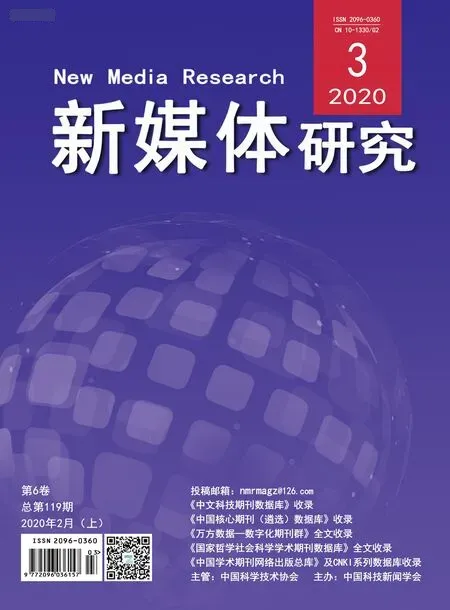弱傳播視閾下的輿論失焦與矯正路徑
齊宇軒
摘 要 新媒體的技術賦權構建了個體討論的公共領域,卻也導致了公眾輿論的頻頻“偏向”。輿論失焦已成后真相時代一大特征,引發的負面效應更不容忽視。以2020年12月被確診新冠肺炎的成都女孩的相關輿論為分析對象,借助弱傳播視角對此次網絡輿論的失焦機制、由此衍生的網絡暴力與用戶隱私問題展開探討,并結合該事件輿論的演變,提出了應對輿論失焦的三個方法論。
關鍵詞 輿論失焦;弱傳播;成都確診女孩
中圖分類號 G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6-0360(2021)03-0011-03
互聯網的數字化記憶中,諸如“湯蘭蘭案”“江歌案”等輿論失焦現象由來已久。有研究者指出:“輿論失焦現象是指由于網絡發展,公眾知情權、話語權提升,事件中輿論難以被一方主導,使得輿情演變的主體脈絡呈現多極化發展,以至逐漸偏離事件的中心議題。”[1]疫情防控常態下,輿論在成都20歲女孩確診新冠肺炎后再度失焦,其有之前類似事件的普遍性,也呈現弱傳播視角下的特殊性。“弱傳播”是輿論研究的系統性公理,由鄒振東教授在《弱傳播:輿論世界的哲學》書中提出,其核心概念是輿論世界的“強肉弱食”法則,即現實中的強者恰恰是輿論中的弱者;基于此衍生出輿論的四大規律:輿論的弱定理、輿論的情感律、輿論的輕規則、輿論的次理律;此外還包括輿論的性別論及輿論的解釋工具等論斷與方法論[2]。
1 “成都確診女孩事件”中輿論的失焦呈現
1.1 輿論次理論下的主次顛倒:次主流話題成焦點
12月8日,成都官方微博通報了3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一對老年夫婦及其20歲的孫女趙某。隨著各地新增病例零星涌現,公示感染者基本信息是為引導公眾聚焦疫情防控,可事實上很快趙某的活動軌跡成公眾熱議,其私人電話、身份證號等隱私信息也被扒出,網民的討論焦點從起初就瞄準了趙某本身并逐漸演化為幾乎讓其“社會化死亡”的網絡暴力,官方的主流輿論被次主流的輿論壓倒。根據輿論生態理論,輿論客體經由輿論主體多種評價的交織而構建多種社會輿論共時性的格局[3]。這說明圍繞客體形成的多個輿論存在力量強弱之別,即事件真正的關注點與衍生的邊緣議題對“焦點”的爭奪。鄒振東教授認為輿論譜系中存在著主流輿論、次主流輿論、逆主流輿論等的交鋒,次主流輿論最為活躍,而主流輿論(主旋律)最不容易傳播[4]。主流輿論可理解為精英群體和權力組織認可并被大多數公眾接受的輿論形態,往往表現為一種共識或常理。在人民日報的公示中,除去感染者信息,重點在于文末“請廣大市民做好防護”的主旋律宣傳,雖然評論中有理智網友表示“零星病例不可怕,及時追蹤接觸者,個人需做好防控”,但類似此般與官方所期待的聚焦防疫本身的主流輿論并未得到廣泛傳播,相反,圍繞女孩“私生活”“社會責任”等衍生出的次主流輿論反占據壓倒態勢,使得輿論整體“偏航”。這也證實了主流輿論作為常理共識的不易傳播性。官方的防疫宣傳從疫情初始就一直持續,網民早已達成了基礎性認同;同時主流媒體關于該主題新表達方式的缺位使得主流輿論陷入陳詞濫調的窠臼,這共同造就了次主流輿論的崛起。群眾自發挖掘事件中新的關注點,或是圍繞女孩“在奶奶確診后還轉場酒吧”進行孝道拷問,或自行腦補其“一夜轉5場”的混亂私生活,最后甚至走向網絡暴力,這些非主流輿論極具戲劇性與新鮮性,從而占領了前期整個輿論生態。
1.2 輿論輕規則內的輕重倒置:個人隱私被圍觀
輿論世界似乎并不遵循現實世界的“重力邏輯”,現實中無足輕重之事在輿論場中卻可能成為焦點。根據“弱傳播”理論,輿論熱點的“輕”表現在內容上可以是輕松甚至輕浮,娛樂化的信息便屬于“輕的東西”,也最易成輿論焦點[4]。新媒體營造了共景化圍觀的監獄,同時放大了公眾的“窺私”心理。女孩的隱私信息被“人肉”,而有關女孩奶奶的信息卻無人問津,這是因為女孩的行動軌跡信息如“嗨藍調美甲店”“playhouse酒吧”等表征了輿論客體的娛樂化、狂歡化,而剩余確診者的活動場所如“菜市場”則不具群氓狂歡的性質。基于對其私生活的“對焦”,網友的輿論熱詞如“轉場皇后”“外圍女”等極具嘲諷性。
此外,輿論的傳播在形式上也依賴一系列“輕符號”:如惡搞圖片、表情包等。該事的輿論場為微博,技術賦權的威力在此體現為網友在評論區通過表情包甚至GIF互動,情感符號的加持放大了傳播效果;關于女孩隱私信息的圖片甚至捏造的視頻成傳播載體,裂變式轉發也輕而易舉,這共同導致了女孩隱私信息被“全景化”圍觀。
輿論主體外,在新技術層出不窮的節點上,算法作為“把關人”也似乎將娛樂化、商業化法則內嵌于代碼編寫中。有研究指出,微博熱搜的把關主要依據四要素,其中時新性與流行性先于導向正確[5],這體現為熱搜排行榜中娛樂化新聞居多,因而成都女孩的隱私最初經一人曝光后就在短短24小時上了多次熱搜,輿論進而失焦。
1.3 輿論情感律支配的網絡暴力
鄒振東教授指出輿論世界是情勝于理的傳播世界,這和勒龐描述的烏合之眾都揭示了群體感染對個體理智的吞噬:“人一到群體中,智商就嚴重降低,為了獲得認同,個體愿意拋棄是非,用智商去換取那份讓人倍感安全的歸屬感。”[6]該事件中,輿論主體呈現兩個顯著心理特征。
第一,刻板印象造就了桎梏女性的污名化標簽。李普曼所言的刻板印象是指人們對特定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簡單化的觀念和印象,它通常伴隨著對該事物的價值評價和好惡的感情。”[7]新媒體環境消解了虛擬與現實場景的邊界,傳統社會中對女性的歧視在虛擬世界得到延續。成都女孩被網暴的輿論暴露了社會對于女性貞潔、生活安分等的刻板印象。據人民網輿情數據中心監測,8日圍繞女孩本身的討論中有近40%的負面敏感情緒[8]。真相到來前,網友的情緒被“酒吧”等固化的“不檢點”符號放大,肆意揣測甚至捏造其“頻繁出入娛樂場所”“生活自由揮霍”等淫婦人設,使女孩深陷“鍵盤俠”的圍攻。
強者身份對輿論弱勢的構建是女孩被網暴的又一動因。輿論的“弱定理”指出:現實中的強者恰是輿論中的弱者,而現實中的強者要在輿論中獲得優勢必須與弱者相連接。客觀來看女孩作為被感染者在現實世界算不上強者,但媒介營造的“擬態環境”讓網友無法深挖真相,僅聚焦表面上女孩“一夜轉5場”的“白富美”生活,從而勾勒女孩在經濟與階層上的“強者”畫像,出于“仇富”心態而對女孩辱罵、人肉。隨著9號女孩通過今日頭條賬號澄清謠言,解釋“轉場”是面試工作所需并道歉后,女孩的強者標簽瓦解,網友找到了同為“打工人”這一弱勢群體共同的鏈接點,對于女孩的輿論發生了反轉,輿論中聲討泄露隱私者及祝愿趙某早日康復的呼聲愈發高漲。
2 輿論的轉移與理性的回歸
美國社會心理學家戴維森對于輿論的形成提出了十階段說,雖然一般情況下單個輿論形成并不完全具備這十要素,但比較關鍵的節點有責任主體的回應和權力部門的介入。輿情監測系統蟻坊軟件數據顯示,圍繞該事件第一次輿論高峰的形成是在8日中午,表現為對女孩的網絡暴力,隨后在8日晚21點形成了輿論最高峰,此時輿論客體已發生轉移,聚焦于對網絡暴力的譴責及泄露隱私者的聲討,到最后9日8時左右形成輿論第三次峰值,以對女孩的鼓勵及理性反思而消散[9]。整個輿論生命周期不過2天,更未經歷后續的“長尾階段”,這也說明輿論失焦是可控的。
8日上午關于趙某的謠言在微博引發熱議,中午有主流媒體對“成都不排除封城”等信息避謠;隨著公安部門對泄露隱私的王某進行調查,央視新聞等媒體迅速跟進,對泄露隱私行為展開批評報道,稀釋了群眾情緒感染的非理智成分,權力部門懲罰王某披露隱私則創造了新的輿論鏈接點,實現了輿論焦點的轉移;責任主體女孩在9日公開道歉并澄清真相則切斷了網絡暴力輿論持續發酵的鏈接點,輿論中的相關訴求與認同都得到解決,圍繞該議題的眾聲喧嘩也迅速消散。但正確的注意力與理性姍姍來遲,隱私泄露與網絡暴力的余波被數字化記憶永久貯存。技術賦權造就了新媒體環境下“記憶成為常態,遺忘成為例外”的困境,類似眾多網暴事件,人類記憶可以選擇遺忘,然而大數據讓女孩的隱私信息被代碼化為永恒,算法推薦也可能對網暴的記憶產生“啟動效應”,輿論的偏航可以引導,但更重要的是前期的瞭望與預防。
3 輿論失焦的矯正路徑展望
3.1 借助輿論“輕杠桿”,創新主流輿論的格式化表達
成都女孩事件輿論的失焦一定程度上暴露了主流媒體在主流議題設置方面創新力的缺失,防疫宣傳固化為微博等社交媒體上模板套話,這種程式化宣傳在“注意力稀缺”的新媒體情境下難以實現“強效果”,甚至在受眾的選擇性接觸中被過濾,從而放大了非理性的公眾注意力在重新獵取輿論客體中失焦的可能性。而輿論的“輕杠桿”指主流輿論表達形式的趣味性及表達載體的易傳播性,或許主流媒體可以嘗試融合動畫、短視頻、H5等表達符號增強信息發布等嚴肅議題的“輕快感”,重新贏得受眾對中心議題的注意,這需要媒體前期對于突發事件的快速反應與短時的巧妙策劃,甚至對團隊綜合素質設置了更高要求,但這種“輕杠桿”卻能達到“舉重若輕”的傳播效果,降低輿論失焦的風險。
3.2 捕捉表層“微波浪”,做好潛輿論動向的瞭望
陳力丹教授指出,所謂潛輿論就是指存在于特定事件之前的公眾對社會事物的既有情緒和意見[10]。現代經濟、政治制度構建了貝克所說的風險社會,社會子系統內各種矛盾的疊加最終會通過顯輿論爆發并對社會產生災難性沖擊,但這是可察覺和預防的。公眾持久的情緒與意見所形成的潛輿論是對顯輿論走向的暗示,這就需要輿情監測部門時刻把握輿情動向,借力輿情監測系統增強輿情預判與分析能力,在前期對輿情走勢進行預估,同時對網絡輿論的暴力傾向保持高度警惕,并及時向政府和官方媒體通報信息并提供輿論引導對策。
3.3 巧用輿論“區隔律”,群像傳播對隱私信息的模糊
反思政府在通報中對個人基本信息與行動軌跡的公示,客觀來講利于全民提高警惕,維護防疫工作。但近來類似于成都女孩的確診患者頻遭網暴的事件卻值得政府探索如何在唱好全民防疫主旋律同時最大限度保護個人隱私信息,這就需要群像傳播的技巧。輿論的區隔律指出:一個事物要得到關注,就必須從龐大的不關注集合里溢出,如果不能游離出來,就會被不關注的“黑洞”吞噬。輿論關注的運動方向絕不是一個隊伍,而是這個隊伍“出列”的人[4]。此次通報的病例共3例,確診者每人的詳細信息及行蹤都被單獨列出,這種極具針對性的區分本身就容易使得患者成為眾矢之的。或許對于多病例的通報,可以將所有確診者的信息融為整體,不以個體為單位而以行蹤、個人信息的條目整合感染者信息,仍能保留必要信息以便防疫,同時也將個體信息區分模糊化,這一定程度上能避免網絡暴力對于特定弱勢個體展開群攻。
4 結語
新媒體情境下,輿論失焦現象的動因是十分復雜的,除文章著重分析的用戶本身媒介素養的缺失,還包括網民結構年輕化、主流媒體輿論引導能力不足等多方面因素,但類似于成都女孩被網暴的輿論失焦所衍生的個人隱私泄露、網絡暴力等問題也應被重視,這需要后續更多研究對輿論失焦現象進行新的解讀,從多個角度不斷探索出矯正路徑,最大限度避免下一個“成都女孩”的悲劇。
參考文獻
[1]嚴利華,陳捷琪.突發事件中的輿論失焦現象及其啟示[J].決策與信息,2016(8):130-137.
[2]董夢霞.弱傳播視角下網絡暴力的現實圖景及治理路徑[J].新聞研究導刊,2020,11(22):84-85.
[3]管秀雪,徐建軍.網絡空間輿論生態系統的發生三要素與邏輯生成[J].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36(2):85-90.
[4]鄒振東.弱傳播:輿論世界的哲學[M].北京: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2018:32,76,98.
[5]王茜.批判算法研究視角下微博“熱搜”的把關標準考察[J].國際新聞界,2020(7):26-48.
[6]古斯塔夫?勒龐,勒龐.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M].馮克利,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7]汪露.新聞傳播學中刻板印象研究綜述[J].云夢學刊,2010(3):154-157.
[8]霍思銘.成都疫情的B面:“他者”視角下的次生輿情與風險[EB/OL].(2020-12-09)[2021-01-11].https:// mp.weixin.qq.com/s/F7bGEBFxrkMH_jDuYAIEiA.
[9]大花呀.成都20歲確診女孩被網暴,網絡暴力的形成機制與反網絡暴力的輿論動員[EB/OL].(2020-12-14)[2021-01-11].https://mp.weixin.qq.com/s/ GNILoPJYGI1xYvyxQ0VFww.
[10]彭廣林.潛輿論?輿情主體?綜合治理:網絡輿情研究的情感社會學轉向[J].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0,49(5):142-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