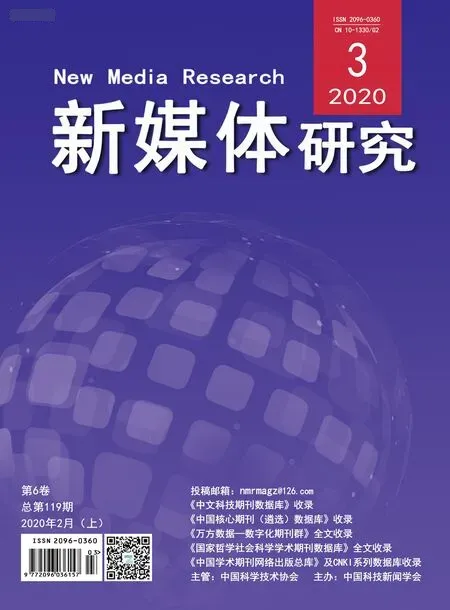新媒體時代飯圈文化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
解文峰 解宸龍
摘 要 “飯圈文化”作為粉絲文化的一種流變和分支,在與新媒體環境與社交環境產生接觸的過程中發生了一系列的嬗變。通過定義飯圈文化,發現飯圈文化存在的問題,旨在采取有效措施對“飯圈”這一青年粉絲群體進行有力引導,使之能夠發揮其正面作用,對社會發展生成助推力。
關鍵詞 飯圈文化;偶像;粉絲;傳播行為
中圖分類號 G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6-0360(2021)03-0077-03
在網絡賦權的技術支持下,現如今的“偶像”文化呈現出不一樣的特點。社交媒體平臺的發展繁榮使得原本分布在天南海北的粉絲可以輕而易舉的在網絡上聚集在一起,進而形成一股強大的“粉絲力量”,這種“力量”使得粉絲群體和偶像本人一起成為話題中心,成為追星過程中的“主角”,同時,這股“力量”在外部環境和一些內部因素的影響下會隨時發生嬗變,引發了社交媒體平臺一系列媒介景觀。
1 “飯圈文化”的內涵及發展特征
1.1 飯圈文化的內涵
傳統意義上的粉絲文化現象,指的是粉絲以個體為單位、以一種游離的狀態而存在的現象。社交媒體平臺不斷發展壯大,零散分布的粉絲開始借助網絡力量在各種虛擬社區(例如豆瓣、微博、晉江社區等)尋找同質群體,進而組成相當規模的偶像粉絲群體。群體內部成員嚴格遵守組織內部規則和群體規范,不同的粉絲群體內部也就產生了不同的粉絲文化。從2018年開始,各類偶像選秀節目橫空出世,并源源不斷的為受眾輸送大批偶像新秀(又稱“愛豆”,英文“IDOL”的簡稱),掀起了內地粉絲群體的一陣陣狂歡。這些自發聚集的粉絲群體在日常的群體性行為中通過各式各樣的傳播行為對“飯圈文化”進行生動演繹。
“新媒體具有資源高度整合、內容個性化定制的優勢,用戶可以通過頁面指導,快速地找到自己想要的信息”[1]。飯圈作為一種“圈子”,“是以情感、利益、興趣等維系的具有特定關系模式的人群聚合”[2],而飯圈文化作為新媒體時代的產物,不僅在技術層面上體現其意義,更多的意義則體現在粉絲群體內部的話語權爭奪和想象力創造上。總的來說,主要由圍繞偶像產生的交往行為、以偶像為載體的文本符號、粉絲和偶像頗具儀式感的集體活動(如控評、應援、打榜)等元素構成。因此,我們可以對飯圈文化進行如下定義:飯圈文化,即新媒體時代粉絲群體依托社交媒體平臺,圍繞偶像這一主體而進行的意義生產行為和集群性交往行為,通過對偶像這一文本符號的編碼與解碼,進行意義生產與再生產,這種交流實踐活動在“我群”中進行儀式化展演并與“他群”中形成較為明確的區分。在這種群體意向性活動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圈層式的文化傳播模式。
同時,飯圈是文化社群的形式之一,飯圈社群是粉絲表達內心情感、創造新生意義的重要場域。參與飯圈活動的粉絲個體,都在自覺不自覺地重復著自我身份的確認與轉換行為,這種行為有明顯的階段性特點;其次,飯圈內部組織架構也具有層級差異性,有嚴謹的高下之分,粉絲個體一般能夠自主選擇進入與退出某個層級,進入層級時一般會有嚴格的審核行為。在飯圈內部,擁有大量粉絲的大V脫穎而出,通過發布高質量圖文信息一躍成為社群的組織者和管理者,組織形式則以官方后援會和粉絲個站的形式出現,在偶像和普通粉絲之間架起一座溝通的橋梁。
1.2 飯圈文化的發展特征
追溯飯圈文化的發展歷程,不難發現其最初是在韓國娛樂圈形成并發展的,后由國內粉絲“翻墻”追星后習得,并將這一文化帶入國內粉絲圈內。目前,在信息傳輸力和影響力巨大的今天,飯圈文化在發展過程中具有以下三點特征。
1)符號:飯圈用語的使用與“出圈”。每個群體在社群內部互動交流都有其特定的語言、邏輯、行為規范等[3],粉絲群體在飯圈內部活動所使用的語言即稱為“飯圈用語”。隨著社交網絡平臺的擴張和網絡亞文化的發展,飯圈用語的意義與形式也不斷創新。目前,國內飯圈用語大致可分為縮略簡稱類,如“xfxy”表示“腥風血雨”“yyds”表示“永遠的神”等;諧音替代類,如“讓我康康”表示“讓我看看”等;舊詞新義類,如“墻頭”一詞原指“矮短的圍墻”現用來代指粉絲頻繁更換偶像的行為;新造詞匯類,如“C位出道”一詞原本指在選秀節目中獲得第一名的成績,后成為近幾年大火的飯圈用語,被社會各行業普遍引用。這也意味著飯圈用語正在逐漸打破圈層壁壘,由飯圈內部逐漸“出圈”走向更廣泛的受眾群體中。
2)行為:飯圈應援、打榜行為的“數據流量之爭”。信息時代,“數據”越來越成為考察一個明星、一個偶像商業價值的重要維度。在飯圈群體中,為偶像應援也已經成為粉絲追星的必備手段和技能,“應援文化”和“做數據”一樣,成為偶像工業時代的一大特征,折射出粉絲經濟巨大的資本體量,隨之衍生出各種職業行為。談及“數據流量之爭”,很多人會不假思索地說出2019年7月引起網民巨大反響的“周杰倫、蔡徐坤超話之爭”事件,在這場打榜行為中,很多對“愛豆”“流量明星”有刻板印象的對家粉絲和“路人”甚至個別明星都參與進來為周杰倫打榜,在“大戰”一天一夜后,終以周杰倫超話登頂榜首結束了這場聲勢浩大的“粉絲行為藝術”,數據流量之爭也因此獲得了空前關注。對此,人民日報發布微評“偶像會發光: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偶像,一個群體有一個群體的向往”。
3)生態:社群內外的互動與博弈。“隨著移動互聯網終端設備的普及,互聯網技術創造的網上虛擬社區使得粉絲實踐不再是個人行為”[4],作為自發形成的一種網絡社群,粉絲群體一直備受媒體和學界關注,在傳統的大眾眼中,粉絲群體尤其飯圈社群一直擁有“集體”身份,認為他們擁有一致對外的訴求、一致擁護的群體規范和目標,其實,飯圈社群內部也是一個極具復雜性和多樣性的群體,也會產生群體內部的互動和博弈行為,構成獨特的“飯圈生態”。
2 “飯圈文化”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
飯圈文化在與中國本土文化進行交流、碰撞、融合中也不可避免的產生了以下問題。
2.1 飯圈狂歡下的消費主義盛行
根據鮑德里亞“符號消費”理論中“消費系統建立在某種符號和區分的編碼之上”[5]的觀點,社交媒體和經紀公司在對偶像進行包裝的過程中,也在對偶像本身進行編碼,賦予偶像各種“人設”和“符號”,飯圈群體的追星行為等同于消費系統中的編碼——解碼過程、對符號的釋義過程,現今,這種對應關系可以嫁接到對偶像專輯、明星代言、周邊等購買與支持行為中。
一些明星周邊將偶像本人進行文本符號化,粉絲的購買行為實際上是對這些充滿意義的文本符號進行消費。只是在這個過程中,各種缺乏理性、鼓吹金錢至上的聲音不斷出現,將粉絲建構為消費者,將購買力和購買程度與忠誠度、粉絲黏度掛鉤,不斷催生出一個又一個所謂的“銷量奇跡”和“爆款產品”,在這種經濟消費的背后折射出一個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即形成學生黨追星族省吃儉用甚至借錢貸款也要為偶像花錢的畸形消費主義觀。
2.2 群體極化的非理性行為
法國學者塞奇·莫斯科維奇在《群氓的時代》一書中論述了群體極化產生的作用機制,他指出:“當個人聚集在一起時,一個群體就誕生了。他們混雜、融合、聚變,獲得一種共有的窒息自我的本能。他們屈從于集體的意志,而他們的意志則默默無聞”[6]。飯圈的非理性行為一種是當自家偶像遭到他人攻擊時,飯圈內部情緒高漲,掀起罵戰,一心只為維護自家偶像的利益,另一種群體極化行為是“私生”現象,指的是個別粉絲為了滿足自己的偷窺欲和占有欲,不惜一切跟蹤偶像行程,給偶像生活造成極大困擾的同時也會給自身安全帶來不穩定因素,干擾了正常運行的社會秩序[7]。
2.3 信息時代下流量數據造假
新媒體時代背景下“數據”愈來愈成為衡量一個產業或者一個偶像明星影響力及商業價值的重要參數[8]。在文娛市場上,不少所謂的業內人士鼓吹“數據為王”,導致數據造假現象泛濫成災。商家們抓住和利用粉絲心理從中瘋狂牟利,制造各種數據造假App,更有甚者僅用半年時間就瘋狂吸金千余萬元。這種數據造假行為損傷了社會誠信,屬于非道德行為,成為我國娛樂產業發展的一大阻力,更會影響和諧社會的構建。
3 對飯圈群體的引導策略建議
雖然飯圈群體中存在的一些不理性行為影響了社會秩序,造成了一些不良的社會影響,但是隨著粉絲群體的不斷壯大,“粉圈基數”成為我們考量類似問題時必須參考的一個重要參數,對此,我們應該拿出一些有效措施引導飯圈群體,使之能夠對社會產生重要的正面推動力量。
3.1 主流媒體發揮引領作用,帶動粉圈群體積極向上
“多數情況下,媒體的發言會引導受眾的思維與做法”[9],主流媒體要充分發揮自己的權威引導作用,要及時對粉絲事件進行公正、客觀的評論報道,引導正確的輿論風向,發揮主流媒體對的策劃職能,多策劃一些功能正面的新媒體活動或者社會公益活動,邀請粉圈基數和影響力比較大的偶像明星參與其中,發揮群體正面效應的最大值[10]。例如央視在慶祝澳門回歸20周年之際,邀請蔡徐坤參與拍攝了慶祝澳門回歸祖國20周年唯一官方紀錄片《十三行》,引發其粉絲一系列愛國行為,對飯圈群體中年齡較小的粉絲來說是一次潛移默化的愛國主義教育。
3.2 加強媒介素養教育,人人爭做網絡“把關人”
縱觀所有的流量造假事件,行業“潛規則”和“平臺數據”無疑是導致此類事件發生的根源所在,肅清流量造假事件一定要從源頭治理。“在‘公民新聞時代,人人都可能是新聞的參與者”[11]。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46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6月,初中、高中/中專/技校學歷的網民群體占比分別為40.5%、21.5%,受過大學專科及以上教育的網民群體占比為18.8%。網民群體低學歷化成為不爭事實,優質的媒介素養教育必須要全面展開,做到“人人都是把關人”[12]。除此以外,媒介從業者更應加強媒介素養教育,在發布和傳播信息時做到嚴密篩查、仔細核對,拒絕虛假營銷等等,讓社交媒體真正成為創意和靈感迸發的公共平臺[13]。
3.3 相關部門加強監督,完善法律法規規范社交平臺
“僅憑自律規范的軟性約束是遠遠不夠的,同時需要加強他律制度的建設,賦予其強制約束力”[14]。一方面,國家相關部門要出臺打擊流量造假行為的法律法規,讓這種行為治理起來有法可依,完善法律細節,體現法律權威;另一方面,相關部門要及時約談相關社交網絡平臺的負責人,厘清誘使飯圈群體“刷榜”“刷數據”的危害[15]。例如之前微博一直熱衷于號召粉絲在明星勢力榜中“買花、送花”由偶像收到花的數量(實際為經濟價值)來評定該偶像的影響力,后該行為受到了上級主管部門的重視,決定取消明星勢力榜的“送花”機制。
4 結語
“飯圈群體”作為信息時代的一大媒介景觀,在為偶像助力不斷進行“展演”的過程中要形成、制定和自覺遵守正確的群體規范,進而不斷輸出正能量、有價值、可持續的“飯圈文化”,相信只要我們多方聯動、形成合力,對飯圈群體多一些理解、引導與支持,“飯圈女孩為阿中哥哥外網打CALL”的熱情不會消減,“風清氣正”網絡空間美好目標終會早日到來。
參考文獻
[1]鞠凌莉,楊蓉.移動互聯網背景下廣播轉型的動因分析:以喜馬拉雅FM為例[J].藝術科技,2019(7):121,201.
[2]彭蘭.網絡的圈子化:關系、文化、技術維度下的類聚與群分[J].編輯之友,2019(11):5-12.
[3]管蘭蘭.論新媒體時代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影像傳播[J].大眾文藝,2019(12):159-160.
[4]劉雨婷.偶像養成類網綜《偶像練習生》熱播因素探析及啟示[J].大眾文藝,2019(22):189-191.
[5]劉建明.符號消費理論的認知邊界與假命題[J].新聞愛好者,2019(8):4-8.
[6]賽奇?莫斯科維奇.群氓的時代[M].李繼紅,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7]李弋.動物世界:淺析《荒蠻故事》中人物的動物性[J].藝術科技,2019(8):82-83.
[8]管蘭蘭.論微博平臺上新聞資訊類短視頻的傳播[J].戲劇之家,2019(28):189-190,193.
[9]尤旖蕓.新媒體語境下粉絲形象的污名化探析[J].東南傳播,2019(12):116-119.
[10]韓東池.圈層文化背景下“網紅”式KOL與傳統文化傳播[J].漢字文化,2020(20):148-149.
[11]薛靜.自媒體時代下短視頻的內容生產與網絡文化傳播:以微博博主李子柒為例[J].漢字文化,2020(19):65-66.
[12]劉日照.論我國媒體社會責任缺失現象[J].今傳媒,2018(12):36-40.
[13]徐紫薇.論“中央廚房”背景下記者生產新聞的困難[J].戲劇之家,2019(29):216-217.
[14]張劉剛.生態文化傳播中的語義特征[J].戲劇之家,2019(30):235-236.
[15]胡銘.社交平臺“網紅式KOL”與地方民俗文化推廣[J].漢字文化,2020(22):146-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