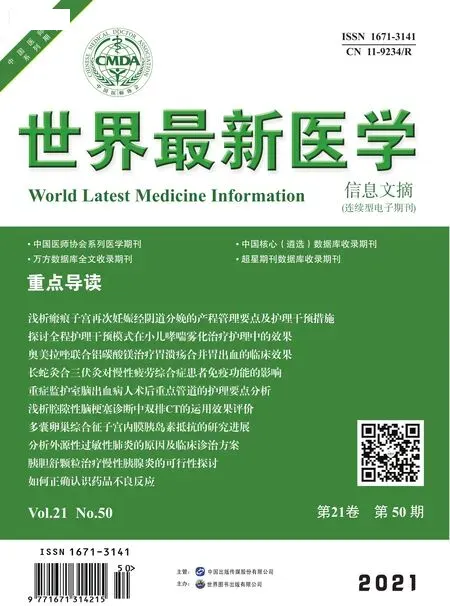神經調節輔助通氣在創傷性濕肺合并ARDS患者中的應用
郭毅,韓大賀,李海泉
(徐州礦務集團總醫院,江蘇 徐州)
0 引言
創傷性濕肺為外傷導致的肺實質損傷,主要病理改變為肺泡和毛細血管損傷(充血及出血)及肺間質水腫[1]。由于創傷性濕肺的嚴重程度和范圍大小不同,臨床表現有很大的差異,輕者僅有胸痛、胸悶、氣促、咳嗽、血痰等,嚴重者則有明顯的紫紺、呼吸困難、血性泡沫狀痰、心動過速和血壓下降等。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是重癥創傷性濕肺的常見并發癥,其是一種高死亡率的一種病癥,患者因身體受到巨大創傷,機體呼吸系統受到影響,出現急性的呼吸窘迫現象。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發病比較急促,且病死率較高,病人表現為呼吸困難,需要及時進行治療,確保呼吸暢通無阻[2]。但一部分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患者予以吸氧,甚至是高流量吸氧,其呼吸困難和缺氧的情況依舊不能夠得到有效改善。神經調節輔助通氣是一種新型機械通氣模式,其主要是通過隔肌電信號觸發和NAVA支持水平控制的一種通氣模式[3]。本研究選取2020年10月至2021年2月在我院接受治療的20例重癥創傷性濕肺合并ARDS患者作為研究對象,對其應用神經調節輔助通氣,探討PSV通氣模式和NAVA通氣模式的不同效果,具體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將2020年10月至2021年2月在我院接受治療的20例重癥創傷性濕肺合并ARDS患者分為對照組和觀察組,每組10例。對照組男性5例,女性5例,年齡25~58歲,平均(43.28±4.56)歲,車禍外傷6例,墜落傷 3例,爆炸傷1例;觀察組男性7例,女性3例,年齡26~57歲,平均(42.72±4.25)歲,車禍外傷6例,墜落傷4例。對兩組基本資料進行比較,不具有統計學差異(P>0.05)。
納入標準:所有患者及患者家屬對本次研究完全知情并同意;經臨床各項檢查確診為重癥創傷性濕肺合并ARDS患者。
排除標準:存在肺部基礎疾病患者;高位截癱患者;嚴重心、肝、腎功能障礙患者;惡性腫瘤患者。
1.2 方法
所有患者在入院后均給予對癥治療,采用PICCO技術監測血流動力學,采用呼吸機輔助通氣,在呼吸機在呼吸機EAdi模塊監測下通過鼻腔將膈肌電極導管置入到準確位置。對照組小潮氣量為6~8 mL/kg,呼吸機壓力支持為8~13 cmH2O。觀察組小潮氣量為6~8 mL/kg,NAVA水平設置為 0.7~2.0 cmH2O/μV。
1.3 觀察指標
比較兩組通氣24 h后的呼吸力學指標,包括PIP、Pmean、EAdi峰值信號、WOBp、WOBv、WOBp/WOBt。比較兩組的人機同步性指標,采用NAVA分析軟件進行計算,包括觸發延遲時間、吸/呼氣切換延遲時間、呼吸機通氣頻率。比較兩組通氣48 h后血流動力學指標,包括HR、CI、CVP、ELWI。比較兩組通氣24 h后氣體交換能力,包括PaCO2、PaO2、SaO2。
1.4 統計學方法
使用統計學軟件(SPSS 22.0版本)進行分析,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s)表示,采用t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比較兩組通氣24 h后的呼吸力學指標
觀察組通氣24 h后的呼吸力學明顯優于對照組,組間差異明顯(P<0.05),如表 1。
表1 比較兩組通氣24 h后的呼吸力學指標(±s)

表1 比較兩組通氣24 h后的呼吸力學指標(±s)
組別 例數 PIP(cmH2O) Pmean(cmH2O) EAdi(μV) WOBp(J/L) WOBv(J/L) WOBp/WOBt(%)觀察組 10 11.54±2.12 7.23±0.81 9.36±0.48 0.11±0.08 0.78±0.18 14.62±5.23對照組 10 15.89±2.32 8.48±0.95 8.64±0.32 0.25±0.09 0.98±0.21 21.68±5.88 t 4.377 3.166 3.947 3.677 2.287 2.837 P 0.001 0.005 0.001 0.002 0.035 0.011
2.2 比較兩組的人機同步性指標
觀察組的人機同步性明顯優于對照組,組間差異明顯(P<0.05),如表 2。
表2 比較兩組的人機同步性指標(±s)

表2 比較兩組的人機同步性指標(±s)
呼吸機通氣頻率(次/min)觀察組 10 211.73±30.28 518.66±98.48 28.23±5.84對照組 10 104.29±28.67 147.64±52.39 20.12±5.02 t 8.148 10.518 3.330 P 0.001 0.001 0.004組別 例數 觸發延遲時間(ms)吸/呼氣切換延遲時(ms)
2.3 比較兩組通氣24 h后血流動力學指標
觀察組通氣24 h后的血流動力學與對照組相比無明顯差異(P>0.05),如表 3。
表3 比較兩組通氣24 h后血流動力學指標(±s)

表3 比較兩組通氣24 h后血流動力學指標(±s)
組別 例數HR(bpm)CI(L/min/m2)CVP(mmHg)ELWI(mL/kg)觀察組 1088.22±17.03 4.23±0.56 10.13±2.05 6.53±1.08對照組 1091.89±17.01 4.62±0.62 11.46±2.23 6.12±1.12 t 0.482 1.476 1.389 0.833images/BZ_71_486_1805_488_1806.pngP 0.636 0.157 0.182 0.416
2.4 比較兩組通氣24 h后氣體交換能力
觀察組的氣體交換能力與對照組相比無明顯差異(P>0.05),如表 3。
表4 比較兩組通氣24 h后氣體交換能力(±s)

表4 比較兩組通氣24 h后氣體交換能力(±s)
組別 例數 PaCO2(mmHg) PaO2(mmHg) SaO2(%)觀察組 10 37.26±3.27 95.28±13.29 92.36±2.94對照組 10 36.94±3.34 94.87±13.33 93.02±2.87 t 0.217 0.069 0.508 P 0.831 0.946 0.618
3 討論
創傷性濕肺是一種在重癥創傷患者中常見,多見于高空墜落、車禍傷、鈍性的胸部損傷等。創傷性濕肺系外力作于胸壁而引起肺組織充血、肺間質水腫和微小肺不張為特點的綜合病變,嚴重時可引起氣胸、血胸、肺不張,甚至發展為呼吸衰竭[4]。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是創傷性濕肺的常見并發癥之一,一旦患者出現此病癥,就表明患者的情況較為危急,需立即予以相應的治療。機械通氣在患者出現呼吸功能障礙,不能依靠自身能力正常呼吸以維持機體對氧氣的需求時,幫助患者呼吸[5]。傳統的PSV通氣模式存在著人機不同步的缺點,易導致患者出現相關肺損傷,增加患者的不適感[6]。NAVA是一種新型無創通氣模式,它保留了PSV模式的優點,且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PSV模式的缺點,其在此基礎上逐漸發展起來的[7]。NAVA通過膈肌電活動來調節呼吸的觸發和循環過程,當膈肌收縮時EAdi升高,從而觸發吸氣,當膈肌放松時時EAdi下降,從而觸發呼氣,其能夠保證呼吸機通氣啟動和轉換與患者的呼吸需求保持一致,最大限度的提高人機協調性[8]。
從本次研究結果可得知,觀察組的呼吸力學明顯優于對照組(P<0.05);觀察組的人機同步性明顯優于對照組(P<0.05);觀察組通氣24 h后的血流動力學與對照組相比無明顯差異(P>0.05);觀察組的氣體交換能力與對照組相比無明顯差異(P>0.05)。表明對重癥創傷性濕肺合并ARDS患者應用神經調節輔助通氣,NAVA通氣模式的表現更優于PSV通氣模式。
綜上所述,對重癥創傷性濕肺合并ARDS患者應用神經調節輔助通氣,NAVA通氣模式的表現更優于PSV通氣模式,值得在臨床中推廣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