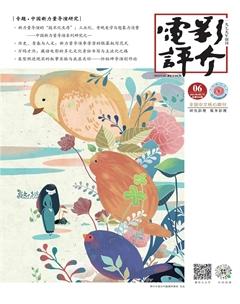類型照進現實的敘事實驗與底層關懷
申朝暉
從《心迷宮》到《暴裂無聲》,青年導演忻鈺坤顯現出穩定而出色的類型偏好和作者風格。他講述的故事懸念環生、邏輯縝密,又留給觀眾充分的想象空間。然而,忻鈺坤并不滿足于講述一個懸疑故事,他對電影類型的探索始終扎根于中國的現實土壤,聚焦當下的社會問題,在看似冷靜的剝離背后卻不乏深情的底層關懷。
一、本土電影節走出來的電影新人
區別于第六代導演走國際電影節獲獎的成名路徑,忻鈺坤是從國內電影節“FIRST青年電影展”走進大眾視野的代表,繼他之后出現了文牧野、張大磊、王一淳、李非等,他們的成功見證了通過本土電影節孵化和培育電影新人的可行性,以及中國電影產業鏈的漸趨完善。
忻鈺坤1984年出生于內蒙古包頭市的一個知青家庭,17歲高二輟學開始學電影。他先是跑到西影集團下屬的西安電影培訓學院讀了一年,在私交甚好的老師的指點下他回家備考北京電影學院以期走上學習電影之正途。然而,忻鈺坤似乎并不擅長考試,他2003年報考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和導演系均在初試階段被淘汰,2005年報考北影旁聽生再度失敗。直至2008年他考取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進修班學習一年,之后在北京以拍攝宣傳片、廣告等謀生,期間遇到與他一樣闖江湖還想大干一番事業的制片人任江洲。
2005至2008年期間,多次備考北京電影學院失敗后,忻鈺坤回到西安,在當地一家電視臺打雜。一直做著導演夢的忻鈺坤一邊拍欄目劇,一邊自學電影,他的學習路徑主要是反復觀摩經典影片,并現學現賣把這些經典類型片中的拍攝手法運用于欄目短片的拍攝當中,這段經歷訓練了忻鈺坤最初的編導拍剪能力。
2014年《心迷宮》通過FIRST青年電影展嶄露頭角,這部“三無”(無大明星、無大導演、無大制作)電影獲得了第8屆FIRST青年電影展的最佳導演獎和最佳劇情獎,而且以遠低于業界公認基準線的170萬元成本進入院線,最終票房突破1067萬元,刷新了中國獨立電影在院線的最佳成績。忻鈺坤的成功見證中國電影工業體系的逐步完善,隨著中國電影市場的擴大與繁榮,電影行業需要發掘富有原創精神的新銳導演和帶有實驗意義的獨立電影。實際上,從好萊塢或者世界范圍經驗來看,獨立電影對于一個國家電影產業化的意義是多重的。首先,投資相對小巧的獨立電影作為商業主流電影的補充,滿足日益分眾的市場對多樣化電影產品的需要,也是資本試探新興市場的試金石。因此,“商業電影成就最高的美國,也是全世界獨立電影最發達的地方。”[1]其次,獨立電影和各類獨立影展作為電影創作者尤其是新人的演武場,也是電影工業化體系遴選和培育人才的重要機制,美國的圣丹斯、日本的東京FILMeX電影節、韓國的釜山電影節等致力于挖掘新人新作,尤其是荷蘭鹿特丹國際電影節還設置了一個HBF基金,用于專門資助發展中國家的電影制作,中國第六代導演從張元、何建軍、王小帥、丁建成到賈樟柯等的早期電影多數都獲得過它的資助。
但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獨立電影海外融資緊縮,而另一方面由于行業技術發展,獨立電影制作的成本愈來愈高,中國獨立電影人只得紛紛轉向國內融資。“FIRST青年電影展”2011年落地西寧,旨在發掘和推廣青年電影人以及作品,FIRST影展在運行模式上多借鑒外國獨立電影節的慣例,比如規定參賽作品必須是參賽者的前三部作品,另外,每年定期在全國范圍開展巡邏主題放映,設置了訓練營、創投會及產業放映等,為電影新人提供較為完整的產業渠道。2014年,《心迷宮》在獲得第8屆FIRST青年電影展中最佳導演獎和最佳劇情獎之后,在太和娛樂和北京海平面影視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的聯合出品下進行了包括影片更名等在內的后期處理,最終使影片成功進入院線發行。
當然,“FIRST青年電影展”對于忻鈺坤的意義不僅是其處女作《心迷宮》得以進入公眾視野,其第二部影片《暴裂無聲》也是FIRST與并馳影業合作開發的“并馳計劃”推出的首個項目。從電影節遴選佳作到建立募集資金、成立實驗室,孵化和扶持新人計劃,“并馳計劃”這種“扶上馬送一程”的模式對于高資本運作的電影業新人而言無疑是雪中送炭。這種模式在美國圣丹斯電影節、日本和瀨廣美電影節、韓國釜山電影節都有相對成熟的產業對接,從這種意義上說“并馳Lab”對于FIRST而言也是產業鏈的必要延伸。忻鈺坤的電影之路為電影新人點亮了一盞明燈,隨著數碼技術普及,導演準入門檻大大降低,而像第五代導演那樣一個“班”或一個“系”就撐著中國電影半邊天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這批新力量導演的構成更為多元,有些人是演而優則導,有些人是從小說家轉型,有些人是工科背景,而像忻鈺坤這樣的電影草根二十出頭即躋身職業導演行列,對于中國廣大青年電影愛好者無疑是勵志的榜樣與標桿。
忻鈺坤從獨立電影階段開始就旗幟鮮明地進行類型片的嘗試與試驗,在類型的框架內反觀現實,關注社會的底層生活,這種創作思路無論對中國類型電影的產業化還是對于電影新人而言,都具有積極意義。許多電影新人的處女作或者早期的獨立電影,即便斬獲多項國際大獎,有時也很難在國內公映。忻鈺坤的處女長篇《心迷宮》能在制作較為粗糙的情況下成功進入院線播放,在“并馳計劃”的扶植下,其第二部《暴裂無聲》緊隨其后,并在體量、制作團隊和藝術上均有大幅度提升,這得益于中國電影工業體系的逐漸成熟,學者陳旭光認為:“通過不斷地向好萊塢‘取經,中國電影產業也逐步走向了更加規范、穩健的機制化發展道路,電影創作不再是作坊式的單打獨斗,也不是閉門造車,電影工業的標準和運行準則開始與國際全面接軌。”[2]以“FIRST青年電影展”為代表的本土(獨立)電影節為行業遴選新人新作,并致力搭建他們與電影產業之間的浮橋,這正是中國電影工業體系朝成熟化、體系化發展邁進的里程碑式的勝利。
二、故事本位、類型敘事及其話語實驗
人類需要故事。從原始先人到孤獨的現代人,我們個體的經驗是有限的,而通過故事人們獲得經驗,同時賦予世界以意義。尤其對電影這類面向“常人”的大眾藝術形式,故事是吸引觀眾和表達意義最根本的載體。因此,講好故事是一個導演或編劇的基本功,也是一部電影成敗的關鍵所在。忻鈺坤的電影都有著扎實的故事基礎,從《心迷宮》《再見,在也不見》到《暴裂無聲》,無論敘事話語是追求線性的沉穩,還是崇尚非線性的奇異,忻鈺坤都牢牢恪守故事本位這一敘事王道。《心迷宮》圍繞燒焦了的尸體到底是誰,真相是否能大白于天下這一核心事件展開,《暴裂無聲》的核心事件是張保民尋找兒子,合拍片《再見,在也不見》則講述了一個成名后的男學生異國他鄉重遇暗戀多年的女教師的故事。忻鈺坤關于“鄉村現實”“人性暗影”“社會階層分化”以及“愛情與時間”等問題的思考都是基于故事的核心事件自然派生出來,導演的“理路”表達沒有游離于“言荃”之外。巴贊早在電影入主藝術殿堂的初期就斷言:“電影的危機主要還不在審美方面,而在智力方面。影片的主要毛病是胡編亂造,窮極無聊。結果,美學的爭論也就被擠到次要地位。”而他認為一部影片是否可以稱之為“佳作”,“我們也并不過分苛求。我們要求它不胡編亂造,要求它通過運用電影特有的表現手段拍得巧些。”[3]這種擔憂在今日之中國電影依然存在。巴贊所說的“不胡編亂造”,即強調故事的可信度,因果情節的邏輯自洽性,依然是當下中國電影工業產業鏈的“老痼疾”。編劇汪海林在2020年橫店影視節“中國電影美術學會高峰論壇”時就中國電影劇作和故事的退化問題提出擔憂:“今年中國電影工業水平有較大提高,這是公認的。但現在連普通觀眾都發現了一個問題,就是劇作在某種程度上非但沒有升級,好像還出現了降級……在劇作上的問題都沒有得到解決。”[4]忻鈺坤恪守故事本位、經營劇作懸念設置,注重故事與現實的關聯性,其獨立編導《心迷宮》和《暴裂無聲》以現實主義手法捕捉當下中國的痛點,用地道的中國故事折射深廣的社會現實,是中國電影的正途,也正因此,忻鈺坤被譽為最有潛力的青年導演之一。
如果說故事是一個導演創作的起點,那么類型往往是他講述故事的模式、策略與風格。尤其對于有市場追求的導演而言,類型如同約定俗成的契約,是導演與觀眾之間交流的一種默契,通常以特定題材、相對穩定的人物設置、固定化的敘事模式,甚至相似的敘事元素和價值體系以達成某種共同的“期待視野”。從《心迷宮》到《暴裂無聲》,從相對單一的懸疑類型,到標簽更為鮮明和多元的融合懸疑、暴力于一體的黑色電影,忻鈺坤對于類型的追求與駕馭逐漸清晰并趨于成熟。或許由于“溫柔敦厚”的文化傳統與美學精神,中國文學與中國電影中的懸疑類型一直都有欠發達。當忻鈺坤的《心迷宮》以嚴謹的敘事邏輯、“羅生門”式的多重敘事視角講述一具“焦尸”的三次認領,在國產電影的現實語境中,《心迷宮》這種層層遞進、環環相扣的懸疑敘事給了觀眾一次難得的審美體驗。
懸疑電影作為一種類型在經典好萊塢時期即得到了充分發展,誕生了像希區柯克那樣舉世聞名的懸疑大師,并在如何制造懸念、誘導觀眾進入劇情、參與“猜謎”游戲等方面積累了相當豐富的敘事經驗。希區柯克將懸疑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天衣無縫地鑲嵌,其所涉人性之深度至今無人能步其后塵。在懸念的設置上,忻鈺坤大量借鑒經典懸疑電影中反復出現的有關“謎題”敘事、非線性的時間倒錯,以及運用人物內視角營造“旁觀者清,當事者迷”的敘事效果。近年來,好萊塢黑色電影大量采用非線性復雜敘事,劇情設置謎題,形成一批被影迷稱之為燒腦片、高智商片的新黑色類型,比如《記憶碎片》《穆赫蘭道》《蝴蝶效應》《盜夢空間》等等。忻鈺坤很明顯受到這些電影的影響,他早期在西安一家當地的電視臺做欄目劇時,就把經典大片中的非線性敘事技巧引入欄目劇的拍攝,而根據他自己的采訪錄,早期《心迷宮》曾嘗試著剪輯了一個線性敘事的版本,但很快棄之不用。從敘事學角度考察,一部作品的意義不僅取決于它講述了一個什么樣的故事,同時也關乎這個故事是怎么被講述的,即故事的話語呈現形式。《心迷宮》從線性敘事到非線性敘事的修改,導演將故事分割成若干微小的“敘事模塊”,并通過人物內聚焦重組,這樣故事的講述不再依賴于傳統的因果鏈接,而是建立在觀眾與故事人物信息的差異接受所產生的步步錯位與懸念當中。如影片片頭設置了全篇最大的“謎題”:回鄉路上,大壯在猶豫要不要殺搭他順風車回鄉的陳自立,以便娶暗戀多年的陳自立老婆;而在村里,陳自立老婆和村民正在為陳自立的出殯做最后準備。明明活著的人卻正在被舉行喪禮,那么殯棺里躺著的人究竟是誰?大壯掄起的磚頭會不會最后砸下?開篇伊始,這組平行蒙太奇伴著詭異和令人不安的金屬感音響配樂,直接牽制住觀眾的敏感神經,并把觀眾迅速拉到了敘述者設局的“猜謎”當中。當然,此處敘述者與觀眾之間是“共謀”的關系,在懸疑與謎題類型中,觀眾期待的觀影體驗便是一場心靈游戲,而故事的講述者在環環相扣的鋪墊中要給觀眾留出競猜的空間。《心迷宮》的“謎題”在開篇不久敘述者就主動解謎,交代了尸體是被肖宗耀誤殺的白虎。在《暴裂無聲》中的“謎題”則一直持續到了影片的最后,觀眾才知道磊子是被煤老板誤殺的,而且一直在瘋狂尋找兒子的父親張保民到最后也不知道兒子的尸骨何在,人物命運充滿悲劇感。
忻鈺坤在《心迷宮》和《暴裂無聲》中嫻熟地運用差異視點來制作懸念。《心迷宮》中燒焦的尸體原來是“混混”白虎,這一信息一開始敘述者就告知了觀眾,猶如希區柯克所說的當觀眾一旦知道了桌子底下的爆炸,他們自然情不自禁地參與到劇情的解讀當中,并持續到影片的終結。當村民一會兒認為死者是失蹤的黃歡,一會兒又認為是有身份證信息的陳自立,全知的觀眾被吸引到懸念的解讀當中,并因為自己掌握的信息量多于劇中人物而產生一種觀影的優越感。在《暴裂無聲》中導演忻鈺坤很明顯不想簡單重復這種技巧,此片中觀眾與劇中人物基本保持同樣的限知視角,而故事的講述采用三線并進,每條線索都采用人物限知視角以生成懸念和制造沖突。采礦老板認為律師拿走了自己的殺人證物,律師卻不知采礦老板死纏爛打要的東西究竟是什么。采礦老板擄走了律師的女兒作為要挾的籌碼,卻陰差陽錯的被礦工張保民當作自己的兒子救走了。差異視點生成懸念,使故事的講述搖曳多姿。而張保民救出了律師的女兒,但律師最終并沒有說出張保民兒子死亡的真相,這種對比直擊社會痛點,發人深省。
忻鈺坤通過非線性敘事、人物視角的信息錯位分配等營造的謎題敘事,是當代好萊塢電影的新寵。沃倫·巴克蘭(Warren Buckland)在《謎題電影:當代電影的復雜敘事》和大衛·波德維爾(David Bordwell)在《好萊塢敘事方法》都用了相當的篇幅討論。從《低俗小說》《羅拉快跑》《記憶碎片》到《盜夢空間》,這些復雜敘事的電影正越來越走向大眾市場,而且由于數字儲存技術和網絡播放平臺等新媒體環境,電影文本如同紙質小說一樣可以被任意拉片、反復回看,而泛懸疑一類的謎題敘事,使得電影的故事與敘事成為雙重觀看對象,觀眾的體驗性和參與性得以突顯,這也符合現代觀眾多元化價值觀的審美追求。由于中國傳統文化一直強調“子不語怪力亂神”,懸疑和謎題在中國的敘事傳統中一直處于邊緣地帶,觀眾能參與解碼的優秀電影文本相對較少。因此,《全民目擊》(2013)、《白日焰火》(2014)、《心迷宮》(2015)、《追兇者也》(2017)等影片的出現,通常能受到觀眾的熱捧,并收獲市場與口碑的雙贏。
三、類型照進現實的底層關懷與文化癥候
在《心迷宮》和《暴裂無聲》中,忻鈺坤以紀錄片似的影像風格塑造了一個真實而略顯粗糲的鄉村中國。塵土飛揚的馬路、低矮簡陋的房屋、粗糙廉價的人物衣著,影像在肩扛攝影機略顯搖晃的拍攝捕捉下徐徐展現中國式鄉村的日常丑陋。在影調風格上,導演處理得相對灰暗而沉悶,他將兩個故事的時空都安排在蕭條的北方秋冬農村,《心迷宮》蕭條的農村加上大量的夜景拍攝,更顯氣氛凝重,而《暴裂無聲》中光禿禿的石頭山,昏黃的枯草,滿山隨處可見傷痕累累的廢棄礦洞,使影片的調子更顯悲涼。特別在拍攝張保民為主線的農村戲份時,影像采用黃色、黑色為主打色,外景拍攝在后期也不做過多的柔光處理,而是刻意營造出一種冷峻、粗糲的農村原生態的生活質感。《心迷宮》中孫家老爺子葬禮的那場流水席上的村民甚至都寥寥無幾,村長的兒子一心只想去闖蕩外面的世界。這其實不僅是《心迷宮》劇組經費短缺所致,也恰恰隱喻了今日中國農村十分嚴重的空心化現象。這一景象在《暴裂無聲》中仍有沿襲,攝影鏡頭隨著張保民四處尋找兒子,但即便使用變形寬銀幕鏡頭,張保民在農村所經之處人煙稀少,一片蕭條,只有源源不斷往外輸送礦產的巨型卡車在貧瘠的山村公路上塵土飛揚。此時,忻鈺坤在類型的外衣之下潛藏了一種文藝片的文化訴求,他以敏銳的洞察力捕捉被喧鬧的文藝界集體漠視的“鄉村之殤”,相比近年來其他農村電影對中國鄉土的詩意想象,忻鈺坤的冷峻、粗糲和真實中體現了一個電影人難得的社會責任感。
《暴裂無聲》以“羊”為文本故事的草蛇灰線,隱喻社會生存的“叢林法則”和“弱肉強食”的社會食物鏈。以張保民為代表的底層社會養羊、兒子張磊在保護小羊中慘遭毒手,但這一階層仍保留著食草者的樸實和善良,“悍民”張保民在危難中救下了律師的女兒,屠夫丁海的一只眼睛曾被張保民戳瞎,但面對上門尋子的保民,丁海忍住了怒火,甚至在打手大金追打保民時,仍能及時出手相救。昌萬年所代表的食利階層處于食物鏈的頂端,他們通過非法手法打壓底層、擠兌同行,而在非法攫取巨額財富后,再通過樂善好施搖身一變為有良心的“民營企業家”。然而,導演對處于金字塔塔尖的食利者進行了臉譜化的描寫:他們在完成資本原始積累后,追求“體面”的生活,衣食住行分外考究,并把自己打造為某種“酷玩”的資深玩家,但光鮮的外表難掩飾其可怕的“吃相”,就如導演用特寫鏡頭凸顯出的昌萬年“吃西紅柿”和“吃羊肉”大席中表現的貪婪。
影片還通過多角度對比強化這兩者的對立與差異。首先是兩個階層所居住的空間布景,昌萬年的辦公室奢華無度,而張保民家徒四壁;昌萬年一人食滿桌羊肉,而張保民饅頭就著腐乳干吞。最為可怕的是影片中對兩個階層下一代的歸屬隱喻,昌萬年的孩子在國外留學,未來仍處在食物鏈的頂端,而張保民和丁海們的兒子只能在石頭、放羊和奧特曼超人想象中度過匱乏童年,張保民最終也沒能知道自己兒子尸骨的下落,有智力缺陷的丁海兒子漢生雖然見證了慘案的全過程,卻同樣無法言說。
《暴裂無聲》將律師徐文杰的家庭設置處理得稍顯隱晦,他應該原本擁有幸福美滿的家庭,在孩子的追問下,我們可以判定他的生活遭遇了突變,他的妻子可能不在了,他還需要一大筆錢,最后他鋌而走險以買通關鍵證人做偽證,來賺取昌萬年的50萬元現金報酬,從而把自己卷入了昌萬年的非法采礦案和兇殺案。徐文杰作為律師,本應是社會的良知和不公的代言人,然而卻在錢權交易中同流合污。《暴裂無聲》以“象征和隱喻手法”在“類型外衣下躍動著一顆直視社會痼疾和生態隱憂的責任心”,這是一個時代的癥候,“提示我們在娛樂至上的當下審視真實的生活,反思社會發展的困境”。[5]
這個故事的現實邏輯與20世紀30年代茅盾的《林家鋪子》有相似之處,說的都是社會叢林法則中的食物鏈問題,是大魚吃小魚的故事,但區別于《林家鋪子》的中產立場,《暴裂無聲》十分難得地采用了底層視角。相比在《心迷宮》中導演不免以最殘酷的世俗眼光忖度赤裸裸的人性之惡,描繪了一個人心崩塌,陷落失序狀態下的真實鄉村;在《暴裂無聲》中,忻鈺坤有意修正了這種客觀審視的敘述方式,賦予了身處底層的張保民們一種樸素的善良,以及他們之間共命運的互信、互助。屠夫丁海、親鄰栓子,以及礦工幫廚等等,在這個充滿暴力與冷酷的故事里,導演給予這些底層人物以淡淡的溫情和些許的慈悲,以慰藉他們苦難的靈魂。
青年導演忻鈺坤是典型的新一代導演,他是本土電影節遴選和扶植出來的新人,他的成長見證了中國電影工業體系的日趨成熟。從《心迷宮》到《暴裂無聲》,忻鈺坤的電影類型清晰,以故事見長,熱衷于電影語言的話語實驗,市場接受度好;尤為可貴的是他在類型的敘事外殼之下,關注和反思當下社會的現實問題,堅守電影的藝術本性,值得期待。
參考文獻:
[1]沈曉平.當獨立電影遇到產業化:一個偽命題[ J ].電影藝術,2013(05):28.
[2]陳旭光,張立娜.電影工業美學原則與創作實現[ J ].電影藝術,2018(1):101.
[3][法]巴贊.電影評論辯[ J ].崔君衍,譯.世界電影,1986(1):91.
[4]胡言.我站在橫店,嗅到2021劇集創作新風[ J ].武漢廣播影視,2020(11):51.
[5]路春艷.《暴裂無聲》:沉默的憤怒[ J ].當代電影,2018(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