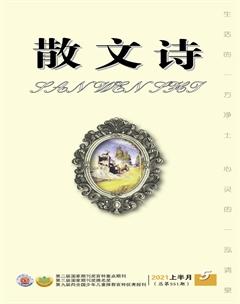詩意的棲居
草樹
1500多年前,陶公辭去彭澤縣令,作《歸去來兮辭》,為中國農耕文明,描繪了一幅“詩意棲居”的愿景,它的影響力之大,天下少有匹敵,或許唯19世紀美國作家梭羅的《瓦爾登湖》,與之有著幾分相似,或可媲美。中國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思想,在詩人和作家的個人性寫作中,陶公體現得最為充分。歷代文人雖有一份歸隱田園的宏愿,卻沒有幾人能夠付出決絕的行動。當代社會處于第三次信息革命浪潮之后的互聯網時代,整個世界是符號和擬像的狂歡,轟轟烈烈的城市化運動加劇了人和自然的疏離——與其說是人和自然的疏離,不如說是人與自我的疏離。快節奏的生活,喧囂的環境,應接不暇的快餐文化,就像洪水裹挾樹葉一樣,沒有人能夠抱住岸邊一棵垂柳稍加回望,而身不由己,隨波逐流。在詩人楊鍵眼里,長江岸邊的蘆葦是守望者和哀悼者,唯有蘆葦,在守望和哀悼著那一遠逝的文明中心。在現代社會的宏大敘事中,每個人作為個體,無不是被邊緣化的。在這個物質主義的時代,詩人更如是。詩人呂德安冀望在語言中建立一個“無地點的天堂”,他借用了一個美國北部小鎮的名字:曼凱托。對他來說,曼凱托是一個短暫的寄居地,他并沒有與那個地方發生真正的生存意義上的交集,因而曼凱托于他更多是一個異國的審美存在、一個符號。他在這個符號里注入了馬尾的童年記憶。在當代詩人中,很少有詩人能夠在當下,“此時此地”,在語言中建構一個“詩意的棲居地”,不是帶著哀怨,或者存有幾分幻想,而是真切地沉浸其中。
詩人繆克構的《浮廬筆記》是一個“語言學的特例”。在文體上,雖然采用了散文詩的形式,但是,并不能說它在語言形式上與分行詩就有著高下之分。事實上,詩與散文的區分,更多是內在的而不是形式上的。散文詩同樣有著聲音的停頓和語言形式的凝聚,有藝術上的區分和命名,只是在形式上比分行詩更自由一些。《浮廬筆記》顯然具足詩的特征,采用散文詩的形式,也許是出于語言呼吸上的考慮,或許在詩人看來,這樣的形式更契合內心碎片化的感受。德里克·沃爾科特曾經盛贊圣瓊·佩斯在《遠征》中重拾碎片,拼湊出一部想象的史詩。繆克構的《浮廬筆記》同樣是碎片化的,只是大致依著時序,去描述景物四時的變化和內心吉光片羽的明悟。也許正是散文詩的形式,敦促了詩人棄置意象化的表達,而回歸于一種古典主義的語言路徑,道法自然,情景交融,當然,也并非全然如此,高架路和浮廬,蟬聲和汽車喧聲,始終處于二元對立,只是詩人以自我客觀化之法形成自我對話,消解了二元對立的焦慮。
廬,本指簡陋的房屋。《浮廬筆記》之廬,是有著大落地窗和花園的,可見遠非簡陋,而是有幾分奢華的公寓了。作者不說“公寓”而言“廬”,大約僅將其看作一個寄身之所,并不為其奢華而得意。所謂“浮”,就更坐實寄身之所的意思了。在詩人看來,這一城中公寓,也不過一“浮廬”而已,要真正讓此“浮廬”扎下根,讓它成為一個真正的詩意棲居地,內心還得與這一片花園、這里的綠樹紅花灰墻紅瓦發生關聯。“早春二月,十二株櫻花蠢蠢欲動,到三月便已是滿目潔云了。桃花‘接龍,而后石榴;爬滿棚架的是紫藤,盛夏里開出一朵又一朵驚艷的喇叭花。”春花次第綻放,如同接龍,有此一現代性的命名,詩人的內心大約也開了花,有了曼妙的“接龍”。“與汽車的喧鬧聲相比,在城市快節奏的腳步中,蟬聲是可以忽略的。緊閉窗門,在開著空調的房間里坐著,耳中何曾能有蟬聲如注?其實,蟬聲說不上有多美,更談不上有多重要,只是,靜下心來聽一聽呀,這也是生活的腳步聲。”現代都市中,車流如潮,行色匆匆,又有幾人能聽見自己的腳步聲?自然也聽不見蟬聲。由此足見詩人內心的寧靜和心思的敏銳,一個靜立窗前依簾眺遠的詩人形象也儼然在眼前。
詩人繆克構出生于東海之濱,我曾得其惠贈詩集《鹽的家族》,在我的閱讀記憶中,他的詩視域開闊,風格粗糲,真正有著鹽的苦澀,也不無語言上的“百味之母”的意象。《浮廬筆記》顯示出他寫作的另一風味的語言樣貌,仿佛脫盡了鹽的粗糲,而不無細沙的質地——柔軟,表面光滑,但并非沒有阻力。這種物理上的阻力,即是語言的張力——
啊,這冰河開裂的聲響。我一陣狂喜!
啊,是河流解凍的吶喊!
河面隱隱傳來不易覺察的裂紋,那是春天吻上河水的羞澀的唇紅,是初戀少女最為大膽的在你肩頭輕輕一拍……
仿佛經年的堅守,都是為此刻這一開裂的果實而存在。內心的甜蜜和憂傷,就這么輕輕被一陣輕柔的微風破譯。撕裂的口子是如此細小,密如蛛網,無從修補。一切歷歷在目,如青春的模樣在中年的狂雪中跳動,如少女吹彈可破的肌膚中,手臂遮羞處的顫抖……
冰河開裂,萬物復蘇,這一被慣常審美框定在生命力勃發或革命浪漫主義昂揚的定式,詩人給予了全新的命名,且溫婉而柔美。這是中年境遇下真正的大動靜——浮廬之野,并非寂靜的草木枯榮、花開花謝,而是連冰河開裂也有著生命的柔軟質地。
《浮廬筆記》筆觸細膩,安于孤獨而并無孤憤,憐惜自然之美而并不物哀,很有幾分川端康成的古雅嫻靜,或豐子愷的平實雍容。一個詩人沉浸于物、于四時,方能抵近自我之不變、人生之從容,從而得以脫身于喧嘩與騷動之外而詩意棲居。《浮廬筆記》所示,“浮廬”不再浮,而是有根的,如同奧德修斯的故土伊塔克那張床是有根的,他說出來,盡管滿面滄桑人不識,他的存在卻得到了印證。詩人繆克構說出了浮廬的四時之變,無論櫻花的絢爛,還是紫藤的枯萎,溪水枕著鳥鳴或馬槽引來寂靜嘶鳴,直觀的或想象的,這就夠了,足以擺脫高架路上兩盞燈的盯視,而在現代社會的浮華中實現真正的詩意棲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