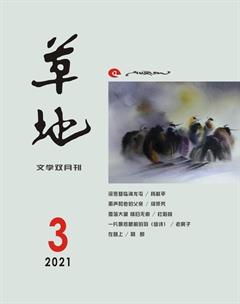心靈世界的藝術之美
羊子
四川作家中,王慶九很多人不太熟悉,但在阿壩州這片熱土上,幾乎沒有一個文藝工作者不感動于他的文藝作品、不敬重于他的為人。尚不認識他的人,可以有三個途徑去了解,一是閱讀他的文藝作品,二是傾聽他人講述他的為人處世,三是直接接觸他本人。
在眾多文藝家里面,令我肅然起敬、高山仰止的,常常是那些從底層出發、一路勤勉開掘奮發、成就不斷、并且不忘謙遜獎掖提攜鼓舞后進的長尊者。王慶九就是其中亦師亦友的一個人。
文友王慶九出身教師行列,處處閃爍著“為他人做嫁衣”的犧牲品行。曾經一心為教育,而今一心為文學藝術,竭盡全力在以藏族羌族為主體民族的自治區工作,甚至達到全心全意的地步。無論誰,不管其籍貫年齡族別性別,只要愛好,只要作品優秀,都可以在他主編的《四川民族教育報》《九寨溝》以及后來的《阿壩文藝》上刊登發表。幾十年下來,但凡認識他的人,都會喜歡他這個人,記住他的謙遜、寡語、真誠和任勞任怨、兢兢業業,記住他的文章彌漫性靈,欣賞他的攝影唯美別致,感嘆他的美術升華現實。毫不夸張地說,仰慕他這樣“純棉性質”的藝術家的人,豈止是濃情的女性。所以,文友王慶九這種從心靈世界中釀造呈現給這個時代的文學之美、藝術之美、生活之美,常常令我等男性不禁為之喝彩,擊節贊賞。這里,只想談談他的散文集《獨唳無聲》及其美學特征。
讀過這本散文之后,總體來說,我的審美世界意外收獲了這樣一份恬美難得的意境:院壩上一堆一堆的糧食,在麗日和風中,閃射出小麥或玉米、稻谷的金色光芒。偶爾有人的說話聲從屋檐下傳來,清澈,透亮。雞鳴攀沿炊煙,飄逸又嘹亮。井水淌出的水流倒映現出微笑的面容。田疇四野,翠竹籠屋。這院壩是唯一的火塘,燃燒出光芒溫暖四周安靜的心。
文若其人。我的這個閱讀印象,本質上應是王慶九本人精神心靈的獨唳無聲:自足、自我、豐碩、燦爛、溫馨、唯美、白玉一般的人品與熠熠生輝的文章形成互照對應。我被他這個文友澄澈的心靈世界與純凈的語言辭章交融綻放出來的多重美好深深感動。
第一重美是勇于自塑、甘于自我的孤獨之美。孤獨是人的本性。凡成就事業者,莫不享受孤獨。作為偏居一隅的文友王慶九,不離不棄曾經歲月中的種種自我,那是源自生命也源于生活的孤獨,是身體的孤獨,更是心靈的孤獨。這孤獨,猶如一把凌厲的小刀,清晰而深刻地刻畫出當初與眼前的記憶和生活。好一個“獨唳無聲”,坦然為題,毅然成書!將一個熱忱于文學藝術和生活的文人精神孤獨與心靈孤獨,宣泄得如此嘹亮鏗鏘,仿佛撕開自己的胸膛,將五臟六腑的癡情與忠貞,展覽給天地萬物看。聽——他是這樣說的,“不管怎樣,能夠在紛雜與炎涼中坐下來內視自己,如長空孤雁般自由地呼鳴幾聲,而不計較前方是槍口還是回應,便能獲得一些撫慰與寧靜。如此,也能在藝術世界或夢中完成一次次無聲的獨唳之后,更厚重踏實地續走俗世人生。”看——獨唳無聲的落腳點,是前行,是暖色,是人生,不是悲觀的形影相吊。任性而坦蕩,是孤獨之美的魅力所在。
第二重美,是心地善純、情真意深的情感之美。不管是“負笈為誰”“夢且隨風”,還是“靈蘊山水”“世事囈語”,這四個小輯,從童年書寫到青年,再到中年,無不一以貫之以晶瑩純粹的濃濃情意,發乎本善本真的那顆寶石般的心。閱讀他的文章,就是與寧靜孤獨脆弱而且堅強勇敢善良純粹的另外一個自己相逢、相知,并且,浪漫而富于真情,彰于才情。看見他的行走感嘆,也會不由自主地同時看見自己的過往歷歷在目。
第三重美該是形象生趣、思考幽邃的思想之美。獨孤求敗是武俠劍魔,也是作家金庸獨步寰宇的心境反照,而獨唳無聲的王慶九則在孤獨中傾聽大千世界,觀察物候社會萬般景象,一面開啟思維的鉆頭,獨自向那自己未知的自然世界與人類社會,細心探掘,抒寫出屬于自我精神世界的各路主題思想和情感姿色,遇見的往往是砥礪而行、高舉自尊的那一個覺醒的和有價值的自己。譬如《活著》中擲地有聲地說道,“同樣是在孤燈獨照時,我又可以一次次高昂起人的自尊,一遍遍用想象的磚石架構自由和正義的天庭,盡情享受個性、人格和理解與愛的精神盛宴——或許我們永遠不會抵達某種境界與高度,但有一點可以自慰,那就是我們有一顆真誠、善良的靈魂。因為權貴盡管可以永垂不朽,但那只是少數人僵死的歷史,而真善之美無須鐫刻碑銘卻可以萬古流芳,而且因千千萬萬人精神的滋養永葆生命的激情與活力。”
再看他的第四重美,用語端莊、修飾唯美的文辭之美。著名羌族作家谷運龍先生為這部散文集撰寫序言時,即以“獨唳之中的靈心妙語”為題,可見王慶九作為一個作家的語言文辭運用之純熟、感染力之強烈,著實撞擊著讀者心扉。看家居之美,“溫煦的陽光在嫩綠的柳芽上歡快地撲閃著它的亮翅,這詩意的舞蹈中,女兒啼鳴如歌……”再看《問禪大慈寺》中的出入,“一杯清茶,容納百味。不管是苦澀、甘爽,還是清香、寡淡,飲者淡然品之,豁然容之。……禪是茶的中心,茶是禪的表象,禪與茶的共同訴求和憑藉是心,是感悟,是頓想,是自我修為……”可以說,這般珠圓玉潤的閃爍文辭之光的話語比比皆是。
第五重美,是創新意境、恪守審美的文藝之美。王慶九是一個虔誠執著于文學藝術的人,對于自我苛求甚嚴,不管謀篇,還是出題,或是敘事情景,還是抒發心懷,都注重塑像、造境,而且還要讓華章透射出自我良好的審美修養和審美主張。他的攝影總能從尋常中發現另外一種景致,陶冶自我,打動他人。他的美術也是在神思的熔爐里冶煉鍛打之后,將生活中的信仰和社會中的變遷,空靈又深邃地表達出來,給人以獨特的鑒賞意蘊和心靈呼應。他的文章更是不愿跌入簡易通俗的尋常表達,而是總在落筆時給予自我和預設的讀者以特別的精妙滋味與超拔,進而播種新的啟迪和感動。
這些探索、創新和守護、拓展,從精神層面上回應著文人王慶九自身的渴求與訴求,自洽與自重。從文集中不難看出,每一篇文章都是他的藝術寵兒,都能夠從不同界面不同角度回答安撫他人生的“獨唳無聲”,也就順理成章發現他的第六重美——且行且為、言為心聲的心靈之美,這是最本質的、也是最核心的美。觸發于心,抵達于心,收放自如于自我觀賞與讀者惠覽之間,不慍不火,不卑不亢,始終與自然、與歲月、與社會并列對視、平行交流。這樣的人生平凡而華麗,孤獨又豐盈。唯有經過心靈的覺醒和時間的洗滌,任何一種藝術的觀賞、體味或營造、產生,才能通達到天人合一的自由境界,也才能實現精神和肉體的相擁互惠。成就卓著的文友王慶九一路沉穩地走來,懷著一顆自我珍重、自我反思、自我超越、自我陪護的文藝之心,與人為善,助人為樂,喜于創新,甘于創造,為這個可以更好的人世間奉獻出新的作為,好的品質。
因之,作為另一個結緣鐘情于中國語言文字的人,在與文友王慶九的交往交際中,我也時不時會感受到一些超越于眼下氣候和季風的韌勁和定力,風云際會,漂流或泛濫。身邊有這樣慧心深懷的文藝家的映照和堅守,孤獨的膽識和睿智的生命也會獲得另外一種天意的加持和遞進。更為慶幸的是,可以與之為伍,可以與之言笑晏晏,忘卻歲月漫漫將一個人的肉體格制以沖刷磨蝕。我相信,心靈世界的藝術之美,讓沉穩的王慶九們學會了與外部世界的握手言和,二律背反,彼此成就。
忽然,我恍然發現,展開的書卷對面,藍色天空明媚而親昵,楚楚動人的云彩仿佛書中閃亮的文字,笑而不語的樣子好似受了王慶九的滋味而特別顯露出來。這樣的美好,恰如郁郁春風,撫弄目光,香徹心扉,久久不可散去。
唐俊高先生與阿彌陀湖
——長篇小說《一湖丘壑》閱讀后的一次現實追蹤
“世上有就是戲上有,戲上有就是世上有。”這是母親對我講的。那時,我在讀高中,回到岷江峽谷半山上梯田簇擁的家中,母親是在一次交談中,深有感觸說的。
許多年后的今天,當我想起這句話的時候,卻在由衷感嘆著唐俊高先生的一本小說。簡單抽象地講,這部小說反映的是赤子回報桑梓,搭上時代的快車,一方面漸次改變了故里世界的面貌,一方面理想性地承遞上了鄉村傳統文明的精神,五味雜陳又充滿生機地帶動著父老鄉親一起發家致富。小說是好小說,里面各色人等性情鮮朗、命運關系層出交錯,故事情節起落有致、顯隱分明,終究不失重構中國新農村的理智理念與實踐實際相統一的有機探索,出色地顯示了冰山理論的藝術魅力。文壇在北京還專題召開作品研討會,盛贊這部作品與著名作家周克芹《許茂和他的女兒們》同等重要。小說是《一湖丘壑》,這里的湖,就是阿彌陀湖,而這個湖本身是不存在的,源于茆家灣第一個考出去的那個后生偶得外財,一心回鄉緣溝谷地勢而筑壩蓄水以養魚的水庫。然而,正因為這個湖從無到有、艱難而幸運的存在,像一枚突然嘹亮的信號彈,照亮了中國尋常偏僻卻默默沉浮的一隅鄉村。隨之而來的,是愛心月亮、政治陽光、企業雨露,助推著茆家灣這個小小世界的自我生長和人文復興。
讀完小說,再看書名《一湖丘壑》,仿佛是一幅線條簡約的國畫,或者色彩明快的油畫,情節與主題、本意與寓意都是融洽得體,既是自然的,也是社會的。然而,在我固執的心中,還是念念不忘那個本該是水到渠成的《阿彌陀湖》。
后來與唐俊高先生交談,我的兩個疑團才得以解開。一個是阿彌陀湖這個存在,我與他的認識就源于《一湖丘壑》這本小說,從文學的形象和意義上來說,這個湖顯然是作家虛構出來的,服務于小說的需要,雜取種種而塑造出來的“這一個”。俊高先生卻說“你去不去看一下阿彌陀湖”的時候,我的腦海頓時飄起一叢疑惑的云煙。后來,當我真實看見這一片倒映天空和鄉村丘巒的湖水的時候,還是堅持認為,這是從小說《一湖丘壑》中走出來的湖水,換句話說,這湖水就是從唐俊高先生內心深處的愛意中挺拔起來的。第二個疑團是關于書名,我說最好還是《阿彌陀湖》,俊高先生十分肯定地說,書名本來就是《阿彌陀湖》,終究因為作品在面世之前的某種原因,才輾轉剖腹取出這個名字《一湖丘壑》。真是難為這個可愛的作家了。“五年后以再版,得其所哉,還是復歸原名的好。”我理解著作家,堅持著說。
殊不知在同一天下午,與唐俊高先生一行,邁過鐫有“凈土信愿念佛路,佛地三寶般若門”楹聯的山門,參觀完一個廟宇后,我的內心獲得了不可言說的加持。我前面的那些堅持,在這里,仿佛是冥冥之中契合著人生的另一個要旨。阿彌陀佛。這里,首先我要說的是,關于兒子與母親的一個故事。兒子的母親因為自己的機緣,四十年前出家并且做了寺廟的主持,弘法興寺,直至眾望所歸,身隱塔林。這個寺廟叫做水觀音寺。母親的兒子奔走于人世間,一路做了不改癡情的作家,如今寫出《一湖丘壑》這樣的佳作名篇,即便本身就是《阿彌陀湖》。這個故事,于我而言,是情懷的一種滋養和福報,但是,借此也可大膽推導出,阿彌陀湖就是兒子敬獻給今生今世唯一的母親及其四野鄉親的一腔慈悲。
真是一派好水!阿彌陀湖就是這樣,恬恬的,靜靜的,鋪開在我的眼前,在中國的西部,在四川盆地中央的丘陵地帶,與天空平行。一條大河絲綢一般,從丘巒當中穿流不息,這就是沱江,從岷山東側流淌而來,水觀音寺即在這條深情的沱江東岸的巖壁之上,而我是從岷山西側的岷江上游走來。因為岷山,我與沱江相會,因為沱江,我與這個廟宇結緣。當然,這是觀覽過楚楚湖水之后的美情。
晴朗的天空,白的流云忽而遠去,忽而消散,總在變換著阿彌陀湖的水色。阿彌陀湖在四面丘巒的中央,淺淺的丘巒上站著一排排蔥郁的杉樹。喔,阿彌陀湖,層層綠色的田疇環繞著她,嶄新的水泥路若隱若現地環繞著她,規劃中建筑起來的第一期十五家鄉村樓房映襯著她,幾處早先的農家舊房新舍偎依著她,透出小姑娘一樣好奇眼光的新建棧道環繞著她,蘆葦、柳樹、青松、蒼柏環繞著她,即將出場的二期三期規劃中的新村樓房同樣簇擁她。啊,阿彌陀湖,因為峽口山崖上一塊形似佛陀的巖石而喚作阿彌陀佛石,然后因為湖水徹底淹沒了這塊巖石而得名阿彌陀湖。真好,既是小說中的湖,也是現實中的湖。
其實啊,阿彌陀是梵語,意為無量,阿彌陀佛就是無量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出家人和俗家人時常善積的口德。想來,阿彌陀湖與阿彌陀佛一樣,不管在小說《一湖丘壑》或《阿彌陀湖》中,還是在現實的中國鄉村中,都是美好,都是祈愿而起的勝境。再想想,阿彌陀佛與阿彌陀湖一樣,無論在兒子的母親口中,還是母親的兒子心中,都是修行,都是溫婉在心的思量。這讓我不得不憶起,當時出了水觀音寺山門,觸眼可及的一聯福祉:“千處祈求千處慮,萬事吉祥萬事興。”
唐俊高先生是我的朋友,在他盛情的陪同下,我的身心才得以走近清清亮亮、幽深蜿蜒的阿彌陀湖。而且,就在當天,就在湖邊,與小說中曾縣長原型人物之一的新朋友、茆家灣陀表叔原型之一的湖畔新居主人、新浪四川網年輕的女記者等一行,圍坐一桌,享受著燦日的春光湖水,品嘗著阿彌陀湖中剛剛打撈的新魚美味,我的思緒卻一直處于虛虛實實,既在置身的現實中,也在記憶的小說情節中,時而與小說中風車車、酸果果舉杯,時而在盛宴中與唐俊高先生言笑晏晏,時而在阿彌陀湖的靈眸深情中,歡聲笑語一個新農村在當代中國的蓬勃與新生。
注:阿彌陀湖,位于資陽市雁江區東峰鎮楊家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