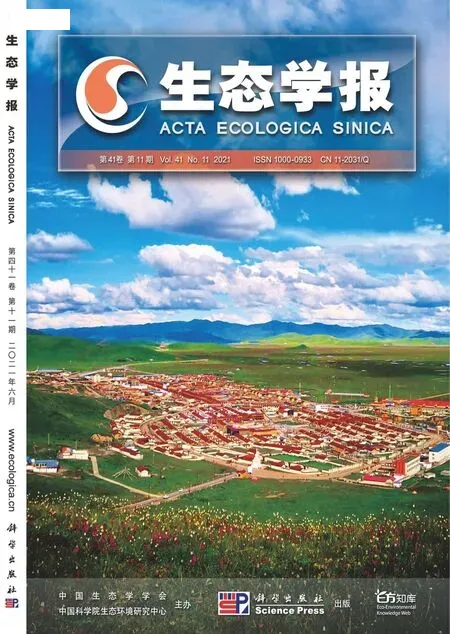內蒙古荒漠草原防風固沙服務變化及其驅動力
朱趁趁, 龔吉蕊, 楊 波, 張子荷, 王 彪, 矢佳昱, 岳可欣, 張魏圓
北京師范大學地表過程與資源生態國家重點實驗室,北京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部, 北京 100875
土壤作為一種不可再生資源,為陸地上廣泛的生物多樣性提供基本材料,并為人類社會提供商品、服務和資源,對維持地表生態系統的正常運行至關重要[1- 2]。土壤侵蝕不僅造成表土流失和土壤質量退化,還會導致河流淤積、水污染、空氣污染等次生環境問題的產生[3]。其中風蝕作為中國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區的重要環境問題,是引起該地區土地退化和制約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原因,受到了研究者的廣泛關注[4- 7]。
風蝕的動態變化是自然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共同作用的結果,在所有人類活動中,土地利用/土地覆蓋變化與生態系統提供生態系統服務能力的變化最為相關[8- 9]。作為風蝕的主要動力,近地面風通過移除表土來強烈的影響風蝕過程,張等人[10]應用風洞實驗和數值模擬發現近地面風速的減緩可以顯著減弱同一植被覆蓋下的風蝕[11]。降水可以直接影響土壤含水量,土壤水分在土壤顆粒間產生張力,增強顆粒間的粘結力,降低土壤的可侵蝕性,最終提高土壤表面抗風蝕能力[12]。而在內蒙古荒漠草原,強風和干燥松散的土壤表面之間的相互作用可能會導致嚴重的侵蝕[13]。植被通常被認為是保護土壤表面免受侵蝕的關鍵因素,有利于保持土壤水分,改變地表粗糙度,降低風速或增加閾值風速,從而降低風蝕潛力[12]。相比于裸地,有植被覆蓋的土壤不僅有助于通過根部的機械加固提高土壤強度,還能通過蒸散作用影響土壤系統的持留能力[14]。有研究表明,植被覆蓋率低于20%幾乎不會降低土壤表面的風速,而超過約60%,土壤侵蝕基本停止[15]。在相同植被覆蓋率下,不同植被覆蓋類型間表面粗糙度、冠層結構的差異對土壤的抗侵蝕能力有顯著影響[16- 17]。在風蝕危害嚴重和土地利用/覆蓋發生變化的地區,土地利用、氣候和風蝕之間的相互作用可能相當復雜。而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驅動侵蝕過程的應力之一,且大多基于風洞模擬,集中在沿海和內陸沙漠地區,很少在半干旱地區的荒漠草原進行[10]。因此,目前荒漠草原區土地利用、氣候變化與區域防風固沙能力之間的相互作用機制尚不清楚。
內蒙古荒漠草原處于荒漠與典型草原的過渡地帶,是最脆弱的生態系統之一,對氣候變化和人類擾動都十分敏感[18- 19]。低降雨量、頻繁的干旱和強風使該地區經常發生嚴重的沙塵暴,長期遭受嚴重的土壤侵蝕,具有發生荒漠化的潛在風險[5,20]。但同時內蒙古荒漠草原作為中國北部的生態屏障,又在防風固沙等方面起著無可替代的作用[21]。因此,本研究以內蒙古荒漠草原為研究區,采用修正風蝕方程(Revised wind erosion equation, RWEQ)量化該地區2000—2017年防風固沙能力變化及其與氣候、植被蓋度和土地利用/覆蓋的關系,以支持綜合決策,為提出控制該地區荒漠化所需的長期解決辦法提供理論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研究區位于內蒙古中西部的荒漠草原地帶。荒漠草原是典型草原向荒漠過渡的地帶性植被類型,主要分布于內蒙古高原中部,其地域范圍東起蘇尼特,西至烏拉特區,北與蒙古人民共和國荒漠草原相連,南抵陰山北麓低丘陵,整體上以狹長帶狀呈東北至西南方向分布,是中國北方草原的重要組成部分,約占中國北方草原的 34.7%[22](圖1)。該地區屬干旱大陸性氣候,年降水量100—300mm,年平均氣溫約3—9℃。,棕鈣土為荒漠草原的地帶性優勢土壤,隨著濕潤度的增加,土壤類型由淡棕鈣土、棕鈣土逐漸過渡為栗鈣土,土壤肥力較低,有機質含量一般低于2%。荒漠草原群落組成單一,由于氣候條件惡劣,植物生長較差,草群稀疏矮小,總蓋度15%—35%[18]。植物主要是多年生旱生叢生小禾草,并有一定數量的旱生、強旱生小半灌木或小灌木組成。在氣候進一步變干的情況下,草原群落中旱生小半灌木的作用逐漸增強[23]。

圖1 研究區地理位置Fig.1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study area
1.2 數據與方法
1.2.1數據來源與處理
本研究采用的數據包括氣象數據、遙感數據、土壤數據以及土地利用數據。其中氣象數據(包括風速、降水、溫度等)來源于中國氣象科學數據共享網(http://data.cma.cn),并在ArcGIS中采用Kriging方法進行插值;遙感數據來源于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使用中分辨率成像光譜儀(MODIS)時間序列NDVI (Normalized Vegetation Index)數據集(MOD13Q1產品) (https://modis.gsfc.nasa.gov/),分辨率為250m。所用數據具體序列為MOD13Q1.A2000193、MOD13Q1.A2000209、MOD13Q1.A2000225、MOD13Q1.A2000241、MOD13Q1.A2017193、MOD13Q1.A2017209、MOD13Q1.A2017225、MOD13Q1.A2017241.并在MRT(Modis Reprojection Tool)中進行拼接,在ENVI中對數據進行校正,采用最大合成法(MVC)得到半月NDVI數據[24];土地利用數據來源于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科學數據中心(http://www.resdc.cn/default.aspx),分辨率為30m,本文中的土地利用分類采用中國土地利用/覆蓋遙感監測數據分類系統,其中林地包括有林地、灌木林、疏林地以及其它林地,草地包括高覆蓋度草地、中覆蓋度草地及低覆蓋度草地;高覆蓋度草地指覆蓋度>50%的天然草地、改良草地和割草地,中覆蓋度草地指覆蓋度在>20%—50%的天然草地和改良草地,低覆蓋度草地指覆蓋度在5%—20%的天然草地。土壤屬性數據來源于寒區旱區科學數據中心(http://westdc.westgis.ac.cn/),基于世界土壤數庫(HWSD)的中國土壤數據集(V1.2)。本文中制圖與分析均以250m分辨率為基礎進行。
1.2.2防風固沙服務量化方法
植被引起的風蝕量的減少可以看作是防風固沙服務的物理量,以裸露土壤條件下潛在風蝕量與植被覆蓋條件下實際風蝕量的差值表示[25]。本研究選取修正風蝕方程(RWEQ)作為風蝕量的計算工具估算內蒙古荒漠草原生態系統潛在風蝕SL潛和實際風蝕量SL,以兩者之差G表示固沙量[26]。固沙量計算公式如下:
G=SL潛-SL
(1)
(2)
S潛=150.71(WF·EF·SCF·K′)-0.3711
(3)
Qmax潛=109.8(WF·EF·SCF·K′)
(4)
(5)
S=150.71(WF·EF·SCF·K′·C)-0.3711
(6)
Qmax=109.8(WF·EF·SCF·K′·C)
(7)
式中,G為固沙量(t km-2a-1);SL潛為裸土條件下的土壤風蝕量(t km-2a-1);SL為有植被覆蓋下的實際土壤風蝕量(t km-2a-1);Qmax為風力的最大輸沙能力(t km-2a-1);S為關鍵地塊長度(m);Z為下風向最大風蝕出現距離(m);WF為氣象因子;EF為土壤可蝕性因子;SCF為土壤結皮因子;K′為地表糙度因子;C為植被覆蓋因子。各因子計算方法如下。
(1) 氣象因子
氣象因子即風速、溫度及降雨等各類氣象因子對風蝕綜合影響的反映[26],其表達式如下:
式中,WF為氣象因子;Wf為風力因子(m/s)3;SW為土壤濕度因子;SD為雪蓋因子;g為重力加速度(m/s2);ρ為空氣密度(kg/m3);u2為距地面2m處的風速(m/s);u1為距地面2m處的起沙風速 (m/s);Nd為風速測定周期的天數(一般為15d);N為測定周期內風速的測定頻率(一般為500)。由于從氣象站獲取的風速為距地面10m高處的每日數據,因此采用“七分之一定律”對不同高度的風速進行轉換,并以日均風速和日最大風速進行降尺度擬合[27- 28]。ETp為潛在蒸發量(mm);R+I為降雨和灌溉總量(mm);Rd為降雨和灌溉天數。
(2) 土壤可蝕性因子
土壤可蝕性因子大小與土壤質地有關,其表達式如下:
式中,sa為土壤粗砂含量(%);si為土壤粉砂含量(%);cl為土壤粘粒含量(%);OM為土壤有機質含量(%);CaCO3為碳酸鈣含量(%)。
(3) 土壤結皮因子
式中,cl為土壤粘粒含量(%);OM為土壤有機質含量(%)。
(4) 植被因子
植被覆蓋因子表示一定植被條件對風蝕的抑制程度,其表達式如下:
C=e-0.0483(SC)
式中,SC為植被覆蓋度(%)。
(5) 地表糙度因子
地表糙度因子是由地形所引起的地表粗糙程度對風蝕影響的反映,其表達式如下
式中,Kr為地形糙度因子;Crr為隨機糙度因子(本文中取0);L為地勢起伏參數;ΔH為距離L內的海拔高程差。
1.2.3統計分析
以2000、2017年土地利用圖為基礎,在ArcGIS中利用疊加分析功能對2000—2017年各土地利用類型間的轉換進行統計并制圖。并統計2000、2017年不同土地利用類型的平均防風固沙量。采用雙變量局部空間自相關分析降水、風速和植被覆蓋度與固沙量間的空間相關性。雙變量空間自相關分析得到Moran′sI指數及LISA集聚圖。Moran′sI指數在[-1,1]之間,Moran′sI>0代表變量間呈正相關,Moran′sI<0代表變量間呈負相關,Moran′sI=0代表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變量間表現為空間隨機分布。LISA集聚圖按照變量間的局部空間相關性分為High-High(高高型)、Low-Low(低低型)、 High-Low(高低型)、Low-High(低高型)、Not Significant(非顯著相關型)。其中High-High 和Low-Low型為正相關,High-Low和 Low-High為空間負相關[29]。
2 結果
2.1 防風固沙服務的時空變化
內蒙古荒漠草原的防風固沙服務表現出明顯的空間異質性。2000年區域防風固沙量均值為14.63t/hm2,服務高值主要集中于研究區南部及東南部,而西南部的防風固沙服務較低(圖2)。2017年區域防風固沙量均值為22.53t/hm2,防風固沙服務熱點主要分布于研究區東南部,冷點分布于研究區西南部。2000—2017年,區域防風固沙服務整體表現出升高的趨勢,固沙物質總量增幅為53.95%,其中防風固沙服務提高的區域主要分布在研究區東南部。不同土地利用類型提供的防風固沙服務也有所差異,草地在該區域防風固沙中起主要作用。2000和2017年草地的固沙物質量分別占區域總固沙量的87.9%和89.2%,其中高覆蓋度草地的平均防風固沙量在兩年中均最高。2000年,各土地利用類型的平均防風固沙量大小依次為高覆蓋度草地>林地>中覆蓋度草地>建設用地>耕地>低覆蓋度草地>未利用地>水體,2017年,該序列為高覆蓋度草地>中覆蓋度草地>建設用地>低覆蓋度草地>未利用地>水體>林地>耕地(圖3)。2000—2017年間,各土地利用類型的平均防風固沙量除耕地、林地、水體降低外其余均有所增加。

圖2 2000、2017年防風固沙服務空間分布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sand fixation in 2000 and 2017

圖3 2000、2017不同土地利用類型的平均防風固沙服務Fig.3 Zonal average sand fixation in 2000 and 2017 in different land use types
2.2 土地利用時空變化
草地為研究區的主要土地利用方式,約占該區域總面積的84%。其中高覆蓋度草地主要分布在研究區東南部,中部為中覆蓋度和低覆蓋度草地,西南部主要為未利用地及低覆蓋度草地(圖4)。2000—2017年,土地利用類型的轉換主要發生在不同覆蓋度的草地和未利用地之間。總的來說,土地利用方式發生變化的面積占研究區總面積的5.6%,其中林地、高覆蓋度草地、低覆蓋度草地、水體、建設用地面積表現出不同程度的擴張,其增幅分別為74.11%、8.55%、1.74%、1.85%、63.07%。耕地、中覆蓋度草地和未利用地面積呈減少趨勢,其變化幅度分別為-4.41%、-3.36%、-1.16%。其中高覆蓋度、低覆蓋度草地和建設用地面積的增加均主要來源于中覆蓋度草地,林地面積的增加主要來源于耕地和草地,草地整體呈現出凈轉出的特征(圖5)。2000—2017年,土地利用類型的轉換主要發生在研究區中部和東北部,其中東北部主要為未利用地與中、低覆蓋度草地以及高覆蓋度草地與低覆蓋度草地之間的轉換,中部主要為不同覆蓋度草地之間的轉換。在土地利用發生變化的區域,其固沙量的變化占研究區總固沙量變化的9.65% (圖6)。

圖4 研究區2000、2017年土地利用/覆蓋Fig.4 Zonal land use/cover in 2000 and 2017

圖5 2000—2017年土地利用/覆蓋變化Fig.5 Transformation of land use/cover from 2000 to 2017

圖6 2000—2017年土地利用/覆蓋變化空間分布Fig.6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and use/cover transformation from 2000 to 2017
2.3 防風固沙服務與氣候因子及植被覆蓋度間的關系
研究區內年平均降水量呈現出從東南到西北遞減的趨勢,2000、2017區域年平均降水量分別為151.88mm、139.56mm(圖7)。研究區內年平均風速從東北到西南遞減,2000、2017年區域年平均風速分別為3.42m/s、3.72m/s。由表1可知,2000年降水、風速及植被覆蓋度均與固沙量表現為正相關,其中植被覆蓋度與固沙量間的相關性較強。2017年降水與固沙量間為負相關,風速、植被覆蓋度與固沙量間為負相關,其中風速與固沙量間的相關性較強。從雙變量局部LISA圖來看,降水量與固沙量的空間相關性在研究區東北部以Low-High型為主,在研究區西南部以Low-Low型為主,而在研究區東南部主要由High-High型及High-Low型組成(圖8)。風速與固沙量的空間相關性在兩年間發生了較大變化,其中2017年風速與固沙量的空間關系以High-High型和Low-Low型為主,分別分布在研究區東北部和西南部(圖8)。植被覆蓋度與固沙量的空間關系中High-High型和Low-Low型分別分布在研究區東北部和西南部,Low-High型的分布從研究區中部向東北部轉移(圖8)。。

圖7 2000、2017年平均降水量和年均風速空間格局Fig.7 Spatial patterns of average annual precipitation and wind speed in 2000 and 2017

表1 2000、2017年荒漠草原降水、風速、植被覆蓋度與固沙量間的雙變量局部自相關指數

圖8 2000、2017年降水、風速、植被覆蓋度與固沙量的局部LISA圖Fig.8 LISA cluster map between precipitation、wind speed、vegetation coverage and sand fixation in 2000 and 2017
3 討論
3.1 土地利用/覆蓋及植被覆蓋度對內蒙古荒漠草原防風固沙服務的影響
植被作為生態系統中的一種重要自然資源,一直被認為是保護土壤免受風蝕的關鍵因素,通過增加表面粗糙度和吸收周圍空氣流的向下動量在防風固沙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30]。不同植被引起的表面粗糙度和土壤理化性質的差異對防風固沙能力有顯著影響[31]。不同植被覆蓋下的土壤在質地、化學成分和有機質含量上各不相同,這影響著土壤的顆粒大小和重量,以及土壤保持水分和形成外殼的能力,從而決定土壤的可蝕性[13]。且隨著時間的變化,同種植被覆蓋類型的防風固沙能力也會有所變化。在本研究中,2000年高覆蓋度草地、林地以及中覆蓋度草地具有較高的防風固沙能力。灌叢和林地植被呈高度斑片狀,由冠層斑塊和相對裸露的冠層間斑塊拼接而成,相對于草地有更大的無植被間隙[32-33]。因此,盡管具有低懸枝的灌木和林地會降低土壤表面附近的風速并捕獲沉積物,但稀疏植物的“漏斗效應”可能會加速風,增加侵蝕,而天然草地在土壤地表硬度、含水量等方面表現出較好的特征,輸沙量少,從而使林地的固沙量低于高覆蓋度草地[9,34]。2017年高覆蓋度草地、中覆蓋度草地以及建設用地的平均防風固沙量較高,且與2000年相比都有所提高,其變化幅度分別為67.26%、58.33%、30.08%。一般來說,人類活動對土壤表面的擾動會使建設用地的防風固沙降低,但本研究區在荒漠草原,土壤表面疏松,更容易受到風蝕,建設用地中普遍存在的硬質化表面反而對土壤起到了加固作用,從而提高建設用地的防風固沙服務[35]。2000—2017年本研究中林地的固沙量降低。雖然有研究表明長期造林顯著提高了土壤肥力、團聚體比例、飽和水電導率、有機質含量、總氮含量,使土壤抗侵蝕能力顯著增強[36]。但是,由于干旱地區的水供應不足,無法支持大規模和長期植樹,且林地多來源于人工造林活動,對土壤表面有一定的破壞作用,并導致蒸散量的增加,從而降低土壤含水量,影響林地防風固沙服務的提供[9,37]。王彥武等對民勤縣綠洲邊緣固沙林防風蝕效應的研究也表明30年生梭梭林在降低風沙流流量和減少風蝕深度方面的效應高于40年生梭梭林,因此擁有最佳草、樹和灌木配置的物種對于防止干旱地區的風蝕至關重要[38]。本研究中耕地的固沙量在2000—2017年降低,這可能是由于長期耕作降低了土壤團聚體的穩定性,并使土壤孔隙度和持水量下降,土壤表層粗化嚴重,從而使土壤的抗風蝕能力下降,受風蝕程度加劇[39]。
土地利用/覆蓋變化,如土地撂荒、森林砍伐、植樹造林等,是土壤侵蝕發生和影響風蝕強度的重要因素之一[40]。土地利用/土地覆蓋變化通常通過長期改變土壤表面粗糙度和土壤化學和物理特性來影響風蝕,這一過程比氣候因素要慢[5]。近年來,內蒙古荒漠草原的土地利用方式的變化主要表現為建設用地的擴張、林地的恢復以及草地的轉換。土地利用方式發生變化的面積占研究區總面積的5.6%,而在土地利用發生變化的區域,其固沙量的變化占研究區總固沙量變化的9.65%,說明土地利用變化對防風固沙服務的影響不容忽視。然而,土地利用/土地覆蓋變化,尤其是在風蝕嚴重的地區,會增加土壤對風蝕的敏感性。本研究中林地面積的增加主要源于耕地和草地,雖然退耕還林提高了林地面積,但同時也增加了草地和林地的脆弱性,破環草地和林地的土壤水分狀況和表層土壤結構,且在轉換過程中有可能形成裸露地表,產生新的沙源[5]。總體來說,2000—2017年固沙量變化的90.35%來源于土地利用未變化的區域,其中,中覆蓋度草地未變化的區域固沙量呈升高趨勢,且在固沙變化總量中占54.23%,說明較為穩定的生態系統更利于生態系統服務的保持和提供,而在防風固沙服務的提供方面,中覆蓋度草地可能是最適于內蒙古荒漠草原的土地利用類型。
植被覆蓋度作為環境變化的量化指標,長期以來被認為是土壤保持功能的重要指標,在減緩風速和有效地保護表層土壤方面有重要作用[41]。有研究表明植被覆蓋度增加使土地表粗糙度增加,從而提高風蝕閾值,顯著降低風蝕風險[11]。Munson 等人的研究表明在20年的監測期內,美國科羅拉多高原植被覆蓋的下降顯著增加了風蝕速率[33]。2000—2017年,研究區的植被覆蓋度均值由0.265增加至0.402,同時固沙量也表現出明顯的提高,且兩年的植被覆蓋度均與固沙量呈正相關,體現出植被覆蓋對控制侵蝕的正向效應。這可能是由于起沙風速隨植被覆蓋度的增加而增大,從而使近地表的輸沙量減少[44]。空間上,植被覆蓋度與固沙量在研究區東北部和西南部表現為正相關,呈正相關關系區域占研究區總面積由2000年的44.87%降至2017年的31.24%,而植被蓋度在研究區96.84%的區域都表現為增加現象,說明2017年植被蓋度對固沙量的影響力減弱,這與植被蓋度和固沙量間相關系數的變化趨勢一致。
3.2 氣候因素對內蒙古荒漠草原防風固沙服務的影響
氣候是風蝕的主要控制因素之一,特別是在我國干旱半干旱地區,氣候侵蝕力主要受降水和風速的影響,其中風是引起風蝕的主要驅動力[43-44]。一般來說,風速越大,侵蝕作用越強,降水和溫度決定了一個地區的干旱程度,干旱的土壤更容易發生侵蝕[45]。內蒙古荒漠草原的降水、風速在時間和空間上均存在較大變率,其中降水集中在夏季,年際波動較大,自東南向西北逐漸減少,大風日則主要集中在春季[46]。降水可通過直接影響土壤含水量和土壤粘性以及間接影響植被生長來調節風蝕[47]。本研究分析結果表明,降水量與固沙量在2000年整體表現為較弱的正相關關系,在2017年表現為負相關,這表明在較干旱的荒漠草原地區,夏季降水對土壤和植被的影響不足以控制多發生在春季的土壤侵蝕。雖然降水與固沙量之間的相關性較低,其對土壤風蝕的影響不容忽視。風速與固沙量在兩年間均為正相關,且二者的相關性在2017年表現出明顯的增加,這可能是由于區域風速的普遍提高通過置換或移除表層土壤增強了風速對土壤侵蝕的影響,此結果與其它研究中風速強烈影響旱地土壤侵蝕的結論一致[11,48]。固沙量由潛在風蝕量和實際風蝕量共同決定,本研究中二者的空間分布基本一致,說明植被因子對風蝕空間分布的影響較小。本研究中風速與固沙量在研究區北部為正相關關系,這是由于研究區東北部具有較高的風速和較低的降水量,使潛在風蝕量高,而該區域植被覆蓋度相對較高,削弱了實際風蝕量,最終使東北部的防風固沙服務優于其它地區。因此,本研究中風速與固沙量為正相關的統計結果與其它研究中風速與風蝕量為正相關關系的結論并不矛盾。2000和2017的防風固沙在空間分布上存在較大差異,主要表現為研究區中部的固沙量的降低。對比影響防風固沙服務的各個因子的空間分布及大小,發現2000和2017年防風固沙服務分布的差異主要是由風力因子(Wf)引起的。結合圖7也可知,兩年的風速分布模式發生了變化,說明防風固沙服務在時間上的變化主要受氣候因素影響。
4 結論與展望
2000—2017年,研究區的防風固沙服務空間分布發生了明顯變化且區域固沙量升高。植被因子不是防風固沙服務空間分布特征的主導因素,總體來說,研究區內固沙量受降水影響較小,而受風速和植被覆蓋影響較大。2000、2017年區域固沙量分別主要受植被蓋度和風速的影響。本研究中雖然高覆蓋度草地的固沙量較高,但中覆蓋度草地可能是較適合荒漠草原的土地利用類型。因此結合區域氣候特點確定不同土地利用類型的適宜配比可能更有利于區域防風固沙服務的提供。由于本研究只基于土地利用方式、降水、風速、植被覆蓋度這四個因子對荒漠草原防風固沙服務的變化進行了分析,但實際上防風固沙服務的提供還受土壤質地、土壤含水量、土壤有機碳含量、植被冠層結構、放牧等因素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存在一定不足,還需要進一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