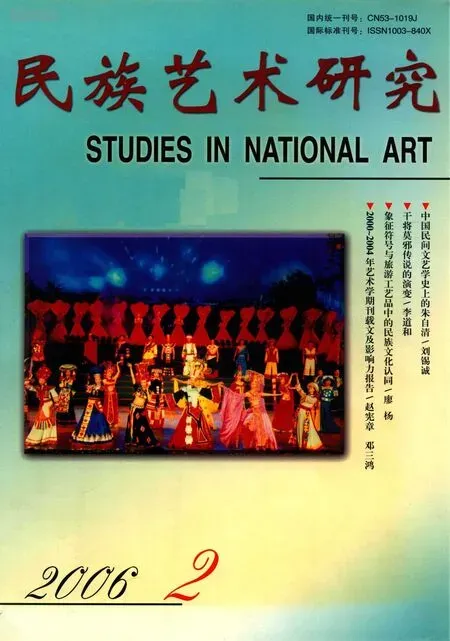田聯(lián)韜先生的藏族音樂研究及其學(xué)術(shù)傳承
銀卓瑪
自1953年田聯(lián)韜先生(后文稱田先生)第一次進(jìn)藏以來,先后共7次前往藏區(qū)考察,由采錄、記譜、創(chuàng)作逐漸轉(zhuǎn)型為研究及教學(xué)。他是藏族音樂研究的先驅(qū)之一。田先生1980年開始接受《中國大百科全書·音樂舞蹈卷》的少數(shù)民族音樂分支的編撰工作,從創(chuàng)作一線逐漸轉(zhuǎn)入研究教學(xué),是先生重要的轉(zhuǎn)型期。20世紀(jì)80年代以來,田先生致力于少數(shù)民族音樂研究和人才培養(yǎng)。其中,藏族音樂研究是先生眾多研究領(lǐng)域中的重中之重。田先生及其門下學(xué)者的藏族音樂研究成果為此領(lǐng)域?qū)W術(shù)發(fā)展奠定了扎實(shí)的理論基礎(chǔ)。
一、一脈兩支的藏族音樂研究
田先生學(xué)術(shù)一脈可分為兩個(gè)分支。第一個(gè)分支為他于1960—1984年在中央民族學(xué)院講授作曲理論及創(chuàng)作課時(shí),通過理論作曲專業(yè)和作品分析課,培養(yǎng)了一批作曲專業(yè)背景的藏族音樂研究人才,比如扎西達(dá)杰(青海省)、馬阿魯(西藏)、洛桑三旦(西藏)、白登朗吉(康巴)、多杰仁宗(青海省)、瑪交巴塔(青海省)及才讓當(dāng)周(甘肅省)等;涉及藏族三大方言區(qū),衛(wèi)藏、安多及康巴的人才培養(yǎng)。這幾位藏族作曲家到地方后,發(fā)揮的作用很大。他們有一個(gè)共同的特點(diǎn)是:對(duì)本民族音樂非常熟悉;他們可以在創(chuàng)作和研究中自由轉(zhuǎn)換。
第二個(gè)分支是田先生1984—2020年在中央音樂學(xué)院任教時(shí)親授的第一代中國少數(shù)民族音樂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第二代學(xué)人)及中央音樂學(xué)院、中央民族大學(xué)第二代培養(yǎng)的第三代學(xué)人。先生于此時(shí)正式開始進(jìn)入了藏族音樂研究、教學(xué)及培養(yǎng)人才階段。回顧40年前,中國少數(shù)民族音樂研究起步較晚、人才匱乏、缺少學(xué)科理論的情況在藏族音樂研究中顯得更為突出。培養(yǎng)民族干部是先生的初衷,培養(yǎng)藏族音樂研究人才更是先生的愿望。而現(xiàn)實(shí)是:藏族音樂薄弱的研究能力與豐富的藏族音樂形成較大反差,藏族音樂研究尤其缺乏藏族本土學(xué)者。然而,藏族生源普遍文化基礎(chǔ)弱、外語水平低,很難考取。所以,培養(yǎng)藏族音樂研究人才又成了極為困難的事情。
近40年來,經(jīng)先生不斷努力、引領(lǐng)、開拓,相關(guān)藏甘青川滇等省區(qū)藏族音樂研究的學(xué)科發(fā)展,從無到有,由弱變強(qiáng)。其門下已培養(yǎng)出嘉雍群培(簡稱嘉雍,康巴藏族,曾任職于中央民族大學(xué),已逝)、格桑曲杰(簡稱格曲,衛(wèi)藏藏族,現(xiàn)任職西藏大學(xué))、銀卓瑪(簡稱卓瑪,安多藏族,現(xiàn)任職于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及次仁朗杰(簡稱次諾,衛(wèi)藏藏族,現(xiàn)任職西藏大學(xué))等第二代藏族學(xué)人,已涵蓋藏族三大方言及不同藏區(qū)。除藏族生源外,受先生影響,還有他族學(xué)人將藏族音樂研究納入研究體系中。例如,和云峰(納西族)、王華(漢族,已逝)等第二代。歷經(jīng)數(shù)十載,藏族音樂研究分支現(xiàn)已有第三代學(xué)人。嘉雍群培培養(yǎng)出高翔(漢族)、王曉東(漢族)、馬良(漢族)等博士和盧婷(又名梅朵、嘉絨藏族)、武斌(漢族)、于曉菲(漢族)、銀爍(漢族)等碩士①其中,由于嘉雍早逝,于曉菲、武斌在博士階段入包愛軍(包·達(dá)爾汗)學(xué)門;銀爍博士階段入門于嘉雍群培,畢業(yè)于柯琳;馬良讀博期間入門于嘉雍群培,畢業(yè)于包愛軍門下。格桑曲杰培養(yǎng)多位以藏族音樂研究為主的研究生。。此外,楊民康與和云峰傳承田先生衣缽,也培養(yǎng)了一批藏族學(xué)者,如楊民康為合作導(dǎo)師的博士后研究員李娜(又稱勒毛措,安多藏族);央金卓嘎(嘉絨藏族)現(xiàn)隨和云峰攻讀藝術(shù)管理專業(yè)碩士學(xué)位。
通過一脈兩支及三代學(xué)人的共同努力,藏族音樂研究學(xué)科隊(duì)伍不斷壯大,研究領(lǐng)域逐漸拓展,學(xué)科分支縱深發(fā)展。
二、學(xué)術(shù)理念的承襲成為研究的先導(dǎo)
數(shù)十年來,田先生身體力行,親為表率,通過自己大量的學(xué)術(shù)理論創(chuàng)新、田野實(shí)踐行為及課堂教學(xué)活動(dòng),為后輩學(xué)生們鋪設(shè)出一條凝聚其精深文化觀點(diǎn)和學(xué)術(shù)理念的傳承通道。可歸其幾個(gè)觀念的要點(diǎn)示下。
(一)走出書齋,進(jìn)入田野,再做深入思考和案頭書寫的實(shí)踐研究觀
不同于時(shí)下諸多傳統(tǒng)音樂學(xué)者對(duì)“集成”、曲牒的盤桓和依戀,田先生在研究中非常重視一手資料的搜集、整理和運(yùn)用,然后在此基礎(chǔ)上進(jìn)行翔實(shí)的音樂特征和文化分析。由于早年音樂創(chuàng)作的需要,先生常常奔赴藏區(qū)與其他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采風(fēng),較早的一次就是1975年4—8月帶領(lǐng)學(xué)生去西藏山南的隆子縣,“開門辦學(xué)”和為音樂創(chuàng)作收集民間音樂素材。到了80年代,他三赴藏區(qū)做田野調(diào)查,分別去了西藏的日喀則、江孜、薩迦等六個(gè)縣;甘肅、青海和西藏三地;四川甘孜的康定、德格等四縣市,轉(zhuǎn)而來到鄰近的西藏昌都地區(qū)。90年代去了兩次,分別到西藏山南、拉薩、日喀則等地;最后一次是到云南的迪慶,即今天的香格里拉。②田聯(lián)韜:《走向邊疆——田聯(lián)韜民族音樂文論集》,北京:中央音樂學(xué)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9頁。從研究思維和視野來看,這些實(shí)地考察活動(dòng)一方面培養(yǎng)了先生和弟子們一切從實(shí)際出發(fā),重視理論與實(shí)踐相結(jié)合的學(xué)術(shù)理念,另一方面為他們從事相關(guān)的重大科研項(xiàng)目和展開理論學(xué)術(shù)研究及課堂教學(xué)打下了堅(jiān)實(shí)的實(shí)踐性基礎(chǔ)。
從學(xué)術(shù)研究的角度看,通過20世紀(jì)70年代的“采風(fēng)”活動(dòng),先生搜集整理了一批藏族音樂素材,秉著奉獻(xiàn)和共享的服務(wù)理念,同袁炳昌、李耀宗于1981年合作主編了《中國少數(shù)民族愛情歌曲集》③田聯(lián)韜、袁炳昌、李耀宗:《中國少數(shù)民族愛情歌曲集》,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內(nèi)含多首藏族情歌。此后的田野考察成果,便在1997年先生主編的《西藏傳統(tǒng)音樂集萃——著名民間藝人窮布珍演唱集》④田聯(lián)韜:《西藏傳統(tǒng)音樂集粹——著名民間藝人窮布珍演唱集》,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和所寫的藏族音樂研究論文中逐漸展現(xiàn)出來。歌曲集里收錄了窮布珍演唱的93首歌曲,內(nèi)容包括“堆諧”“囊瑪”“果諧”“熱巴諧”和民歌五類,較早向外界呈現(xiàn)了西藏豐富多彩的民間歌舞音樂和民歌。書中還配有藏漢雙語歌詞對(duì)照,最大程度地保存歌曲原貌,為音樂專業(yè)工作者及或音樂愛好者留下珍貴的資料。由此,先生對(duì)藏族音樂所采取的上述學(xué)術(shù)態(tài)度,直接影響了其作曲學(xué)生分支及第二代、第三代藏族音樂學(xué)人。如藏族作曲家才讓當(dāng)周曾經(jīng)記錄大量甘南藏族民歌,1989年由甘南藏族自治州文化局編輯出版《藏族民間歌曲選》(藏文)①甘南藏族自治州文化局:《藏族民間歌曲選》,西寧:青海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并搜集、記譜大量熱巴音樂近200首,收錄于歐米加參所著的《雪域熱巴》(藏文)②歐米加參:《雪域熱巴》,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
(二)以中國少數(shù)民族音樂為對(duì)象的全局與局部(民族)整體研究觀
田先生歷年來一直致力于藏族的整體性研究。他于20世紀(jì)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先后7次到藏、甘、青、川、滇五省區(qū)考察藏族傳統(tǒng)音樂,收集到大量一手資料。在此基礎(chǔ)上,他先后申報(bào)并獲批《文化背景中的藏族傳統(tǒng)音樂》(1990年,國家教委“七五”規(guī)劃博士點(diǎn)科研項(xiàng)目)、《中國少數(shù)民族傳統(tǒng)音樂系統(tǒng)研究》(2001年,國家教委“八五”規(guī)劃博士點(diǎn)科研項(xiàng)目)、《中國少數(shù)民族傳統(tǒng)音樂研究》(2001年,北京市教委“高等教育教學(xué)改革”科研項(xiàng)目)、《中國藏族音樂考察研究》(2003年,文化部國家十五規(guī)劃重點(diǎn)科研項(xiàng)目)、《中國少數(shù)民族宗教音樂考察研究》(2004年,教育部重點(diǎn)科研基地重大科研項(xiàng)目)等多項(xiàng)重要科研項(xiàng)目。他的學(xué)生申請(qǐng)的相關(guān)課題中,則有包愛軍的《蒙藏佛教音樂文化關(guān)系研究》(2005年,教育部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研究一般項(xiàng)目)、格桑曲杰的《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西藏卷》(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xiàng)目)和《中國西藏佛教寺院儀式音樂研究》(2014年,國家社科基金項(xiàng)目)、銀卓瑪?shù)摹恫貍鞣鸾讨袧h藏音樂文化交流遺存的考察研究》(2019年,國家社科基金藝術(shù)學(xué)一般項(xiàng)目),先生的課題方向逐漸從微觀至中觀、宏觀研究轉(zhuǎn)變。1991年6月,先生赴香港參加國際傳統(tǒng)音樂學(xué)會(huì)(ICTM)第31屆年會(huì),提交論文《藏族音樂色彩區(qū)考察研究》,文中將藏族音樂按衛(wèi)藏、安多、康巴劃分為三個(gè)色彩區(qū)。這是他首次根據(jù)自己的藏族音樂研究體驗(yàn),在國際會(huì)議上發(fā)表藏族音樂研究成果。1993年他又獲邀參加德國柏林舉行的國際傳統(tǒng)音樂學(xué)會(huì)第32屆年會(huì),發(fā)表論文《中國境內(nèi)藏族民俗音樂考察研究》,進(jìn)一步闡述了他提出的可以將藏族三大方言區(qū)視作三大藏族音樂色彩區(qū),其他處于藏族文化邊緣區(qū),流傳范圍較小的可視為亞色彩區(qū)的學(xué)術(shù)觀點(diǎn)。③田聯(lián)韜:《中國境內(nèi)藏族民俗音樂考察研究》,《中國音樂學(xué)》1996年第1期,第18頁。田聯(lián)韜:《走向雪域高原——青藏高原音樂考察研究》,北京:中央音樂學(xué)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407頁。以上述觀點(diǎn)為基石,不僅由此建立了他以藏、甘、青、川、滇五省區(qū)藏族聚居區(qū)及三大方言區(qū)傳統(tǒng)音樂為基礎(chǔ)的局部整體性音樂研究觀,而且也順此確定了可為后輩學(xué)人遵從和運(yùn)行的中國少數(shù)民族乃至中華民族的整體性傳統(tǒng)音樂研究觀。田先生主編的《中國少數(shù)民族傳統(tǒng)音樂》④田聯(lián)韜:《中國少數(shù)民族傳統(tǒng)音樂》(上下),北京:中央民族大學(xué)出版社,2003年版,第607—700頁。書稿及其中的藏族傳統(tǒng)音樂章節(jié),乃是目前為止國內(nèi)外較全面展示該對(duì)象領(lǐng)域的研究成果。該著作奠定了田野調(diào)查法在藏族音樂研究中的重要性,并結(jié)合文獻(xiàn)、比較和分析,將藏族音樂進(jìn)行分類和歸納。通過該書及其中的藏族音樂部分,展示了田先生這一時(shí)期已經(jīng)形成的,以中國少數(shù)民族音樂為對(duì)象的全局與局部(民族)整體研究觀。2014年,田先生發(fā)表《藏族音樂的地域性特征與音樂色彩區(qū)研究》⑤田聯(lián)韜:《藏族音樂的地域性特征與音樂色彩區(qū)研究》,《中央音樂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4年第4期,第3—16頁。一文,進(jìn)一步完善了對(duì)藏族三大方言區(qū)地域性特征及音樂色彩區(qū)進(jìn)行分析和歸納的思路和方法,提出了可在藏族三大音樂色彩區(qū)之間進(jìn)行比較研究的學(xué)術(shù)設(shè)想,并且希望后輩學(xué)人進(jìn)一步去關(guān)注“藏彝走廊”中眾多較小的藏屬族群的民間音樂。2015年先生最終完成《走向雪域高原——青藏高原音樂考察研究》一書,該書涵蓋了樂器、民間歌曲、民間舞蹈、說唱、藏戲、宗教音樂、宮廷樂舞噶爾及音樂人物志等內(nèi)容,囊括了先生一生對(duì)藏族音樂研究的心力和成果⑥田聯(lián)韜:《走向雪域高原——青藏高原音樂考察研究》,北京:中央音樂學(xué)院出版社,2015年版。。在先生學(xué)術(shù)觀念和研究成果的引領(lǐng)下,中國藏族音樂研究逐漸向縱深發(fā)展。
歸結(jié)上文,在田先生手中創(chuàng)下了對(duì)藏、甘、青、川、滇五大藏族聚居區(qū)傳統(tǒng)音樂及宗教音樂進(jìn)行整體、全面的考察研究這一重大佳績。在此基礎(chǔ)上,第二代藏族學(xué)人的學(xué)位論文及后續(xù)研究均延續(xù)此研究方法和分類原則。通過他后來培養(yǎng)的6位(含4位藏族)博士,完成了對(duì)其中不同方言區(qū)及民歌、戲曲、歌舞及宗教音樂等不同體裁內(nèi)容各有專精的完整學(xué)術(shù)布局。這一項(xiàng)學(xué)術(shù)傳承工作,對(duì)于藏族音樂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可持續(xù)性發(fā)展意義。
(三)提倡描述與分析、形式與內(nèi)容相結(jié)合,以樹立正確的民族藝術(shù)觀
田先生在研究過程中非常注重音樂形態(tài)特征的綜合分析。2013年,先生83歲高齡時(shí),撰寫《藏族傳統(tǒng)音樂形態(tài)特征研究》①田聯(lián)韜:《藏族傳統(tǒng)音樂形態(tài)特征研究》(二、三),《西藏藝術(shù)研究》,分別載于2013年第1期第10—26頁、第2期第12—23頁、第3期第4—19頁。在西藏藝術(shù)研究連載3期,從理論技術(shù)層面,對(duì)藏族傳統(tǒng)音樂構(gòu)成的基本要素進(jìn)行分析,尤其體現(xiàn)于涉及藏族多聲部分析、詩歌及唱詞格律的分析、歌唱發(fā)聲方法與演唱特點(diǎn)等方面;田先生此文為后學(xué)提供了最重要的藏族傳統(tǒng)音樂形態(tài)特征研究的本體研究方法。先生培養(yǎng)藏族學(xué)人的過程中,總是結(jié)合本族音樂或區(qū)域音樂風(fēng)格,重視音樂形態(tài)特征分析,并指出文化研究與音樂本體應(yīng)該并重的道理。先生一脈的藏族音樂研究都是建立在扎實(shí)的田野作業(yè)、對(duì)音樂本體的詳盡分析基礎(chǔ)之上。第二代藏族學(xué)人格桑曲杰和銀卓瑪先后獲中央音樂學(xué)院優(yōu)秀博士論文,即采用此類教學(xué)方法的直接結(jié)果。
(四)以學(xué)術(shù)為紐帶,建造起藏族音樂學(xué)術(shù)共同體的網(wǎng)絡(luò)和認(rèn)同感
為了締結(jié)藏族音樂學(xué)術(shù)共同體的網(wǎng)絡(luò)并喚起學(xué)人的認(rèn)同感,田先生愿意竭盡一己之力去培養(yǎng)、教育后輩學(xué)生,并且樂于幫助、扶持任何愿意加入這一共同體的學(xué)人。就此,他無私地幫助過諸多藏族地方學(xué)者,扶持他們的藏族學(xué)術(shù)研究課題,為基層藏族音樂研究增添羽翼,補(bǔ)充力量。他先后為更堆群培《西藏音樂史略》②更堆群培:《西藏音樂史略》,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序言。、西藏大學(xué)覺嘎博士后論文《論藏族傳統(tǒng)樂器扎念》③覺嘎:《論藏族傳統(tǒng)樂器扎念》,北京:中國藏學(xué)出版社,2007年版,序言。《藏族傳統(tǒng)樂器——嗶旺》④覺嘎、米瑪加布:《藏族傳統(tǒng)樂器——嗶旺》,北京:中國藏學(xué)出版社,2015年版,序言。、更堆群培與覺嘎《絕耷——雄色尼姑寺“絕耷”音樂生態(tài)與形態(tài)研究》⑤更堆群培、覺嘎:《絕耷——雄色尼姑寺絕耷音樂生態(tài)與形態(tài)研究》,米瑪加布譯,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年版。、多杰仁宗《青海藏傳佛教音樂文化研究》⑥多杰仁宗、滿當(dāng)烈、晁元清、王玫等:《青海藏傳佛教音樂文化研究》,蘭州:蘭州大學(xué)出版社,2007年版,序言。及馬郎吉、洛桑《巴塘弦子曲集》⑦馬郎吉、洛桑:《巴塘弦子曲集》,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序言。等專著出版作序。平時(shí),他還經(jīng)常關(guān)心、幫助作曲專業(yè)的藏族后輩學(xué)人,從中凸顯了先生的學(xué)術(shù)胸懷和文化大局意識(shí),因此受到藏族音樂學(xué)人和作曲家的愛戴和敬仰。
三、研究方法的融合與創(chuàng)新
(一)重視田野作業(yè)與歷史文獻(xiàn)資料的相互印證
田先生在藏族音樂研究中非常重視田野作業(yè)與歷史文獻(xiàn)資料的相互印證,第二代、第三代藏族學(xué)人對(duì)此類研究方法也有較好的傳承。2002年,田先生在《藏族音樂文化與周邊民族、周邊國家之交流、影響》一文中,通過漢、藏文獻(xiàn)闡釋周邊民族、周邊國家的音樂文化對(duì)于藏族的影響以及印度、尼泊爾、巴基斯坦及中亞、西亞各國音樂與藏族傳統(tǒng)音樂的交流與影響。同時(shí)關(guān)注境內(nèi)、外藏族后裔音樂的關(guān)聯(lián)性研究,并且提出應(yīng)當(dāng)對(duì)于藏族之間傳統(tǒng)音樂的交流與影響展開深入考察和研究⑧田聯(lián)韜:《藏族音樂文化與周邊民族、周邊國家之交流、影響》,《西藏藝術(shù)研究》2002年第3期。。
(二)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的“兼納中西”品格與研究方法的“中西貫通”
田先生主張?jiān)诓刈逡魳费芯恐幸惨龅窖芯糠椒ǖ摹爸形髫炌ā保@也是對(duì)中央音樂學(xué)院“兼納中西”品格的繼承。他要求每一位藏族學(xué)人在學(xué)習(xí)中國傳統(tǒng)音樂理論及音樂風(fēng)格的基礎(chǔ)上,借鑒西方前沿學(xué)術(shù)理念和學(xué)術(shù)方法,得以中西貫通、靈活運(yùn)用。先生要求幾位博士均要修讀楊民康開設(shè)的《民族音樂學(xué)與文化人類學(xué)》《音樂民族志研究的理論與方法》等課程,以獲取較為前沿的西方民族音樂學(xué)研究理論方法;同時(shí)鼓勵(lì)他們到北京大學(xué)旁聽民族學(xué)、人類學(xué)、語言學(xué)課程。在先生86歲高齡時(shí),撰寫《綜合運(yùn)用中西方理論方法分析藏族傳統(tǒng)音樂曲式結(jié)構(gòu)》①田聯(lián)韜:《綜合運(yùn)用中西方理論方法分析藏族傳統(tǒng)音樂曲式結(jié)構(gòu)》,《中國音樂》(季刊)2017年第3期。一文,將此教學(xué)理念上升為具體的方法論,文中列舉實(shí)例,針對(duì)藏族音樂曲式結(jié)構(gòu)與其他民族音樂的共性和個(gè)性特征,闡述中西方理論方法的可操作性;特別提出藏族音樂結(jié)構(gòu)的三分性(引入、正曲和結(jié)尾三個(gè)部分),認(rèn)為衛(wèi)藏藏戲、布達(dá)拉宮的噶爾樂舞演唱的噶爾魯樂曲及囊瑪歌舞等傳統(tǒng)音樂的結(jié)構(gòu)基本相同,此文對(duì)于藏族傳統(tǒng)音樂的曲式結(jié)構(gòu)分析具有較強(qiáng)的指導(dǎo)性和借鑒性。
(三)讓學(xué)生獨(dú)立思考,靈活運(yùn)用不同的研究觀念和方法
田先生提出,研究方法不可拘泥于一種或某一種,要嘗試各種方法的結(jié)合運(yùn)用。先生強(qiáng)調(diào):不可守舊,不可盲從;不要追風(fēng),不要禁錮,希望他們擁有“跳出—跳進(jìn)”“局內(nèi)—局外”的雙視角觀念。為每一位藏族學(xué)人的學(xué)位論文撰寫及后續(xù)研究奠定了扎實(shí)的學(xué)術(shù)基礎(chǔ)和研究理念。
四、研究領(lǐng)域及現(xiàn)狀的梳理和闡析
田先生開創(chuàng)的各藏族方言區(qū)音樂研究領(lǐng)域,縱向囊括宗教音樂、民間音樂、宮廷音樂等不同階層類型;橫向包含了藏、門巴、珞巴等民族和夏爾巴人和僜人的音樂及周邊跨界族群音樂。
(一)藏族宗教音樂研究
田先生參與主編、策劃的《中國大百科全書·音樂舞蹈卷》少數(shù)民族音樂分支(1998年)和擔(dān)任主編的《中國少數(shù)民族傳統(tǒng)音樂》(2001年)等書中,已對(duì)中國各少數(shù)民族的宗教音樂有所涉及,其中包含藏族宗教音樂。2004年,田先生負(fù)責(zé)主持教育部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重點(diǎn)研究基地中央音樂學(xué)院音樂學(xué)研究所重大研究項(xiàng)目“中國少數(shù)民族宗教音樂研究”,第二代學(xué)人格桑曲杰、多杰仁宗、嘉雍群培等負(fù)責(zé)藏族宗教音樂部分,包愛軍負(fù)責(zé)內(nèi)蒙古的藏傳佛教音樂,四川的旦木秋負(fù)責(zé)四川阿壩羌族、藏族宗教音樂。其中多杰仁宗負(fù)責(zé)的子項(xiàng)目《青海藏傳佛教音樂文化研究》②多杰仁宗、滿當(dāng)烈、晁元清、王玫等:《青海藏傳佛教音樂文化研究》,蘭州:蘭州大學(xué)出版社,2007年版,序言。已出版,內(nèi)容涉及青海藏傳佛教音樂的各個(gè)方面,是一項(xiàng)拾荒性的研究課題。時(shí)至2020年,先生去世前夕,此重大項(xiàng)目基本完稿。
就宗教音樂來說,田先生的第二代藏族作曲學(xué)生陸續(xù)刊發(fā)拓荒性文章,如扎西達(dá)杰《藏傳佛教樂譜體系》(1993年)③扎西達(dá)杰:《藏傳佛教樂譜體系》,《中國音樂》1993年第1期,第24—26頁。、洛桑三旦《讓藏傳佛教音樂藝術(shù)走向世界——組曲〈吉祥九重天〉創(chuàng)作始末》④洛桑三旦、饒?jiān)瘢骸蹲尣貍鞣鸾桃魳匪囆g(shù)走向世界——組曲〈吉祥九重天〉創(chuàng)作始末》,《西藏藝術(shù)研究》1990年第4期,第52—66頁。及才讓當(dāng)周《拉卜楞寺道得兒樂隊(duì)及其樂譜》⑤才讓當(dāng)周:《拉卜楞寺道得兒樂隊(duì)及其樂譜》,《中國音樂》1990年第2期,第38—40頁。等。先生親授的音樂學(xué)學(xué)生以嘉雍群培和格桑曲杰為代表。嘉雍群培博士論文《藏傳佛教密宗“死亡修行”儀式音樂研究》,作為藏傳佛教亡靈超度儀式音樂研究的典范,其“死亡修行”儀式中的音樂思想、藏傳佛教臨終關(guān)懷與亡靈超度儀式音樂研究等內(nèi)容至今仍居前沿。嘉雍群培完成的《西藏本土文化、本土宗教——苯教音樂》(2014年)①嘉雍群培:《西藏本土文化、本土宗教——苯教音樂》,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一書,是國內(nèi)外學(xué)術(shù)界首部以苯教音樂文化為研究對(duì)象的專著。此外,嘉雍群培完成《藏傳佛教樂舞“羌姆”中的中原文化》②嘉雍群培:《藏傳佛教樂舞“羌姆”中的中原文化》,載中央音樂學(xué)院、韓國東北亞音樂研究所:《第一屆中韓佛教音樂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論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窺商日本與西藏佛教傳承及佛教音樂的異同》③嘉雍群培:《窺商日本與西藏佛教傳承及佛教音樂的異同》,《黃鐘》(武漢音樂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8年第3期,第18—23頁。及《藏傳佛教“因明”中的音樂學(xué)方法論》④嘉雍群培:《藏傳佛教“因明”中的音樂學(xué)方法論》,《中國音樂》2014年第2期,第51—54、第59頁。等論文,《藏族文化藝術(shù)》(2007年)⑤嘉雍群培:《藏族文化藝術(shù)》,北京:中央民族大學(xué)出版社,2007年版。、《雪域樂學(xué)新論》(2007年)⑥嘉雍群培:《雪域樂學(xué)新論》,北京:中央民族大學(xué)出版社,2007年版。和《藏文佛經(jīng)中的音樂史料》(2013年)⑦嘉雍群培:《藏文佛經(jīng)中的音樂史料》,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等著作,上述宗教音樂論著均成文于一手資料基礎(chǔ)之上,文筆樸素,卻不乏高度和深度。格桑曲杰博士論文《中國西藏佛教寺院儀式音樂研究》對(duì)藏傳佛教儀式音樂進(jìn)行了全面、深入、細(xì)致的考察與研究,在田先生宗教音樂研究的基礎(chǔ)上有了進(jìn)一步延續(xù)。其論文涉及西藏宗教的淵源歷史,誦經(jīng)調(diào),器樂、羌姆等內(nèi)容,包含大量藏、漢雙譯的吟唱、誦唱譜例及器樂譜例⑧格桑曲杰:《中國西藏佛教寺院儀式音樂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他先后完成和發(fā)表《藏傳佛教銅號(hào)鼓鈸樂隊(duì)》⑨格桑曲杰:《藏傳佛教銅號(hào)鼓鈸樂隊(duì)》載中央音樂學(xué)院、韓國東北亞音樂研究所:《第一屆中韓佛教音樂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論文集》,2003年版,第156—166頁。《獨(dú)具特色的西藏佛教旋律樂器甲林和銅欽》⑩格桑曲杰、張鷹:《獨(dú)具特色的西藏佛教旋律樂器甲林和銅欽》,《西藏藝術(shù)研究》2006年第4期,第36—41頁。《西藏佛教寺院儀式音樂研究》?格桑曲杰:《西藏佛教寺院儀式音樂研究》,《中央音樂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9年第3期,第3—19頁。《人類絕頂超低聲,藏傳佛教格魯派大寺院中的“左蓋”》?格桑曲杰:《人類絕頂超低聲,藏傳佛教格魯派大寺院中的“左蓋”》,《西藏藝術(shù)研究》2010年第3期,第4—7頁。等研究論文。在他的博士學(xué)位論文《西藏佛教寺院儀式音樂研究》及發(fā)表的相關(guān)論文中,將西藏佛教寺院紛繁眾多的儀式活動(dòng)分為內(nèi)道層(核心層)即供養(yǎng)儀式、中道層(中間層)即含禮拜、供祭儀式和穰災(zāi)祈福儀式、外道層(外圍層)即禮儀儀式等三部分。第一次將藏傳佛教傳統(tǒng)結(jié)構(gòu)構(gòu)建層次概念,是文化分層理論研究的學(xué)術(shù)創(chuàng)新。此外,第二代學(xué)人和云峰完成和出版專著《云南藏傳佛教音樂文化》?桑德諾瓦、鞏海蒂:《云南藏傳佛教音樂文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三代學(xué)人,嘉雍群培的研究生也完成了多篇與藏族音樂有關(guān)的學(xué)位論文,如盧婷《藏傳佛教覺囊派中壤塘確爾基寺歲末驅(qū)魔法會(huì)音樂研究》是首篇相關(guān)藏傳佛教覺囊派的學(xué)位論文;延續(xù)嘉雍的藏族宗教音樂文化研究,武斌碩士學(xué)位論文是《平武厄哩寨白馬藏族“跳曹蓋”儀式音樂研究》;馬良博士論文《莫朗切默法會(huì)誦經(jīng)音樂研究》等。
(二)藏族歌舞音樂與民歌研究
田先生的藏族民間音樂研究涉及藏族說唱、民間歌舞、藏族民歌、藏族民間器樂等內(nèi)容。他早期的作曲學(xué)生馬阿魯《西藏民間音樂基本規(guī)律初探》?馬阿魯:《西藏民間音樂基本規(guī)律初探》,《音樂研究》1989年第4期,第37—45頁。及扎西達(dá)杰《藏蒙〈格薩爾〉音樂比較研究》?扎西達(dá)杰:《藏蒙〈格薩爾〉音樂比較研究》,《西藏藝術(shù)研究》1995年第3期,第14—16頁。等文也都是此方面的拾荒性研究。
在民間歌舞音樂方面,田先生本人對(duì)藏族巴塘弦子?田聯(lián)韜:《藏族巴塘弦子音樂考察研究》,《中國音樂》2012年第1期,第40—47頁。和藏族熱巴音樂?田聯(lián)韜:《藏族熱巴音樂考察研究》,《中國音樂學(xué)》2013年第3期,第56—70頁。均有研究。2002年前后,先生建議第二代學(xué)人王華關(guān)注藏族熱巴藝術(shù),并選《西藏昌都熱巴藝術(shù)研究》?王華:《西藏?zé)岚鸵魳肺幕芯俊罚本褐醒胍魳穼W(xué)院出版社,2011年版。田聯(lián)韜就此書序言寫于2010年4月。為博士論文,對(duì)西藏昌都、那曲地區(qū)進(jìn)行多次實(shí)地調(diào)查;其內(nèi)容涉及昌都熱巴歷史脈絡(luò)、文化語境、家族實(shí)錄、表演形式、音樂形態(tài)及宗教模式等;通過對(duì)熱巴藝術(shù)的全面考察和研究,成為第一部比較系統(tǒng)、深入的藏族熱巴音樂藝術(shù)的研究論著。
格桑曲杰延續(xù)了田先生的藏族多聲部民歌研究,在其論文《西藏堆諧、囊瑪音樂中多聲部的形成與發(fā)展》①格桑曲杰:《西藏堆諧、囊瑪音樂中多聲部的形成與發(fā)展》(上、下),《西藏藝術(shù)研究》1992年第3期,第61—69頁;《西藏藝術(shù)研究》1992年第4期,第72—76頁。中,以實(shí)例闡析堆諧、囊瑪中伴奏音型式、支聲復(fù)調(diào)式、支聲與對(duì)比性復(fù)調(diào)式混合結(jié)構(gòu)等多種多聲形式。此后,田先生指導(dǎo)的銀卓瑪,其博士論文名為《藏族“拉伊”(情歌)及其文化研究》,作者選取果洛、黃南、海南及海北等藏族自治州及幾個(gè)下屬縣,進(jìn)行“拉伊”的考察與研究。此論文延續(xù)了田先生關(guān)于安多藏族情歌的研究課題,并且將之向縱深拓展,后來作為研究安多藏族“拉伊”(情歌)的專著正式出版②銀卓瑪:《藏族情歌安多拉伊》,北京;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2020年版。。第三代藏族學(xué)人,如李娜的博士后課題為“洮岷地區(qū)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研究——以“沙目”儀式音樂為研究個(gè)案”,其田野考察涉及岷縣、卓尼兩個(gè)縣的8個(gè)村落,對(duì)岷縣“巴當(dāng)”傳承人楊勇、“沙目”表演老者、四川省茂縣羌族釋比法器“鼓”等進(jìn)行全面考察。作者在文中提出“族群認(rèn)同與文化建構(gòu)”是造就“沙目”儀式被不同民族共享且各具特色,并且是多民族雜居區(qū)文化構(gòu)成及表述的一般性特征的理論預(yù)設(shè)。意圖將“沙目”場域中(跨時(shí)空、跨地域)的“行為”——不僅包含音聲,還包含體態(tài)律動(dòng)的各種線索,納入“沙目”儀式音樂的研究中,探究音聲、體態(tài)律動(dòng)、儀式、信仰體系四者之間的互動(dòng)關(guān)系。
此外,從田先生開始,有關(guān)藏族音樂音響及數(shù)字化的錄制和發(fā)行工作也一直在進(jìn)行之中。繼先生主編和出版《西藏傳統(tǒng)音樂集萃——著名民間藝人窮布珍演唱集》,所收集整理的《藏戲音樂選段》1993年由荷蘭NRECORDS音像公司出版激光唱盤之后,次仁朗杰策劃、錄制《藏戲經(jīng)典唱腔欣賞——名人名段精粹》《凈土弦音》《美麗琴韻》《藏族傳統(tǒng)兒歌》等多部音像制品。呈現(xiàn)文本及實(shí)踐共同發(fā)展的趨勢。
(三)藏族傳統(tǒng)器樂的多元性研究
在藏族傳統(tǒng)音樂研究中,田先生一直比較重視傳統(tǒng)器樂的多元性研究。早于1986年,先生到達(dá)甘肅夏河拉卜楞寺、青海塔爾寺、玉樹當(dāng)卡寺等地考察。1989—1991年,他以藏族傳統(tǒng)樂器為研究對(duì)象,分別聯(lián)載了《藏族傳統(tǒng)樂器》(1—7)等文③《藏族傳統(tǒng)樂器》(一)至(七)共7篇文章分別聯(lián)載于《樂器》1989、1990、1991年1—4期。,這既是先生多年田野基礎(chǔ)上的學(xué)術(shù)總結(jié),也是首次向國外學(xué)術(shù)界較為全面地呈現(xiàn)藏族傳統(tǒng)樂器。研究成果涉及宗教、民間兩大類,地域包含西藏、青海、四川及甘肅等省區(qū),每一件樂器均有細(xì)致的繪圖及測量。第二代學(xué)人相關(guān)藏族器樂研究成果不斷深化,對(duì)各地藏族器樂的不同類型基本都有涉及和研究,如嘉雍群培《藏傳佛教中的“扎年琴”》④嘉雍群培:《藏傳佛教中的“扎年琴”》,《佛教文化》2010年第1期,第64—71頁。和格桑曲杰《西藏民間樂器簡介》⑤格桑曲杰:《西藏民間樂器簡介》,《西藏藝術(shù)研究》2001年第1期,第25—31頁。《西藏傳統(tǒng)民族器樂曲綜述》⑥格桑曲杰:《西藏傳統(tǒng)民族器樂曲綜述》,《西藏藝術(shù)研究》2002年第2期,第23—30頁。等論文相繼發(fā)表。第三代學(xué)人銀爍完成《扎念琴的改良》碩士學(xué)位論文,標(biāo)志著藏族樂器變革研究的開啟。2008年,格桑曲杰發(fā)表《西藏佛教寺院音樂中的漢地器樂形式——楚布寺甲瑞居楚樂(漢樂十六種)》,詳盡介紹了楚布寺漢樂的宗教文化背景及各個(gè)樂器的演奏、用樂及特征;并結(jié)合西藏噶瑪噶舉派與明、清兩朝廷之間的文化往來,兼及楚布寺噶瑪巴在兩朝廷的特殊地位和政治關(guān)系,加以歷史沿革的追溯。⑦格桑曲杰:《西藏佛教寺院音樂中的漢地器樂形式——楚布寺甲瑞居楚樂(漢樂十六種)》,《西藏藝術(shù)研究》2009年第1期,第42—54頁。鑒于格桑曲杰的此研究,田先生于2014年發(fā)表《藏傳佛教寺院的漢傳佛教音樂》,就少數(shù)藏傳佛教寺院中保存和使用漢傳佛教宗教器樂的現(xiàn)象進(jìn)行闡述,列舉拉卜楞寺“道得兒”、青海塔爾寺“花架音樂”、玉樹當(dāng)卡寺“加若音樂”、西藏楚布寺“賈瑞居楚樂”等具有漢樂特征的藏傳佛教音樂,將格桑曲杰的楚布寺漢樂的考察研究納入此文,并特別點(diǎn)到藏傳佛教寺院的漢樂遺存與五臺(tái)山佛教寺院有一定的關(guān)系,淵源有待追溯①田聯(lián)韜:《藏傳佛教寺院的漢傳佛教音樂》,《民族藝術(shù)研究》2014年第3期,第23—31頁。。2014年銀卓瑪進(jìn)入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博士后流動(dòng)站,其課題定為“拉卜楞寺‘道得兒’佛樂研究”。由此,銀卓瑪遵循先生教導(dǎo),并在田青先生的指導(dǎo)下,完成博士后課題“拉卜楞寺‘道得爾’佛樂研究”,并于2017年發(fā)表《拉卜楞寺“道得爾”與五臺(tái)山佛樂的比較研究——以拉卜楞寺〈色和〉與殊像寺【萬年歡】佛曲為例》一文,文章以實(shí)地考察和音樂本體分析為主,使兩寺佛曲的共性特征一覽無余②銀卓瑪:《拉卜楞寺“道得爾”與五臺(tái)山佛樂的比較研究——以拉卜楞寺〈色和〉與殊像寺【萬年歡】佛曲為例》,《中央音樂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7年第1期,第65—78頁。。解決了“道得爾”某一佛曲源自五臺(tái)山的學(xué)術(shù)猜測,使藏傳佛教漢樂遺存的淵源追溯研究推進(jìn)一步。
(四)藏戲研究
藏戲研究是藏族音樂研究不可缺少的內(nèi)容之一,先生于2012年發(fā)表《藏戲劇種分類研究》一文,較為宏觀地闡述了藏戲概況、分布及其他民族戲劇對(duì)藏戲的影響,特別提到藏戲劇種系統(tǒng)的構(gòu)建問題③田聯(lián)韜:《藏戲劇種分類研究》,《歌海》2012年第2期,第21—24、30頁。。次仁朗杰2009年發(fā)表《略論藏戲唱腔(囊達(dá))的演唱藝術(shù)》④次仁朗杰、衛(wèi)英:《略論藏戲唱腔(囊達(dá))的演唱藝術(shù)》,《西藏藝術(shù)研究》2009年第1期,第64—68頁。,其博士論文選題為《西藏衛(wèi)藏地區(qū)阿吉拉姆音樂文化研究》。博士畢業(yè)后,他陸續(xù)發(fā)表《藏族戲劇文化及其分類研究》⑤次仁朗杰:《藏族戲劇文化及其分類研究》,《西藏藝術(shù)研究》2016年第2期,第55—63頁。、《當(dāng)代西藏阿吉拉姆戲劇表演的文化面向》⑥次仁朗杰:《當(dāng)代西藏阿吉拉姆戲劇表演的文化面向》,《西藏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8年第2期,第131—137頁。、《藏族傳統(tǒng)戲劇歷史文化源流考辨(上)(下)》⑦次仁朗杰:《藏族傳統(tǒng)戲劇歷史文化源流考辨(上)》,《西藏藝術(shù)研究》2018年第1期,第51—63頁;次仁朗杰:《藏族傳統(tǒng)戲劇歷史文化源流考辨(下)》,《西藏藝術(shù)研究》2018年第2期,第65—78頁。及《衛(wèi)藏藍(lán)面具阿吉拉姆四大流派的歷史源流與藝術(shù)特征》⑧次仁朗杰:《衛(wèi)藏藍(lán)面具阿吉拉姆四大流派的歷史源流與藝術(shù)特征》,《西藏藝術(shù)研究》2019年第5期,第139—145、161頁。等相關(guān)藏戲論文;獨(dú)立承擔(dān)撰寫文旅部《中國戲曲劇種全集》西藏六大劇種《夏爾巴嘛呢戲劇》和《白面具戲》(計(jì)劃2021出版),成為藏戲研究的藏族繼承者和延續(xù)人。此外,第三代學(xué)人中,嘉雍群培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高翔(漢族),以藏戲“覺木隆”為研究對(duì)象,2012年完成博士學(xué)位論文《覺木隆職業(yè)藏戲及唱腔音樂研究》;論文涉及“覺木隆”職業(yè)藏戲的淵源梳理、表演程式、唱腔分析及文化闡釋等內(nèi)容,是首次對(duì)此職業(yè)藏戲的全面研究。包愛軍的博士生于曉菲發(fā)表《管窺藏戲——阿吉拉姆研究的幾個(gè)問題》⑨于曉菲:《管窺藏戲——阿吉拉姆研究的幾個(gè)問題》,《藝術(shù)教育》2015年第2期,第168—169頁。等文。
(五)關(guān)于珞巴族、夏爾巴人和僜人音樂的研究
在田先生在有關(guān)西藏少數(shù)民族音樂的研究中,對(duì)當(dāng)?shù)厝丝谳^少的珞巴族、夏爾巴人和僜人傳統(tǒng)音樂的研究⑩參見田先生在其主編的《中國少數(shù)民族傳統(tǒng)音樂》一書中撰寫的相關(guān)篇章內(nèi)容。也較具有開創(chuàng)性。格桑曲杰繼承先生接力棒,自2010年開始招收研究生,便親自為學(xué)生們選定、指導(dǎo)研究門巴族、珞巴族、夏爾巴人、僜人音樂的論文選題,并推出了一批經(jīng)過扎實(shí)田野考察,采用民族音樂學(xué)學(xué)科理論與方法進(jìn)行分析研究的成果,填補(bǔ)了這些西藏少數(shù)民族音樂研究領(lǐng)域的空白。
五、研究領(lǐng)域的不斷拓展及擴(kuò)充
目前三代藏族學(xué)人的研究成果逐漸深化和拓展。不同藏區(qū)、不同方言區(qū)藏族音樂研究已有一定的學(xué)術(shù)成果。
(一)藏族音樂的跨境研究的新探索
對(duì)藏族音樂開展跨境研究是田先生的學(xué)術(shù)夙愿。隨著“一帶一路”政策的推進(jìn),“絲綢之路”“一帶一路”等相關(guān)研究在學(xué)術(shù)界落地生根。2011年9月16—18日,在北京中央音樂學(xué)院舉辦的“2011中國少數(shù)民族音樂文化學(xué)術(shù)論壇——中國與周邊國家跨界族群音樂文化”學(xué)術(shù)會(huì)議,成為當(dāng)年少數(shù)民族音樂研究會(huì)議中最具代表性的學(xué)術(shù)活動(dòng)。會(huì)議6項(xiàng)議題中,包含了“中國藏、維、漢諸族與南亞、中亞、東亞組”的主題。田先生發(fā)表了題為《藏文化圈邊緣化跨界民族音樂初探》的學(xué)術(shù)報(bào)告,以藏文化圈為個(gè)案,就跨界族群音樂研究相關(guān)理論“文化圈”“跨界民族界定和形成”及“研究目的”等進(jìn)行闡釋和分析,對(duì)于這一新興研究領(lǐng)域的年輕學(xué)者給予指導(dǎo)和建議①田聯(lián)韜:《藏文化圈邊緣化跨界民族音樂初探》,“2011中國少數(shù)民族音樂文化學(xué)術(shù)論壇——中國與周邊國家跨界族群音樂文化參會(huì)論文”第163—170頁;田聯(lián)韜:《藏文化圈邊緣區(qū)跨界民族音樂研究》,《人民音樂》2011第12期,第55—59頁。。2018年5月,湖北省宜昌市五峰縣召開的“中國少數(shù)民族音樂學(xué)會(huì)第十六屆年會(huì)暨巴楚藝術(shù)創(chuàng)新教育學(xué)術(shù)會(huì)議”上,格桑曲杰和銀卓瑪就藏族音樂的跨界研究分別進(jìn)行了學(xué)術(shù)報(bào)告。后于2019年在云南藝術(shù)學(xué)院舉行的“第二屆中國少數(shù)民族暨跨界族群音樂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上,格桑曲杰發(fā)表了論文《絲綢之路上的中、西亞音樂對(duì)藏族音樂的影響——“卡爾”歌舞音樂傳入西藏的時(shí)間與路徑考》,通過藏文、漢文、烏都爾文等文獻(xiàn)的比較和引用,結(jié)合實(shí)地考察,圍繞巴基斯坦巴爾蒂斯坦藏族后裔,就巴爾蒂斯坦卡爾歌舞音樂傳入西藏的時(shí)間和傳播路徑進(jìn)行分析②格桑曲杰:《絲綢之路上的中、西亞音樂對(duì)藏族音樂的影響——“卡爾”歌舞音樂傳入西藏的時(shí)間與路徑考》,《西藏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9年第1期,第83—91頁。。同年,銀卓瑪刊發(fā)《“一帶一路”與少數(shù)民族音樂研究——巴基斯坦藏族后裔的跨界研究為例》,以國內(nèi)外現(xiàn)有文獻(xiàn)為基礎(chǔ),對(duì)巴爾蒂斯坦藏族后裔的歷史、文化、現(xiàn)狀及音樂等方面進(jìn)行梳理,并將可進(jìn)行跨界音樂研究的巴爾蒂問答歌“索瑪萊克”和“格薩爾”說唱進(jìn)行簡述③銀卓瑪、擁巴:《“一帶一路”與少數(shù)民族音樂研究——巴基斯坦藏族后裔的跨界研究為例》,《中國音樂》2019年第1期,第76—83頁。。兩位藏族后學(xué)傳襲先生教誨,在有限的條件下,通過國內(nèi)外相關(guān)文獻(xiàn),將跨境藏族音樂研究向前推進(jìn)。先生的藏族音樂全局研究觀,影響了幾代人。隨著藏族音樂的“跨境”“跨界”研究不斷推進(jìn),“環(huán)喜馬拉雅”藏族音樂研究興起。2015年,中央音樂學(xué)院張伯瑜主編出版《環(huán)喜馬拉雅山音樂文化研究》一書,其中,格桑曲杰撰寫了名為“喜馬拉雅山北巔:西藏傳統(tǒng)音樂”的相關(guān)章節(jié);2019年,西藏大學(xué)藝術(shù)學(xué)院的覺嘎作為項(xiàng)目負(fù)責(zé)人獲批“2019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xiàng)目”,其項(xiàng)目為“環(huán)喜馬拉雅藝術(shù)圖譜繪制”(19ZDA045),次仁朗杰承擔(dān)子課題負(fù)責(zé)人,旨在挖掘、收集、整理和研究環(huán)喜馬拉雅的文化資源。
(二)藏族音樂教材及學(xué)科發(fā)展口述史研究
多年來在藏族傳統(tǒng)音樂的教學(xué)中,缺乏藏族音樂教材的問題比較突出。經(jīng)過幾代學(xué)人共同努力,在田先生主持撰寫《中國少數(shù)民族傳統(tǒng)音樂》④田聯(lián)韜:《中國少數(shù)民族傳統(tǒng)音樂》(上下),北京:中央民族大學(xué)出版社,2003年版,第607—700頁。(2001年)和《中國少數(shù)民族音樂史》⑤袁炳昌、馮光鈺:《中國少數(shù)民族音樂史》(上),北京:中央民族大學(xué)出版社,1998年版,田聯(lián)韜先生做為編委審閱第十一、十二和十八章。馮光鈺主編:《中國少數(shù)民族音樂史》(三卷),北京:京華出版社,2007年版。(1998年、2007年)兩部著作中藏族音樂部分的基礎(chǔ)上,第二代學(xué)人也在不斷推進(jìn)和拓展有關(guān)藏族音樂史志教材的編寫及研究。其中,馬阿魯發(fā)表了《藏族〈視唱練耳〉教材建設(shè)——有關(guān)理論之論述》(1996年)⑥馬阿魯:《藏族〈視唱練耳〉教材建設(shè)——有關(guān)理論之論述》,《西藏大學(xué)學(xué)報(bào)(漢文版)》1996年第1期,第17—21頁。。嘉雍群培完成《西藏藝術(shù)》教材,并參與編寫《中國少數(shù)民族音樂史》①馮光鈺:《中國少數(shù)民族音樂史》(三卷),北京:京華出版社,2007年版。“藏族音樂史”部分及《中華民族發(fā)展史》“藏族發(fā)展史”部分②尤中:《中華民族發(fā)展史》(第3卷),北京:晨光出版社,2007年版,第1346—1350頁。;桑德諾瓦(和云峰)完成《中國少數(shù)民族音樂文化》,其中包括藏族音樂傳統(tǒng)文化舉要及創(chuàng)編新作品賞析③桑德諾瓦:《中國少數(shù)民族音樂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27—63頁。等內(nèi)容。此外,格桑曲杰擔(dān)任主編,嘉雍群培擔(dān)任副主編,組織編撰、記譜、整理后完成《中國民間歌曲集成·西藏卷》等重大項(xiàng)目。
隨著學(xué)科研究隊(duì)伍的不斷壯大,藏族音樂研究也出現(xiàn)了多元化發(fā)展。第三代學(xué)人于曉菲完成《藏族音樂學(xué)家邊多研究》④于曉菲:《藏族音樂學(xué)家邊多研究》,中央民族大學(xué),碩士學(xué)位論文,2015年。碩士學(xué)位論文和《論田聯(lián)韜少數(shù)民族音樂研究的學(xué)科構(gòu)筑模式及承傳實(shí)踐》⑤于曉菲:《論田聯(lián)韜少數(shù)民族音樂研究的學(xué)科構(gòu)筑模式及承傳實(shí)踐》,中央民族大學(xué),博士學(xué)位論文,2019年。博士學(xué)位論文,學(xué)界因此出現(xiàn)首位聚焦藏族音樂學(xué)家的人物研究學(xué)人,藏族音樂學(xué)家口述史研究也由此得到進(jìn)一步推進(jìn)。2018年,于曉菲以《口述史在當(dāng)代音樂家研究中的意義與實(shí)踐——基于對(duì)西藏音樂學(xué)家邊多口述史工作的思考》一文獲第四屆中國少數(shù)民族音樂學(xué)會(huì)“學(xué)會(huì)杯”論文評(píng)選三等獎(jiǎng);2014年發(fā)表《放夢高原——記西藏民族音樂家邊多先生》⑥于曉菲:《放夢高原——記西藏民族音樂家邊多先生》,《西藏藝術(shù)研究》2014年第2期,第57—62頁。,2020年獲批國家社科基金項(xiàng)目“當(dāng)代藏族音樂學(xué)家口述史研究”。近年來,第二代及第三代學(xué)人開始關(guān)注田先生及其研究成果,涉及先生藏族音樂研究歷程及成果內(nèi)容的論文不斷出現(xiàn)。例如田先生口述、銀卓瑪記錄整理的《民族音樂之路、學(xué)術(shù)研究之徑——田聯(lián)韜訪談錄》⑦田聯(lián)韜,銀卓瑪:《民族音樂之路、學(xué)術(shù)研究之徑——田聯(lián)韜訪談錄》,《民族藝術(shù)》2020年第6期,第12—13頁。,于曉菲先后完成《以赤誠之心培養(yǎng)高層次少數(shù)民族音樂專業(yè)人才——田聯(lián)韜教授學(xué)術(shù)訪談》⑧于曉菲:《以赤誠之心培養(yǎng)高層次少數(shù)民族音樂專業(yè)人才——田聯(lián)韜教授學(xué)術(shù)訪談》,《人民音樂》2019年第11期,第8—13頁。、《厚德載物 桃李芬芳——記田聯(lián)韜教授對(duì)少數(shù)民族音樂人才的培養(yǎng)》⑨于曉菲:《厚德載物 桃李芬芳——記田聯(lián)韜教授對(duì)少數(shù)民族音樂人才的培養(yǎng)》,《歌海》2019年第2期,第51—54頁。等文章。由此,藏族音樂學(xué)家口述史研究的推進(jìn),標(biāo)志著第二代及第三代學(xué)人藏族音樂研究的新視域。
結(jié) 語
田先生不僅是國內(nèi)著名的作曲家、教育家及民族音樂學(xué)家,更是在國際上有一定影響力的藏族音樂研究學(xué)者。通過先生及其親授的第二、第三代藏族研究學(xué)人的研究成果,可見其中體現(xiàn)出對(duì)前人藏傳佛教音樂和民間音樂研究的延續(xù)性,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則顯現(xiàn)出一定的系統(tǒng)性和超越。其中第二代6位(含4位藏族)博士的研究課題涵蓋了三大藏族方言區(qū)或三大音樂色彩區(qū),并且延及周邊跨界族群音樂研究,由此完成了對(duì)其中不同方言區(qū)及民歌、戲曲、歌舞及宗教音樂等不同體裁內(nèi)容各有專精的完整學(xué)術(shù)布局。這一項(xiàng)學(xué)術(shù)傳承工作,對(duì)于藏族音樂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可持續(xù)性發(fā)展意義。他們的論題兼顧研究對(duì)象的“大傳統(tǒng)、小傳統(tǒng)”“主文化、亞文化”以及研究方法論中的文化哲學(xué)觀、常規(guī)方法論等應(yīng)對(duì)策略及分層關(guān)系。他們繼承田聯(lián)韜先生所創(chuàng)立的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無論第二代或第三代學(xué)人的寫作過程中,均完整呈現(xiàn)了先生的學(xué)術(shù)思想和教學(xué)理念。完整、全面地呈現(xiàn)出藏族音樂研究的整體學(xué)術(shù)成果。
藏族音樂研究是在田先生以中國少數(shù)民族音樂研究總體學(xué)術(shù)理念的引領(lǐng)下所產(chǎn)生的分支研究。通過梳理相關(guān)的研究方法和理論觀點(diǎn),可以就此窺探和檢視藏族音樂研究學(xué)術(shù)全貌下的諸音樂研究分支,并且有助于對(duì)之進(jìn)行必要反思和修整。目前有待解決的問題,仍然在于對(duì)藏族音樂研究尚缺少整體、全面和前瞻性的研究。受限于既有的條件,尤其缺乏對(duì)境外藏族音樂及對(duì)周邊跨界族群音樂定點(diǎn)、多點(diǎn)考察和比較研究。此外,田聯(lián)韜先生所培養(yǎng)的藏族學(xué)者,雖然不乏已經(jīng)邁入國內(nèi)外藏族音樂研究領(lǐng)域前沿者,但從整體上看,仍然有待進(jìn)一步提高國際溝通能力和在國際學(xué)術(shù)界的學(xué)術(shù)交流能力,完成更多、更好的學(xué)術(shù)研究成果,以適應(yīng)國家、民族內(nèi)部和國際關(guān)系的發(fā)展以及“一帶一路”倡議的戰(zhàn)略性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