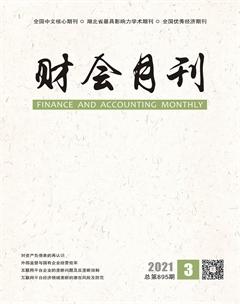對賭協議現金補償所得課稅:形式與實質之爭及其彌合
段曉紅 皮元
【摘要】關于對賭協議現金補償所得應否及如何課稅, 我國尚無明確規定, 導致實踐中征納雙方存在爭議, 稅務機關之間也存在分歧。 對此, 需要從形式與實質兩個方面出發, 以分步交易規則為分析工具, 探尋現金補償之實質: 補償交易并不屬于獨立的交易, 而是對賭交易的一個步驟, 現金補償之實質是對股權轉讓估值之修正。 因此, 對賭協議現金補償所得課稅應當在股權轉讓環節預繳所得稅, 股權出讓方支付現金補償后應調減股權轉讓所得, 同時調減受讓方股權計稅基礎并進行清繳匯算。
【關鍵詞】對賭協議課稅;現金補償;分步交易規則;經濟交易實質
【中圖分類號】 F812.42? ? ?【文獻標識碼】A? ? ? 【文章編號】1004-0994(2021)03-0152-5
近年來, 對賭協議作為一種投資方式, 在國內股權私募領域大行其道。 但我國現行稅收法規缺乏對對賭協議所得稅問題的專門規定, 導致對賭協議所得稅課稅問題在征納雙方之間存在很大爭議, 各地稅務機關的處理也不盡一致, 使簽訂對賭協議的投融資企業面臨不確定的稅法風險。 本文主要通過“斯太爾對賭案”和“李菊蓮與華聞傳媒對賭案”兩個案例, 深入剖析對賭協議現金補償的形式與實質, 進而解答其所得稅課稅問題。
一、問題的提出
案例一:斯太爾對賭案。 斯太爾公司從其股東英達鋼結構公司處收購斯太爾江蘇公司的股權, 英達鋼結構公司對斯太爾江蘇公司未來三年業績作出承諾, 若公司經營業績未達到預期盈利目標, 則需向斯太爾公司支付業績補償。 《國家稅務總局關于企業所得稅應納稅所得額若干問題的公告》第二條規定:“企業接收股東劃入資產(包括股東贈予資產、上市公司在股權分置改革過程中接收原非流通股股東和新非流通股股東贈予的資產、股東放棄本企業的股權, 下同), 凡合同、協議約定作為資本金(包括資本公積)且在會計上已做實際處理的, 不計入企業的收入總額, 企業應按公允價值確定該項資產的計稅基礎。” 據此, 斯太爾公司認為控股股東業績補償款不屬于企業所得稅應納稅收入, 而屬于資本公積, 因此未對此進行所得稅納稅申報。 2017年6月, 斯太爾公司收到湖北公安縣稅務局稅源管理一分局的《稅務事項通知書》(公地一稅通[2017]12號), 要求其針對2015年取得的業績補償款, 補繳2014年度企業所得稅款及滯納金。 荊州市地方稅務局作出《關于斯太爾動力股份有限公司業績補償款征收企業所得稅的批復》, 認為依據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的立法精神, 企業除接受股東投入資本金外, 取得的其他收入均應該并入收入總額, 全面履行企業所得稅納稅義務。
案例二:李菊蓮與華聞傳媒對賭案。 自然人李菊蓮在2014年將所持邦富公司股份轉讓給華聞傳媒, 取得華聞傳媒股份對價和現金對價收入, 并對邦富公司未來三年經營業績作出承諾, 若邦富公司未實現約定的盈利目標, 則李菊蓮需以其所持華聞傳媒股份對華聞傳媒進行補償, 不足部分以現金進行補償。 2014年和2016年邦富公司未實現盈利目標, 李菊蓮以華聞傳媒的股份對華聞傳媒作出補償, 華聞傳媒僅就現金對價部分扣繳了個人所得稅。 2020年, 李菊蓮收到國家稅務總局廣州市稅務局第三稽查局的《稅務事項通知書》(穗稅三稽稅通[2020]421號), 要求其補繳2014年11月1日 ~ 30日的應繳稅款。
案例一的爭議焦點是稅務機關應否對補償所得征稅, 爭議的根源在于稅務機關與斯太爾公司對股權轉讓與補償之間關系的理解有差異。 案例二的爭議焦點是李菊蓮應否就2014年取得的股份對價和現金對價收入全額繳納所得稅, 理清李菊蓮支付給華聞傳媒的補償所得與上述收入之間的關系是判斷這一問題的關鍵。 從稅法法理上看, 上述案例涉及兩個問題:一是對賭協議中股權轉讓所得的屬性為何; 二是現金補償的屬性為何。
二、對賭協議現金補償之形式
關于對賭協議的性質, 學者們存在多種觀點, 如捐贈說、違約金說、擔保說、衍生工具說、合同價款調整說等, 但至今未達成共識。 雖然稅法規則決定了民事交易的經濟后果, 但具有回應性的稅法規則常常滯后于形式的創新。 若稅收征管拘泥于現行稅法規則, 就難以避免囿于交易形式的思維窠臼。
1. 征管爭議之形式:補償是否屬于應稅收入。 從這一角度判斷稅務機關是否應當就補償所得課稅, 其必然的邏輯是從所得課稅構成要件的角度去判斷補償所得是否屬于應稅收入: 一是要判斷補償所得是否具有可稅性。 征稅與否首先取決于是否有收益, 這是征稅的基礎; 如果有收益, 且收益的主體不是以公益為目的, 其宗旨和活動具有突出的營利性, 則應當征稅[1] 。 二是如果確定補償所得具有可稅性, 則需要進一步明確補償所得是否已經實現。案例一中斯太爾公司與稅務機關就補償所得應否課稅產生爭議, 根據上述兩個條件判斷該補償是否屬于應稅收入: 斯太爾公司獲得的補償收入使其凈資產增加, 存在收益, 且斯太爾公司取得該筆收益并非以公益為目的, 符合可稅性中收益性、營利性和非公益性的要求; 斯太爾公司獲得的補償收入確實已經獲得, 可由其自由支配, 且該收益能夠在程度和數量上進行確定, 補償所得已經實現。 因此, 從形式上看, 斯太爾公司應當就補償所得繳納所得稅。 同理, 案例二中華聞傳媒也應當就補償所得當期繳納所得稅。
2. 對賭協議履行之形式:兩次交易。 對賭協議之履行從形式上看, 包括股權轉讓之履行和現金補償之履行, 只要締約當事人就合同的主要條款達成合意, 即合同經過要約、承諾的完成而成立, 承諾生效, 合同即成立, 合同是否生效取決于國家通過法律對當事人合意進行的評價[2] 。 股權轉讓協議自股權轉讓協議生效時成立, 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完成股權變更手續后股權轉讓行為生效。 現金補償協議屬于附條件合同, 自補償協議生效時成立, 自約定的條件確定成就或不成就時生效。 從對賭協議履行的外觀形式來看, 對賭協議的履行包含股權轉讓交易和補償交易兩次交易。 如“斯太爾對賭案”包括斯太爾公司和英達鋼結構公司的股權轉讓交易和補償交易, “李菊蓮與華聞傳媒對賭案”包括李菊蓮與華聞傳媒的股權轉讓交易和補償交易。 將對賭協議中的股權轉讓交易和補償交易認定為兩次交易, 股權轉讓方應當就股權轉讓所得繳納所得稅; 若有現金補償發生, 則股權受讓方應當就補償所得繳納所得稅。 案例一、案例二中的股權轉讓方英達鋼結構公司、李菊蓮, 應當就股權轉讓所得當期繳納所得稅; 若有現金補償發生, 則股權受讓方斯太爾公司和華聞傳媒應當就補償所得當期繳納所得稅。
3. 股權轉讓所得之形式:股權轉讓收益。 對賭協議中的股權轉讓所得, 從形式上看屬于股權轉讓之對價, 即股權轉讓收益。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關于貫徹落實企業所得稅法若干稅收問題的通知》的規定, “企業轉讓股權收入, 應于轉讓協議生效、且完成股權變更手續時, 確認收入的實現”, 股權轉讓方應在股權轉讓協議生效且完成股權變更手續時確認股權轉讓收益實現, 并就該筆股權轉讓所得申報繳納企業所得稅或按財產轉讓所得繳納個人所得稅。 因此, 英達鋼結構公司和李菊蓮應在股權轉讓協議生效且完成股權變更手續時確認股權轉讓收益實現, 前者就該筆股權轉讓所得當期繳納企業所得稅, 后者按財產轉讓所得當期繳納個人所得稅。
4. 補償之形式:對賭條件未成就之對價。 從形式上看, 對賭協議中的補償屬于現金補償協議中所約定條件確定未成就之對價, 即約定的條件確定不成就時, 融資方需向投資方支付的現金補償。 現金補償協議屬于附條件合同, 接受補償的投資方應當將補償作為收入, 在當期繳納企業所得稅; 作為給付現金補償的融資方若為企業, 其給付的補償可作為投資損失在所得稅稅前扣除, 若為個人, 則不能申請退稅。 案例一、案例二中的股權受讓方斯太爾公司和華聞傳媒, 在對賭條件確定不成就時, 應以接受的現金補償作為收入, 在當期繳納企業所得稅。 但對于股權轉讓方, 英達鋼結構公司給付的補償可作為投資損失在所得稅稅前扣除, 而李菊蓮不能就其支付的補償申請退稅。
三、對賭協議現金補償之實質
在適用所得稅法時, 交易的實質而非交易的形式具有控制作用。 對賭協議屬于包含多個交易形式的復雜交易。 當一個交易的形式較為復雜, 包含多個交易步驟時, 要確定各個交易的法律意義及彼此之間的關系, 以判斷各個交易步驟是否具有獨立性, 即某個交易步驟是可以獨立存在的, 還是僅僅屬于整體交易中的一部分。 確定這一問題通常需要運用實質重于形式原則、經濟交易實質和分步交易規則。 雖然在具體的個案中究竟應該適用哪一種原則并沒有非常清晰的標準, 但這三種原則存在一個共同前提:交易的實質決定稅收后果。 因此, 若要明確對賭協議現金補償所得如何課稅, 就需要探明對賭協議補償所得課稅的實質。
實質重于形式原則最早發端于美國聯邦所得稅法, 但美國法院逐漸不再直接援引實質重于形式原則, 而是將其發展成幾個專門學說, 經濟交易實質和分步交易規則就是由其發展形成的兩個重要分支。 美國法院對分步交易規則最為經典的表述是:對一個沒有意義和不必要的事件不予理會, 因為在一條直線盡頭的既定的結果, 不會因為走了一條迂回的道路而使結果有所不同。 分步交易規則通常適用于判斷存在多個交易步驟的綜合交易是屬于一個整體交易, 還是各個交易步驟都能成為一個獨立的交易。 因此, 在探究對賭協議這一復雜交易之實質時, 宜采用分步交易規則。
1. 征管爭議之實質:補償屬性之爭。 要解答對賭協議補償所得如何課稅, 首先要明確這一征管爭議的實質, 即現金補償協議的法律屬性究竟為何, 也就是要確定現金補償協議是屬于一個獨立的交易, 還是屬于對賭交易的一部分。
對于這一問題, 可以借助分步交易規則的“三種檢測標準”進行判斷。 這些測試既不是相互排斥的, 也不是相互依賴的, 一個稅收案件存在同時滿足一個以上測試要求的可能, 但為了使分步交易規則能夠有效運行, 只需要滿足其中一個測試即可。 分步交易規則的檢測標準之一是相互依賴測試, 即要求一系列交易中的各個交易存在相當程度的依賴, 如果沒有一系列交易的完成, 各個交易所形成的法律關系也就不復存在。 可采用相互依賴測試來判斷現金補償協議的屬性。 對賭協議包括股權轉讓協議和現金補償協議兩個交易形式, 投融資雙方簽訂股權轉讓協議時約定了一定的條件, 如果約定的條件不成就, 融資方應支付一定的現金補償給投資方。 該補償協議的目的是為了化解投融資雙方對股權估值的分歧, 確保股權轉讓交易的順利進行。 現金補償協議的存在以股權轉讓協議的存在為前提條件, 若無股權轉讓協議, 那么現金補償協議得以存在的法律基礎也就不復存在。 根據分步交易原則, 在一個復雜交易中相互關聯但形式上不同的步驟, 可能不能被認為是獨立于整體交易的。 因此, 補償協議依賴于股權轉讓協議而存在, 僅屬于對賭協議中的一個交易步驟, 而非一個獨立的交易。
案例一和案例二中的補償協議依賴于股權轉讓協議而存在, 若斯太爾公司和英達鋼結構公司、李菊蓮和華聞傳媒的股權轉讓交易也不存在, 則兩個案例中的補償協議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礎。 因此, 基于補償協議對股權轉讓交易的依賴性, 補償協議不能構成一個獨立的交易。
2. 對賭協議履行之實質:分步交易。 確定對賭協議履行之實質, 就是判斷對賭協議中股權轉讓協議和現金補償協議的關系為何, 即股權轉讓交易和補償交易是兩個獨立的交易, 還是一個交易的兩個交易步驟。 若股權轉讓交易和補償交易是兩個獨立的交易, 則對賭協議履行之實質為兩次交易; 若股權轉讓交易和補償交易是一個交易的兩個交易步驟, 則對賭協議履行之實質為分步交易。
分步交易規則的另一檢測標準是最終結果測試, 即要求有證據證明當事人一開始的意圖是追求某種特定的結果, 并且各個交易步驟的計劃和實施都屬于為實現預期結果的整體計劃的一部分。 可采用最終結果測試來判斷對賭協議中股權轉讓協議和現金補償協議的關系。 在1986年Brown v. United States一案中, Brown作為承租人簽訂了一份煤礦租賃合同, 隨后他將煤礦開采權轉租給第三人, 美國稅務法院認為其簽訂租賃合同的目的不是為了行使煤礦開采權(這屬于事實問題, 有賴于相關證據證明), 而是轉租, 因此可適用分步交易規則將租賃協議和轉租協議看作一筆交易。 法院適用最終結果測試來判斷是否可以適用分步交易規則, 并提出判斷能否適用分步交易規則的關鍵在于判斷簽訂租賃合同的意圖。 因此, 判斷對賭協議中股權轉讓交易和補償交易是否屬于一個整體交易的關鍵就在于投融資雙方簽訂現金補償協議的目的。
對賭協議產生的根源在于重組并購和風險投資的當事各方對標的資產未來盈利能力的不確定性, 其目的是盡可能實現交易的基本公平與合理[3] 。 因此, 補償本來就是為了實現股權交易的公允價值, 平衡當事人在股權交易中的利益, 從而推動股權交易的順利進行, 除此目的之外現金補償并無其他目的。 補償交易和股權轉讓交易設計的最終目的是使股權轉讓交易價格符合股權公允價值, 股權轉讓交易和補償交易這兩個形式上不同的交易, 屬于對賭協議履行的兩個交易步驟, 可歸屬于一個整體交易。 案例一中斯太爾公司與英達鋼結構公司、案例二中李菊蓮與華聞傳媒簽訂補償協議是為了彌合雙方對股權交易估值的分歧, 使股權交易最終價值為雙方都能接受的公允價值, 保證雙方股權交易的順利進行, 因此這兩個案例中的股權交易和補償交易均屬于一個交易整體。
3. 股權轉讓所得之實質:股權轉讓估值。 從股權轉讓所得的形式來看, 股權轉讓所得屬于股權轉讓收益, 在股權轉讓協議生效時確認股權轉讓所得實現。 但基于分步交易規則, 股權轉讓交易和補償交易屬于一個整體交易, 股權轉讓交易不具有獨立的稅法效果, 股權轉讓協議生效時股權轉讓所得尚未實現, 該所得并非股權轉讓收益。 根據美國聯邦所得稅的收入實現原則, 所得實現要求“財產所有者已經確實獲得財產收益”。 對于“已經確實獲得財產收益”, 判例法形成了兩個標準:一是獲得的財產收益必須能夠在程度上或數量上進行確定①; 二是獲得的財產收益可以被用來自由支配和享受②。 股權轉讓所得是融資方與投資方合意處分自己的股權而獲得的經濟性利益, 融資方當然可以自由支配和享受該所得。 但是, 股權轉讓所得尚不能在程度上或數量上進行確定。
從對賭協議履行之實質來看, 對賭協議中包含的股權轉讓交易和現金補償交易應當被視為一個完整交易, 對賭協議股權轉讓收益在股權轉讓協議生效時尚不能在程度上或數量上進行確定, 只有在現金補償協議約定的條件確定不成就, 融資方確定向投資方支付補償時, 股權轉讓收益才能在程度上或數量上確定, 才能確定獲得股權轉讓收益。 股權轉讓收益的實現時點是補償協議約定的條件確定不成就時, 因此股權轉讓所得并非股權轉讓之收益, 應當是股權轉讓的估值。 案例一與案例二中的股權轉讓交易和補償交易均屬于一個完整交易, 其中股權轉讓交易雙方的股權轉讓協議生效時股權轉讓收益尚未確定實現, 只有在補償協議生效時才確定實現。 因此, 案例一和案例二中的股權轉讓所得不屬于股權轉讓收益, 僅僅是股權轉讓的估值。
4. 補償之實質:股權轉讓估值之修正。 在分步交易規則下, 不能孤立地觀察一系列相互關聯交易的稅收后果, 而要將它們作為一個整體交易綜合考慮其稅收后果。 因此, 要從補償所得和股權轉讓所得之間的關系來考慮補償所得之實質。 在1991年Campbell v. C. I. R.一案中, 美國法院認為現金補償款是對“不公允價值的補償”, 其不屬于一個獨立的應稅事件。 在Brown v. United States一案中, 法院適用分步交易規則將租賃協議和轉租協議視為一個整體交易, 計算Brown在這筆交易中的所得稅時, 以其支付給出租人的特許權使用費沖減其從第三人處獲得的特許權使用費收益。 Brown獲得的特許權使用費收益被支付給出租人的特許權使用費所修正。 補償交易是依賴于股權轉讓交易存在的不具有獨立性的交易步驟, 其目的在于調整投融資雙方對股權轉讓價值的錯誤估計。 因此, 在計算對賭協議中融資方的股權轉讓收益時, 應當用補償所得沖減股權轉讓所得。 股權轉讓所得之實質為股權轉讓估值, 而補償之實質為對股權轉讓估值的修正。 因此, 案例一中斯太爾公司的補償收入和案例二中華聞傳媒的補償收入的目的都是調整股權交易價格, 是對股權轉讓交易中股權估值的修正。
綜上所述, 對賭協議補償所得課稅之實質為補償交易不屬于獨立的交易, 而是隸屬于對賭交易的一個步驟; 對賭協議履行之實質是分步交易, 即股權轉讓交易和補償交易屬于一個整體交易; 股權轉讓所得之實質是股權轉讓的估值; 補償之實質是對股權轉讓估值的修正。
四、對賭協議現金補償所得課稅爭議之彌合
稅收后果取決于交易的實質, 而不是交易的形式。 從實質重于形式原則出發, 當契約自由所致的交易形式與交易實質相一致時, 稅法可以直接承接私法, 當交易形式和交易實質存在“形—實”沖突或者“名—實”沖突時, 則不能依照外觀或形式進行判斷, 只能依照其實體或實質加以判斷[4] 。 有人認為實質課稅原則更多的是用來處理違法避稅問題, 但是, 如果僅僅從反避稅的角度和國庫主義傾向的角度來理解實質課稅原則又未免過于狹隘。 實質課稅原則實際上可以在更廣闊的范圍發揮作用, 它可以作為私法和稅法之間的橋梁, 實現稅法和私法的順利接軌。 實質課稅原則發揮著事實解釋的作用, 其不僅僅是反避稅的利器, 也可以在更大程度上為納稅人所用, 成為減輕納稅人稅收負擔和保護其合法權益的制度武器, 這兩種目的之間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天然對立關系, 而是可以和諧共存的。 因此, 在分析對賭協議補償所得課稅問題時, 也應當堅守實質重于形式原則, 追求對賭協議的經濟交易實質, 從而明晰對賭協議現金補償所得課稅規則的完善方向。
1. 股權轉讓所得應預繳所得稅。 股權轉讓所得并非對賭股權轉讓之收益, 而是對股權轉讓價值之估值。 在股權轉讓協議生效時, 對賭股權轉讓所得尚未實現, 對賭股權轉讓所得實現的時點是現金補償協議約定的條件確定不成就時。 雖然我國的所得稅法尚未明確計算納稅人的“應稅所得”應遵循的原則或具體方法, 但在征稅實踐中, 納稅人計算其“應稅所得”時主要依據的是財務會計制度核算出來的已“實現”的收入[5] 。 納稅人納稅義務產生的時點就是所得實現的時點, 也是實質性交易發生的時點[6] 。 因此, 在股權轉讓協議生效時, 融資方的納稅義務尚未產生, 融資方在現金補償協議約定的條件確定不成就時產生納稅義務。
考慮到對賭協議作為一種長期投資工具, 投資周期往往是三到五年, 歷時較長, 而且在這樣一個較長的周期中, 現金補償協議約定的條件成就或不成就處于一種不確定的狀態, 使得股權轉讓收益也處于不確定狀態, 這容易造成稅收流失。 同時, 股權轉讓收益不確定的狀態會損害稅法制度本身的安定性和穩定性, 也會使稅務部門對對賭協議的稅務管理、稅務檢查和監督工作變得復雜, 導致稅收稽征成本增加。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 在設計對賭協議現金補償所得課稅規則時, 可考慮建立股權轉讓所得預繳所得稅制度, 即融資方在股權轉讓協議生效時預繳所得稅, 在補償協議約定的條件確定成就或不成就時, 就預繳所得稅進行匯算清繳。
2. 補償應調減股權轉讓所得。 股權轉讓所得之實質是股權轉讓的估值, 補償之實質是對股權轉讓估值的修正。 補償不屬于應稅收益。 在對賭協議約定的條件確定不成就時, 股權轉讓收益確定實現。 對賭協議之股權轉讓可以理解為一種股權的買賣, 支付給投資方的現金補償款就相當于企業因售出商品的質量不合格等原因而在售價上給予的減讓[3] 。 股權轉讓收益應當為補償所得調減股權轉讓所得后的結果。 投資方收到現金補償, 應沖減長期股權投資成本, 在當期不繳納企業所得稅, 待投資轉讓時按照投資收益繳納企業所得稅。 若融資方為企業, 支出的補償可以沖減以前年度收入, 補償所得調減股權轉讓所得后涉及退稅情況的, 可申請退稅; 若融資方為個人, 支出的補償可申請退稅。
案例一與案例二中的股權受讓方斯太爾公司和華聞傳媒收到的補償不應當作為當期收入繳納企業所得稅, 而應沖減長期股權投資成本, 待投資轉讓時按照投資收益繳納企業所得稅; 而股權轉讓方英達鋼結構公司和李菊蓮支出的補償可沖減以前年度收入, 涉及退稅的可以申請退稅。
3. 修正估值的同時應修正股權計稅基礎。 股權轉讓的計稅基礎并非股權轉讓所得, 即股權轉讓的估值, 而是股權轉讓收益, 即補償所得調減股權轉讓所得后的結果。 因此, 在用現金補償修正股權轉讓估值確定股權轉讓收益時, 也應當以股權收益作為股權的計稅基礎, 對預繳所得稅時股權受讓方的計稅基礎進行修正。 案例一與案例二中的股權受讓方斯太爾公司和華聞傳媒, 在對賭協議約定的條件確定不成就, 股權轉讓收益確定實現時, 應當對股權轉讓協議生效時預繳所得稅的股權計稅基礎進行修正, 其計稅基礎為現金補償調減股權轉讓所得后的股權轉讓收益。
【 注 釋 】
① 在1953年Seligmann v. C. I. R.一案中,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
財產所有者已經確實獲得財產收益是認定收益已經實現的最后一步, 并且指明已實現的經濟收益必須能夠在程度上或數量上進行確定, 才具有可征稅性。
② 在1966年Herbert v. C. I. R.一案中,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進一步
提出, 納稅人通過使用或處分自己的權利而獲得的具有經濟性的收益, 可以被用來自由支配和享受時, 可以被認定為所得已經實現。
【 主 要 參 考 文 獻 】
[1] 張守文.論稅法上的“可稅性”[ J].法學家,2000(5):12 ~ 19.
[2] 李永軍.合同法(第三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2:65.
[3] 毛謝恩,崔國.對賭協議的企業所得稅處理[ J].稅務研究,2017
(6):125 ~ 127.
[4] 葉金育.稅法與私法“接軌”的理念與技術配置——基于實質課
稅原則的反思與超越[ J].云南大學學報(法學版),2014(3):63 ~ 70.
[5] 張春燕.美國聯邦所得稅體系中的收入實現原則研究[ J].經濟
法論叢,2018(1):249 ~ 274.
[6] 段曉紅,李羿錦.非貨幣性資產投資所得稅規則反思——以所得
構成要件為分析工具[ J].財會月刊,2019(17):165 ~ 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