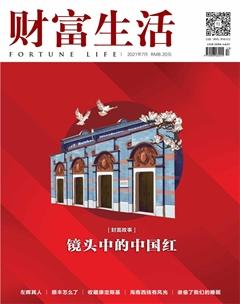以縣城為根
吳曉波
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縣是一個非常古老的行政地理名詞。縣作為地方行政機構,并非出自秦朝的郡縣制,它最早誕生于周代。《說文解字注》中記載: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為百縣則系于國,秦漢縣系于郡。
從西周到春秋戰國,縣的誕生方式千奇百怪。有的縣是大國吞并小國而設立的,有的是從貴族那里瓜分了土地,有的則是幾個鄉合并一起而形成的。
到了戰國秦孝公時期,商鞅變法廢除分封制,設立三十一縣,縣成為直屬中央的行政單位。秦始皇統一六國后,在全國推行郡縣制,郡下設縣。縣也由此成為大一統王朝最小的官方行政細胞。
在后來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中,不管高級行政單位是變成了州、道,還是省,縣始終是最堅挺的基本行政單位。
在古代,縣是農村和城市的紐帶。古人來到了異鄉,往往自稱來自“某某縣”,縣是地方歸屬感形成的基礎。
“縣志”則是一本當地的百科全書,把歷史、人口、山林、物產、民俗等等都寫得清清楚楚。從此,小地方也擁有了自己歷史的書面載體,其內容甚至比歐洲小國的古代史都來得精彩。
直到有一天,縣迎來了最大的競爭對手——市。
漢代長安曾設“東西九市”。隋唐時期,長安城設東市和西市,日中而市,東市賣漢人的商品,而西市因離絲綢之路起點開遠門較近,所以胡商聚集,酒店業發達,李白就常常“笑入胡姬酒肆中”。
中國古代重農輕商,市受到了嚴格管理,所以地位低下。而中華民國以后,工商業取代了農業,人員流動更頻繁,這要求行政機構需要更強的組織能力和管理能力,縣老爺就有些捉襟見肘了。于是,市作為新的行政機關出現了。1921 年,廣州建市,成為中國首個行政意義上的市。
如今,中國城市發展基本上是以超級城市為核心,進行大幅度的外延式擴張。而城市的規模和競爭力的提升,都需要經歷一次又一次行政區劃的調整。
“北上廣深”這樣超一線城市的縣基本已經消失了,武漢、南京等新一線城市,也大多實現了“無縣化”。無論是撤縣改市,還是撤市縣改區,背后都是城市化的鋼鐵洪流,以及星巴克、肯德基、火車站、飛機場和大型醫院拔地而起的喧囂。這確實是歷史的進步。
唯一傷感的是什么?是“縣志”將被丟進圖書館或載入電子檔案,是最原始的“我是某某縣人”的身份被“殺死”了。
人永遠該為家鄉自豪,小地方的人也有小地方的血氣。
獨山縣人民不會厭棄自己的“世界第一水司樓”,長興縣人民會為自己花20億元打造的縣衙而自豪,曹縣的李老板還是一邊吹著家鄉的牛皮,一邊悶聲不響地造棺材。
因為這是屬于一個地方縣的宏偉敘事,它承載著方言、尊嚴和榮耀,它和經濟發展沒有必然的關系。
蒙古人說,我的故鄉是那片草原。此時你很想說,咱們的故鄉是哪座縣城。但是,你欲言又止,你對新區尚未有歸屬感,你和你的后輩們,只能在一座沒有草原的偌大巨籠中,做一個沒有根的流浪人。
是的,中國人的根在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