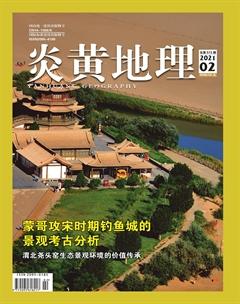火與土碰撞的政治產物
劉祎恒 吳京霓



秦磚漢瓦是火與土融合出的產物,雖陶土材質非貴重之料,但對今天的考古工作來說卻有著相當大的意義,甚至成為今人了解秦漢兩代最直接的物證。漢代瓦當的考古發現與研究給后人留下了無限暢想,透過方圓之間我們不僅可以窺探漢代人的生活習慣、建筑結構,更能體味漢代人的文化信仰以及某些政治意涵。“單于天降”“單于和親”“四夷盡服”三種瓦當的出現無疑是漢王朝發展史的見證,也能從瓦當文字中窺探出大漢之雄風。
瓦當,即中國古代木結構建筑中屋檐頂端的構建,俗稱瓦頭,最早出現在西周中晚期,至今仍有使用。在古代木制建筑中起到保護瓦片,阻擋雨水滲漏以及對建筑整體的美觀都有相當大的作用,具備了實用和審美的雙重功能。到戰國時代瓦當的形制逐漸發展成熟,常見的戰國瓦當以半圓形制居多,被稱為“半規瓦”,最終在秦漢時代達到成熟期,其規制多為圓形,從出土瓦當的數量及制作工藝的精美不難看出漢代是瓦當發展最為鼎盛的時期。常見的瓦當紋飾有篆體漢字、神獸紋、常見動物紋、文字等,如“長樂未央”“延年益壽”、方位神獸、鹿、蛙等。
1954年,內蒙古包頭市召灣漢墓中發掘的“單于和親”“單于天降”“四夷盡服”瓦當,雖在文字瓦當的范疇中,但其蘊含的重大政治意義和考古意義使其與眾不同。單于天降瓦當出土伴隨著很多爭議,由于解讀順序和“降”的讀音不同,其解讀的結果不盡相同。“單于天降”的解讀方法可分三種,第一種是“jiang”,這樣此類瓦當的含義就應通釋為單于降生或者是單于由天而降。中國封建社會中皇帝始終是最高統治者,同時擁有無限的權力。單于雖為外族部落首領,但這種解釋將單于比作天降之子,這顯然不符合封建社會的制度,在當時外族始終被漢人視為威脅的存在,將其稱之為“夷”,充滿著歧視情緒。另外,以單于為主體也就是漢人對單于有褒揚、贊頌之意,這與歷史不符。原因是包頭漢墓群的考古斷代是西漢武帝時期到西漢晚期(漢宣帝、漢元帝時期),早在漢武帝時期,包頭所處地區盡已歸屬漢朝統治,此時的匈奴也已經開始由盛轉衰,漢武帝時用武力征服了匈奴,所以并不需要通過歌頌匈奴首領這種軟弱手段達到政治上的穩定,所以這種說法存在很大的疑問。另一種關于“jiang”的解釋是參照古漢語中的注音和解釋,“降,和同也”,意思是和好之意,歷史上呼韓邪單于結束了與漢代歷年戰爭,降服于漢王朝,《前漢書·元帝紀》:“虖 ( 呼 ) 韓耶單于,不忘恩德,向慕禮儀,復修朝賀之禮,愿保塞傳之無窮邊陲,長無兵革之事”。雖然這段文字是以漢人為出發點記錄,但歷史事件地可信度較高,印證了漢代元帝時期漢王朝接受了呼韓邪單于的示好,漢匈和好,放棄邊事之爭。包頭漢墓群的斷代契合了漢元帝時期的史書記載,這種譯法與歷史記載相符合,故而這一觀點可信度較高。
第二種譯法為“xiang”。“降”有“投降”“降服”之意,意為單于被天而降,這里的天指漢代天子,古代漢語中動詞作為被動是常有出現的,因此“被降伏”在語義上可以解釋得通。隨著漢代建國之初取用黃老之學的無為而治作為國家發展的基本政策,漢朝休養生息的發展模式為后來的強大打下堅實基礎,直到文景之治開始,一個強大的漢王朝出現在世界舞臺中央,特別是漢武帝時期,漢代在此時進入全盛時期,這一時期漢朝對匈奴強硬政策使漢王朝在真正意義上鞏固了大一統,歷史記載中有關此時匈奴被漢朝軍隊打敗的事件的記載眾多,比如廣為流傳的衛青、霍去病均大勝匈奴,在綜合國力的巨大懸殊下,匈奴的對抗節節敗退,勢力不斷收縮。隨著雙方多次交兵,匈奴貴族內部也開始出現戰和兩派,甚至出現內亂,最終在漢宣帝時期以呼韓邪單于為首的一支投降漢王朝,故而這一觀點是可信的。
第三種是解讀順序的不同,可以解讀為“天降(xiang)單于”,蒼天懲罰單于的意思,古人對自然現象不甚了解,出現了恐懼,依賴甚至崇拜,漢代對神靈的崇拜更是從無消亡,從考古遺跡發掘的祭祀臺遺跡和封天遺跡看得出,秦漢時期帝王常常舉行祭天活動,因此對自然和神靈的依賴在這一時期十分明顯。這里瓦當上文字“天”可能指漢代人認為的無法解釋的自然力量,某些天災造成了匈奴勢力的削弱。史料記載,西漢中后期由于西漢軍隊的不斷征討,導致匈奴人口急劇減少,領土的喪失導致放牧地區不斷減少,牲畜數量逐漸殆盡,這也就成了這一解讀的支撐點,漢王朝在這種形勢下燒制這一類瓦當也是有可能的。
筆者更傾向于單于天降(xiang),原因是歷史上確實存在呼韓邪單于降服于漢王朝,并且西漢王朝在發展期大致分為強弱兩個階段,漢武帝時期西漢進入興盛時期,在這之后對匈奴也一直采取武力壓制政策,即便是和親也是匈奴為與漢王朝鞏固關系,穩固政權做出的主動和親。
“單于和親”瓦當的出土意義是見證了西漢初期至西漢中期采取的休養生息、委曲求全的政策以及建朝時孱弱的歷史史實。關于漢代的和親制度最早出現在漢朝建立初期,公元前200年,漢高祖劉邦由于在國力薄弱時期急于解決北方匈奴的威脅,發動與匈奴的戰爭,最終以失敗告終,不得以通過和親解決,史稱“白登山之圍”。這場戰役是漢王朝建立之初為鞏固根基維穩的統治發起的,最終以失敗告終,反映出漢朝初期國力衰弱,外夷強大。這一時期國內采取“無為而治”政策與民休息,外交上主要采取“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遣翁主如故約”的政策,但這種政策是帶有屈辱性的、被迫性的,漢朝之所以采取和親制度是為了暫時性的喘息,爭取時間取得邊境和平以及發展經濟和國力。至西漢武帝征伐匈奴大獲全勝,漢王朝這種屈辱性政策也隨之作廢,漢弱匈強的格局不復存在。在漢代中后期匈奴與漢王朝戰爭中的失利,加之匈奴內部矛盾分裂,分成了以郅支單于為首的主戰派和以呼韓邪單于為首的主和派,在五原塞降服于漢王朝,在此時為了拉近與漢王朝的關系,元帝時期呼韓邪單于向漢王朝提出和親請求,元帝賜昭君于匈奴,“單于和親”文字瓦當就應是這一時期的政治產物。這也就從史料中找到了有關“單于和親”瓦當出現的證據,在包頭中晚期漢墓中出現這種瓦當也可以解釋得通。
“四夷盡服”瓦當也是在內蒙古包頭漢墓群中出土,“夷”在漢語中通常所指漢地以外的各地區,漢代時期疆域周邊除北方匈奴外,還有南方蠻人,西方貳師、大宛等國,東方有三韓等政權,其中有歸屬漢王朝的小國,但也有時常騷擾邊境的政權,漢代對外的軍事不止存在于與匈奴的對戰,漢武帝時期南方越人諸多政權先后被漢朝軍隊所滅,西南地區也逐漸被漢王朝控制,設立郡縣。“四夷盡服”瓦當文字解釋為四方夷地皆被漢王朝所征服。此類文字瓦當并非憑空出現,在漢武帝所作詩歌《天馬歌》中就出現了“涉流沙兮四夷服”的壯志之言,西漢出現“文景之治”“漢武盛世”、擊敗匈奴、開疆拓土皆為歷史史實。西漢陳湯曾言:“但凡犯我大漢天威者,雖遠必誅之。”足見西漢武帝后漢朝國力強盛,此文字瓦當雖僅僅四字,卻氣勢磅礴,為西漢國力鼎盛之時的見證,這類瓦當的出現以及史料的佐證,足以說明漢武帝以后的漢王朝俯瞰世界的史實。
值得一提的是在出土的“單于天降”尺寸大于“單于和親”的尺寸,這似乎也在告訴著人們這時期的漢王朝對待和親的態度并不是十分贊許的,因為瓦當作為房檐的裝飾品,特別是出現在邊境地區的宮殿上的裝飾物代表了國家的形象,宮殿的大小和所用到裝飾物的尺寸有很大的考究,宮殿的規模也在一定程度上昭示著國力的興衰。此時漢王朝國力興盛,宮殿建筑也會十分龐大,而且瓦當必定是抬頭可見的東西,其規格若大,可以起到宣揚國威的效果,相反形制若小或許是有意避諱或者是不想張揚和親之事。此時與匈奴的和親已經不再是漢朝建立之初漢高祖劉邦時期為求穩定發展被迫的屈辱性和親,而是在匈奴歸降漢朝,漢朝國力鼎盛的歷史背景下進行的“非對等地位”的和親行為,此時的和親與漢初時的和親的意義顯然是不同的。
從“單于天降”到“單于和親”再到“四夷盡服”,見證著漢王朝國力由弱到強,也在述說著漢朝不同歷史時期下采取的不同的政治制度,這些磚瓦曾經是富有政治意義的建筑上的一角,雖已無法窺見當時建筑的雄偉壯闊,但這些磚瓦中承載了兩千年前漢代的厚重歷史,后人關注的不應只是瓦當中文字本身的解讀,瓦當背后的歷史文化更有意義。歷史遺物會以無聲的方式向我們傳遞千年前古人的氣息,其背后隱藏的秘密也會以自己的方式向后人傳遞,考古發掘的遺物出現的價值在于讓后人還原歷史真相,過程艱辛卻很有必要。就如漢代“單于天降”瓦當,短短四字卻有多種解讀,這并不是歷史遺留的難題,而是古人無意間留給后代的“厚禮”,在歷史史實的支撐下,無論怎樣解讀,都是對古人和遺物的尊重。歷史上火與土的碰撞不僅能產生精美的藝術品,更能把背后的故事千年傳承,使后人為之探究、挖掘,文物的魅力就在于此。
作者單位:1.西安美術學院美術史論系;2.中央美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