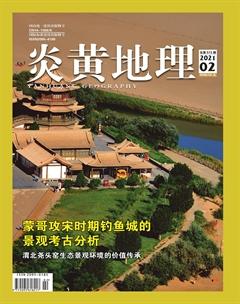陳寅恪的史學個性
李婧怡



以提倡“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聞名的陳寅恪先生,一生涉獵廣泛學術領域,掌握多國語言,一生雖多年在國外留學,但受祖父三代影響,中國傳統文學功底深厚,他利用文學與歷史的緊密關系,整合中西,探索出一套獨特的治史方法,為我國文學研究做出了獨樹一幟的貢獻,可謂中國近年來最受學者追捧的集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詩人于一身的不可多得的學術界泰斗。文章僅從家世、學術成就及文學研究方法等因素來探求陳寅恪的史學思想與家國情懷。
陳寅恪的曾祖父陳偉琳從小讀書,“六、七歲授章句,已能通曉圣賢大”,成人后雖不求名,但胸懷經世大志,創辦義寧書院以培養賢才。祖父陳寶箴自小英毅,二十一歲時中舉進京,以高超的政治才能和卓爾不群的才識位至晚清封疆大吏,曾平定湖北民患,任湖南巡撫后整頓湖南吏治,積極推行新政,開展文化教育事業,為國鞠躬盡瘁,在政壇、學界皆享有清譽。父親陳三立舉人出身,與譚嗣同、徐仁鑄、陶菊存并稱為“維新四公子”,曾協助其父陳寶箴推行湖南新政,戊戌變法后無意仕進,雖不再關注政治,但他的思想仍是較為開放的,兼容中西,反對康有為為變法而歪曲傳統史學,認為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并始終處于正統地位,強調個人對文化守護與傳承的重要意義。這些思想對之后陳寅恪的治史方法起到了關鍵影響作用,他畢生堅持中華文化本位、學術獨立與思想自由大致淵源于此。
父親陳三立還有著與尋常人家不同的教育理念,不要求祖孫應科舉考試,求取功名,而是鼓勵他們接受西方教育,學習西洋知識。陳寅恪從十三歲就開始留學,三十六歲才學成回國任教,除去期間回國養病的幾年時間,留學生涯長達十六年之久。雖吸收西學,但幼承家學,愛好閱讀,且家學淵源,藏書豐富,陳寅恪自小便埋頭于浩如煙海的古籍及佛書中,奠定了良好的中國傳統史學根基。基于這樣的深厚家學基底、多年留學經歷和開明的家風,陳寅恪沒有喪失對傳統文化的信心,對西學不排斥也不崇拜,在他的思想里沒有中西文化的沖突,只是自然而然地作為學問來研究,認為“取人之長,補人之短”“洋為中用不失本體”,留洋時間雖久,但并不曾“洋化”。
陳寅恪獨特的家庭背景與人生經歷使他的史學思想實現了中西文化的結合,一方面,深厚家學舊底的影響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使他具有堅定的文化自信;另一方面,留學日本、游歷歐美的豐富經驗使他吸收國外史學理論及方法為其史學思想增添新光彩。
所謂“史詩互證”并非陳寅恪首創,而是在宋明清史學發展基礎上,吸收了以蘭克為代表的德國歷史語文考證學派后,將西方觀點與中國傳統文獻加以融會貫通,他開創了“用中國史詩的特點來研究歷史”的方法,在經受時間磨煉后運用得爐火純青,達到非他人所能企及的“引詩證史、從詩看史”的高超境界。所以“史詩互證”方法并非單純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自然演變形成,而是中西文化嫁接后的產物。
在中國古代詩學中,以詩證史由來已久。宋人通過杜甫詩中所寫歷史事實窺探唐朝社會風氣及重大事件,即從“以史證詩”到“以詩證史”的轉變,宋人的這種史詩觀不僅影響到對杜甫詩歌的理解,也影響到其他詩歌的箋注方法,明末清初出現了第二次注杜高潮,著名學者錢謙益用“史詩互證”的方法完成了《杜工部詩箋注》,標志著“史詩互證”方法的正式確立。“史詩互證”在經歷過前人的一系列有效嘗試和清朝乾嘉學派的推波助瀾后,又得到進一步發展。到了現代,陳寅恪創造性運用“史詩互證”方法,使此方法發揚光大。陳寅恪受錢謙益影響,認為治杜詩要將治史與說詩結合在一起,他進一步對唐詩進行系統性研究,對元稹 、白居易兩位詩人的詩箋證史事寫成《元白詩箋證稿》一書,此書的出版是陳寅恪正式形成“史詩互證”方法的里程碑。在這本書中,陳寅恪認為《長恨歌》:“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中的“破”字不僅含破散或破壞之意,且又為樂舞術語,用之更覺渾成耳。”這是他用音樂的知識來箋證。又如《長恨歌》:“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關于賜浴華清池之事,按唐六典一九溫湯湯監一人正七品下注略云:“辛氏三秦紀云驪山西有溫湯,漢魏以來相傳能蕩邪蠲疫。今在西豊縣西,后周庾信有溫泉碑”。陳寅恪認為,溫泉之浴意在治療疾病,除寒祛風,非若今世習俗,以為消夏避暑只用者也。這是陳寅恪用地理四季的知識來箋證。由此可見陳寅恪在釋詩的同時還兼顧史實的考證,史詩交融,力求補充和糾正歷史記載。總之,在《元白詩箋證稿》一書中,陳寅恪注意到史與詩所具有的融通性和差異性特點,將詩歌與歷史合二為一,用詩文證史的方法考證歷史真偽,追求學術準確性與完整性。
陳寅恪在思想上承繼家風,認為穩健、折衷才是應有的政治和文化態度,反對以康有為為代表的頑固派不顧歷史事實,而以西方觀念附會中國歷史的托古改制的做法,在寫給王國維的挽詞中,陳寅恪盛贊張之洞的“中體西用”之說,但與張之洞等人不同的是,陳寅恪沒有固守中國歷史文化傳統體系,他認為任何民族文化都不可能獨立于世,皆是受外來影響,只有早晚之區別,而西方文化確有勝于中國傳統文化的部分,需取其精華為中國所吸收。“以中學為體,以西學為用,體用之說不僅不排外,且明言接納外來文化,所謂接納外來文化并非拋棄本土文化,亦非喧賓奪主”,這是陳寅恪對“中體西用”的新表述。同時也反對以胡適為代表的“新文化派”,認為文化可以現代化,但現代化并不是西化,中國文化有自身特性,不可自亂其宗。陳寅恪認為中國文化乃是“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于《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所謂 Idea者。若以君臣之綱言之,君為李煜亦期之以劉秀;以朋友之紀言之,友為酈寄亦待之以鮑叔。其所殉之道,與所成之仁,均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體之一人一事。夫綱紀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為具體表現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現者,實為有形之社會制度,而經濟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變易,則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由此來看,陳寅恪的文化立場是一種“中國文化本位”的立場,堅持“本位”并不一定要排斥外來文化,而是相信本國文化有其特性,可以吸收外來文化,但不能舍己從人。陳寅恪在新舊中西文化交融之際,猶能“處身于不夷不惠之間,托命于非驢非馬之國”,始終堅持“中華文化本位論”。
陳寅恪一方面吸收輸入西學,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不斷挖掘新史料提出新問題,既不死守中國傳統,又不被西洋學說所左右。他承認西學有先進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地方,同樣中國傳統文化也需注入西學才能迸發出新的生命力,但中國文化有其固有特性,外來西學思想需做出相應改變來適應中國環境,與中國本土文化相融合方能“為我所用”,振興中華。“中華文化本位”文化觀是陳寅恪治學的重要思想基礎之一,這基于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了解、對中西文化的對比及對本民族文化的自信與堅守,可以稱其為融貫中西的學術大師。
復旦公學及其前身震旦學院是由著名愛國主義教育家馬相伯于1905年帶領廣大愛國師生創立的,復旦公學不僅繼承了當初創辦震旦學院的辦學宗旨,還將學術獨立與思想自由作為辦學理念和方針。1907年,因足疾從日本輟學回國的陳寅恪插班考入復旦公學,在這里完成了兩年學業并以第一名的優異成績畢業。陳寅恪在復旦公學的學習生涯雖然短暫,但是馬相伯的教育理念以及復旦公學“學術獨立,思想自由”教育氛圍對青少年期的陳寅恪影響深遠,“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此初見雛形。畢業后的陳寅恪選擇繼續留學海外,1925年留學歸來的陳寅恪到清華任教,1927年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之一王國維投頤和園昆明湖自盡,陳寅恪悲痛不已,他在題寫王觀堂紀念碑銘的最后說:“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這標志著“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主張被陳寅恪正式提出。陳寅恪提出的這一思想并非心血來潮,而是多年來對復旦公學所提倡的“學術獨立,思想自由”思考與實踐的結果。
陳寅恪一生將“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為人生追求與最高信仰,并認為中國學術最主要的是要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他指出學術獨立是保證民族獨立、國家發展的根本前提。留學歸國后,陳寅恪雖專心學術研究,未曾表達過任何政治主張,但這并不意味著他不關心國家時局,他認為學術研究固有其獨立性,但并不能“完全脫離政治”。1940年,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逝世,需要重新選舉院長,陳寅恪拒絕以政府指派的政客為院長,堅持民主選舉,以表學界之正氣,可見陳寅恪主張學術自由,與政治保持距離的一種自矜的學術態度,真正是以“獨立自由”之品格,行實事求是之研究。陳寅恪一生專心治學,從未參與政治,但他絕非脫離現實的人物、象牙塔中的學者,陳寅恪的學術實踐表明,他始終保持著一份理性,一方面試圖擺脫政治權力對學術的制約,一方面又自覺將憂心國家、關心時局的人文精神融入他的治史實踐中,他畢生都在關心著國家民族興亡、關心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展,繼承了中國自古以來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的優良傳統。陳寅恪用一生時間,身體力行地踐行著“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陳寅恪史學思想中的家國情懷
陳寅恪的文史研究選題大多都顯露著他對國家時事的關心,例如陳寅恪主張將唐史“看作與近百年史同等重要的課題來研究”,《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是他在唐史研究方面最重要的一部論著,在書中提出了“關中本位”政策,從李、武、韋、楊四姓中看中央政治勢力的發展,他認為唐史“蓋中國之內政與社會受外力影響之巨,近百年來尤為顯著”。在談論中國古代儒釋道三教關系時,指出三教融合的經驗足以應對如今中西文化交匯之前鑒。陳寅恪雖致力于研究歷史史實,其目的卻是“以古鑒今”,將中華民族的興衰與中國古代文化發展結合在一起,從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
陳寅恪上承祖與父的愛國主義傳統,一生經歷坎坷復雜,自13歲東渡日本,此后二十多年來多次往返中國、日本、美國及歐洲國家求學進修,此后遭遇國仇、家恨、流離、失明等悲劇,一生漂泊無定,顛沛流離,所以在他身上所表現出來的家國情懷比他人更加深刻。1926年,陳寅恪到清華園任教,至“七七事變”大約十年時間,這段時間是其一生中讀書最勤、研究成果最多的日子。1931年,清華改制為大學,又適逢建校二十周年,陳寅恪借此機會對當時的學術現狀作出了語重心長的一些學術建議和批評,讓他最為憂慮的是,中國學術未能獨立。顯然,陳寅恪憂心中國學術不振,關心中國學術獨立,希望清華作為學術前沿陣地能夠擔當起民族精神所寄托的學術文化獨立之職責。從學生們對陳寅恪的回憶中也可知他既是認真而受歡迎的老師,也是書齋中的學者,他雖不喜歡管實際事務,也很少拋頭露面,但這并不代表他不關心國事。從他發表的一些學術論文和詩篇中可以窺知他有著強烈的愛國情懷,陳寅恪從不是慷慨激昂的政客,也不是學術與政治之間的風頭人物,他的愛國心是植根于中國歷史與文化中的。但好景不長,陳寅恪對中國學術的期望以及個人的理想抱負被日趨惡化的時局所打斷,當時國家內憂外患,多數人只顧及眼前的國難,已無暇考慮百年大計,“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侵占東三省,書生救亡無力的無奈感,唯有“酒共愁添哭是歌,悲秋意苦奈秋何”。
西安事變后,雖停止了內戰,但中日戰爭一觸即發,陳寅恪不得不結束平靜的校園學者生活,踏上了苦難的流亡之路,轉徙在西南天地之間。1938年,陳寅恪已近五十歲,戰火燒至長沙,只好攜一家大小逃亡香港,國破家亡,傷別之情,不能自已。1940年,陳寅恪在戰亂中完成了《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一書,提出了“關中文化本位說”思想,是想以此說明中國軍隊此時在抗戰中雖處劣勢,但只要中華文化精神不滅,哪怕中國滅國,也能再次復興。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占領香港,陳寅恪一家困居香港。據說陳寅恪因略懂日文,日軍對他還算客氣,曾送面粉給陳家,被陳寅恪夫婦堅決拒絕。之后日軍又有意請陳寅恪到淪陷區上海或廣州任教,還以40萬日幣委任他辦東方文化學院,陳寅恪堅決不肯為日本人服務,之后設法出逃香港,取道廣州灣抵達桂林。陳寅恪給大女兒取名“流求”,二女兒取名“小彭”,為的就是要后代銘記國恥,兩姐妹的取名寄托著陳寅恪對人生的態度、對女兒的關愛,更飽含著他濃濃的家國情懷。
根基深厚的國學基底和掌握多國語言的國際學術視野為陳寅恪之后的學術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在中西文化交融之際,他堅守“中華文化本位”立場,堅信中國傳統文化的魅力,力圖以“史詩互證”研究喚醒國人對傳統文化的關注,振興中華文化。他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受政權干擾,保證學術純粹。縱觀陳寅恪的一生,他的整個生命是和學術連在一起的,他用自己的錚錚鐵骨和博學堅韌書寫著屬于自己治史思想中的文化情結與愛國情結。
作者單位:青海民族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