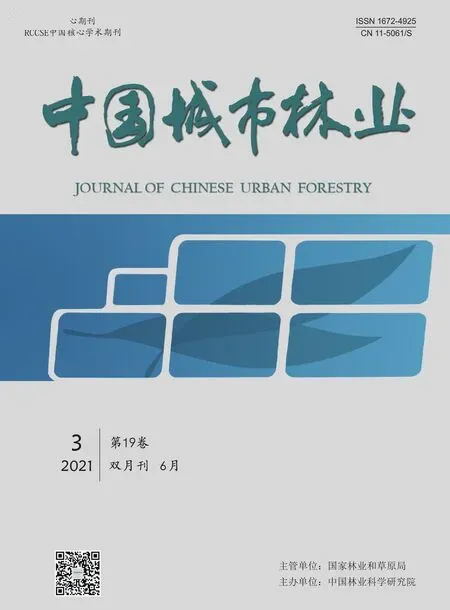基于CiteSpace的國外植物修復技術研究進展*
沈葆菊 黃 婧 李 昊
西安建筑科技大學建筑學院 西安 710055
植物修復是利用植物及根際微生物進行環境凈化的生態修復技術[1],在被污染的環境中,植物能利用其提取、降解、揮發、固定和過濾等機制凈化土壤、水體和空氣中的無機和有機污染物[2-3]。植物修復技術相較化學或物理修復方法成本較低,適用于污染面積較大且污染程度不高的場地[4]。在過去的30年間,植物修復技術在國內外工業廢棄地修復實踐方面被廣泛應用,被公認是一項有效、低成本、環境友好、可持續的工程技術。國外研究學者從實踐需求中不斷探索,逐漸將植物修復技術理論化,形成了具有多學科交叉、多內容層次、多視角拓展的研究成果。本文基于科學知識圖譜分析軟件CiteSpace,對近20年國外植物修復研究的文獻進行綜合分析,客觀呈現國外植物修復理論研究的相關脈絡,明確研究基礎與熱點方向,為國內相關領域提供科學、有價值、有前瞻性的研究參考。
1 數據提取與研究方法
植物修復技術于20世紀80年代在美國正式命名;20世紀90年代,“大量關于植物修復技術的實驗室成果公開發表,但其結果不甚理想,部分人鼓吹植物修復技術是清除污染物的‘靈丹妙藥’,卻在田間應用時以失敗告終,植物修復技術的發展經歷了‘繁榮之后蕭條的戲劇轉變’”[5]。其后,直到21世紀相關研究才進入穩定增長階段,學界對植物修復的認知更加理性,對修復機制理解更加透徹。
本文選取2000至今的文獻作為分析研究對象。研究數據來源于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數據 庫, 以主題為 “phytoremediation” 或“phytotechnology”進行檢索,時間跨度為2000—2019年,最終獲取11 324篇文獻。從圖1可看出,國外植物修復研究文獻的發表數量從2000年至今增長了約10倍,整體呈現持續增長趨勢,尤其近3年文獻增長幅度較大,說明該領域的關注度有了大范圍的提升。從目前的文獻總量看,總體處于較為成熟的研究階段。

圖1 國外植物修復研究文獻數量的年度變化
文獻分析運用CiteSpace 5.1版本軟件,一方面結合文獻學科分布與共被引期刊分布數據分析國外植物修復研究的學科交叉情況、研究基礎和研究動態變化;另一方面結合高被引文獻及關鍵詞聚類圖譜分析,聚焦當下的研究熱點。
2 國外植物修復研究的整體特征
2.1 學科交叉概況
使用CiteSpace對文獻的學科分布進行學科方向的聚類分析(圖2),結果發現:1)環境科學(Environmental Sciences)、植物學(Plant Sciences)、環境工程(Engineering Environmental)是文獻量最多的3大學科,其次是生物技術與應用微生物學、土壤學等,說明植物修復從本質上是環境科學、植物學、環境工程的跨學科研究領域。2)植物學的中心性為0.23,環境科學的中心性為0.22,中心性較高表明此學科在植物修復研究領域與其他學科的聯系密切,發揮多學科間的樞紐作用。3)工程學(Engineering)的中心性為0.2,但是當前該學科研究主要停留在理論基礎深入挖掘與實驗模擬方面,對工程應用的研究則相對較少。

圖2 國外植物修復研究學科分布網絡圖譜
為了考察植物修復研究領域知識獲取的主要來源,利用CiteSpace對高被引期刊進行分析統計(表1),得到以下結果:1)主要涉及自然科學類期刊,以生態環境、環境科學、生態工程等類型的期刊為主。2)Chemosphere與Environmental Pollution的被引頻次遠大于其他刊物且影響因子較高,在一定程度上引領了國外植物修復研究的前沿。3)中心性排名前2的期刊為Plant And Soil和Current Opinion In Biotechnology,植物修復的大量研究都發表于這兩種期刊。

表1 國外植物修復研究高被引期刊一覽表
2.2 研究基礎
高頻被引文獻的研究內容構成知識基礎(表2)。相關研究內容主要涉及3個方面:一是植物對重金屬污染的修復。Hazrat Ali等[7]針對重金屬的植物修復提出相關概念和應用,提出當下需要篩選更多樣的超富集植物用于恢復重金屬污染的土地和水體,并通過植物提取開發新型高效的金屬超富集劑;分子工具被用來更好地理解植物對金屬的吸收、轉移、隔離和耐受機制。二是修復植物選擇。I.D.Pulford等[8]重點關注不同植物的修復差異,總結出喬木具有地上和地下的巨大生物量、樹根降低水土流失風險、落葉促進養分循環和土壤持水能力等優勢,因此適用于植物修復。三是植物修復效率提升。Stéphane Compant[9]和Bernard R.Glick[10-11]等提出了細菌在促進植物健康和生長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這些細菌包括生物降解細菌、促進植物生長的細菌和通過其他方式促進植物修復的細菌。

表2 國外植物修復研究的高頻文獻及作者統計表(前10篇)
2.3 研究動態變化
高頻被引文獻按照時間線索可梳理出當前植物修復技術研究的發展脈絡。植物修復技術并不是一項新興技術,植物修復研究首先緣于全球工業化產生的大量重金屬污染物,它是伴隨如何解決工業化帶來的環境威脅這一具體問題而展開;其次是為了解決農用化學品(肥料、殺蟲劑和除草劑等)使用過量導致的土壤污染[12]。
1983年,RL Chaney[13]首次提出利用超富集植物清除土壤重金屬污染以實現消除或降低污染程度,從而修復環境。2010年以前,植物修復技術在對污染物的吸收、轉運和降解的機理有了實質性認知,并建立了針對清除不同類型污染物的植物物種的在線數據庫[14];同時,學界了解到這項技術也受限于場地環境條件、修復時長和植物耐受性等因素[15]。2010年以后,植物修復的研究重點轉向如何提高修復效率以及培養篩選高耐受力植物等方向。近年來,隨著植物修復的理論研究不斷深入,植物修復與景觀設計的結合勢在必行,主要以哈佛大學Niall Kirkwood教授為代表,主要研究工業廢棄地再利用以及植物修復與景觀設計的結合。
3 國外植物修復研究熱點
關鍵詞是文獻核心內容的提煉,高頻關鍵詞可反映研究領域的熱點方向。對文獻關鍵詞進行知識圖譜繪制,結果發現除phytoremediation以外,出現頻 率 較 高 的 關 鍵 詞 是 heavy metal,plant,accumulation,contaminated soil,phytoextraction等,且此類關鍵詞的中心性較高。從關鍵詞分布的時間維度上看,相關研究從早期關注特定環境中的污染物去除,到對超富集植物種類的深入挖掘,再到通過生物工程技術提高植物修復效率,直到近些年這項研究逐漸走出實驗室關注真實的空間環境中植物生長的周期性變化對修復的效果影響,以上構成了當前植物修復研究的熱點(圖3)。按照學科可將這些研究熱點整合為3個方向,即“基于生物工程的植物修復效率優化”“基于植物學的修復植物類型拓展”和“基于環境工程的植物修復應用”(表3)。

表3 國外植物修復研究高頻關鍵詞聚類信息表

圖3 國外植物修復研究熱點網絡圖譜
3.1 基于生物工程的植物修復效率優化
一般情況下,植物修復技術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缺乏大規模的應用。這些局限性包括修復周期過長、地上生物量低而不利于污染物提取;此外,植物長勢還受土壤、水、光照等基礎條件的影響[16]。這些限制促使研究人員嘗試通過調整植物本體基因及其生境來提高修復效率。
1)植物基因改良在植物修復中的應用。植物對某種污染物的超富集特性與遺傳背景相關。來自微生物、植物和動物的基因被成功地用于增強植物對污染物的耐受、去除和降解能力,通過基因工程可定向培育出具有高生物量的超積累或抗性強的植物[17]。提高植物修復效果的一個直接方法就是在植物中過度表達與特定污染物的代謝、吸收或運輸有關的基因,Amna Ijaz[18]的研究結果表明:含有降解、積累和代謝基因的轉基因物種對土壤和水中的有機污染物或重金屬污染有強化修復的作用。
2)根際微生物強化在植物修復中的應用。土壤微生物幾乎參與土壤環境的一切生理生化活動,利用土壤—微生物—植物的共存關系,充分發揮植物與微生物的各自優勢可提高土壤污染物的修復效率[19-20]。在微生物—植物共生系統中,植物根系分泌物為微生物提供充足的營養,而此類微生物分泌的激素可促進植物生長或增強植物抗逆性[21]。目前,根際微生物通常可以分為根瘤菌、叢枝菌根真菌、溶磷微生物和內生細菌等。有關污染土壤的植物—微生物聯合修復形式主要有植物與專性菌株的聯合修復(如將土壤芽孢桿菌與油菜結合修復鉛污染土壤)、植物與菌根的聯合修復(如外生菌根真菌對Cu、Cd有很強的吸收積累能力)。
3.2 基于植物學的修復植物類型拓展
植物作為環境修復的主體,篩選適宜植物種類是污染環境修復成功的關鍵。修復植物的篩選主要基于植物的生長速率與根系長度、污染物和土壤性質、區域氣候條件、當地植物品種等自身因素,并且需要同時考慮各類植物景觀搭配的協調性。在污染對象中,最嚴重的一類就是重金屬,重金屬因其不可降解性,在環境中日益積累深重污染整個食物鏈,危害巨大。基于植物學的研究往往聚焦在篩選與培育超富集植物上,即挑選出對重金屬的耐受力和富集力強、生物量大和生長周期短的植物品種。Nicoletta[22]指出“超富集植物是指對重金屬的吸收累積量超過一般植物100~1000倍以上的植物,且重金屬不再停留在根部,而是轉移并積累到地上器官,特別是葉片中”。目前確認的超富集植物有700多種(廣泛分布于植物界的45個科中),分為3大類:第一類為生長周期短、生物量大的蕨類草本植物,這類植物生長速度快、生物量大,大多數對As具有良好的富集作用,代表性的植物為蜈蚣草(Pteris vittata)、粉葉蕨(Pityrogramma calomelanos)等。第二類為具有經濟價值的藥用或食用的草本植物或農作物,如印度芥菜對Cd,Zn,Pb,Cu均有較高的耐受性和吸收能力,遏藍菜是Zn和Cd的超富集植物且目前被研究最多的植物。第三類為木本植物,這類植物生長速度相對較慢,但形成一定規模后,對修復重金屬污染土壤和生態恢復的效果與可持續性良好。
3.3 基于環境工程的植物修復應用
1)針對土壤污染的植物修復技術。修復往往是在土壤條件較差的場地進行,土壤的肥力水平較低。因此,根據植物生長發育的生理需要,需要對植被修復過程的土壤條件進行適當優化,如調整土壤pH,施用或添加螯合劑、生物菌肥等,建立合適的水肥條件,促進修復植物生長,增強植物的抗逆性[23]。針對土壤的植物修復還必須考慮植物的根深長度,大多數草本植物的最大根系深度為0.6 m,直根系喬木則可達3 m。植物修復最為有效的深度范圍為0.9 m內,最大不超過3 m。
2)針對水體污染的植物修復技術。水體污染對自然環境、人的生產生活有著嚴重的危害。目前,采用人工濕地的方式進行水體修復為主要修復方式。在以植物為核心搭建的濕地系統中,通常采用生物量較大的水生植被,通過過濾、吸附、沉淀、降解、鈍化和離子交換等過程,通過物理、化學和生物過程相互作用、協同工作,從而實現凈化水體的目的。常用于人工濕地的水生植物有挺水植物和沉水植物兩大類:海芋(Alocasia macrorrhiza)、蘆葦(Phragmites australis)、香蒲(Typhaangustifolia)、 風 車 草 (Clinopodium urticifolium)等挺水植物易于存活且更新能力強,對污水凈化效果明顯且具有景觀美化作用,目前被廣泛應用于有機物和富營養化污染的河流生態修復區[24];苦草 (Vallisneria natans)、金魚藻(Ceratophyllum demersum)、狐尾藻(Myriophyllum spicatumL)和黑藻(Hydrilla verticillata)為常見的沉水植物,能夠降低水體富營養化因子和提高水體透明度[25]。目前經常應用的水質凈化植物種類不到50種[26],未來還需不斷篩選凈化能力強、具有一定抗逆性、適應性強的植物。在實踐應用中,被污染的水體將被開發為人工活動的景觀區域,因此,植物修復方案除了要考慮水體凈化的效果之外,還需考慮整體植物群落的觀賞性。
4 展望
本文通過對近20年國外植物修復相關文獻分析可知,針對植物修復的研究是多學科交叉研究,運用植物對環境的積極影響促進良好的生態環境品質提升符合當前生態文明建設的相關議題。一直以來,植物修復技術由于其自身局限性,缺乏大規模應用,但植物修復所提供的生態回報為其廣泛研究提供了驅動力。以下3個方向可以進一步拓展應用:
1)針對工業污染場景的工程應用。植物對工業產生的各類無機污染物與有機污染物有明顯的修復效果,可應用于城市工業區修復、礦區修復、垃圾填埋場修復、河流濕地修復等。隨著修復技術和對自然修復過程認知的不斷提升,植物修復以其美觀和低成本的優勢將會越來越多地應用于城市既有工業區存量更新與環境提升項目中。
2)植物的生態修復作用與景觀效應相結合。隨著植物開發與修復技術的不斷成熟,植物修復技術可被廣泛應用于棕地修復的最后一步,使其作為一種良好的種植景觀長期為棕地提供可持續的生態修復與景觀效應。
3)具有修復潛力植物物種的進一步開發。土壤與水體通常受到多種污染源的復合污染,因此具有復合功能的植物篩選有待進一步開發,同時兼備兩種以上修復能力的物種對修復環境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同時,應開展多種植物聯合修復,如喬、灌、草植物群落優化搭配,修復植物和農作物通過農業種植措施合理配置,構建高效的植被生態修復群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