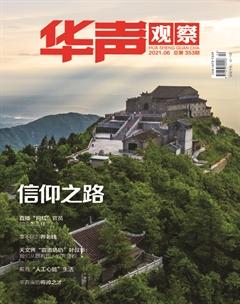百年前這個大會 為何改變了中國命運
洪俊杰 顧杰
厚重的文物庫房門被推開。一個牛皮紙袋從藏品柜中拿出,戴著白手套的工作人員小心翼翼取出一張冊頁,上書“作始也簡,將畢也鉅”,落款為“董必武 一九五六年二月”。
這幅字是國家一級文物,是董必武來上海時為中共一大會址所題。原文出自《莊子》“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意為有些事情開始極其微小,后來逐步發展壯大,最終成就一番大事業。
回到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發源之地,記者感慨萬千。故事,要從百年前風云際會的上海講起。
“相約建黨”
1920年2月中旬,上海十六鋪碼頭,一艘外國輪船上走下一名中年男子。他就是新文化運動領袖陳獨秀。
在上海,陳獨秀從他最熟悉的教育和宣傳做起,行程密集。此時他的心中,還藏著一件重要的事。在從北京南下途中,李大釗親自送他至天津。在一輛不起眼的騾車里兩人聊了一路,從對思想文化的研究和傳播,談到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留下了一段“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佳話。
經歷過北京五四學生運動的陳獨秀,已然發現“僅有學界運動,其力實嫌薄弱,此至足太息者也”,“六三大罷工”更讓他看到了上海工人階級的巨大力量。
在上海,陳獨秀重編《新青年》,很快聚集起一批將民族危亡視為己任的知識分子。上海逐漸成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新中心。當代表先進生產力的工人階級與代表先進文化的馬克思主義結合時,一股偉力噴涌而出。
后來的歷史證明,這的確是一個頗具先見的判斷——時代巨幕已然拉開,火種開始點亮舞臺。
“弄堂里的火種”
穿過茂密的法國梧桐,石庫門房舍成排出現。走進南昌路100弄2號(原法租界環龍路老漁陽里2號)逼仄的天井,抬頭看,二樓一扇漆紅木窗開著,雕花窗楣邊靜擺著一張空無一物的舊式書桌。
時間撥回到100年前的那個夏天。這張漆黑的小木桌上堆滿了各類待校編的文章,伏案的陳獨秀正忙著為即將付印的《新青年》雜志做最后的校改工作。如今,在舊址一樓的大廳里,還懸掛著一塊小黑板,上有粉筆寫就的一行繁體小字:“會客談話以十五分鐘為限。”當年盛況可見一斑。
時間到了1920年8月,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早期組織——中國共產黨發起組在這間宅子里正式成立。這座不起眼的石庫門建筑,已然成為各地共產主義者進行建黨活動的“樞紐”。從那時起到第二年春,一封封信函從這里發出、一個個“使者”奔向各地,先后在國內6個城市及旅日、旅法華人中建立共產黨早期組織。
1921年6月,在與來滬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克爾斯基商議后,上海早期組織成員李達和李漢俊寫信給各地黨組織,通知速派兩名代表赴上海開會。老漁陽里2號發出的一封封“邀請函”,醞釀著一個大事變。
“絕不是為個人命運”
行走在繁華的上海新天地,太倉路127號并不起眼。這里是博文女校舊址,一棟內外兩進、兩層磚木結構的老式石庫門建筑。
1921年6月末到7月中旬,9位“北京大學暑期旅游團”成員陸續住了進來。他們都是在收到李達、李漢俊的書信后,趕來上海出席中共一大會議。
有學者做過分析,早期的50余名中共黨員多為知識分子:“南陳北李”是大學教授;13位出席代表中,8人有大學學歷,其中4人留學日本、3人就讀于北京大學;4人有中師學歷;1人是中學學歷。正因為有較高的學養、開闊的眼界,他們接受俄國“十月革命”送來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成為民族最先覺醒的人。
1921年酷暑7月,上海灘群賢畢至。看似平靜的博文女校之下,激蕩的卻是之后中國紅色畫卷的“初心之作”。據史料記載,一大會議多項籌備工作在此完成。
“有力的爭論”
7月23日晚,望志路106號,一大代表李漢俊之胞兄李書城寓所。李漢俊把一樓的客堂間布置成會場。一個長方形餐桌,十幾把圓形椅凳,15名年輕人、包括兩個高鼻梁老外,帶著興奮心情齊聚于此。
當晚,第一次會議舉行,兩位共產國際代表致辭,隨后代表討論大會任務與議程。24日第二次會議,各地代表報告當地區黨、團組織情況。之后休會兩日,起草黨綱和今后工作計劃,27日、28日和29日,代表舉行三次會議,對黨的綱領與決議做了詳盡討論。
多位參會者日后回憶,會場上發生過多次“有力的爭論”。最激烈的思想碰撞,發生在兩位飽讀馬克思著作的代表之間:李漢俊主張,共產黨要走什么路,最好派人去俄國和歐洲考察,之后再來決定。而被稱作“小馬克思”的劉仁靜則認為,應該武裝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現共產主義。
此外,就是關于是否支持“黨員經執行委員會許可能否做官和當國會議員”。即便在最終通過的綱領中采納雙方意見,但仍在注釋中留了個小尾巴:“此條款引起激烈爭論,最后留至1922年第二次會議再作決定。”
真理越辯越明,爭論的意義莫過于此。
“嶄新的政黨走了出來”
走在嘉興南湖邊,靠近湖心島處,一艘復建于上世紀50年代的單夾弄中型畫舫靜靜停泊著。當年,正是這艘不起眼的小船,改變中華民族的前進航向。
7月30日晚,李公館內突然闖進不速之客。“他張目四看,我們問他‘找誰,他隨便說了一個名字,就匆匆走了。”李達日后回憶。有地下工作經驗的馬林建議大家緊急轉移,經李達夫人王會悟牽線,部分代表登上開往嘉興的火車。幾小時后,南湖上聚集起這批革命者的身影。
在浩渺煙波中,代表們在畫舫上召開最后一次會議,通過黨的綱領和關于工作任務的決議,選舉臨時領導機構中央局,黨的一大順利閉幕。
這些意氣風發的年輕人或許沒想到,這次會議會如此深刻改變中國命運。或許相較于他們之后的崢嶸歲月來說,這只是歷次有驚無險經歷中的一次。以至于多年后,他們竟難以回憶出開會的具體日期——這,是“作始也簡”的最好注腳。
曾撰寫《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的胡喬木感慨:“‘一大開過了,似乎什么也沒有發生,連報紙上也沒有一點報道。”但歷史已然發生,當一個新的革命火種在沉沉黑夜的中國大地上點燃時,“中國的偉大事變在實質上卻開始了”。
建黨24年后,毛澤東在以黨的七大名義召開的中國革命死難烈士追悼大會上說:“‘巨就是巨大、偉大,這可以用來說明是有生命力的東西,有生命力的國家,有生命力的人民群眾,有生命力的政黨。”此時,中共黨員人數已從一大召開時的50多人發展到121萬人——這,是“將畢也鉅”的確鑿鑒證。
正是這份生命力,成就了一番震爍古今的事業。盡管一大確立的黨的原則是那樣簡單、質樸,卻在一代代共產黨人心中孕育成長,成就參天大樹。歷史終于可以宣告:當紅色的激流匯入黃色的土層,這個偉大的黨堅定選擇馬克思主義,徹底改寫人民命運與國家前途。
偉大仍在繼續。當我們在向“兩個百年”目標昂首邁步時,一定會想到這個畫面——
天邊破曉,望志路106號的門緩緩打開,一個嶄新的政黨走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