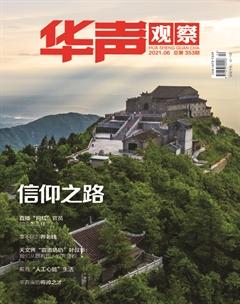“中流砥柱”的密碼
朱珉迕 茅冠雋 杜晨薇
關家垴,山西武鄉蟠龍鎮東部一個典型的太行山區小山村。70多年前,這里是太行抗日根據地的腹地,距離武鄉八路軍總部磚壁村僅十多里路。1940年,這里見證過一次堪稱慘烈的戰斗。
有人說,一部抗戰史,讓中華兒女嘗盡了人間所有的滋味,有悲慘和屈辱,有抗爭和犧牲,有獨立和覺醒。這一切疊加在一起,才有了最后的勝利。
這是一段怎樣的歷史?我們從這里出發,沿著太行山,重尋八路軍的足跡,尋找勝利的答案,尋找“中流砥柱”的密碼。
18次必死的沖鋒
講到關家垴,崔韶光哽咽了,她是在八路軍太行紀念館干了一輩子的講解員,這段故事不知講了多少次。
關家垴戰斗發生在1940年10月30日到31日,是百團大戰第三階段最大的一次進攻戰役。那兩個血戰的晝夜,八路軍究竟犧牲了多少人?崔韶光說她看到的許多公開資料寫著,“我軍犧牲了500多人”。一位親歷的老戰士卻告訴她,戰爭結束的時候,關家垴滿坡滿溝鋪滿了戰士的尸體。“500?或許遠遠不止。”
關家垴村是我們臨時決定去的。在當地的紅色景點列表里,這里甚至排不進前三位,當地人說,那不過一座孤寂的山頭罷了。
70歲的關衛平是我們在山上偶遇的。關家垴打仗時,他的父親30多歲,參與了埋尸。打掃戰場前后花了十二三天,當年很多村民都來埋烈士。一層尸體,一層土,一層尸體,一層土,就這么埋。埋了多少?沒人敢去數這個數。也實在沒法數,埋的有時是一只胳膊,有時是一條腿,有時是半個腦袋……
“關家垴戰斗,18次的沖鋒,人人都知道,沖上去就是送死,他們還是上去了。”在八路軍太行紀念館,崔韶光無數次重復過這句話,每每哽咽。
崔韶光搶救式地采訪過很多革命老戰士。她每次都問對方一個問題,關家垴究竟犧牲過多少人。她所能見到的八路軍和他們的子女,沒有一個人能說清這個數字。有一位老八路制止她:“你不要問了,我不會告訴你的。如果當時你在,你也會上去的。”
“因為這不是生死。這是我們的土地。”
料敵制勝,計險隘遠近
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召開洛川會議,決定開辟敵后戰場。太原失守后,正面戰場幾無勝算。八路軍創建了晉察冀、晉西北、晉冀豫、晉西南等敵后抗日根據地,打起了“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游擊戰。
如果把當時的時局比作棋局,那么一塊塊敵后根據地就像是下圍棋做活的“眼”——日本兵力供給不足,無法占領全中國;在敵后,看起來是日軍圍困我們,其實是一個個“棋眼”在爆破敵方勢力。這樣的策略既分散和削弱侵華日軍的力量,減輕了正面戰場的壓力,且能迅速填補因正面戰場作戰失利留下的空白,壓縮敵占區的范圍。
而在山間,還有特別的戰術。
“峪”,北方地區多見的山谷。平型關大捷,發生在“蔡家峪”,八路軍總部,也曾設在“王家峪”。
王家峪的八路軍總部,是4座相連的四合小院,小院依山而建,靠山一側房屋為窯洞結構,窯洞里不僅能藏糧食、武器,還能當地道。當時,太行山西麓的武鄉溝連溝、洞連洞,既能藏身,又能戰斗。
平型關以北老爺廟附近的山溝有一條馬路,叫喬溝,是日本車隊必經之路。喬溝地形一邊高一邊低,從軍事角度看很適合伏擊。起初,八路軍靠的,就是這種經濟實用的作戰方式。
打到淶源,還是依靠伏擊。雁宿崖三面環山,中間是一條溝,有點像個口袋。雁宿崖戰斗持續了一天,大早上鉆進伏擊圈的日軍,除了指揮官和少數幾個人逃跑,其余全軍覆沒。八路軍繳獲了炮、機槍、步槍、騾馬和部分軍品。伏擊的那個連隊,一半戰士換了槍。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隘遠近,上將之道也。”“小米步槍”到底是怎么贏過“飛機大炮”的?這里有部分答案。
勝利之最深厚的根源
但還有答案。
游擊戰的主力并非傳統意義上的“正規軍”。這是一支不斷變化的特殊軍隊。1937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部隊規模大約5萬人,到1940年8月,已經發展到50余萬人,還有大量的地方武裝和民兵。
1939年到1940年的兩年,敵后抗日作戰1萬余次,粉碎日軍1000人至5萬人的“掃蕩”近百次。后來記述時,對這些作戰主體的描述用了一個詞——“抗日軍民”。
《論持久戰》中,毛澤東用了一個相似的詞:“兵民”。“兵民是勝利之本,”他寫道,“戰爭的勝利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
八路軍駐扎的武鄉,當年不過是一個14萬人口的小縣,武鄉百姓卻為八路軍做了49萬雙軍鞋,送了240萬擔軍糧。半個多世紀后,崔韶光在各處講故事,總要說一句話:老區的人民“最后一尺布用來縫軍裝,最后一碗米用來做軍糧,最后的老棉襖蓋在了擔架上,最后的親骨肉送他上戰場”。
還有許多八路軍的子女,是“太行奶娘”養大的。魯藝木刻廠廠長嚴涵的兒子,出生后取名白樺。孩子滿月當天,兩口子執行任務要走,只能把孩子托給北上合村的奶娘高煥蓮。奶娘養了孩子整整4年。期間日軍掃蕩村子,奶爹爹替白樺堵了一刺刀,被捅死了。白樺受了驚嚇,奶娘去山上給他采草藥治病,一腳踩空落下終生殘疾。
4年后嚴涵來接兒子,一看自己的兒子又白又胖,高煥蓮的親兒子又黑又瘦。家里的大兒子說,自從白樺來了,我弟弟就斷奶了,讓他吃我娘的奶。我飯量大,每次吃飯娘就讓我少吃點,要是我吃得多了,娘就打,每頓飯都是白樺先吃飽了,我才能吃,我娘叫他親疙瘩……
在當年的太行山,這樣的故事比比皆是。還有這樣的故事——
1991年,參加過抗戰、擔任過靈丘縣長的董信回憶,1937年八路軍到靈丘,第一個過的就是他家所在的青羊口村。那是農歷八月十七日,正是秋收大忙時節,老百姓聽到八路軍來了,能跑的都上山了,原因很簡單,一怕當差抓兵,二怕“共產共妻,貧富難逃”。村民們一度聽人宣傳,“共產黨的軍隊要殺人”。
幾天后,部隊開拔了,老百姓們站在村口送部隊;直到部隊轉過山頭看不見了,還手搭涼棚望著。“當時正是剛剛收打完核桃的季節,老百姓的房上院內到處堆放著核桃,戰士們一個也不動,有的坐在核桃堆上也不吃一顆。他們在臨走前給你把家里、院里打掃得干干凈凈,還讓房東親自看看丟了、壞了什么東西沒有。”
1995年,八路軍總部機要科副科長林桂森老人站在八路軍太行紀念館序幕廳一邊哭一邊講:就是因為一把玉米,彭老總罵了娘。“他說別的人碗里沒有玉米面,我的碗里怎么會有玉米面,有那么一個人幫助老子搞落后。當時炊事員站門檻上,頭都抬不起來。”
林桂森一輩子記得彭德懷的一句話——“共產黨八路軍只有一個特權,那就是吃苦。”
而在紀念館內,一面碩大的展示武器裝備的玻璃柜下,最醒目的則是毛澤東的話——
“武器是戰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