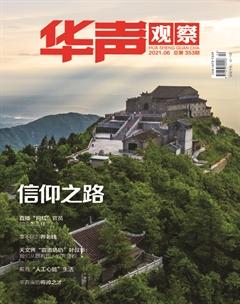閱讀障礙:可以避免的悲劇
李慕琰
閱讀障礙雖然會(huì)伴隨終生,但他們的困境并非無解,政策和社會(huì)環(huán)境大有可為,有些并不復(fù)雜的調(diào)整,足以改變?cè)S多人的一生。
在中國,大約5%~8%的適齡兒童患有閱讀障礙,每10到20個(gè)孩子中就可能有一個(gè),人數(shù)可達(dá)上千萬。這是學(xué)界給出的保守估計(jì)。
閱讀障礙雖然會(huì)伴隨終生,但他們的困境并非無解,政策和社會(huì)環(huán)境大有可為,有些并不復(fù)雜的調(diào)整,足以改變?cè)S多人的一生。
“很多家長連閱讀障礙這個(gè)詞都沒聽說過。”
閱讀障礙,又譯為失讀癥或讀寫障礙。給家長講座時(shí),李虹(北京師范大學(xué)教授,她的研究團(tuán)隊(duì)正在為閱讀障礙兒童提供干預(yù))會(huì)刻意避免“癥”或“障礙”的提法,改稱“閱讀困難”,以免觸及他們的痛處。
閱讀障礙的具體表現(xiàn)不一,有些人眼里看到的文字?jǐn)D成一堆,可能會(huì)閃爍不定,還有人形容看字的時(shí)候“有一股力量把眼珠子往外拽”。他們認(rèn)字會(huì)看漏看錯(cuò),寫字增減筆畫、顛倒部件。
在西方,閱讀障礙的研究已有上百年歷史,但漢語研究從1980年代末才開始起步。很長時(shí)間里,外國學(xué)者以為漢語并不存在閱讀障礙,他們認(rèn)為看漢字就像看圖,不會(huì)有形音對(duì)應(yīng)的困難。1982年,心理學(xué)泰斗張厚粲去美國訪學(xué),有一次作完報(bào)告,有人站起來提問:中文有沒有閱讀障礙?她只能說,“我們還沒有做過系統(tǒng)的研究,現(xiàn)在還不能回答你。”
北京師范大學(xué)教授舒華是研究漢語閱讀障礙最早、最權(quán)威的學(xué)者之一。她做過好幾次涉及幾千人的大規(guī)模篩查,最初的比例就很驚人。如果一個(gè)孩子有正常的智商和教育機(jī)會(huì),排除情緒和動(dòng)機(jī)等因素,若閱讀能力明顯比同齡人落后,可以認(rèn)定為閱讀障礙。
兩三代學(xué)者的研究證實(shí)了漢語閱讀障礙的存在,并且它的發(fā)生率和其他語種基本相似。香港和臺(tái)灣地區(qū)也確認(rèn)了閱讀障礙的存在,逐步建立了針對(duì)性的特殊教育系統(tǒng)。但在內(nèi)地,一切尚處于起步初期。
如果一位家長懷疑孩子有閱讀障礙,可以尋求的診斷渠道屈指可數(shù)。李虹只能推薦家長去北醫(yī)六院,該院應(yīng)用北師大團(tuán)隊(duì)開發(fā)的測驗(yàn)題,是為數(shù)不多能為閱讀障礙提供明確診斷的機(jī)構(gòu)。“很多家長連閱讀障礙這個(gè)詞都沒聽說過。”
兒子校校診斷出注意缺陷與多動(dòng)障礙(ADHD)之后,李綠壇沒打算瞞著他,“你的大腦和多數(shù)小朋友不一樣。”“那……我會(huì)死嗎?”“不會(huì)不會(huì),你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容易控制不住自己。”
之后她覺得越來越不對(duì),就算是多動(dòng)癥,分?jǐn)?shù)也不至于這么低,一共就學(xué)那么幾個(gè)字。在疑惑中度過了一年半后,李綠壇帶校校在北醫(yī)六院確診了閱讀障礙。
拿到診斷后,李綠壇感到釋然,“不知道怎么回事是最難受的,影響不影響他的生長?他會(huì)不會(huì)變傻?你一旦知道這事,你就不怕了。”
有些家長在孩子確診后不愿讓孩子知道,李綠壇理解這種心態(tài)。“孩子不一樣,如果孩子比較敏感,對(duì)這件事情很介懷,你公布出去,不是給他增加負(fù)擔(dān)嗎?”
診斷與訓(xùn)練需要整個(gè)社會(huì)支持體系
確診之后,家長都會(huì)問王久菊(北京大學(xué)第六醫(yī)院助理研究員)該怎么辦,她會(huì)指明一條簡單的路:假如孩子不只有閱讀障礙,有其他精神或心理問題,掛兒童精神科,藥物治療;假如是單純的閱讀障礙,她會(huì)推薦相熟的大學(xué)研究團(tuán)隊(duì),嘗試干預(yù)的實(shí)驗(yàn)。
“通過訓(xùn)練是可以提高的,他固有的一些缺陷到底能不能治愈?可能不那么容易,一旦有就終身伴隨。但是可以克服,可以想辦法去拿一些高級(jí)的功能來代償它。”王久菊看過一位美國詩人寫的書——他有閱讀障礙,從小很難閱讀密密麻麻的字,只喜歡讀詩,后來成為優(yōu)秀的詩人。
李虹的團(tuán)隊(duì)為孩子提供五次干預(yù),每周一次,由她的本科生進(jìn)行輔導(dǎo)。“你可以理解這五次干預(yù)只是課程實(shí)習(xí),讓家長知道這件事情。你想,這些孩子在有些文獻(xiàn)中被稱為‘對(duì)教育沒有反應(yīng)的孩子,你提供五個(gè)小時(shí)、十個(gè)小時(shí)的訓(xùn)練,孩子就能怎么著了嗎?不可能的。”她非常坦誠地說,“想要幫助孩子,真的是需要很多的人力、時(shí)間、精力的投入,沒有靈丹妙藥的。”
很多家長寫信向她求助,希望讓孩子接受訓(xùn)練。李虹有強(qiáng)烈的無力感和愧疚感,“我只是一個(gè)做研究的,我知道你的孩子可能是需要幫助的,但是我提供不了這個(gè)幫助,就很不忍心。”
“首先什么人來做,要培訓(xùn)、去學(xué)習(xí),大多數(shù)人其實(shí)都不了解,愿意來做的人不多,還挺難的,就算有也幫助不到幾個(gè)人,我覺得再給我一個(gè)小朋友我都做不到了。”李虹的研究生羅明玥告訴記者,“我們每次看國外文獻(xiàn)里做的一些干預(yù)研究,有多少個(gè)研究者去參與干預(yù)、可以每周多少次,非常羨慕,我們什么時(shí)候能有這么多人?”
“它真的是一個(gè)很大的體系。”李虹認(rèn)為,閱讀障礙兒童的診斷與訓(xùn)練需要整個(gè)社會(huì)支持體系,“一定要有后面配套的干預(yù)與服務(wù)。”
“這太難理解了”
家長得知孩子是閱讀障礙后,北京市西城區(qū)融合教育中心教研員王玉玲遇到過兩種極端的反應(yīng),她認(rèn)為都不太妥當(dāng):一類就是放棄孩子的學(xué)業(yè),指望他找份不用文字的工作;另一類是對(duì)孩子抓得更緊了,逼迫他們學(xué)習(xí)。
王玉玲勸家長不要急躁。后來再給家長講課,她會(huì)先說閱讀障礙的優(yōu)勢,“你不要認(rèn)為孩子是閱讀障礙,他這輩子就毀了。毀你孩子的不是閱讀障礙,可能是環(huán)境和成人的誤解。”
事實(shí)上,很多閱讀障礙者成年后都能如常生活。張佳立在英國確診閱讀障礙的時(shí)候已經(jīng)為人母親,她學(xué)不好語文和英語,雅思考了八九次才過關(guān),一直覺得自己就是差。但她從小有美術(shù)天賦,有超強(qiáng)的視覺記憶能力,通過藝考順利進(jìn)入復(fù)旦大學(xué)。
她利用藝術(shù)設(shè)計(jì)的專長,設(shè)計(jì)了一種專門給閱讀障礙孩子的尺子,可以把上下文遮擋,讓人更專注在眼前的段落上。
很多閱讀障礙者成年后懂得利用各種策略,最終領(lǐng)會(huì)文字的意思。“這個(gè)詞不太知道,我就溜一眼看個(gè)大概,能夠獲得意義,意義理解是閱讀的終極目標(biāo)。他們會(huì)有很多策略,我們稱之為‘意識(shí)補(bǔ)償。”李虹解釋。
李綠壇的一位服裝設(shè)計(jì)師朋友也有閱讀障礙,她甚至做過一段時(shí)間文字編輯,讀字的精確性始終有問題,但只是慢于常人,不影響理解。
李綠壇身邊的每個(gè)家長各有各的憂愁,有的愁成績不好,有的愁孩子性格,有的孩子什么都好,家長又愁他不愛吃飯,怕營養(yǎng)不夠。她發(fā)現(xiàn)每個(gè)家庭都有困擾,“總有一款適合你”。
“我認(rèn)為他現(xiàn)在就是一個(gè)正常的小孩,閱讀障礙是他身上帶的一個(gè)特點(diǎn),我不想治愈他,也不想改變他。”李綠壇始終相信,閱讀障礙不值得大驚小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