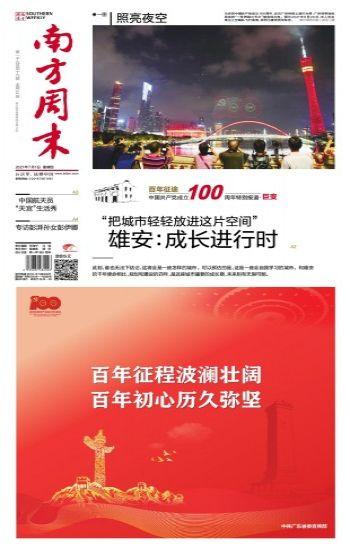“改造”宋陵
南方周末記者 王華震發自河南鞏義

宋哲宗永泰陵的“武士”石像,下半截埋進了土里。圖中的土堆子是原來皇陵中雀臺的遺址。
南方周末記者 ? 王華震 ?圖

永昭陵是復建的,永泰陵和永裕陵依然在田野里,其他是初步修復的。 馮慶超 ? 制圖
北宋帝陵不是景區,地下沒有“寶藏”,沒有抵達這里的旅游大巴,也少了旅行團的喧囂。農田和民居環繞著石像生長,農民耕種于帝陵的神道兩旁,石像的陰影供村民乘涼。神道對面村委會的家長里短,石像仿佛也能聽到。
康永波希望宋陵被更多人看到,但更多的建設與宣傳意味著宋陵的改變,這種微妙的矛盾考驗著當地人民與政府的智慧。
這一季的麥子收割完畢,露出了矗立在麥田里的石像的根部。麥子像是以年為周期的潮水,麥收時節上漲到這些高大石像的膝部。麥浪起伏,石像遠遠看去像被什么輕輕托起,麥子一割,它們又落到了地上。
一千年來,這些立于河南鞏義的石像,被植物的“潮汐”沖刷著。陸游的詩“京洛雪消春又動,永昌陵上草芊芊”,說的就是趙匡胤的永昌陵被荒草覆蓋的情景。
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將鞏義辟為帝陵區域,他的父親趙弘殷、弟弟宋太宗趙光義,以及太宗的后代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的八座陵墓,散落在鞏義的平原之上。皇帝陵附近,還祔葬有皇后、皇室宗親、包拯、寇準等勛貴大臣的上百座高等級大墓。每座陵墓的神道兩邊,依等級的高下立著不同的鎮墓石像,翁仲、瑞獸、武將、大象,1027件石像,讓面積近180平方公里的陵區成為一個露天的北宋石刻博物館。
多年以來,荒涼而富有“野趣”的北宋帝陵和其它朝代的帝陵有著明顯的區別。網絡上走紅的照片和短視頻,往往配著斜陽殘照、荒原石像,與其它被辟為景區供游人參觀的皇陵如秦始皇陵、明十三陵、清東西陵相比,別有一番歷史滄桑之美。
盡管也是“國保”,但北宋帝陵不是景區,地下沒有“寶藏”,沒有抵達這里的旅游大巴,也少了旅行團的喧囂。農田和民居環繞著石像生長,農民耕種于帝陵的神道兩旁,石像的陰影供村民乘涼。神道對面村委會的家長里短,石像仿佛也能聽到。
北宋滅亡之后,金人以及金人扶植的傀儡政權“齊”,都對宋陵進行了大規模、有計劃的地毯式盜掘。金元戰爭期間,宋陵再次遭到嚴重破壞,元人將陵區辟為農田,使人耕種其上。經此二劫,北宋帝陵的地面建筑基本被鏟平,地下隨葬品也基本被搶掘一空,帝陵徹底脫去了皇家陵墓的豪華氣派,成了平原上的荒塚——一座座高高聳起的大土堆子。只有神道兩旁的石像因為體量過大,盜運不便,才幸存至今。可以說,今日在鞏義看到的帝陵的荒敗景象,并不是今人保護不力導致的,而恰恰是某種歷史的見證。
1990年代以來,地方政府的多輪修復讓八座皇陵的面目變得參差多樣。近年來,民間保護之聲日隆,河南本地媒體多次呼吁對其進一步保護。2019年,地方政府對宋陵的保護與開發開始加速——帝陵周圍的農田陸續被政府征收,用于未來的“北宋皇陵遺址生態文化公園”的建設與開發。得到保護的同時,宋陵漸漸地脫去了往日的風貌。2021年的麥收季與往年有些不一樣。“政府不讓種了。”永昌陵的護陵人老孫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也許明年的麥收季節,就再也看不到“彼黍離離”的景象了。
護陵六百年
夏晝悠長,晚上七點鐘了,太陽還沒下去,暴曬了一整天的永昌陵石像,摸上去還是滾燙。老孫遠遠走來,夕陽把他的身影拉得老長。
老孫是來永昌陵換班的。從鞏義市區驅車,沿著永安路一直往南開10公里左右,便可以看到路邊掛著永昌陵的牌子。順著牌子朝西看,原野上兩排石像巍然站立,這便是永昌陵了。
鞏義位于洛陽盆地內的東北角、伊洛河與黃河交匯處,邙山余脈和嵩山余脈(當地人稱為青龍山)兩山夾峙,逼出一片緩緩向北面伊洛河河谷傾斜的坡面小盆地。
八座陵墓就散落在這個小盆地內:鞏義市區里,被民居和高樓環繞的,是仁宗永昭陵和英宗永厚陵。市區往南5公里,是真宗的永定陵;再往南5公里,是滹沱村,村里有宋太宗的永熙陵,往東南走十幾分鐘,就是永昌陵和趙弘殷的永安陵。滹沱村再往西南四五公里,是八陵村,離市區最遠的神宗永裕陵和哲宗永泰陵就在八陵村。
老孫的值班時間是晚上七點到凌晨一點。帝陵的護陵人每天有四班,六個小時一班。上午、下午的兩班各一個人,晚七點以后的上半夜兩個人,下半夜一般有三個人。每個帝陵配有六七個護陵人,且每個帝陵旁邊都建有被稱為“保護站”的小房子,里面有簡單的寢具、巡視工具、對講機,供護陵人休息與工作。六小時的值班時間內,護陵人需要每小時巡回陵區一次,巡邏路線上有攝像頭和打卡點,打卡點上的設備會讀取護陵人的打卡,每月存檔。
這套24小時輪班巡邏的護陵制度,完善于2007年到2008年之間,但其淵源可以上溯到明代。歷經金元兩代的破壞和荒廢,到明朝建立時,陵區已經荒木叢生,明政府不得不下令禁止在陵區采樵。以驅逐蒙古人、恢復漢人正統自居的明朝,對待宋陵的態度自然與元人不同,他們分撥附近民戶專門看守陵區,形成了一套較完備的護陵制度。后來的清政府繼承了這套制度。老孫的家就在離永昌陵不遠處的滹沱村,他和其他護陵人一樣,也是受當地政府征召來護陵的。
護陵人有干得久的,也有新來的。永泰陵的護陵人老曹已經守了五年多,平時自己種地,護陵是兼職。永定陵的小趙則才來幾個月,小趙還年輕,覺得這份工作無聊,錢少。“一個月才一千多塊錢。”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除了要多觀察周邊土地有無盜洞,每年麥收季節,也是護陵人們最忙的季節。“收割的時候要特別看著,不能讓機械碰著石像。”老曹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原則上明年開始,地里就不讓種莊稼了。但還是要看政府和老百姓的土地補償協議。協議達成了,就不種;達不成,老百姓就繼續種。”
哪種風貌更適合宋陵?
翻看幾年前網友拍攝的永昌陵照片,與現在看到的陵區景象差別很大。永昌陵已經不再是老照片里淹沒于麥浪中的樣子了,陵區內的農田現在已經被黃土覆蓋,成為砂土平地。
2021年5月份,很多網友發現一些陵墓正在進行土地平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官方微博做過回應:“目前所開展的工作是當地根據河南省文物局批復過的方案進行環境整治。此項工作的主要內容是對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因農業生產平整土地導致的原始地形變化進行恢復。”
整個永昌陵陵區從周圍的麥田中分割出來,神道兩頭都有平整道路施工的痕跡,“土地平整是從2019年開始做的。你看前面那頭石獅子,基座也正在慢慢挖出來。”順著老孫所指的方向,可以看到一頭被鐵皮圍起來的石獅子。陵區周圍是新種的成排小樹,用以區隔周圍的農田。永昌陵最后要變成什么樣子,老孫也說不出來。
事實上,如果現在還想要拍到麥田中的石像,只能去離市區最遠的神宗永裕陵和哲宗永泰陵了。其他各個宋帝陵的保護狀態各不相同,這反映了這些年來宋帝陵保護走過的曲折道路。
鞏義市區原本很小,現在位于市區的永昭陵與永厚陵,1980年代之前其實都位于郊區。“我記得小時候鞏義很小,帝陵都在郊外。”鞏義的一位網約車司機對南方周末記者說。1982年,宋陵被國務院確定為第二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開啟了此后四十年的保護之路。
1990年代,隨著鞏義城市建設的加速,威脅到離市區較近的永昭陵,1993年5月,國家文物局下發《關于鞏義市北宋皇陵緊急搶救維修工程方案的批復》。同年6月,河南省文物局同意對永昭陵、永定陵進行整修、完善。經過幾年的建設,1997年,位于鞏義市區的永昭陵按古建筑專家所考定的宋代皇陵原樣復建了地面建筑。永昭陵也是目前唯一完成了地表建筑復原的一座宋帝陵。
2013年,鞏義市投資一千多萬元,對帝陵進行了新一輪的修復。當時的修復重點是永昭陵的祔葬皇后陵、永熙陵和永定陵,它們在這輪修復中鋪裝了神道地磚。
永熙陵正好位于滹沱村的正中央,對面就是滹沱村村委會。陵區周圍的土地已經被民房占滿,鋪好地磚的神道恰好成了村里的休閑小廣場。南方周末記者到達永熙陵的時候正好是傍晚,村民們在神道上散步、在石像下乘涼,兒童在石像的肚子下嬉戲玩耍,一派居民與文物和諧交融的景象。也許在所有的古代王朝帝陵中,永熙陵也是和周邊住戶的生活聯系得最為緊密的一座。
2019年,河南省提出要打造“沿黃國家大遺址公園走廊”,宋帝陵是規劃中核心部分,針對它的修復與開發再次提速。除2019年對永昌陵內的地面進行平整之外,這一輪開發的重點是位于鞏義市區的另一座帝陵——永厚陵。南方周末記者于6月下旬走訪永厚陵發現,目前整個陵區被鐵皮圍欄攔起,內部正在施工,挖掘機、運輸車絡繹不絕,“開工有兩個多月了,將來也要建成一座遺址公園。”北宋皇陵管理處的工作人員王小博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河南地方政府的多輪修復,給八座皇陵留下了不同的面貌:大致保留了元代之后風貌的永裕陵和永泰陵、地面用砂土做過平整的永昌陵和永安陵、鋪了地磚的永定陵和永熙陵、完全復建了地面建筑的永昭陵,以及目前正在大興土木的永厚陵。大致可以分為三種不同的風貌:復建的、初步修復的和依然在田野中的。
由于整個宋帝陵區域面積極大,墓葬眾多,且與后代的民居建筑的關系極為復雜,對陵區進行整體的保護與修復,顯然在財力上并不現實,修復只能一步步來。2017年河南省政府公布的《宋陵保護總體規劃》,其中對保護資金的來源表述為“主要來源于地方各級財政專項撥款,呈平緩增長趨勢”。
到底哪一種風貌更加適合宋陵的保護與開發,網友們莫衷一是。宋陵考古隊前隊長、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院長孫新民拒絕了南方周末記者就這一問題的采訪。河南省文物局官網上的一篇文章《建設遺址生態文化公園,鞏義北宋皇陵如何煥發新生機?》介紹了每座宋陵未來都要建設成為“遺址生態文化公園”,卻沒有給出未來每座公園的風貌區別和建設時間表。可以肯定的是,大規模建設已經走上軌道,夕陽殘照的滄桑之美或許終將逝去。
“宋陵一直是委屈著的”
更嚴密的保護確實讓“國保”變得更加安全。21世紀初,當時的帝陵還沒有嚴密的巡邏制度。“也有人看著,但不重視。”老曹說。2005年1月26日和同年5月26日,一年之內永昌陵連續發生了兩起陵區石像被盜案,三尊石像不翼而飛,震驚了當地文物部門。當時警方輾轉十余個省市,才破案將石像追回。
這兩起大案讓文物部門痛定思痛。盜竊案發生前,整個陵區180平方公里只設四個保護房,每個保護房只有兩個護陵人,根本無法周全看護。2006年,鞏義成立北宋皇陵管理處,全面負責宋陵的文物保護、文物安全。前文所述的24小時巡邏制度也在此后漸次鋪開,護陵人逐漸增多到上百人。
2018、2019年,又發生了兩起盜墓案,這次因為護陵人的及時發現,盜賊沒有成功。老孫的家在永熙陵附近,他和南方周末記者講起那次戲劇性的抓捕過程。2018年底,一位護陵人在離永熙陵的祔葬皇后陵很遠的地方發現了一個洞。“那個洞離永熙陵有幾百米遠,打下去很深,有三四十米。”老孫比劃著當時的情景,他認識那位護陵人。警覺的護陵人懷疑是盜洞,立刻報警,警察趕到的時候,盜墓賊還在洞里沒有出來,警民配合給他來了個甕中捉鱉。“弄住了!”老孫用河南話說。
2019年1月5日,同一伙盜墓賊的其他成員不死心,再次來到永熙陵,企圖利用原先的盜洞再下去一次。“因被巡查人員發現,嫌疑人留下作案工具逃竄。”當時鄭州警方的官方通報這樣寫道。1月9日,這個盜墓團伙一共16人全部落網。
不同風貌的帝陵所面對的“受眾”可能也不一樣。永熙陵與身邊的村民相伴相守,已經成為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復建的永昭陵,門墻巍峨,神道肅穆,四方的雀臺和乳臺飛檐斗拱,頗有古色,面對的是來鞏義一日游的游客;維持原風貌的永裕陵和永泰陵,盡管離市區最遠,但慕名而來者并不比修復過的永昭陵少——他們可能是一群更加愿意跟隨潮流的人。
南方周末記者到達永泰陵時,遠遠看見田間小路上停了多輛越野車。陵區內,長槍短炮、三腳架、無人機,各類裝備發出的機械聲蓋過了野鳥的鳴叫。幾個衣著鮮艷的人迎風手舉絲巾,在石像前擺出各種姿勢——一條短視頻立馬生成。
“喂!不能開無人機,你們快走,有監控的!”老曹看到一架無人機飛得久了,跑過去趕人。“有規定不能拍照的,更不用說無人機了。”老曹苦笑著說,但每天來拍照的人太多,護陵人根本管不過來,只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看見太過分的無人機,就去趕一趕。
“不讓拍照,是怕盜墓的來踩點。”老曹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從無人機上也能對帝陵的風水布局一覽無余。
帝陵都是坐北朝南,地勢卻是南高北低,這使得宋帝陵變得有些奇特。進入陵區,就是逐級而下的坡道,神道兩旁的石像,越往北海拔越低,以致現在很多石像的半截身子都埋在了土里。鞏義市博物館里復原的永昌陵模型,還原了宋帝陵的這種特殊的地勢。風水學家們對此各有解釋,但再好的風水,也擋不住時間的侵蝕和異代鼎革的破壞。“咱也說不清它有個啥風水,總歸是好風水。”老孫笑著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學術上與宋陵保護相關的研究也起步較晚,南方周末記者搜索到的關于宋陵開發與保護的論文,較早的為康永波于2013年發表的《北宋皇陵文化遺產及其保護》。當時康永波還是中國地質大學的碩士生,暑假和同學赴鞏義走訪調研之后寫了這篇文章,“其實文章中很多觀點都是導師孫克勤給我的。”康永波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現在他已經是一位河南鄉鎮基層干部。
孫克勤教授是中國地質大學研究文化遺產的專家,針對宋陵面臨的問題,他在論文中給出了“引導民眾參與”“設立宋陵保護基金、引入社會資金”等建議。盡管這幾年一直忙于工作,對宋陵的關注不像學生時代那樣強烈,但康永波“總感覺在文化遺產領域,宋陵一直是委屈著的”。他希望宋陵被更多人看到,但更多的建設與宣傳意味著宋陵的改變,這種微妙的矛盾考驗著當地人民與政府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