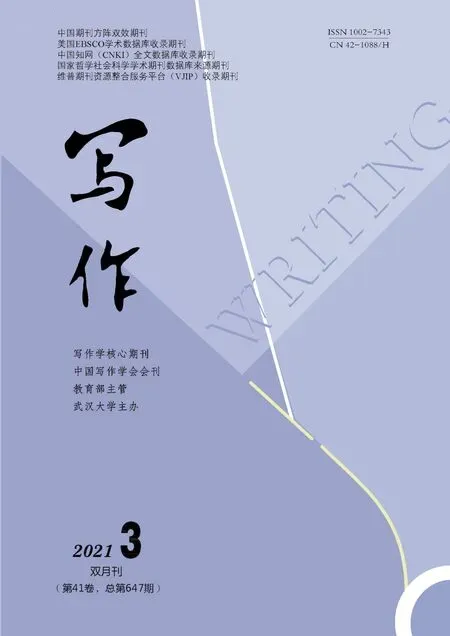主題式寫作:一種大學學術寫作課的教學模式
李成晴
21世紀以來,高等教育界展開了以通識教育為焦點的教學改革實踐,并于近年漸漸尋得一條切實可行的貫徹通識教育理念的路徑,那就是在大學第一學年的“窗口期”開設主題式寫作課(First-year Composition,簡稱FYC)。清華大學開設有“寫作與溝通”課,湖南大學開設有“寫作與表達”課、南方科技大學開設有“寫作與交流”課、中國傳媒大學開設有“寫作與語言藝術”課、中國科學院大學和浙江農林大學開設有“大學寫作”課——盡管課程名稱互有差異,各高校的教學團隊卻都不約而同地采用了“主題式”的寫作課教學模式①朱垚穎:《高校主題式寫作教學的發展現狀與影響研究——以普林斯頓大學、哈佛大學與清華大學為例》,《寫作》2020年第6期。。在大學普遍以學科教學、專業劃分作為教育模式主體架構的狀況下,主題式寫作課回應世界頂級大學“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ity)的教育共識,跳脫出了某一具體學科的藩籬,也揚棄了“大學語文”堂上作文課的既有講授模式,從而為“無專業門檻,有學理深度”的研究性、分析性、說理性寫作教育提供了有力支撐。
一、何謂“主題式寫作”
有一個基本但容易被忽視的事實是,語言文字無法剝離所承載的內容而獨立存在。因此,只要是進行寫作,都會自然帶有一定的主題。“主題式寫作”脫胎于“主題式學習”,這一學習理念“以活動、專題及解決問題等方式作為學習的主軸,強調的是在‘做中學’的學習方式”①珊丹:《基于主題學習的“應用寫作”課堂教學改革研究》,《中國電力教育》2013年第17期。。“主題式寫作”是一種教學模式,同時也是一種學習方式。通過整合相關學習資料,拓展、開發與主題相關的活動,如小組研討、辯論、文字寫生、戶外游學等,讓學生充分浸潤于某一主題內容中,從而使得這一主題的內容伴隨學生的寫作全過程,打下烙印。從課程產出來看,在對主題內容深度了解的基礎上,學生更有興趣,甚至也有一種基于學術研究的責任感,去完成一篇有深度的分析性寫作。
“主題式寫作”是歐美各大高校幾經探索、比較而最終選定的相對成熟的寫作課教學模式②陳樂:《寫作研討:普林斯頓本科生的“前學術訓練”》,《教育發展研究》2018年第17期。,也是“以內容為依托”的教學觀念最具代表性的模式之一,其教學法經由“莫里遜單元教學法”發展而來。莫里遜認為,在一個主題教學單元中,可循探究、提示、理解、推理、表述五個步驟,將以問題為中心的教學法、系統講授的傳統教學法合二為一③玲如:《莫里遜單元教學法》,《上海教育科研》1985年第5期。。“主題式寫作”關注寫作過程的體系性,是以主題為載體,以具體的寫作任務的完成為途徑的教學模式,試圖通過主題的建構和具體寫作任務的匹配來訓練學生的思維能力和寫作表達能力。寫作課主題的大類,包括但不限于人、自然、藝術、文化、政治、歷史、倫理、科技等各個方面。以普林斯頓大學寫作研討課為例,他們每一學期會為學生開出結構、性別、傳染、教育公平、糧食、人工智能、游戲等幾十個寫作課的研討主題④段勇義、楊萍:《重構寫作課——普林斯頓大學寫作課程體系的路徑和啟示》,《寫作》2020年第4期。,學生任選一主題,然后在每周兩次80分鐘的會面中就這一主題涉及的可爭辯性話題進行研討。這樣的研討,更關注寫作的過程,期待通過全過程研討讓學生接受調查、論證的基本訓練⑤張偉:《跨學科教育:普林斯頓大學本科人才培養案例研究》,《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4年第3期。。
從普林斯頓大學的寫作研討課經驗看,主題框架下的知識形態和研究形態是在寫作的探索中不斷形成的,體現了寫作的實踐性和綜合性。很多主題如游戲化、數字人生、傳染病、懷舊、政治、迷人的動物、超越邊界的正義、愛情與社會變遷、公共問題、碎片化的過去,都具有橫向和縱向的可延展性。在充分發揮學生作為寫作主體的能動性的同時,教師在開設課程之前確定總主題之下豐富多樣的子話題,子話題情境的建構由師生共同參與完成。同一寫作課主題的不同班級,會根據學生的參與度與認知度,建構出不同的主題任務,個體獨立、同伴協作,推進寫作過程,“為價值塑造和能力培養提供生動場景”⑥梅賜琪:《遵循三大規律的通識教育課程思政模式創新——以清華大學“寫作與溝通”課為例》,《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21年第3期。。以清華大學“西南聯大”主題寫作課為例,經過寫作研討和子話題分析,學生能夠從這一主題里挖掘出多層面的問題意識,例舉如下:

表1 清華大學“西南聯大”主題寫作課論文選題表
由上可見,在“西南聯大”主題寫作課上,一位工科學生的興趣點可以落在民國時期白話新詩對古典詩詞的“拋棄與重拾”,而一位文科學生也可以去研究民國時期聚集在大普集地區的高等科學研究機構。這樣的“主題式寫作”,對于學生來說可謂“無專業門檻,有學理深度”。誠如有學者已經研究指出:“按照建構主義教學設計的一般流程,在確定教學目標及效果后,應創設盡可能真實的、與所學知識‘主題’相關的情境。”①曹柳星、賀曦鳴、竇吉芳:《“新工科”視角下的“課程思政”實踐——面向理工科專業本科生的主題式通識寫作課設計》,《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1年第1期。主題式寫作首先解決的是“如何提出一個好問題?”在課程中,圍繞問題意識、問題情境,可以將總體的寫作訓練分解成一系列與主題內容有關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寫作任務,這些任務之間彼此關聯,在反復性、層次性中,訓練寫作思維。總的來看,主題式寫作對特定主題的多角度聚焦,能夠有效避免零散研究、散點思考所造成的泛化、不深入的問題。
二、以主題接引通識:中外高校寫作課的共通路徑
主題式寫作課,同時即是一門普適的通識教育課;以“主題”為抓手,進而接引通識性的觀點、技能和素養,在國內外寫作課建設中已達成共識。盡管通識教育理念人言言殊,但有一些目標是有共識的,比如引導受教育者的自我提升、群己并進,綜合各學科知識解決問題,對世界和社會的歷史和現實問題給出理性的分析和解決方案等等。在美國,“學科寫作”與“跨課程寫作運動”(The Writing Across the Curriculum Movement)如同兩翼,都受到了教育界的重視,標志性案例如全國英語教師理事會(NCTE)的建立、因杜威而激發的20世紀30年代的課程運動、海灣地區的寫作項目等等。平心而論,跨課程寫作的聚焦點不在寫作,而在“通過寫作改善學習”②[美]大衛·R.羅素:《寫作的歷史性研究》,[美]彼得·司馬格林斯基編著:《多元視角下的寫作研究:20年變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374頁。,培育大學生作為獨立成人、當代公民的基本素養。相似的,主題式寫作在展開形式上也屬于跨課程寫作,其志趣并不局限于寫作技巧的引導,而更是價值塑造、能力培養與批判性思維訓練的過程,更是“受過通識教育的人所應具備的一個特質(Hallmark)”③陳樂:《理念與實踐:耶魯大學通識教育寫作課之理性探析》,《比較教育研究》2019年第1期。。
(一)“我發現”
在歐美的學術寫作(Research Paper)課堂上,教師會指導學生撰寫一種被稱作“我發現”(I-search)的文章:“我發現”性質的論文,出發點是學生自己的興趣和關切,而非這一領域的專業知識,“‘我發現’不同于專業學術論文那種在別人發現成果基礎上的‘再發生’(Research),它以‘我’而非‘我的專業’需要知道什么為求知動力。”④徐賁:《學會“公共說理”寫作》,《華夏時報》2012年8月9日第23版。在這個意義上,“我發現”式的研究性寫作,能更加突破專業藩籬。寫作者在一段時間內,關注的是一個點線面結合的立體主題,經過持續的、有深度的閱讀與思考,可以對該主題內部一系列問題得出看法或見解。在此基礎上,寫作者在小班課堂上,通過小組研討,淬煉問題意識,進而提出一個既精準又有深度的問題,從而掘井及泉,轉入“深而窄”的問題式寫作。圍繞“解決一個問題”而展開的寫作,具有較強的研究目的性,調研、分析、結論都圍繞著解決這個問題點本身,而這個問題點一旦得到解決,則對于寫作者本身而言,即意味著認知、能力邊際的突破,更會使得寫作者體會到一種基于“卡里斯瑪”特質的激勵。
(二)批判性思維的錘煉
博雅教育、通識教育的理念在現代大學精神的導向下產生、發展,其訴求和實踐模式也在不斷調整。康德對大學的詮釋是“大學是學術共同體,它的品格是獨立追求真理和學術自由”①轉引自劉道玉:《珞珈野火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9頁。;杜威則在《我們怎樣思維》中提出要以反省思維作為教育的目的(反省思維包括:引起思維的懷疑、踟躕、困惑和心智上的困難等狀態;尋找、搜索和探究的活動;求得解決疑難、處理困惑的實際辦法)。在杜威提出反省思維的理念之后,美國批判性思維研究興起,成為教學改革的核心問題,更有許多教育者將批判性思維看作通識教育最具內核屬性的效能之一,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也被認為是所有其他學術素養的基礎。
同時也應該注意到,作為通識教育核心板塊的批判性思維,其培養方式是多元的。美國教師聯盟發布的《批判性思維的目標:從教育理念到教育現實》也明確提出“不存在教授批判性思維的唯一正確方式”②Debbie Walsh and Richard W.Paul.“The Goal of Critical Thinking:from Educational Ideal to Educational Reality”[EB/OL].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 Washington,D.C.1986.http://www.eric.ed.gov/PDFS/ED295916.pdf.2010-09-30.。實際的教學探索中,單獨開設批判性思維課程和將批判性思維訓練植入通識教育課程中,這兩種模式也一直并存。主題式寫作課是批判性思維訓練的另一條路徑。在主題的研討和實際寫作中,解釋分析問題、論證反駁觀點等,都是對批判性思維的反復操練。寫作以“公議”為倫理自律,守持“理性標準”③武宏志:《批判性思維的靈魂——理性標準》,《邏輯學研究》2016年第3期。,在思考和研討中“理性地省察”,本身即是批判性思維養成的過程。同時,思維過程的重復學習也是一種方法論的內化,可以讓學習者學會知識之外的通用能力,在對議題邊界的不斷探索中,形成對待通識的理性態度。
(三)公民教育的起點
有邏輯、有論證的主題式學術寫作,是現代公民應具備的基本素養。麻省理工學院的寫作課理念認為,所有的學生,“不論他們未來選擇哪個學習領域,學會寫清晰、有組織、有效的文章,并把事實和想法整合成為令人信服的書面和口頭陳述應該成為每個人所具備的基本能力。”④王小芳、鄧耿:《美國大學寫作課項目調研及借鑒——以普林斯頓大學為例》,《高等理科教育》2019年第3期。主題式寫作課同時也是一種教養教育,師生在工作坊式的課堂上,不帶有任何功利色彩地去研討人性、倫理自覺、政治責任感、社會參與等各方面問題,其實正是一種公民教育的良性生態。在教育家歐內斯特·博耶(Ernest L.Boyer)看來,在大學求學有稻粱謀的動機無可厚非,不過“大學教育也是大學生們尋求認同感和生活意義的重要時期”,不應忘記“公民的和社會的責任感”⑤[美]歐內斯特·博耶:《關于美國教育改革的演講:1979—1995》,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以韓國慶熙大學為例,本科生必修的基礎課程有四門,分別是“寫作Ⅰ”“寫作Ⅱ”“大學英語”“公民教育”,其中,兩門寫作課程均是主題式寫作課,主題“自我”“世界”的選定,實際與公民的培養目標相結合,前者“目的在于發現和完善自我以及重新定位自我與他人的關系”,后者“目的在于發現不完美的世界和培養批判性的思維方式”。慶熙大學“人類的價值探索”的主題式寫作課,“融合了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等學科領域,通過學習使學生理解、反思和探索一些基本問題,比如,人類如何在悠久的文明發展史中探索和追求價值,哪些是人類重視和追求的價值,等等。最終,引導學生獨立思考和回答‘對我們個人而言重要的價值是什么’這一問題。”慶熙大學不是個例,在韓國,教育界已經達成這樣的共識:“大學不是公民教育的終點,而是真正意義上公民教育的起點。”⑥梁榮華:《基于融合理念的韓國大學公民教育課程研究》,《黑龍江高教研究》2017年第9期。在19世紀30年代,美國教育界把寫作引介為“大覺醒”(Great Awakening)的一部分⑦[美]大衛·R.羅素:《寫作的歷史性研究》,[美]彼得·司馬格林斯基編著:《多元視角下的寫作研究:20年變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相比較而言,中國教育在寫作層面的“大覺醒”,則與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以來對白話文啟蒙作用的預期是車輔相依的。
三、“寫作小組”中的研討與寫作
(一)研究性寫作為主體的課程產出
1984年,博林出版了第一部關于19世紀美國大學的寫作教學研究的著作。在書中,博林探討了哈佛大學寫作課的起源,“將其哲學性地定位于一種‘科學主義’的方法——實證主義。”①[美]大衛·R.羅素:《寫作的歷史性研究》,[美]彼得·司馬格林斯基編著:《多元視角下的寫作研究:20年變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383頁。由此可見,與文學創作不同,主題式寫作注重“實證性”,只有在研究性學術活動深耕過的土壤中才能抽枝開葉,這類學術活動包括研究性閱讀、全過程小組研討、說理性學術寫作等方面。
在某種意義上,寫作對閱讀具有“倒逼”性影響。在文本閱讀過程中往往會產生寫作的沖動,而寫作中又經常會發現自身知識結構上的缺陷,需要實時閱讀相關書籍來補強。長期關注一個寫作主題,在這個主題領域進行閱讀、思考,會在全面掌握研究進展的基礎上培養提出前沿問題的能力。學術寫作是將研究性閱讀、批判性思考以及小組研討的收獲構建成自己的框架性見解,并進而呈現為分析性、說理性的寫作產出。“大學語文”中的寫作,是讓學生將已有的思想見解通過文章表達出來,并不是要求學生通過寫作生發此前沒有過的新思想。主題式寫作則不同,要求的是學生通過對特定主題的系統性研究,有效地形成框架性思考,提出新知新見——這既包括學生自身知識儲備之外的新知,也包括相關主題既有研究之外的新發現和新突破。寫作是創造性活動,除了語言和篇章,更體現為思維的方式和能力,研究性寫作在文章內容和表達方式整體構思基礎上,注重學生思維能力的訓練和外化,培養學生經過充分地分析、比較以及綜合的過程,突破思維定式,產出多元化多樣性的寫作成果。
另外,對大一新生來說,主題式寫作課也是學術精神、學術規范意識的啟蒙第一課。從教學規律來看,“從文心培塑、技能學習、習慣培養三個層面循序漸進,經歷‘自由——規范——自主’三個階段。”②張海兵:《“階梯式寫作教法”攻略》,《江蘇教育》2013年第13期。由學術精神、學術規范進而探究學術倫理與學術擔當,則會進一步與現代公民教育理念相融匯,共同助力梅貽琦所論述的“大學新民之效”③梅貽琦:《梅貽琦談教育》,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4頁。。
(二)交互式課堂的貫通
學術寫作無法完全憑才華和靈感完成,而是需要一定的知識儲備和學術史文獻調研基礎。開展主題式寫作教學,前提便是規劃好一定閱讀量的文獻進行浸潤式研讀。對通識教育理念而言,讓學生“開眼”有著別樣的意義。具體到一門具有通識性質的主題式寫作課上,讓學生“開眼”,尤其重在讓學生見識這一主題領域中的優秀作品。寫作主題的體系化,會帶來文本閱讀系列化、聚焦化的好處。通過主題內文獻泛讀、核心文獻精讀,在積累寫作素材、借鑒寫作方法的同時,也是對通識素養的一次歷練。
主題式寫作課堂,最適合以8-16人的小班模式展開寫作研討,或稱作“工作坊”,或稱作“寫作小組”。區別于傳統大班講授式課堂,在小班研討課堂中,師生之間的交互,不同專業背景學生之間的交互,以至師生與主題之間的交互,都處于一種對知識邊界和問題意識的全新探索狀態之中。在交互的影響中,主題寫作與不同的學科產生聯系,與通識的普遍性問題產生聯系,更為重要的是建立個人與主題的差異化聯系。同時,在“寫作小組”中,寫作成為一種同向同行,可以避免“獨學無友”的孤獨感,尤其能夠預防“語言焦慮”(Language Anxiety)的萌生。習作完成,寫作小組又可以互相評改,收到“他山之玉”的多重效果,誠如葉圣陶所論:“教師修改不如學生自己修改,學生個人修改不如共同修改。”①杜草甬:《葉圣陶論語文教育》,開封: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30頁。
在主題式寫作課堂上,教師重視寫、作融合,強調通過實踐活動中的溝通和互動來交流思想、激發問題意識。具體的課堂展開方式方面,則交替應用以老師為主體的直接教學法,以學生為主體的合作學習法,及以情境為主軸的體驗式教學法、主題式教學法等,冀望以較具創意的教學策略,透過不斷提問與探索,并藉由小組分工、討論、報告等方式,培養群己關系,激發其思考創造的能力。還有多所學校的寫作課會在課外建設在線交流平臺,并依托平臺舉辦讀書會、下午茶等活動,作為課堂教學的補充。在師生、生生工作坊式的寫作研討中,學生可以體會彼此之間的依存、需要以及社群生活所帶來的認同感和傳承使命感。
主題式寫作一般無法像命題寫作那樣當堂完成,而是需要一個長時段、多階段引導的過程。在整個流程中,教師仍應發揮著引導、講解、澄清概念、提供例子、提問、回饋、再分析、總結的職責。在這個大原則之下,教師宜時刻注意保持“權力”的界限,將研究的自由度交予學生,讓學生圍繞自己的經驗、環境中的事物進行寫作,這正合于布朗森·阿爾科特(Bronson Alcott)所倡導的“自我主動”(Self-active)的寫作課教法②[美]大衛·R.羅素:《寫作的歷史性研究》,[美]彼得·司馬格林斯基編著:《多元視角下的寫作研究:20年變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383頁。。
(三)寫作工作坊的意義
寫作工作坊(Writing Workshop),通過工作坊的形式合作學習寫作,利于尋求幫助與相互啟發,削減寫作之旅中踽踽前行的孤獨感。對于思維、心智的訓練,天然地要求課堂不能成為“一言堂”,而是需要師生、生生之間的深度互動。寫作坊更強調寫作的現場感,強化寫作實踐能力的培養和提升。因此,小班化的以工作坊為樣態的課堂形式,是主題式寫作課開展的制度保障,這包括師生問答式地打磨問題意識進而提出一個好問題、小組頭腦風暴梳理文本框架、協作式查閱文獻以核驗觀點、同輩文章互評等。這樣“組織”與“一連串的環節”,將寫作活動以一種較為輕松、有趣、高效的互動方式串聯起來,成為一個系統化的過程,具有了可重復操作的流程。
國內外高校的寫作課教學,在寫作工作坊的實踐方面已經積累了一定經驗。在工作坊的人數和分組上,清華大學寫作課課堂上限16人,以4人為小組;王召強在《主題寫作十二課》中也主張“以四人為一合作性學習小組”③王召強:《主題寫作十二課》,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4頁。;而美國高校的寫作課一般不超過12人,甚至很多小班課堂在10人以下。康奈爾大學有著統一的要求,“各個課程班必須有充足的課堂時間(大約一半的時間)用于直接的寫作指導與實踐”④莊清華:《“大學語文”或可向“學科寫作”轉型——以美國康奈爾大學的FWS為借鑒范例》,《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5期。,并且,至少要有3篇論文是在教師指導下完成,包括修改、同學間互評、回應閱讀、分析研討等。
在工作坊中,老師當面指出學生寫作的得失,學生可以即時性地進行補充說明,從而更好地增進師生的溝通了解,實現梅貽琦《大學一解》所論“從游”之精義,“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工作坊中的學生,由自由選課而匯聚,自然而然就具有了跨學科性質,這種基于跨學科的學術論辯,在淬煉學生思維、邏輯與表達的同時,也涵泳一種從容的氣度、對不同觀點的尊重以及尋求共識的研判力,進而涵育一種共同體意識。普林斯頓大學的寫作課,從制度設計層面也有著這樣的期待:為學生提供盡早融入活躍的學術社區(Lively Academic Community)的機會,在緊密的學術社區(工作坊)——整合學者、教師、學生在內的知識群體,組成學術共同體,一起討論,一起寫作①Princeton University.General Education Requirements[EB/OL].https://odoc.princeton.edu/curriculum/general-educa?tion-requirements,2017-10-26.。
四、余論
早在軸心時代的東西方,寫作能力都已很受重視,比如孔子曾提及撰寫文章的謹嚴程序說:“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②劉寶楠:《論語正義》第17卷,高流水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560頁。據古迪的研究,“在古希臘寫作作為一種技能”,并且讀寫能力被引介為一種口頭文化③[美]大衛·R.羅素:《寫作的歷史性研究》,[美]彼得·司馬格林斯基編著:《多元視角下的寫作研究:20年變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373、388頁。。回顧中國近現代寫作教育史,其實在民國初期,已經有學者嘗試采用了“主題式寫作”教學模式。蔣伯潛《習作與批改》曰:“民國十年左右,劉大白諸先生在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教國文,選編的教材,便是以‘問題與主義’為唯一中心的論說文。”④蔣伯潛:《習作與批改》,劉半農等:《怎樣教作文》,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09頁。大約1917到1918年間,教育界已經引入了美國的設計教學法:“這種教學法是將實際生活的問題應用到教學上,打破科目的界限與論理的組織,分成若干教學單元,經過確定目標、計劃、實行、批評四種步驟去學習。”⑤周予同:《中國現代教育史》,陳學恂:《中國近代教育史教學參考資料》中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47-448頁。這種教法,在當日教育界的普遍觀感是“覺得很新”,實際上在今天看來也很具有超前性。因此,在當今大學主題式寫作課的建設過程中,也宜注意到傳統寫作教育的經驗和思考,秉持寫作教育史的研究姿態,激活可被當下借鑒的具有古典屬性的寫作教育理念。
最后值得思考的是,大一寫作課(FYC)的制度化設計是教授非文學的學術寫作,在同一教育階段,是否需要有意識地配置純文學的選修課呢?據大衛·R.羅素研究,在蘇格蘭修辭學家Blair等人的影響下,一類純文學(源于不論任何體裁中的“優美的文字”)的課程被系統開設,“既作為智力和道德品味的教育,又作為取得實用修辭技巧的方式”⑥[美]大衛·R.羅素:《寫作的歷史性研究》,[美]彼得·司馬格林斯基編著:《多元視角下的寫作研究:20年變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373、388頁。。因此,在踐行通識教育的歷程中,主題式學術寫作不會是唯一的訓練方式,只是一條在原理、方法、體系上接近“成熟”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