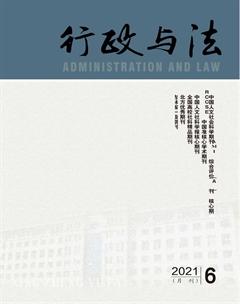民法典背景下補充責任裁判執行問題研究
馬登科 韓強
摘? ? ? 要:民事補充責任是非終局性的風險責任,是將債權人求賠不能的風險轉化為補充責任人因過失所承擔的追償不能的風險。補充的基礎在于先訴抗辯權,作用場域主要是強制執行程序,以順位性和窮盡執行為原則。實踐中對于突破執行順位原則的把握不統一,應以申請執行人與補充責任人間的利益平衡為重點,不能僅以公法上的執行困難為突破點。執行依據所附條件為強制執行開始之條件,條件成就前不得對補充責任人財產采取保全措施,符合執行前保全的除外。執行補充責任人的條件成就與否包含實體法因素,現行“異議+復議+執行監督”模式不足以提供充分救濟,救濟程序設計應兼顧效率與權利保障。
關? 鍵? 詞:補充責任;先訴抗辯權;執行順位原則;執行窮盡原則;財產保全
中圖分類號:D926.2? ? ? ? 文獻標識碼:A? ? ? ? ?文章編號:1007-8207(2021)06-0062-11
收稿日期:2021-04-02
作者簡介:馬登科,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民事訴訟法、強制執行法;韓強,西南政法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民事訴訟法、強制執行法。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國家治理體系中民事執行現代化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0&ZD195;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2021年學生科研創新項目“個人破產主義下參與分配的程序轉向問題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FXY2021119。
一、問題的提出
民事補充責任兼具實體法屬性和程序法屬性,是一種特殊的民事責任方式,以侵權補充責任和一般保證責任為典型代表。實體法學者對補充責任的概念、本質特征、理論基礎、責任范圍、追償權等展開了全面研究。程序法學者對補充責任與先訴抗辯權的關系、補充責任訴訟形態、補充責任人訴訟地位等也進行了有益探索,但從總體上呈現出一種實體重于程序、訴訟階段重于執行階段的研究局面。[1]
補充性是補充責任最鮮明的特征,也是補充責任與按份責任、連帶責任區分的關鍵。有學者將補充責任的程序問題劃分為訴訟程序的責任確定階段與強制執行程序的責任實現階段,并開始對補充責任的執行程序問題展開宏觀研究。[2][3][4]這些研究成果強調補充責任功能發揮的主要場所是執行程序,具有一定的進步性。同時,這些研究的重點是宏觀層面的概念及原則確立,缺乏更加具體的、系統的研究,不能提供充分的理論供給。當載明承擔補充責任的裁判文書進入到執行程序時,法院對補充責任的執行條件、非處分性執行行為的實施條件、執行順位原則及例外情形的把握均存在不同理解,亟待統一觀點。
二、補充責任補充性的實體與執行程序展開
靜態的實體法本質屬性決定了動態的程序法具體實現。補充責任的本質特征是補充性,既是實體法研究的核心主題,也是執行程序關注的重點。
(一)實體法補充性的爭議
實踐中,對于補充責任補充性的內涵、是否為終局性責任以及補充責任人是否享有追償權等問題所采取的立場直接影響著執行程序中補充責任實現程序的具體建構。其中,補充性內涵的理解涉及執行程序中補充性的體現問題,另外兩個涉及補充責任人在執行程序中的地位及其權利保護的應有力度問題。主流觀點認為,補充性的關鍵是責任履行的順位性:直接責任人承擔第一順位的賠償責任,補充責任人承擔第二順位的責任。[5]也有觀點認為,補充性是對直接責任人的補充,不強調直接責任人無法確定或無力承擔這一前提條件。[6]筆者認為,主流觀點更具合理性。一方面,補充性在于增加不足或彌補缺漏,只有先對直接責任人進行強制執行后才能確定是否不足以及不足的范圍;另一方面,一般保證人享有先訴抗辯權,在主債務關系未經審判并經強制執行后仍不能完全清償前可以拒絕承擔保證責任,在責任履行上有明顯的順位性特征。補充責任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借鑒了保證責任的理論模型。[7]通說認為,補充責任人所享有的拒絕給付的權利性質應該被界定為先訴抗辯權,[8][9][10]故補充責任的補充性應當被理解為責任履行的順位性。
補充責任是否為終局性責任與補充責任人是否享有追償權之間具有高度關聯性:責任性質影響追償權的有無。以侵權責任為例,侵權責任法沒有明確規定補充責任人是否享有追償權,理論界對此存在多種觀點。觀點一:補充責任人和直接責任人因自身過錯承擔侵權責任,不能彼此追償。[11][12]觀點二:補充責任人承擔的是非終局性責任,補充責任人承擔責任后可以向直接責任人追償。[13]觀點三:直接責任人承擔后可以向補充責任人按比例追償。[14]觀點四:只有在直接責任人主觀存在故意或惡意等情形下允許補充責任人行使追償權。[15]觀點五:僅補充責任人享有追償權。[16]針對這一問題,《民法典》第1198條、第1201條規定安保義務人、教育機構承擔補充責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償,確立了侵權補充責任人的追償權。在筆者看來,《民法典》的選擇是合理的。因為補充責任人享有追償權是補充責任的內在要求,[17]把補充責任作為一種追償不能的風險責任,并沒有失去法律對補充責任人做出的否定性評價,補充責任人存在的過錯因風險責任的承擔得到了化解。這種風險責任的作用原理是將權利人向直接責任人求償不能的風險轉移給補充責任人承擔,轉化為補充責任人追償不能的風險,既能為權利人完全受償提供雙重保障,也能對直接責任人與補充責任人間基于過失而應承擔的責任關系做出很好的解釋。[18]
綜上所述,補充責任的補充性的核心在于責任履行的順位性,補充責任人在承擔責任后享有追償權。補充責任是補充責任人追償不能的風險責任,在權利人與補充責任人間存在著緊張的利益關系:補充責任人與權利人在直接責任人所應承擔全部責任的范圍內進行利益博弈,直接責任人履行的責任越多,補充責任人追償不能的風險范圍越小。法院在執行時應當考慮這種關系,并力求實現二者之間的利益平衡。補充責任人是在直接責任人財產不足以清償的范圍內承擔風險責任,因此,是否先就直接責任人財產執行并窮盡執行涉及補充責任人是否承擔風險責任及其責任范圍大小,具有重要意義。
(二)補充性的程序法映射:執行順位原則
⒈執行順位原則基本理論。補充責任的補充性在程序法上體現為責任履行的順位性。對此,不應在訴訟程序中糾結,造成不應當出現的訴訟難題。[19]因此,當載明承擔補充責任的裁判進入強制執行程序時,需要遵循特殊的原則以保障補充責任人的利益,即執行順位原則。執行順位原則是指在執行時應先執行直接責任人的財產,不能對補充責任人直接執行。有學者認為,這是由權利人按照先申請強制執行直接責任后申請履行補充責任之順序實現。[20]如前所述,補充責任的順位性在于先訴抗辯權,執行順位原則的正當性基礎在于從執行層面消極保障補充責任人的先訴抗辯權,即無需補充責任人主張先訴抗辯權而主動將其履行責任的順位后置,體現了對補充責任人順位利益的關照。執行順位原則的法條依據是《擔保法》第17條第2款規定:“一般保證的保證人在主合同糾紛未經審判或者仲裁,并就債務人財產依法強制執行仍不能履行債務前,對債權人可以拒絕承擔保證責任。”《民法典》第687條第2款也確立了該規則①。
⒉順位利益保障:窮盡執行原則。補充責任人是在直接責任人財產被執行后不能清償的范圍內承擔補充履行責任。如果補充責任人承擔的是相應的補充責任,還需受到進一步的責任范圍限制。為了保障補充責任人的順位利益,承擔獨立賠償責任的直接責任人應當如實報告自己的財產。執行法院也應當遵守窮盡執行原則,盡可能對直接責任人財產進行執行,以避免不當擴大補充責任人追償不能的風險責任范圍。實踐中,一般以法院對直接責任人窮盡查控措施變價執行后仍不能完全清償作為執行窮盡原則的判斷依據(詳見[2018]云03執復25號、[2019]魯16執復8號執行裁定書)。
(三)順位性原則的例外:利益平衡
實踐中,補充責任執行的具體情況較為復雜,如果機械性地遵守執行順位原則,申請執行人的合法權益容易遭到侵害。補充責任是非終局性的風險責任,也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評價。如果對補充責任人風險責任利益的堅守嚴重阻礙了申請執行人債權的實現,就無法實現二者間的利益平衡。因此,無論立法還是實踐都對執行順位原則進行了突破。立法沒有直接規定執行順位原則,而是根據一些特殊條文總結出來的。所以,執行順位性原則的例外情形,可以通過對這些特殊條文中的例外規定進行歸納和借鑒得出。
⒈立法層面。在立法層面可借鑒的特殊條文中的例外規定主要是阻礙先訴抗辯權行使的規定。遵守執行順位原則是因為補充責任人有先訴抗辯權,一旦先訴抗辯權的行使受到阻礙,就無須再遵守執行順位原則。有學者認為,先訴抗辯權應當進行適當限制。其對立法中的例外情形進行了歸納和總結,一是根據《人身損害賠償解釋》第6條第2款規定的“第三人不能確定的”總結出應當對先訴抗辯權行使進行限制的情形:直接責任人無法確定;直接責任人無賠償能力(完全沒有責任財產);直接責任人下落不明且無財產可供執行。二是根據《擔保法》第17條第3款與《擔保法司法解釋》第25條總結出應當對先訴抗辯權行使進行限制的情形:債務人下落不明、移居境外且無財產可供執行;債務人進入破產程序;債務人放棄先訴抗辯權,即執行程序中主動放棄順位利益。[21]
上述例外情形主要考慮的因素是直接責任人無法確定使得執行難度過大或直接責任人無財產實質上已經滿足補充責任承擔條件。實踐中對于債務人進入破產程序是否應當突破執行順位原則的做法不統一,還需要在后文作進一步探討。值得注意的是,《民法典》第687條第2款增加了限制一般保證人先訴抗辯權行使的規定,即“(三)債權人有證據證明債務人的財產不足以履行全部債務或者喪失履行債務能力”。是否應當將這個規定借鑒到執行順位原則的例外情形中,也需要在后文作進一步探討。
⒉執行實踐樣態。截至2020年8月5日,筆者在“聚法案例網”以“補充責任”“審理程序:執行”“法院層級:中院”為關鍵詞,共檢索到383個裁判文書。對這些裁判文書進行一一閱讀,篩選出與補充責任執行相關的案件,發現實踐中是否應當突破執行順位性原則的案例有很多。現將主要情形分述如下:一是被執行人下落不明且無財產可供執行。此時,法院認為對補充責任人的執行條件已經成就(詳見[2014]廣執復字第2號、[2014]廣執復字第3號、[2014]廣執復字第4號執行裁定書)。二是被執行人在執行程序中進入破產程序。與前述立法層面上的特殊規定不同,當發現本院或其他法院已經受理關于直接責任人的破產申請時,法院既沒有將其認定為直接責任人已無財產可供執行,也沒有將其作為執行順位性原則的例外情形加以處理。法院認為在完成最終的破產分配之前,直接責任人尚有財產未執行完畢,相應地,其未清償部分也無法確定,也就無法確定補充責任人應當承擔的責任范圍。因此,不能對補充責任人財產進行執行(詳見[2017]鄂05執191號、[2019]浙10執復60號、[2018]皖16執156號、[2018]豫01執1640號執行裁定書)。然而,不同案件的具體處理辦法并不統一,有的案件要求申請執行人自行申報破產債權,并終結本次執行(詳見[2017]鄂05執191號執行裁定書)。有的案件則是裁定中止執行,暫停查控措施(詳見[2018]豫01執476號之一、[2017]鄂01執復136號執行裁定書)。三是直接責任人財產被其他法院查封。當直接責任人財產被其他法院查封或者直接責任人有可參與分配的債權尚未參與分配時,法院認為直接責任人的財產尚未執行完畢,應當先通過參與分配程序進行先順位的清償以確定是否足以清償或未清償的范圍,才能對補充責任人進行執行(詳見[2016]黔02執127號、[2019]粵18執異60號執行裁定書)。因此,僅從執行效率因素出發,法院并不傾向于突破執行順位原則。四是因客觀情況導致直接責任人財產無法認定或者無法執行(詳見[2017]豫04執復50號執行裁定書)。當因客觀原因導致無法執行直接責任人財產時,如果機械地遵守執行順位原則和執行窮盡原則,就不利于保護申請執行人。實踐中主要有以下幾種情形:因直接責任人股權無法鑒定而不能執行,可以執行補充責任人(詳見[2017]吉01執異977號執行裁定書);因主標的物流拍無法變現而無法清償,可以執行補充責任人(詳見[2020]皖02執異6號執行裁定書);當直接責任人財產不宜執行(如土地使用權)時,應當終結本次執行,不能執行補充責任人(詳見[2018]桂06執150號之二執行裁定書);直接責任人財產被稅務部門查封導致暫時無法處置,可以先行執行補充責任人財產(詳見[2017]魯11執異4號執行裁定書);當直接責任人的財產不方便法院執行時,如財產被其他法院查封并且不便分割,可以執行補充責任人(詳見[2014]合執異字第00013號執行裁定書);直接責任人的財產為固定收入,雖然可以預期該固定收入足以清償,但需要較長時間才能執行完畢,不符合執行效率原則,可以先執行補充責任人(詳見[2019]魯16執復8號執行裁定書)。
⒊例外情形應當考慮的因素。考察前述立法規定和實踐樣態,可以發現有些情形表面上是對執行順位原則的突破,實際上是涉及補充責任執行條件成就的理解問題。如被執行人下落不明、移居境外且無財產可供執行或者被執行人確實無力賠償,其關鍵在于無賠償能力,即使對被執行人進行執行也無法獲得執行款項。此時,執行補充責任的條件已經成就,不違反執行順位原則。對執行順位原則的突破,立法和實踐主要考慮了以下因素:直接責任人財產是否便于執行、執行周期和效率、直接責任人財產是否暫時無法處置、破產和參與分配問題。
補充責任是追償不能的風險責任,是否先就直接責任人財產執行并窮盡執行涉及補充責任人是否承擔風險責任及其責任范圍,必須重視和保護其應有的順位利益。因此,僅就被執行人財產不方便法院執行等原因,不足以突破執行順位原則。應結合以下因素綜合考慮:突破的特殊性、已窮盡執行措施、補充責任人追償不能的風險大小。首先,實踐中幾乎所有對執行順位性原則的突破均考慮到了具體案件的特殊性,如直接責任人失蹤、財產無法處置,因此,設置這樣一個斟酌因素并且交給個案法官具體把握標準是必要且妥當的。其次,法院在執行直接責任人遇到阻礙時就不加區分地以諸如直接責任人財產不方便執行或者已經被其他法院查封暫不能執行作為理由,執行補充責任人。這些做法暴露出法院對補充責任人的應有權利不夠重視,沒有窮盡查控執行措施,不當加大了補充責任人的風險責任范圍。因此,突破順位性原則須以法院已經窮盡執行措施仍然無法處置標的物或代價太大為前提。在這種前提下突破順位原則,程序傾向于保護申請執行人就具備了正當性。再次,當滿足補充責任執行條件時,直接責任人已無財產可供執行。補充責任人雖然有追償權,但追償權實現的風險往往很大,需要保護補充責任人的順位利益以減少損失。不過,實踐中出現了這種情形:直接責任人財產為工資等固定收入,要實現最終清償需要好幾年的時間,執行周期過長。此時,如果執行補充責任人,在其履行責任后,追償該部分財產風險是較小的。因此,可以突破執行順位原則,將這種執行完畢的時間成本和較小風險轉嫁給補充責任人負擔。按照這一思路,在直接執行人財產暫時無法處置(最終可以轉化為可處置的狀態),時間成本較高,追償風險較小時,也可以執行補充責任人的財產。追償權實現的風險越低,突破順位原則的正當性就越足,如果程序供給能保障盡快行使追償權,就更加有利于突破順位原則。總之,在設置執行順位原則的突破標準時,必須以“申請執行人—補充責任人”之間的利益平衡為重點,法院的執行行為是公權力行為,不應成為考慮的重點,尤其不能單獨成為突破順位原則的理由。
法院受理直接責任人破產案件應否阻礙先訴抗辯權行使,實踐做法與立法規定相反。立法規定法院受理債務人破產案件是阻礙一般保證人先訴抗辯權的事由。實踐中認為直接責任人財產尚未執行完畢,不可直接執行補充責任人。有學者支持實踐的做法。[22]對于該問題,應分情形討論:一是破產財產能實現完全清償。如申請執行人是優先受償權人,其在破產程序中清償順位靠前,可能實現清償,則應保護補充責任人順位利益,以實現二者利益平衡。否則,補充責任人履行責任后的追償權在破產程序中是否具有優先受償權就會成為更加復雜的問題。二是破產財產明顯不足以全部清償則應當遵循立法的價值選擇。一方面,補充責任人拒絕履行義務的權利,被學界主流觀點界定為先訴抗辯權,對一般保證人先訴抗辯權行使的限制規定,補充責任人也應當一體化的遵循;另一方面,“有證據證明債務人的財產不足以全部履行債務”也作為阻礙先訴抗辯權的事由被規定在《民法典》第687條,二者共同的核心在于債務人財產不足以全部清償且尚未執行完畢,但立法者選擇了保護債權人利益。所以,《民法典》生效后,司法實踐應當遵循這種價值選擇。
(四)順位利益的執行救濟
⒈現行實踐方案。補充責任的執行條件是否成就,在申請執行人和補充責任人之間常常有爭議。實踐中,申請執行人申請執行補充責任人,法院以對直接責任人尚未執行完畢駁回申請。申請執行人可以根據《民事訴訟法》第225條向執行法院提出執行行為違法的異議,對異議裁定結果不服的,可以申請復議。補充責任人認為執行條件尚未成就,也可根據該條規定提出異議和復議。有學者贊同這種把執行異議和復議作為救濟方式的做法。[23][24]此外,雙方當事人如果仍然不服,還有機會申請執行監督程序。但補充責任人不是案外人,不能根據《民事訴訟法》第227條的規定提出執行異議之訴。上述方案可概括為“異議+復議+審判監督”模式。一般來講,這種救濟路徑是針對程序違法行為,保障程序權利而配置的。補充責任是非終局性的風險責任,先訴抗辯權是一種實體法上的權利,因此,實踐方案能否為救濟當事人權利提供足夠的程序供給,如何強化其程序保障,需要進行理論上的探討。
⒉理論探討:執行名義附有條件的救濟。補充責任的執行名義,在理論上屬于附條件的執行名義。[25]執行名義附有條件的,只有在條件成就后,才能開始強制執行。執行名義附條件一般有兩種情形:執行名義上載明的請求權附有條件;執行名義本身附有條件。[26]在我國,執行依名義條件、附期限、對待給付和擔保等特殊情形并不多見,對此類特殊執行依據的理論研究也較為有限。
執行名義附有條件,一般涉及實體問題,日本、德國均將其作為執行要件中的實體性要件。[27]補充責任的特殊執行條件也是實體性要件。在有執行文制度的國家(地區),執行名義所附條件是否成就,需要由執行文授予機關進行審查。如果對審查結果不服,當事人可以提出異議。同時,也有必要通過訴的方式來解決這種爭議。因此,相關國家(地區)還設置了執行文授予之訴和對執行文授予的異議之訴。前者由申請執行人對條件成就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后者則由被執行人對條件未成就的事實承擔證明責任。[28]日本的執行條款發放之訴和反對執行條款發放之訴的原理與德國基本相同,在此不做贅述。在沒有設置執行文制度的我國臺灣地區,執行依據所附條件是否成就是由執行法院作形式審查,債權人和債務人分別就條件成就的事實和未成就事實承擔舉證責任。對條件事實是否成就發生爭議,由當事人另訴解決,不得逕行開始執行。[29]目前,我國基本缺乏關于執行名義附條件、期限、對待給付等法律規定,也缺乏解決執行要件爭議的規定。如前所述,實踐中采用的是“異議+復議+執行監督”的救濟路徑。[30]對此,學界提出三種方案。方案一:在未來的《強制執行法》中參照德國做法,建立執行文制度,對執行文的種類、審查、授予、程序性救濟和實體性救濟均做出相關規定。[31]對于補充責任的執行條件是否成就的救濟可以通過執行文賦予之訴和執行文賦予的異議之訴予以救濟;方案二:建立債務人異議之訴。補充責任執行條件爭議由債務人異議之訴解決;[32][33]方案三:在立案登記制下,判決主文請求權所附條件是否成就,由執行機關判斷。當事人對審查結論不服,如果屬于程序上的瑕疵就通過異議和復議路徑解決,如果實體上不服,應當允許其提出異議,并賦予訴權保障,即執行許可之訴和執行許可異議之訴。[34]
方案一中,強調建立執行文制度并配套執行文賦予之訴及執行文賦予的異議之訴,但實務界對如此精密的理論的接受程度并不高。方案二中,債務人異議之訴就解決執行名義所載請求權與實際權利狀況不符的制度功能似乎難以涵蓋補充責任條件成就的問題。方案三中,強調借鑒我國臺灣地區解決執行當事人適格爭議的執行許可之訴和執行許可異議之訴,但實際上我國臺灣地區對執行依據所附條件爭議的救濟卻是通過另行起訴解決的。因此,上述方案雖然在立法層面和理論建構上具有重要意義,卻不能對補充責任執行救濟提供現實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方案的共同點是認定執行名義請求權所附條件的爭議具有實體因素,僅提供程序瑕疵的救濟是不夠的。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觀點,條件是否成就,發生在案件審結之后,如果形成了新的實體權利義務爭議,就不是簡單的事實判斷問題,不能在執行程序中直接加以認定①。有學者直接將附條件執行依據的條件成就作為實體性執行受理要件處理。[35]可見,附條件執行依據的條件成就,并非絕對的事實認定問題。
補充責任的擔責條件與一般的附條件執行依據存在區別:條件成就必須依賴法院的執行,條件是否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執行法院是否先行執行直接責任人并且窮盡執行措施。現行救濟程序中執行法院審查由自己主導的條件事實是否成就的做法,很可能遭受司法中立性原則的詰難。現階段,引入執行文賦予之訴和執行許可之訴難度較大,而且不符合執行效率原則。因此,利用現有程序資源充分保障補充責任當事人利益是目前應當努力的方向。
⒊短期解決方案:激活執行聽證程序。出于兼顧執行效率與程序保障的目的,可以考慮借用和改造我國在實踐中摸索出來的民事權益略式判定程序,即激活現行“異議+復議+執行監督”路徑的基本框架中的執行聽證制度,并對該制度進行完善,以提供更充分的程序保障。值得說明的是,關于執行異議、復議的司法解釋規定了案情復雜、爭議較大的異議、復議案件應當進行聽證,但沒有形成系統的法律規范。目前的執行聽證制度并不完善,許多核心問題分歧較大。[36]此外,聽證程序較為耗費司法資源,現行救濟模式下聽證程序的適用及效果與期望相差較大,遠不能提供足夠的程序供給。
判斷補充責任執行條件是否成就的核心問題在于直接責任人是否有可供執行的財產,這種判斷的標準其實與終結本次執行或者終結執行的條件基本相同。當申請執行人對終結本次執行程序提出異議,法院應當進行聽證。因此,補充責任的執行救濟適用聽證程序存在法規范層面的基礎。申請執行人或補充責任人就補充責任執行條件是否成就提出異議或復議時,法院應當依職權啟動聽證程序。基于裁決的中立性以及執行局內部裁執分離的職能劃分,可以由未實施該執行行為的執行人員組成合議庭,在正式的場所,以公開的方式主持聽證,聽取當事人的主張,組織當事人舉證和發表意見,進行實質審查。有關補充責任執行條件成就與否等事實的證明責任,參照適用法規范說:由申請執行人就補充責任執行條件成就的事實以及阻礙先訴抗辯權的事由承擔主張和證明責任;由補充責任人對執行條件未成就的事實進行主張和反證。如果申請執行人對條件成就事實的證明無法達到證明標準,駁回其要求執行補充責任人的申請。如果補充責任人對條件未成就事實的證明無法達到證明標準則開始對其進行執行。至于證明標準,“即使爭訟性判定程序更加注重效率而采取表見證明、大致推定之類的蓋然性證明標準。”[37]實施執行行為的執行人員在聽證程序中作為第三人,就案件的執行情況以及是否窮盡執行措施提供相應材料并進行說明,充實裁決主體的心證基礎。
三、補充責任裁判執行的財產查控措施適用條件
民事執行措施可以分為處分性執行措施和非處分性執行措施。財產查控措施是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后,法院采取查封、扣押等措施控制被執行人的責任財產,不對責任財產進行處分和變更。關于補充責任裁判執行的財產查控措施適用條件,實踐中各法院的觀點不統一。這些不同的觀點所針對的共同問題是:針對補充責任人的執行保全措施是否也應遵守執行順位原則和窮盡原則,在直接責任人執行完畢后才可以實施。
觀點一:補充責任人是執行名義所載明的被執行人,雖然附有條件,但已經具備執行力。因此,即使沒有對直接責任人采取執行措施,也可以逕行對補充責任財產采取查封、扣押等財產控制性措施(詳見[2019]湘01執復135號、[2018]冀10執復1號、[2016]寧02執復20號、[2016]寧02執復21號執行裁定書)。
觀點二:根據《民事訴訟法》第244條,在沒有對直接責任人執行完畢時,也可以對補充責任人財產實施查封、扣押等執行措施(詳見[2020]湘01執復38號、[2020]湘01執復39號、[2017]桂03執異29號、[2017]贛07執復9號、[2017]魯02執異404號執行裁定書)。對此,有持完全相反觀點的裁定,認為在沒有對直接責任人執行完畢時,不能確定補充責任人是否需要承擔責任及其責任范圍大小,不能對其采取執行措施(詳見[2019]豫05執異61號、[2019]豫05執異61號、[2018]川08執異7號執行裁定書)。
觀點三:只要補充責任人存在承擔責任的可能性就可以對其財產進行查控(詳見[2019]黔23執復8號執行裁定書)。
觀點四:直接責任人財產尚未執行完畢,當財產明顯不能清償全部債務時,補充責任人一定會承擔責任,可以對補充責任人的財產采取查控措施(詳見[2018]粵20執復124號、[2019]粵18執異60號、[2019]遼01執復443號執行裁定書)。有裁定認為,即使直接責任人財產是否足以清償處于不確定的狀態,也可以先對補充責任人財產進行查封、扣押(詳見[2016]黑10執復35號、[2017]桂03執異27號、[2017]桂03執異28號、[2017]桂03執異30號執行裁定書)。
從上述觀點可以看出,實踐中對于補充責任人財產查控條件的把握寬嚴程度不統一。無須等到直接責任人執行完畢就可以查控補充責任人財產觀點的主要依據是附條件執行名義具有執行力、防止補充責任人轉移責任財產、執行措施的非處分性。反對觀點則基于對附條件執行名義執行力的不同理解、查控范圍的不確定等理由。筆者認為,問題的核心是附條件執行名義的執行力問題,同時也對應著執行行為的合法性問題。
判決發生效力,執行名義就已經成立。我國執行名義的生效條件有明確法律規定,如《民事訴訟法》第155條。一般情形下,給付判決生效即具備執行力,但立法沒有規定附條件執行名義的執行力問題。條件是否成就,應該理解為是否可以開始強制執行的條件,但“開始強制執行的條件”是否包括非處分性的執行措施還存在疑問。從程序的發展性角度來講,強制執行程序可劃分為啟動階段、財產查控階段、實體權屬判斷階段、變價交付階段和執行救濟五大階段。[38]開始強制執行應該屬于執行啟動階段,而實施查封、扣押等非處分性措施應屬于財產查控階段。只有具備執行要件,執行案件的受理和具體執行行為的啟動才具有合法性。按照這個邏輯,在執行順位原則的一般情形下,對直接責任人財產尚未執行完畢前,不能對補充責任人財產采取查封扣押措施。財產查控措施對補充責任人的利益也會造成較大影響,應當對其合法利益進行保護。基于這種執行措施的非處分性,并不涉及實體爭議,可以采用“異議+復議+執行監督”的路徑提供救濟。在條件成就前,補充責任人可能通過處分或隱匿財產的方式來逃避法院的執行,申請執行人可以根據《民事訴訟法解釋》第163條的執行前保全制度保全補充責任人的責任財產。與執行中的財產查控措施不同,法院不能依職權啟動執行前保全,需要由補充責任人提出申請,并提供相應擔保。
綜上所述,在執行順位原則的例外情形中,法院可以直接對補充責任人財產采取查封、扣押等財產控制措施。在執行順位原則的一般情形中,未對直接責任人執行完畢前,即使直接責任人明顯不能清償,也不能對補充責任人采取財產查控措施。如果補充責任人可能轉移、隱匿財產以逃避執行,申請執行人可以依法申請執行前保全進行救濟。
【參考文獻】
[1][2][25]張海燕.民事補充責任的程序實現[J].中國法學,2020,(6):184-198.
[3][19][20][23]肖建國,宋春龍.民法上補充責任的訴訟形態研究[J].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6,(2):7-10.
[4][22][24]宋春龍.訴訟法視角下的先訴抗辯權研究——兼評民法典各分編草案中的先訴抗辯權[J].政治與法律,2019,(3):31-34.
[5]王竹.補充責任在《侵權責任法》上的確立與擴展適用——兼評《侵權責任法草案》(二次審議稿)第14條及相關條文[J].法學,2009,(9):86.
[6]姬新江.共同侵權責任形態研究[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12:343.
[7]王竹.侵權責任分擔論——侵權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分擔的一般理論[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184.
[8]張新寶,唐青林.共同侵權責任十論——以責任承擔為中心重塑共同侵權理論[J].民事審判指導參考,2004,(2):160.
[9]陳清.論我國侵權責任法中的補充責任[J].探索與爭鳴,2011,(9):126.
[10]袁秀挺.論共同責任中補充責任的確認與適用——兼與非真正連帶責任的比較[J].法治論叢,2005,(6):103.
[11]楊立新.侵權責任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283.
[12]程嘯.侵權責任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354.
[13]黃龍.民事補充責任研究[J].廣西警官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7,(4):25-28.
[14]朱巖.侵權責任法通論·總論·上冊·責任成立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345-346.
[15]王利明.侵權責任法研究(下卷)[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194.
[16]張新寶.侵權責任法原理[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284.
[17][21]鄔硯.侵權補充責任研究[D].西南政法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5:30-44.
[18]王竹.論風險責任概念的確立[J].北方法學,2011,(2).
[26][29]楊與齡.強制執行法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99.
[27][34]馬登科.案外人救濟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179-185.
[28][31]劉穎.執行文的歷史源流、制度模式與中國圖景[J].中外法學,2020,(1):249-258.
[30]張春光.執行與執行異議疑難問題全解與典型案例裁判規則[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9:286-287.
[32]金印.論債務人異議之訴的必要性——以防御性司法保護的特別功能為中心[J].法學,2019,(7):58.
[33]王娣.我國民事訴訟法應確立“債務人異議之訴”[J].政法論壇,2012,(1):183-184.
[35]馬家曦.立案登記制下執行要件之分擔審查論[J].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2):64.
[36]劉爽.我國民事執行聽證制度的完善[J].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8,(1):67-68.
[37]黃忠順.論執行當事人變更與追加的理論基礎[J].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2):107.
[38]馬登科.審執分離運行機制論[J].現代法學,2019,(4):168.
(責任編輯:苗政軍)
On the Enforcement of Supplementary Responsibility Judg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ivil Code
Ma Dengke,Han Qiang
Abstract:Civil supplementary liability is a non final risk liability,which transforms the risk that the creditor cannot claim into the risk that the supplementary liability person cannot recover due to his fault.The basis of supplement lies in the right of plea in advance,and the scope of action is mainly the compulsory execution procedure,with the principle of order and exhaustive execution.In practice,it is not unified to grasp the principle of breaking through the order of execution.We should focus on the balance of interests between the applicant and the supplementary responsible person,not only on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ublic law.The conditions attached to the basis of execution are the conditions for the commencement of compulsory execution.Before the conditions are fulfilled,no preservation measures shall be taken against the property of the supplementary responsible person,except those tha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preservation before execution.The current mode of “objection+reconsideration+enforcement supervision” is not enough to provide adequate relief.The relief procedure design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efficiency and rights protection.
Key words:supplementary responsibility;the right of plea in advance;carry out the principle of order;implement the principle of exhaustion;property preserv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