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經(jīng)通督法針刺對血瘀型腰椎間盤突出癥疼痛程度及血清疼痛遞質(zhì)的影響
張慧森 劉健 溫石磊 田斌武
腰椎間盤突出癥是由多種因素引起腰椎盤中髓核、軟骨板、纖維環(huán)發(fā)生不同程度的退行性病變,髓核組織從纖維環(huán)破裂處突出于椎管或后方,導致脊神經(jīng)根受到壓迫,產(chǎn)生腰部疼痛等一系列臨床癥狀[1]。近年來腰椎間盤突出癥的發(fā)病人群不斷擴大,且趨向于年輕化,受到社會的高度重視[2]。中醫(yī)認為腰椎間盤突出癥與人體督脈關(guān)系密切。督脈為陽脈之海,經(jīng)氣虧虛、陽氣不足則易外感風寒濕邪,導致水濕痰飲內(nèi)聚,阻塞經(jīng)絡(luò),造成氣滯血瘀,不通則痛,發(fā)為本病[3]。血瘀是導致腰椎間盤突出癥患者腰腿痛的主要原因,當以舒經(jīng)通督、活血祛瘀為主要治則[4]。本研究對47例腰椎間盤突出癥血瘀型患者在西醫(yī)常規(guī)治療的基礎(chǔ)上,聯(lián)合舒經(jīng)通督法針刺治療,分析其臨床療效,為臨床研究提供參考。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選取保定市第一中醫(yī)院2019年2月至2020年5月收治的97例腰椎間盤突出癥血瘀型患者,其中脫落3例,剩余94例按照隨機數(shù)字表法分為研究組與對照組,每組47例。研究組中男性30例,女性17例,年齡45~72歲,平均(60.32±5.07)歲,病程6個月~7年,平均(4.08±1.13)年,病變部位L4-5段15例、L5-S1段20例、L4-5S1段12例。對照組中男性27例,女性20例,年齡44~71歲,平均(60.10±5.07)歲,病程6個月~7年,平均(4.20±1.18)年,病變部位L4-5段17例、L5-S1段17例、L4-5S1段13例。兩組患者的平均病程、病變部位、年齡、性別等資料無明顯差異(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符合保定市第一中醫(yī)院倫理委員會相關(guān)規(guī)定。
1.2 納入標準
(1)符合腰椎間盤突出癥的診斷標準[5]:下肢痛、腰痛、典型腰骶神經(jīng)根疼痛,下肢區(qū)域放射性疼痛,臀上椎旁有壓痛,神經(jīng)障礙中有兩種證型,直腿抬高試驗、股神經(jīng)牽拉、神經(jīng)根張力試驗呈陽性,X線顯示腰椎生理幅度或脊柱側(cè)凸異常,脊柱間隙變窄,CT掃描腰椎間盤突出;(2)滿足《中醫(y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中血瘀型的診斷標準[6],包括腰骶疼痛、下肢放射性疼痛、腹壓增加時疼痛加劇、腰腿針刺痛、痛處拒按、痛有定處、腰硬如板、活動受限,舌紫有瘀斑,脈弦緊;(3)依從性良好,遵醫(yī)囑進行服藥;(4)患者自愿參與本研究,簽訂知情同意書。
1.3 排除標準
(1)腰椎骨折、骨髓損傷、骨腫瘤等其他病變;(2)明顯手術(shù)指征;(3)對本研究所用的藥物過敏;(4)機體重要器官心、肝、腎、肺等嚴重病變者;(5)參與其他臨床療效評價研究;(6)近1個月內(nèi)激素、免疫抑制劑治療史;(7)局部皮膚破損不宜進行針刺治療者。
1.4 脫落標準
(1)主動退出研究;(2)治療期間發(fā)生嚴重并發(fā)癥,影響療效判定者。
1.5 治療方法
對照組:給予口服塞來昔布膠囊(輝瑞制藥,生產(chǎn)批號:20190108,20191208)治療,每日2次,每次0.2 g,連續(xù)治療4周。
研究組:在對照組基礎(chǔ)上,聯(lián)合舒經(jīng)通督法針刺治療,選取夾脊、后溪、大腸俞、委中、腎俞、阿是穴、膈俞等,運用透刺法針刺夾脊穴,運用斜刺法針刺膈俞穴、運用直刺法針刺其他腧穴,進針后運用平補平瀉法,以患者酸脹感為度,每次留針20分鐘。每周治療6次,連續(xù)治療4周。
1.6 觀察指標
1.6.1 臨床療效標準 參考《中醫(y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的中醫(yī)癥狀量化評分標準擬定[6],對患者的中醫(yī)癥狀進行量化評分,各癥狀的評分總和作為證候總評分。擬定:(1)治愈:腰痛等癥狀、體征完全消失,日常工作生活恢復正常,直腿抬高不低于70°,治療后證候總評分降低≥95%;(2)好轉(zhuǎn):腰痛等癥狀、體征明顯改善,日常工作生活有所改善,直腿抬高低于70°,治療后證候總評分降低≥30%;(3)無效:癥狀、體征無明顯改變,治療后證候總評分降低<30%。總有效率=(治愈的例數(shù)+好轉(zhuǎn)的例數(shù))/47×100%。
1.6.2 疼痛程度比較 運用視覺模擬評分法(Visual analogue scale,VAS)對患者主觀疼痛程度進行評估[7],分值0~10分,分值越高則疼痛越嚴重。
1.6.3 腰椎功能比較 運用日本骨科協(xié)會評估治療分數(shù)(Japanese Orthopaedic Association Scores,JOA評分)評估患者的腰椎功能[8],包括主觀癥狀(9分)、臨床體征(6分)、日常活動(14分),分值越高則功能越好。
1.6.4 疼痛遞質(zhì)比較 采集患者治療前后晨起空腹時外周靜脈血3 mL,運用放射免疫法測定血清中神經(jīng)肽Y(neuropeptide Y,NPY)、5-羥色胺(5 Serotonin,5-HT)、P物質(zhì)(Substance P,SP)的水平。
1.7 統(tǒng)計學處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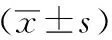
2 結(jié)果
2.1 臨床療效比較
治療后,研究組總有效率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兩組腰椎間盤突出癥血瘀型患者臨床療效比較(%)
2.2 主觀疼痛程度比較
治療前,兩組主觀疼痛程度(VAS評分)無明顯差異(P>0.05);治療后,兩組主觀疼痛程度(VAS評分)均降低,且研究組主觀疼痛程度(VAS評分)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見表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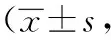
表2 兩組腰椎間盤突出癥血瘀型患者主觀疼痛程度(VAS評分)比較分)
2.3 腰椎功能JOA評分比較
治療前,兩組腰椎功能JOA評分(含主觀癥狀、臨床體征、日常活動)無明顯差異(P>0.05);治療后,兩組腰椎功能JOA評分均提高(P<0.05)且研究組腰椎功能JOA評分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見表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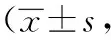
表3 兩組腰椎間盤突出癥血瘀型患者腰椎功能JOA評分比較分)
2.4 疼痛遞質(zhì)比較
治療前,兩組NPY(neuropeptide Y,NPY)、5-HT(5 serotonin,5-HT)、SP(substance P,SP)無明顯差異(P>0.05);治療后,兩組NPY、5-HT、SP均降低(P<0.05),且研究組NPY、5-HT、SP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見表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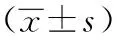
表4 兩組腰椎間盤突出癥血瘀型患者治療前后NPY、5-HT、SP比較
3 討論
腰椎間盤突出癥的發(fā)病機制尚未完全明了,其病因可能與年齡、性別、運動、外傷、生活習慣、肥胖、糖尿病、遺傳、體位不正等因素相關(guān),多種因素可使椎間盤內(nèi)部壓力增大,逐漸導致纖維環(huán)破裂,髓核突出,引起椎間盤退行性病變[9]。目前西醫(yī)治療腰椎間盤突出癥以藥物保守治療為主,塞來昔布是常用的非甾體藥物,能抑制前列腺素合成酶活性,減輕組織間炎癥反應(yīng),降低致痛物質(zhì)的分泌[10]。
腰椎間盤突出癥屬于中醫(yī)“痹癥”“腰腿痛”范疇,以腎精虧虛為本,經(jīng)絡(luò)痹阻為標。筋骨失養(yǎng),不榮則痛;督脈痹阻,腰部氣血瘀滯,不通則痛[11]。中醫(yī)經(jīng)絡(luò)學說認為,腰椎間盤突出癥的發(fā)病與督脈密切相關(guān),腰椎位于督脈的循經(jīng)部位,督脈氣盛則筋柔骨正,督脈經(jīng)氣虧虛則溫煦無力,水濕痰濁內(nèi)聚,經(jīng)絡(luò)痹阻,形成瘀血;加之正氣不足,腠理空虛,外感風寒濕邪,凝滯氣血,痹阻督脈,發(fā)為此癥[12]。舒經(jīng)通督法針刺是以經(jīng)絡(luò)學說為指導,選取夾脊、后溪、大腸俞、委中、腎俞、阿是穴、膈俞等腧穴進行針刺治療。針刺夾脊穴能溫陽通脈,活血化瘀,通經(jīng)止痛;后溪穴與夾脊穴聯(lián)合,遠近相配,提高舒經(jīng)通絡(luò)的作用,有效促進經(jīng)脈功能恢復;委中能通絡(luò)止痛,腎俞穴能溫補腎經(jīng),強腰健骨,祛濕散寒;阿是穴、大腸俞能通經(jīng)止痛,祛邪除濕;膈俞能活血祛瘀,調(diào)暢經(jīng)脈。諸穴合用,共同發(fā)揮通督疏經(jīng),活血化瘀,行氣通絡(luò),散寒祛濕的功效,改善患者腰痛癥狀、體征,調(diào)節(jié)機體氣血運行,促使機體生理機能恢復[13]。本研究結(jié)果發(fā)現(xiàn),研究組療效優(yōu)于對照組,治療后VAS評分低于對照組,JOA評分高于對照組。結(jié)果表明,舒經(jīng)通督法針刺治療腰椎間盤突出癥血瘀型的療效確切,能進一步減輕疼痛程度,改善腰椎功能。
NPY主要存在于交感神經(jīng)系統(tǒng),能提高神經(jīng)源性疼痛和炎癥性疼痛,在腰椎間盤突出癥中呈高表達[14]。5-HT能直接刺激感覺神經(jīng)末梢,產(chǎn)生致痛作用,還能傳導傷害性信號,提高疼痛程度[15]。SP可促使肥大細胞分泌大量組胺,引起局部炎癥反應(yīng),改變血管通透性,對疼痛中樞產(chǎn)生強烈的致痛作用[16]。本研究結(jié)果發(fā)現(xiàn),研究組治療后的NPY、5-HT、SP低于對照組,表明舒經(jīng)通督法針刺能有效降低腰椎間盤突出癥血瘀型患者的疼痛遞質(zhì)分泌,這可能是其發(fā)揮療效的作用機制。
綜上所述,舒經(jīng)通督法針刺能提高腰椎間盤突出癥血瘀型的臨床療效,減輕患者的疼痛程度,改善腰椎功能,調(diào)節(jié)血清疼痛遞質(zhì)分泌,具有良好的臨床研究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