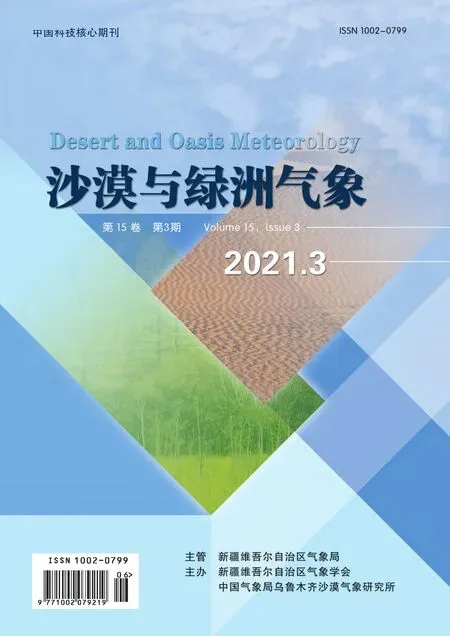2018年廣西東南部一次暴雨過程分析
董良淼,翟麗萍,覃月鳳,梁依玲
(廣西氣象臺,廣西 南寧530022)
廣西地處華南西部高原向沿海的過渡帶,西臨云貴高原、南臨北部灣,地形地貌復雜。在西風帶系統和熱帶天氣系統的交替影響下,易出現暴雨天氣。區域內局地暴雨過程往往具有明顯的中小尺度特征,突發性強、極端降水頻發,業務預報難度較大。
近年來,隨著氣象監測手段的不斷豐富,高分辨率云圖、新一代天氣雷達和風廓線雷達產品、區域加密自動站觀測數據等非常規資料越來越多地被應用于局地、突發性暴雨的預報、預警和分析研究中,成效顯著。周文志等[1]對2002—2010年廣西12個低空急流暴雨個例進行了普查分析,發現廣西大范圍低空急流暴雨是在大尺度背景下,由天氣系統和中小尺度系統共同影響的結果,在有低空急流存在的情況下,對降水量有明顯的增幅作用。王珊珊等[2]利用多種資料對紅安“7·21”特大暴雨分析發現,大別山復雜地形對降水有顯著增幅作用,地形影響氣流理論很好地解釋了此次特大暴雨降水分布。王芬等[3]對一次低渦切變型暴雨進行中尺度分析,指出大暴雨中心的兩個MCS是由沿低渦前側的切變線移到暴雨區上空形成的,強降水主要出現在MCS的中部冷云區及梯度大值區。羅王軍等[4]對一次弱垂直風切變環境條件下發生在兩個592 dagpm副熱帶高壓之間切變區的短時大暴雨分析,發現其對流觸發是地面冷鋒、露點鋒以及地形抬升。沈武等[5]將地面逐時加密觀測資料與衛星云圖、物理量診斷相結合進行分析,揭示出突發性局地特大暴雨與地面輻合場、能量場分布有密切關系。肖安等[6]對比分析南方一次暴雨空報原因和實際暴雨個例發現,中低層較高比濕(高于平均值2~3 g·kg-1)、較好的邊界層觸發條件、較深厚的上升氣流與更強對流不穩定都可能是我國南方春季暖區暴雨重要的預報思路。易新民等[7]運用四要素自動站資料分析,指出地面中小尺度在強降水落區短時預報的指示意義。方翀等[8-10]進一步結合應用天氣雷達、風廓線雷達探測資料及NECP再分析資料對造成北京特大暴雨的對流系統“列車效應”進行了研究,指出低層切變線和地面輻合線交匯處是對流單體初生和強烈發展區域,有助于低質心、高效率降雨形成。伍志方等[11-12]利用多種探測資料詳細剖析了2017年5月7日廣州特大暴雨對流系統各個發展階段的演變過程,強調了各個階段均呈現出“低質心暖云降水”的特點,同時指出目前數值模式尚難做出暖區弱風場環境下的暴雨以上降水預報。葉朗明[13]等對典型回流暖區暴雨的研究表明,超低空東南急流遇到喇叭口地形產生強烈輻合抬升是局地暴雨的啟動機制之一。這些成果均為分析、研究廣西區域的局地突發性強降水過程提供了重要參考。
2018年5月10日,廣西東南部出現了一次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突發性強降水天氣過程,其中有2個國家氣象觀測站實測降水量超過了當月歷史極值。區、市氣象臺業務預報對這次過程的強降水落區把握較好,但對降水的極端性估計不足。事后初步分析表明:各數值預報模式對此次暴雨過程的雨帶位置、強度量級及時間預報均存在明顯偏差;加之主觀訂正預報對東路冷空氣侵入強度估計不足、對東南風加強及地形抬升作用導致的暴雨增幅重視不夠,最終導致過程量級預報失誤。鑒于此,本文借助雷達、衛星和地面中尺度自動站觀測資料等非常規資料,結合NCEP再分析資料對此次暴雨過程的天氣尺度背景、環境場特征及中尺度對流系統特征進行全面分析,試圖揭示出該類突發性天氣過程的關鍵觸發因子及其業務預報預警著眼點,以便今后更有針對性地解決實際預報問題。
1 過程概況
2018年5月9日20時—10日20時(北京時,下同),廣西東南部出現了一次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強降雨天氣過程(圖1a),其中陸川、博白兩個國家氣象觀測站24 h累積降雨量分別達232.9、184.5 mm,打破了當地建站以來5月最大日降雨量記錄,陸川站連續5個時次小時雨強超過了20mm·h-1。本次降雨過程在當地持續時間只有2~5 h,但小時雨強較強,≥50mm·h-1的區域覆蓋了廣西東南部的浦北到北流一帶,包括5個國家氣象觀測站(圖1b),其中最大雨強達到94.2 mm·h-1,可見強降雨落區分布非常集中,時空局地性較強。局地極端性強降雨導致流域內江河水位急速上漲,局地出現洪澇、地質災害及城鎮內澇,共造成受災人口3.73萬人,緊急轉移安置4435人,且因災死亡3人,直接經濟損失4202.57萬元。

圖1 5月9日20時—10日20時廣西24 h累計雨量分布(a)和小時雨量≥50mm/h的國家觀測站點雨量時序(b,單位:mm)
2 天氣背景及環境條件
2.1 環流形勢分析
2018年5月10日08時,200 hPa南亞高壓仍在中南半島到南海北部,廣西上空受脊前西北氣流控制,高空輻散條件不明顯。500、700 hPa青藏高原東南側到華南上空為多小波動,廣西上空有南北兩支弱短波緩慢東移,其中南支短波槽前的弱正渦度平流為強降水的發生發展提供了一定的上升條件(圖2a)。副熱帶高壓控制廣西南部沿海地區,廣西東南部處于副高邊緣,高溫高濕環境明顯,有利于降水出現。850 hPa盛行弱偏南氣流、風速≤8 m·s-1,廣西中部一帶有弱的暖性切變線。925 hPa(圖2b)和地面形勢場類似,北方有弱冷空氣補充南下,與來自南海北部回流東南風在廣西東南部形成切變線及地面輻合線,且切變線偏北于地面輻合線,過程中地面輻合線與925 hPa加強的東南風風速輻合區重疊,這是廣西典型的回流降水形勢,根據以往經驗,類似形勢下可能出現局地暴雨,但大暴雨的情況極為罕見。

圖2 5月10日08時500 hPa(a)和925 hPa(b)環流形勢
2.2 物理量環境條件分析
2.2.1 水汽條件分析
分析5月9—10日的中低層濕度場,廣西區域呈現出一條明顯的東北—西南向濕度鋒區,其中桂東南處于濕度鋒區東側的大濕度區頂部(即濕舌頂端)。5月9日20時—10日08時,桂東南地區850、925 hPa比濕(圖3a)由13、14 g·kg-1迅速增大到14、16 g·kg-1,與歷年同期850 hPa廣西東南部平均比濕(11.8 g·kg-1)相比,低層增濕明顯,表明此次過程低層具備了暴雨所需的水汽條件。

圖3 2018年5月10日08時925 hPa比濕場(a,綠色矩形方框為極端暴雨區,單位:g·kg-1)和沿110°E極端暴雨附近水汽通量散度垂直分布(b,單位:g·cm-2·hPa-1·s-1,▲為22.3°N陸川站所在緯度)
進一步對反映降水系統水汽輸送、匯聚能力的水汽通量及水汽通量散度進行分析發現,10日08時850、925 hPa水汽通量圖上可清楚看到由南海北部經粵西向桂東南有一條強水汽輸送帶。沿110°E做水汽通量散度剖面(圖3b),800 hPa以下大氣層均為水汽輻合區、最大輻合中心出現在925 hPa層上下、23°N附近,即桂東南玉林市境內的陸川、博白一帶,水汽通量散度值達-40×10-7g·cm-2·hPa-1·s-1。研究表明:此次強降水天氣的水汽來源于南海北部,暴雨區出現在水汽通量中心的前端。強降水中心和低層水汽輻合中心有非常好的對應關系。
2.2.2 不穩定條件和垂直風切變分析
選取暴雨中心陸川站附近格點(110°E,22°N)作探空曲線T-log P分析,10日08時廣西東南部對流有效位能(CAPE)小(圖4a),邊界層露點在22℃左右。14時,隨著時間演變,溫度升高、能量條件轉好:CAPE為1850 J·kg-1、LI指數為-5,0℃層在600 hPa以上且濕層條件較好。中心區K指數有37℃(一般K≥35℃時易出現強降水),850~500 hPa溫度差為22℃,滿足廣西短時強降水發生條件。850 hPaθse場,桂東南處于高能濕舌前端θse鋒區前方偏暖區一側。參考暖云層厚度理論,進一步對該區域抬升凝結高度(LCL)到0℃層高度之間厚度進行分析,LCL層到0℃層的高度近5000 m,如此厚的暖云層有利于提升過程降水效率。

圖4 5月10日08時(a)和14時(b)(110°E,22°N)的探空曲線
由垂直風切變分析可知,0~700 hPa、0~500 hPa的風切變數值分別為3.5×10-3、2.1×10-3s-1,與2017年5月7日廣東局地特大暴雨的風切變值(清遠:2.51×10-3、2.10×10-3s-1,河源:2.30×10-3、1.49×10-3s-1)[11]基本相似,各層風切變均不明顯。這種弱垂直風切變條件雖不利于高度組織化的強烈風暴的形成,不易出現雷暴大風、冰雹等強對流天氣,但對低質心對流風暴的形成發展非常有利。2018年5月10日過程的雷達產品分析可以看出,強回波帶集中在0℃層附近、對流單體主體位于0℃層以下,云中粒子以水滴為主,表明該過程是一次低質心、高效率的暖云強降水過程。
3 觸發機制及維持
3.1 初生對流觸發機制
車俊輝等[14]在研究山東一次較為罕見的邊界層輻合線活動過程中指出,天氣尺度過程同地面輻合線發展演變關系密切,輻合線成為魯西北對流天氣過程的觸發系統。本次暴雨過程中,從廣西逐時加密自動站風場演變可以看出,9日晚開始,北方弱冷空氣沿著博白、陸川北面山谷南下滲透,與來自海上冷高壓后部的東南風回流交匯,在桂東南一帶形成一條東北風和東南風的中尺度輻合線,這條輻合線兩側水平溫度差最初只有1℃,隨著冷空氣的不斷補充南下,輻合線北側的溫度下降2~3℃,南面的暖濕氣流北上造成1℃的增溫,即導致10日凌晨,地面輻合線兩側的溫度差達到5℃(圖5a),表明該處水平溫度梯度明顯加強。在強的水平溫度梯度影響下,暖空氣一側出現上升、冷空氣一側出現下沉環流,這種強水平溫度梯度有利于邊界層垂直風切變增強,在輻合抬升運動的觸發下極易形成初始對流,10日06時的可見光云圖已可清晰監測到桂東南一帶有初生對流云團發生發展。
3.2 地面輻合線維持
10日06時強降水發生后,地面輻合線后部的東北風與南側的東南風風速相當,因此地面輻合線穩定少動,且輻合線附近仍存在3~4℃的水平溫度梯度區,新生對流生成后并沒有遠離主體對流,而是直接并入主體系統使得強降水回波面積快速增大,導致陸川、博白一帶的雨強增大。另外,陸川、博白地處喇叭口地形(圖5b),對南面暖濕氣流的強迫抬升又加劇了對流發生、發展,對暴雨有明顯的增幅作用。在南北氣流對峙下,地面中尺度輻合線從06—11時都基本維持不動,使得降水云系在陸川、博白一帶不斷發展和維持,形成極端累計降水。10日12時后,隨著輻合線緩慢東南移,降水系統也隨之減弱并移出廣西。

圖5 5月10日05時地面分析
綜上所述,北方弱冷空氣南下,與來自海上冷高壓后部的東南風回流交匯,在廣西東南部一帶形成地面中尺度輻合線,輻合線附近強的水平溫度梯度在輻合抬升觸發下極易形成初始對流,而地面中尺度輻合線的長時間穩定維持及地形抬升作用,使得降水系統在陸川、博白一帶不斷發展和維持,造成了極端累計降水。
4 中尺度對流系統特征分析
4.1 衛星資料分析
通過FY-4A紅外云圖分析可知,中-β尺度對流系統MCS是造成這次強降水過程的主要系統。10日清晨(圖6a),桂東南一帶中尺度輻合線附近開始有零星中-γ尺度對流單體生成,小時雨強在20~40mm·h-1;其后08—10時(圖6b、6c、6d),對流單體在原地不斷發展并合并增強,云體面積持續膨脹,-32℃冷云區面積從4773 km2擴大至13428 km2,最低云頂亮溫從-61℃迅速降低至-76℃,造成東面的陸川站連續兩個時次出現超過60mm·h-1的雨強。與此同時,西側有對流云團逐漸東移靠近,11時(圖6e),兩個云團合并在原地增強發展,-32℃冷云區面積進一步擴大至38743 km2,最低云頂亮溫維持在-76℃,12時(圖6f)形成中-β尺度的MCS,10—12時,降水中心區的小時雨強均超過了70mm·h-1。

圖6 5月10日FY-4A氣象衛星IR1演變示意
4.2 雷達資料分析
應用玉林新一代天氣雷達逐6 min觀測資料對2018年5月10日桂東南極端暴雨的對流系統階段性演變過程和結構特征進行分析,全過程可分為3個主要階段。
第一階段是對流初生和發展階段。雷達組合反射率演變表明,10日04時左右在玉林市陸川、博白附近以及欽州市浦北附近分別開始有兩簇由若干對流組成的對流云團在原地生成,08:02已迅速發展成熟(圖7a),回波強度在35~50 dBZ;對應該時刻的速度圖(圖8a)上,與浦北這個云團對應有一條中尺度輻合線,陸川、博白對應的有若干小尺度的逆風區。陳鮑發[15]研究表明,逆風區為前方輻合上升、后方下沉的渦管結構,它不僅是暴雨判據,也是強對流天氣的判據。本階段中尺度輻合線和逆風區的存在說明有中小尺度的擾動輻合使得對流單體得到發展。09時,雷達反射率因子增強,最強回波超過55 dBZ,在此期間陸川站的降水達到了67.5 mm·h-1,與此同時,西面云團也緩慢東移靠近東面云團。
第二階段為浦北—博白東西向帶狀回波強降水階段。10時(圖7b),東西2個云團相互靠近合并發展,形成一條呈東西向的帶狀回波,降水云團得到明顯增強,回波強度在45~55 dBZ,對應該時刻的速度圖上(圖8b),在陸川和博白之間存在一個明顯中尺度氣旋性輻合,其明顯的旋轉流場帶來的輻合是非常有利于降水的增強和維持。此外,在西面云團緩慢向東移的過程中,其移向與回波帶的走向基本平行,形成了“列車”效應,造成浦北—博白一帶的強降水。
第三階段為回波帶與弓形回波合并發展階段。11時雷達反射率因子圖上顯示,在回波帶的西南面有一條弓形回波逐漸靠近,隨著弓形回波的靠近,博白附近的降水回波得到加強。11:21(圖7c),弓形回波移近,博白附近的降水回波強度在45~50 dBZ,且>45 dBZ回波范圍增大,此時降水強度達到最大(5 min雨強達到13mm),這可能是隨著弓形回波的移近,弓形回波前側的中尺度低壓使得回波得到輻合加強,從而增強上升運動,增大降水效率。對應該時刻的速度圖上(圖8c)也表現出在博白附近的強降水回波區域存在中尺度氣旋性輻合,此時出現了過程最大小時雨強94.2 mm·h-1。12時以后,隨著弓形回波與強回波合并,形成了一條東北—西南向的線狀回波向東南方向移動并逐漸移出廣西,過程降水趨于結束。

圖7 5月10日廣西玉林新一代天氣雷達組合放射率因子

圖8 5月10日廣西玉林新一代天氣雷達1.5°仰角徑向速度
對產生最強降水回波沿徑向213°進行垂直剖面(圖9),發現該降水回波反射率因子強度不是很強(圖9a),最大僅為45~50 dBZ,強回波分布在6 km高度以下、處于0℃層高度以下,回波質心較低且接地,呈現出明顯的低質心降水回波特征,這種低質心降水回波往往能夠產生很高的降水效率。對應該時刻的徑向速度圖上(圖9b),中低層存在明顯的入流,這種上升入流氣流使得垂直上升運動加強,有利于強降水的發生。

圖9 5月10日11:21廣西玉林新一代天氣雷達沿暴雨附近垂直剖面
5 可預報性分析
本次過程主、客觀預報在24 h降水量級上明顯偏小。廣西氣象臺在24 h預報中只在廣西南部報了部分地區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量級。ECMWF、Japan等全球模式及中國區域模式Grapes中尺度模式、華東區域模式和華南模式對陸川、博白、浦北3個國家站的降水量級預報(圖10)較實況偏小,表明不論是全球模式還是中尺度模式,確定性模式預報對這次大暴雨過程尚缺乏直接預報能力。

圖10 5月8日20時起報5月9日20時—10日20時各家全球模式(a)和中尺度模式對陸川、博白、浦北的雨量預報(b)結論對比
全球模式ECMWF(5月8日20時起報)的24 h降水預報量級達到大暴雨,過程量級與實況接近,但強降水中心落區有偏差,位置較實況偏西偏北超過100 km。進一步對該模式的預報能力進行跟蹤對比,發現8日20時起報的10日08時預報場的500、700 hPa上成功預報出廣西南部上空有短波槽活動、槽的位置與實況較為吻合。925 hPa切變線也與實況基本一致,但是切變線東南側的廣東西南部一帶的模式風場(圖11a)預報東南風風速僅為10 m·s-1,較實況12 m·s-1偏弱,很可能就是這個風速預報偏弱的原因最終導致了模式系統對風速輻合強度以及由此造成的對流上升運動強度、云系發展的程度及可能帶來的降水量級預報偏弱。此外,對應時次地面圖上(圖11b),北方弱冷空氣的實況影響勢力較模式預報結果更為明顯、冷空氣南下緯度也更為偏南,即地面中尺度輻合線的實況位置南壓到了具有特殊喇叭口地形的陸川、博白一帶,而模式地面場的輻合線不明顯且系統影響偏晚。另外模式對地形的刻畫以及邊界層和地形共同作用的模擬效果也不理想,使得實況中東南氣流輻合和地形抬升作用的共同影響導致的過程降雨增幅未能預報出來。因此,在實際工作中,預報員應敏銳捕捉到這種預報場與實況的偏差并及時根據模式前期的評估進行適時訂正,同時疊加地形,將風場與局地地形地貌結合分析,對降水落區和量級進行訂正預報,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過程預報的準確率。

圖11 10日08時925 hPa實況與對應時刻9日08時起報預報對比(a)和地面實況與預報對比(b)
此外,在9日08時起報的預報中,華東快速同化模式成功預報出廣西東南部在10日08—20時將出現明顯的大暴雨,強降雨中心也由早前預報的桂西北調整到桂東南區域,呈現出較好的預報能力,這體現出循環同化最新實況觀測資料能夠顯著改善模式初始場、提高局地極端強降水過程預報效果。遺憾的是,盡管華東模式預報在滾動更新預報中呈現出此次過程廣西東南部將出現大暴雨,但并未引起值班業務員的足夠重視、未在發布預報中予以有效采用。
綜上所述,提高類似過程可預報性的可行做法如圖12。首先,在中短期時效內對比分析各家全球數值模式預報結果,若發現有一家或多家產品呈現出異常量級,應引起值班預報員足夠的警覺。進而,須細致分析一兩種在業務中表現較為穩定的數值模式(如ECMWF)產品,辨析其預報出的天氣尺度背景場、中小尺度環境場以及關鍵影響系統是否與最新實況觀測資料有偏差?若存在明顯偏差,應及時根據模式前期評估結果進行適時且適當的落區和量級訂正。最后,在短時臨近預報上要充分利用中尺度數值模式(如Grapes_meso、華東數值模式等)的輸出結果,參考其反映出的中尺度影響系統信息及各物理量場的極端值表現,同時還要重視局地地形地貌特征在地面及邊界層天氣形勢分析和預報訂正中的重要作用、在預報結論中疊加上地形因素影響,從而更加精細化和精準地做出短時臨近預報訂正決策。

圖12 局地突發強對流過程可預報性分析流程
6 結論
對2018年5月10日短波東傳形勢下廣西東南部暴雨過程的綜合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1)本次過程高層輻散條件不明顯,但中低層環流形勢有利,尤其是具有高壓后部“回流”降水形勢、配合加強的超低空東南氣流及地形抬升作用導致暴雨明顯增幅。
(2)水汽輸送、水汽輻合在低層集中的特征明顯,高溫、高濕環境條件有利。在地面中尺度輻合線抬升觸發下,有利于產生低質心的對流風暴,提升降雨效率。
(3)強的水平溫度梯度有利于邊界層垂直風切變增強,在輻合抬升運動觸發下易引發初始對流;而地面輻合線的長時間穩定維持使得降水回波在陸川、博白一帶不斷發展和維持,雷達回波形成“列車”效應,是造成暴雨天氣的直接原因。
(4)強回波分布在<6 km高度的0℃層高度以下,為低質心、高效率的暖云降水。徑向速度圖上有明顯的輻合、使得垂直上升運動加強,有利于強降水單體發生發展。
(5)ECMWF、Japan等全球數值模式對天氣尺度背景場把握較好,GRAPES、華東模式等中尺度模式能夠提供類似系統形成、發展等有價值的參考信息。通過中尺度模式產品發現暴雨天氣過程苗頭,及時根據同化最新實況觀測資料的模式預報結論進行系統位置和降水量級精細化訂正,并注意疊加局地地形地貌特征信息來輔助短時臨近預報訂正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