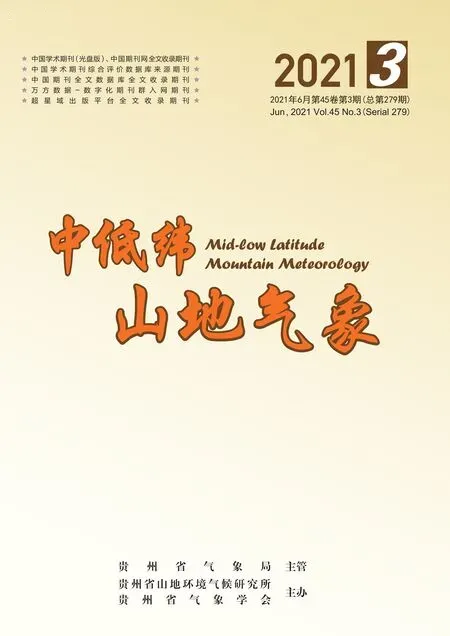山東一次秋季罕見強雷暴成因分析
陳華凱,呂偉綺,王逸鵬
(山東省德州市氣象局,山東 德州 253078)
0 引言
雷暴是山東主要的災害性天氣之一,秋季是一年之中雷暴日數較少的季節。進入秋季后,受到大陸冷高壓影響,大氣層結較為穩定,暖濕氣流減弱,對流天氣明顯減少。有時秋季溫度偏高,暖濕空氣較為強盛,當有強冷空氣東移南下,低層暖濕空氣就會被迫抬升,形成對流不穩定,就會產生雷暴天氣[1-5]。隨著全球氣候變暖,極端天氣頻發,雷暴終日有延后的趨勢,秋季雷暴發生率更是有所增長。針對雷暴天氣,許多學者做過很多有意義的研究[6-14]。山東的雷暴天氣主要集中在5—8月,秋季的區域性強雷暴天氣較為罕見,容易被忽視,更易給人民生產生活帶來嚴重影響,因此加強山東秋季雷暴的成因分析研究十分必要。本文利用ERA5逐小時再分析資料、常規觀測資料、FY-2G衛星資料、閃電定位資料及雷達資料對此次山東強雷暴過程進行診斷分析,以期積累此類天氣的預報經驗。
1 天氣背景分析
2019年11月2日20時—3日06時山東出現了強雷暴天氣,并伴有短時強降水,此次強雷暴過程打破了山東魯西北地區雷暴終日記錄,是一次罕見的秋季強對流天氣。11月2日08時500 hPa高空圖上寬廣深厚的高空槽從河套伸至華北,山東位于槽前西南氣流中,高原東部有南支槽活動。高空槽后的西北氣流引導中高層干冷空氣從內蒙古南下到華北地區,700 hPa和850 hPa上山西到河北中部均存在輻合切變線,850 hPa黃淮到華北南部有大于等于6 ℃的暖區,魯西南到魯西北有大于等于8 ℃的暖脊。低層受小尺度暖空氣團和日變化影響,午后熱力條件有所加強,出現相對暖而干的狀態,加強了不穩定能量的累積。20時500 hPa高空槽東移與北上的南支槽合并加強發展,700 hPa(圖1a)山東西部有明顯冷切,850 hPa(圖1b)有低渦切變線。隨著槽后冷空氣補充南下,提供動力抬升條件,同時又加強了不穩定層結發展,魯西北地區從20時開始出現雷暴天氣。由于缺少低空急流水汽輸送,導致對流區域內整層濕度相對較低,不利于強雷暴天氣的長時間維持,到3日00時強雷暴天氣結束,3日08時系統基本已移出山東,降水過程結束。

圖1 2019年11月2日20時500 hPa高度場和700 hPa風場(a)、850 hPa的風場和溫度場(b)
2日08時地面圖上(圖略),內蒙古、東北和華北被冷性高壓控制,鋒面位于內蒙和河北交界處,鋒區呈緯向分布,高壓前部東北氣流強盛,山東位于高壓前部,14—20時地面倒槽發展北伸,山東處于地面倒槽頂部,暖濕空氣被迫抬升,出現輻合上升運動,促使不穩定能量得以釋放,導致強雷暴天氣發生。
2 物理量場分析
2.1 熱力條件
2.1.1 不穩定層結 850 hPa和500 hPa溫差是秋季強雷暴發生的一個重要條件,溫差值越大,強對流越容易發生。11月2日20時,500 hPa與850 hPa的溫度場在山東地區狀態分布剛好相反,500 hPa冷槽對應著850 hPa暖脊。高空槽后有-20 ℃冷中心相配合。同時850 hPa上有8 ℃暖中心在魯中到魯西北一帶,高低層溫差大于等于26 ℃(圖2a)。中高層空氣干冷,低層暖濕,形成層結不穩定,有利于強雷暴天氣的發生發展。2日21時高空槽逐漸東移,850 hPa和500 hPa溫差仍然較大(圖2b),不穩定層結仍然穩定維持,與山東出現大范圍強雷暴天氣的時空范圍基本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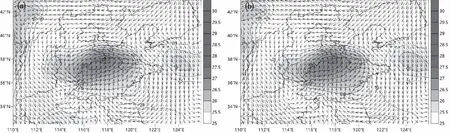
圖2 2019年11月2日20時(a)、21時(b)850 hPa和500 hPa溫差及850 hPa風場分布圖
2.1.2 假相當位溫 θse是氣壓、溫度和濕度的函數,反應了大氣的溫濕特征,其高能舌位置與強對流天氣密切相關。從假相當位溫850 hPa水平分布來看(圖3a),11月2日20時魯西南地區存在一個西南至東北向的θse高能舌并逐漸增強向北伸,在低空偏南氣流的作用下,不穩定能量持續向魯西北輸送,魯西北處于θse大值區,θse值為305~310 K,山東夏季強雷暴發生時θse值一般為320~330 K[15],θse大值區較夏季強雷暴值偏小,3日00時(圖3b)高能舌逐漸減弱,魯西北地區強雷暴天氣也基本結束。θse水平分布中高能舌的位置跟強雷暴發生的區域對應較好。

圖3 2019年11月2日20時(a)和3日00時(b)850 hPa假相當位溫水平分布圖(單位:K)
2.2 動力條件
上升運動是形成強雷暴天氣的主要因子。從2日20時700 hPa的垂直速度圖(圖4a)上可以看出山東北部地區有一個-1 Pa·s-1垂直速度大值區,850 hPa(圖4b)有一個-0.8 Pa·s-1垂直速度大值區,可見對流層輻合上升運動明顯,這一地區正是位于魯西北地區。2日22時700 hPa和850 hPa(圖略)垂直速度大值區依次增大至-1.4 Pa·s-1,上升運動得到進一步加強,與山東出現強雷暴天氣的落區基本一致。山東夏季強雷暴發生時垂直速度值一般在-1.5~-2.5 Pa·s-1[15],可以看出秋季強雷暴垂直速度值較夏季偏大,上升運動較夏季偏小。

圖4 2019年11月2日20時700 hPa(a)和850 hPa(b)垂直速度水平分布圖(單位:Pa·s-1)
2.3 探空要素分析
分析11月2日08時和20時章丘探空站要素值(圖略)可以看出08時對流有效位能(CAPE)值較小,接近于0。但20時增大到161 J·kg-1,增大趨勢明顯,說明白天由于太陽輻射加熱作用使得熱力不穩定度增大,上升氣流強度增強明顯,有利于雷暴天氣的生成和發展。說明CAPE值的大值區或顯著增大區對強雷暴天氣有較好的指示作用[16]。2日抬升凝結高度(LCL)較低,08時和20時分別為864 hPa和865 hPa,說明需要的外力抬升作用較小,有利于雷暴天氣的發生。
3 衛星云圖分析
晴天積雨云系表示大氣層級的狀況,一天內它出現的時間越早,積云云團越大,說明大氣層結越不穩定,越有利于強對流天氣的發生[17]。亮溫云圖能較好地展現雷暴云團的發展演變[18-19]。11月2日20時在魯西北地區上空有雷暴云團發展,到22時雷暴云團加強發展并由西南向偏東北方向移動,低層入流區一直是發展的。從云圖可看出(圖5a、5b),20時魯西北地區都處于TBB≤-22 ℃冷云區中,-30 ℃的冷中心位于魯西北東南部,22時是雷暴云團發展最強盛的時候,TBB值為-32 ℃的冷云蓋范圍達到最大,中心主要位于德州到濱州一帶。此時雷暴云團東南部等溫線比較密集,位于冷云蓋前方的溫度梯度較大,雷暴活動較為劇烈。3日00時-30 ℃的TBB大值中心移出魯西北地區,強度也隨之減弱。山東夏季強雷暴發生時TBB值一般在-40~-60 ℃[20],因此可看出秋季強雷暴發生所需的TBB值較夏季偏高,對流云團高度偏低。魯西北地區雷暴起止時間為2日20時—3日00時,說明雷暴發生在對流云團發展最旺盛的時刻,強雷暴主要發生在雷暴云團前方TBB梯度最大區域內,隨著冷云蓋的移出,本次過程結束。

圖5 2019年11月2日20時(a)和22時(b)衛星云圖TBB(單位:℃)和地閃的疊加分布(“+”為正地閃,“-”為負地閃)
4 雷達產品分析
4.1 反射率因子
濟南多普勒雷達顯示(圖略),11月2日20時04分在河北衡水和山東德州、聊城交界處附近一小片線狀對流回波生成,并不斷發展向東南方向移動。20時59分該回波移到濱州、德州、聊城一帶,強度逐漸加強范圍不斷增大,以上地區先后出現強雷暴天氣,并伴有短時強降水。回波中心反射率達到45 dBz以上并穩定維持,強回波繼續向東南方向移動,一直維持到3日00時左右,此后強回波中心減弱為35 dBz,雷暴天氣結束,但強降水仍然持續,這與實況出現的強雷暴落區一致。
4.2 風廓線
雷達風廓線(VWP)產品顯示,11月2日20—22時(圖6a、6b),850 hPa以下為東風—東南風,850~700 hPa為西南風,500 hPa以上為偏西風,風向隨高度呈順時針旋轉。850 hPa風速約為6 m/s,500 hPa為14m/s,850~500 hPa垂直風切變達8 m/s。1.5~5 km存在非常強的垂直風切變,有利于增強動力抬升機制,對秋季雷暴預報有很好的指示作用。

圖6 2019年11月2日20時59分(a)、21時54分(b)風廓線(VWP)產品
5 結論
①此次強雷暴過程是高空槽東移,中高層干冷空氣入侵和地面輻合線抬升觸發低層不穩定能量釋放造成的,這種上干下濕的大氣層結特征,有利于強雷暴發生發展。
②850 hPa和500 hPa溫差是秋季強雷暴生成的一個重要條件,溫差值越大,強對流越容易發生,此次過程T850-T500≥26 ℃,有利于強雷暴天氣產生和發展。
③θse水平分布中高能舌的位置跟強雷暴發生的區域對應較好。探空資料分析表明CAPE值的大值區或顯著增大區對強雷暴天氣有較好的相關性。
④秋季強對流發生時對流云團高度較夏季偏低,云頂亮溫較夏季偏高。山東夏季強雷暴發生時TBB一般在-40~-60 ℃,此次雷暴過程發生時云頂溫度TBB在-22~-32 ℃,強雷暴主要位于冷云蓋前方TBB梯度大值區域內。
⑤雷達回波中心反射率因子在45 dBz以上,1.5~5 km存在非常強的垂直風切變,對秋季雷暴預報有很好的指示作用。
⑥本文僅對山東一次秋季強雷暴天氣成因進行診斷分析并得到一些初步結論,但是結論的普遍性仍需要更多的個例來進一步證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