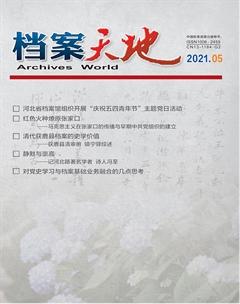靜默與崇高
王東梅
馮至,原名馮承植,字君培,河北省涿州市人。
他是“五四”時期著名的“淺草”社和“沉鐘”社成員,在30年代曾被魯迅譽為“中國最為杰出的抒情詩人”。他的散文和小說也有獨特的成就。
他是我國久負盛名的德語文學專家,對中國古典文學也有專攻,是資深的杜甫專家。他對新中國的外語教學,外國文學的研究和文藝創作,都作出了貢獻,曾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等職。
但是,“一切的形容,一切喧囂”,到他身邊,有的就化成了他的“靜默”。
“何曾一語創新聲”
馮至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破土萌生的詩人。1920年, 15歲的馮至就與同學辦起了《青年》雜志,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邊緣搖旗吶喊,開始了70年的文學生涯。翌年,創作了《綠衣人》,反映了他16歲少年過早的成熟和對社會人生的憂慮。不久,他進入“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北京大學學習,同時以極大的興趣寫詩(還寫散文、小說、翻譯和評論),反映內心的苦悶和彷徨,抒寫對愛情的憧憬與渴望,富有情韻,自領風騷,受到了文學史家王瑤等的好評。魯迅更是獨具慧眼,稱馮至是“中國最為杰出的抒情詩人”。
40年代初,馮至創作了別具一格的《十四行集》,被朱自清稱為“新詩的中年”(《新詩雜話》)。如今,它已被譯成英、德、意、日、荷蘭、瑞典等多種文字。
50年代開始,馮至以滿腔的熱情贊美建國后的新氣象和忘我勞動的人民。從1985年起,他繼續進行那一貫的對人生和宇宙的探索,而且毫不留情地抨擊了腐敗和封建,內容題材更有開拓和創新。
馮至還是一個獨具特色的散文家。比起他的詩,馮至的散文更能反映他的心靈和風格。真誠、純潔、有情韻、有意境,是詩化的散文,代表作是早期的書信和40年代的《山水》。《烏鴉——給M弟》情真意濃,催人淚下;《山水》是另一種形式的《十四行集》,是詩人當時人生境界和文藝思想的反映,在文化史的意義上極有價值。
作為一個小說家,馮至的作品太少,但手法和技巧卻領一代之先——以情緒的流動為中心,注意情境的渲染。從《仲尼之將喪》《伯牛之有疾》到40年代的《伍子胥》等,你會感到80年代的現代派熱,其實在他的小說、詩歌里早已“熱”過。
但是,他自己卻說:“工力此生多浪費,何曾一語創新聲”。
“我不是學者”
經過“五四”洗禮的作家們,大都“學者化”,馮至亦不例外,學貫中西,博古通今。
青年時期他在北京大學度過6年的美好時光,雖然專業為德文,卻選修了國文系的很多課程,認真地聽魯迅、沈尹默、黃節等名師的課。1930年又去德國留學5年,1935年獲取文學博士學位后回國。
抗戰以后,他即開始了對杜甫的研究,80年代初,完成了我國第一部《杜甫傳》——新文學史上較早的文學家傳記。60年代初,他以北大西語系主任身份負責中央宣傳部、教育部主持的高校文科教材中文組的工作。
與杜甫研究差不多同時,他又攻研歌德,1948年出版了《歌德論述》一書。此后,在此基礎上,在恩格斯觀點的影響下,經過近40年的努力,又寫下了一系列閃耀著唯物主義思想光輝和學識光芒的論文,后結集為《論歌德》出版。
還在北大學習時,馮至就開始了翻譯生涯。曾翻譯過歌德、里爾克、海涅、尼采、席勒等著名的德語文學家、思想家的作品近百萬字,寫下了精深的論文。他還是《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文學》卷的編委會主任。
但他卻說:“我不是學者,沒有寫過一定水平的學術著作”,更否認自己是個翻譯家。
“當時只道是尋常”
馮至集詩人、散文家、杜甫專家、德語文學專家和翻譯家于一身,在國內國際獲得了很高的聲譽。但是他卻說:“自念生平,沒有參與過轟轟烈烈的事業,沒有寫過傳誦一時的文章”。他喜歡用清人納蘭性德詞中的一句來概括自己的平凡:“當時只道是尋常”。凡是熟識他的人都會發覺他誠摯寬厚的人品和虛懷若谷、嚴謹嚴肅的學風。
《歌德論述》在當時已達到很高的水準,但他在序中卻說:“不是研究,沒有創見,只求沒有曲解和誤解”。他對魯迅無限景仰,但從不提起魯迅對他的評價,而當別人提起時,他總是誠懇地說:“我不是杰出的抒情詩人,更不是最杰出的。你千萬不要這樣說。”對研究他的人,他先是勸你“不要花時間,不值得”,而當你繼續堅持時,又反復提醒你要客觀,不要溢美,不要影響到別人。當你按響門鈴后,他總是及時地開門,和善地說:“請進”,把你引到客廳,讓座,還親自為你斟上一杯茶。然后,他平等平靜地與你說話,接受你的提問和采訪。你始終感覺不到自己是在與一個名人談話,倒象與自己的父輩、祖父輩,在夕陽西下時,坐在院子里,隨便地對話。
《論歌德》是他幾十年歌德研究的結晶,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但是,他在書前卻用1萬多字的篇幅,敘述了自己歌德研究的歷史,分析不同時期的局限,對不能進一步深入研究表示遺憾。學者的真知灼見,學者的人格和品格,都可見一斑。
對待文學和人本身,他崇尚的實際也是擺脫世俗浸染、能夠反映本來面目的真實。他說,“詩人之可貴,不在于幾首好詩,而在于用詩證明了他的真誠的為人的態度。”不難看出,在馮至眼中,立人高于作文,作文反映立人,于是,有了為人所稱道的人品和學風。
“等待著新的眺望”
“五四”以來的知識分子對光明的向往,真理的追求,是比較執著的,但大都經過長期的跋涉甚至曲折。在上世紀20年代,馮至不滿現實,卻又目無光明,不知路在何方。但在魯迅、楊晦等師友的幫助下,他又無時無刻不與自己的悲觀作斗爭,不甘被黑暗所吞沒。偉大的抗日戰爭和西南聯大的民主運動,終于喚醒了馮至。從1942年起,他越來越關注現實和社會,開始用雜文來抨擊時弊,后來,更冒著風險,夜間收留一個遭到通緝的學生。1945年,在著名的“一二·一”運動中,他與進步師生一道,同國民黨反動派鎮壓學生民主運動的行為作斗爭。慘案發生后,他不顧生命危險,寫出了著名的詩《招魂》——
……
正義,快快地到來,
自由,快快地到來,
光明,快快地到來。
當時,這首詩就被鐫刻在四烈士的墓碑上。
抗戰以后,馮至又積極投入北平人民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和爭民主的運動中。1947年,他又寫了一首盼望新中國的長詩《那時一個中年人述說“五四”以后的那幾年》:
……
如今走了20多年,
卻經過無數的歧途與分手;
如今走了20多年,
看見了無數的死亡與殺戮。
那時追求的在什么地方?
如今的平原和天空,
依然映照著5月的陽光;
如今的平原和天空,
依然等待著新的眺望。
他在回憶錄中說,那時雖然說不清楚新中國是什么樣子,但是總覺得將來比現在好,共產黨比國民黨好。正是基于這種心理,第二年他在有名的“四月風暴”中,站到了與國民黨反動派斗爭的前列。
為鎮壓學生運動,1948年4月7日,北平警備司令部下令逮捕學生自治會理事柯在鑠等12人,限校方于次日中午12時前交人,否則將派兵包圍。這天,學生們齊集北大民主廣場,圍成一層層保衛圈,以血肉之軀,以獻身中國民主運動的大無畏氣概,把12人圍護起來,高喊“一人被捕,全體坐牢;一人受審,全體投案!”的口號。在這緊急關頭,馮至受全體教授的委托,來到了學生中間,說“我們全體教授誓死支持你們的要求!”這時,馮至已和廣大人民群眾在一起,迎接新中國的誕生。
“眼昏昏,心里更光明”
歌德說過,老人永遠是個李爾王,意思是說老人思想僵化,頭腦糊涂。但馮至卻說:
我不愿說老人是個李爾王,
也不愿看癡呆的老壽星,
我欣賞浮士德失明后的一句話:
眼昏昏,心里更光明。
這是他患白內障后所作,雖然有自我解嘲的味道,但卻真實地反映了年過古稀的馮至在新時期改革大潮中的表現。
粉碎“四人幫”后,馮至壯心不已,又熱情地投入了外國文學研究的工作。在很短的時間內,即恢復了《世界文學》,主持制訂了新時期最早的全國外國文學研究工作規劃,修訂了《馬克思文藝理論叢書》等三套著名叢書的選目和計劃,主持了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文學”卷的編著工作,還頻頻出席國內國際有關文學創作、研究、翻譯的各種會議。即使在退下來以后,仍一如往日,積極工作,努力著述、翻譯和創作,參加和主持有關的文藝活動。
他是一個老詩人,在中國傳統的詩歌土壤里長大,受到“五四”新詩的洗禮,曾受到歐洲19世紀浪漫主義詩歌的影響 ,他以熱情又冷靜的態度和成熟的眼光對待五光十色的新詩及其評論,不以勢壓人,不嘩眾取寵。
馮至是一個外國文學專家,也是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一起成長的現代作家, 學識深邃,經驗豐富,但從不亂發議論,特別是在各種文藝思潮不加選擇地紛擁而來之時,他能冷靜地對待這些思潮,提出自己經過深思熟慮的看法。早在1983年,當各種“新名詞”開始狂轟濫炸之時,他在“中國現代文學思潮流派問題學術討論會”上提出“要慎重地使用西方的文學術語”,不要強不知以為知;他又反對極端和偏狹,說“1958年毛主席提出‘兩結合,是很有意義的。”他認為現實主義是多種多樣的,不能亂貼標簽;對于文學與現實、生活的關系,他不顧各種新理論的沖擊,從文學史的角度論證,無論是“反映”“闡釋”還是“理想”“都離不開現實”,各種創作方法都是自然產生的,互有聯系的,“文學上的任何主義強調到了極端,到了絕對化,就會走向反面”“象征本是文學的一個重要因素……可是提倡象征主義,把象征絕對化了,盡在聯想、比喻上耍把戲,這樣喧賓奪主,也就丟掉了現實”。
他是1956年入黨的知識分子黨員,解放前不僅在德國留過學,還曾到過歐洲亞洲許多國家,解放后又曾十幾次到歐洲、亞洲、北美訪問,這使他有所比較和鑒別,認定祖國就是母親,希望在于改革。1984年,他曾參觀珠江三角洲,目睹了改革的巨大成就,情不自禁地寫了《銀湖夜思》一文,不僅歌頌改革,還以一個離國35年回到大陸的朋友的親身感受,說明改革開放的正確。在文中還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性,特別強調要防止和反對海外及港澳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
1987年,經歷了無數個寒暑和風雨的老人,在醫院的病床上,又一次地把自己與祖國聯系在一起:
我曾喝過海外的水,
總象是一條魚陷入泥沙;
我曾踏過異國的土地,
總象是斷線的風箏飄浮在空際。
好也罷,不好也罷,
只有一句話——離不開你。
傾訴了對祖國深沉的愛。就在這一年,他把聯邦德國國際文化協會獎勵的1萬馬克全部獻出,作為德語文學獎基金,以獎掖后進,促進與德國文化交流事業的發展。而對于各種腐敗現象,他更是表現了前所未有的憤慨,在晚年并不很多的詩中從不同的角度予以揭露和抨擊,如《神鬼和金錢》《我痛苦》《我不忍》《剪彩》等,都深刻地反映了他對腐敗現象的不滿,表現了一個作家、學者和教授對民族前進中問題的關心和憂慮;表現了一個老知識分子對改革事業的負責精神。
1989年8月至10月中旬,馮至因患胸膜炎,住北京協和醫院治療。1993年2月22日,于北京去世。
惟其靜默,也才崇高。與那些聲名顯赫的人相比,馮至的名字并不被一般的中國人所熟知。但是,他的創作,他的學術造詣,他的人品,他的學風,他對祖國的感情,他對人生道路的抉擇,卻很能代表“五四”以來渴望祖國走向現代化的知識分子。崇高,在靜默中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