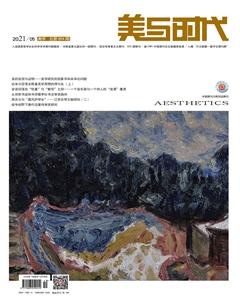戰爭視野下唐代邊塞詩審美研究
摘? 要:戰爭是一個殘酷與嚴肅的主題。從文學發生的角度來看,詩則是優美而生動的文體。唐代具有開放的文化環境,無論是統治者還是文人都或多或少有著“一視華夷”的包納胸襟,因而唐代的文學也相較于前朝有著更為博大與寬厚的格局與境界。但與此同時,一個強大的帝國勢必面臨嚴峻的外患邊防壓力。經年累月的戰事,與文人遠征的仕途軌跡,使得唐代產生了蔚為壯觀的邊塞詩。對于唐代邊塞詩的研究往往集中于對邊塞詩人(如高適、岑參、王昌齡等)的個人情感與征戰歷程的考察,以及對邊塞詩中某個意象的深掘,卻鮮有對邊塞詩描繪的戰爭意象進行審美研究。戰爭視野下并兼用戰爭美學的理論成果,從戰爭這一文化現象來觀照唐代邊塞詩的審美路徑及審美對象的細節考察,可以發現邊塞詩相較于其他題材詩歌所具有的獨特美感。
關鍵詞:戰爭;邊塞詩;唐代;審美研究
一、邊塞詩概念解析
(一)中國傳統的邊塞與邊塞觀念
論及邊塞詩的產生與發展,首先要界定中國文化中傳統的邊塞與邊塞觀念。中國的歷史疆域廣袤而遼闊,而中國傳統上的族群認同又鞏固和強化著疆域的所指,也就是邊界。正如王明珂在《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一書中所認同的法國學者弗雷德里克·巴斯的觀點:“造成族群最主要的是它的‘邊界,而非包括語言、文化、血統等在內的‘內涵。”[1]12王明珂亦在書中從一種地理發現的視角詮釋了邊界與國家文化間的關系,而維護這種邊界的,正是邊塞。
“邊塞”從詞義的理解上有二:一為對邊疆具體要塞城池的特指,二為對國境邊疆的泛指。無論哪一個,其鮮明的地理含義都貫穿其中。而邊塞與邊塞觀念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緣起,與“封疆”和“城邑”有著一定的關系。許慎《說文解字》:“邊,行垂崖也”“塞,隔也”。由此可見最初“邊”“塞”所指不同。《史記·三王世家》云:“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2]如此敘述,才逐漸將“邊塞”二字合用,邊塞逐漸成為了國家邊境地區(尤以戰爭區域)的特指。
邊塞一詞從產生時,便與戰爭這一特殊歷史存在相結合,因而中國傳統的邊塞觀念,也一定與慘烈的對外戰爭有著密切的聯系。類如匈奴等歷史上的游牧民族,經常對農耕民族進行襲擾掠奪。而立足中原的華夏文明,其安定一隅的軍事思維也決定了其對邊疆的策略以駐守為主、進攻為輔,遂能產生較為強烈的邊塞觀念。而這種觀念在中國歷史上最為形象的展現,便是長城的誕生。
因此,正是由于中國在歷史上對邊塞這一軍事事物的長期需求,導致了邊塞觀念的不斷加強,而經年固守的邊塞,也為前往(或未前往)的文人帶來了豐厚的文學及審美素材。運用這些素材創作出的便是邊塞詩歌。
(二)邊塞詩中地理性的模糊與民族性的清晰
邊塞詩中對于地理性和民族性的描繪手法是有區別的,相對而言,地理性略模糊,而其表達的民族性卻很清晰。邊塞詩的形成最早可追至《詩經》,如《出車》《無衣》《鴇羽》《六月》《漸漸之石》《伯兮》《殷其雷》《雄雉》《甫田》《揚之水》《君子于役》等。按《唐代邊塞詩傳》一書中看法,周宣王時期是集中產生邊塞詩的年代,而《詩經》中的這類作品眾多,其描述的戎旅地點也多在偏遠的邊疆,但是這種對于邊疆的地理刻畫往往是不具體的[3]。如《小雅·出車》在敘述其戰役經過時如此寫道:“我出我車,于彼牧矣”“天子命我,城彼朔方”。這其中“彼牧”指的是郊外,“朔方”指的是北方,但是均沒有具體的地理名稱,后人只能想象這場戰爭的準備由郊外開始,而對抗的則主要是來自北方的敵人。
邊塞詩至唐時,進入了快速發展期,但這種地理模糊的情況依然存在。如在唐時作為戰略要地的“陰山”“薊北”“遼東”在使用時經常混用,“樓蘭”“燕然”“龍城”等漢時稱呼也經常出現于唐詩之中。如虞世南《從軍行》“冀馬樓蘭將,燕犀上谷兵”,王維《使至塞上》“蕭關逢候騎,都護在燕然”,王建《隴頭水》“謂是西流入蒲海,還聞北去繞龍城”等均體現出了這一點。邊塞詩的地理模糊現象,有其成因,一是邊塞詩中對于戰爭的描述多是詩人對于邊塞戰況的想象而非親歷,而從文學的角度來說,沿用漢制地名也更易呈對偶之勢。如果還有一種成因,那即是模糊的地理性更容易造成邊塞生活與征戰的神秘與詩歌的意出象外。因為戰爭是無情而殘酷的,詩歌則是優美且具有意境的,一首邊塞詩不該成為或僅成為一場戰爭的傷亡與勝負戰報。
至于邊塞詩中的民族性,主要體現在詩中對敵我的情感分明。而這之中隱含的則是華夏民族自始至終對自身抱有的自豪認同。以漢代為例,“漢代華夏對四方異族的描述,也就是以‘哪些人不是華夏來定義‘誰是華夏”[1]230。正是由于這種強烈的自我民族認同,中國邊塞詩才得以形成了強烈且清晰的民族性。即使是文化開明、擁有著外來民族血統的李氏家族治下的唐朝,其產生的邊塞詩中對戰爭的描述也從來是敵我分明的。這種民族性的分明與地理感的模糊,使得唐代的邊塞詩同樣具有著一以貫之的獨特性,而只有從戰爭本身來探討其清晰與模糊的共存成因,才能構建出邊塞詩的戰爭視野輪廓。究其底,詩歌是文學,其文字描繪中地理性的模糊與民族性的清晰涉及到物質與意識在文藝作品中存在的基本方式。如西方《伊利亞特》及《奧德賽》這兩部古希臘長篇史詩中,也涉及到對戰爭細節的刻畫,但詩中所著重表達的,依然是傳說中人物面對戰爭時所展現出的可歌可泣的不屈精神。因此不論東方還是西方,描繪戰爭的詩歌都有著相似的著力點與模糊點。過于拘泥于對戰爭地理的精確定位,勢必會進一步對戰爭抱有冷靜與客觀的態度,如此一來,戰爭成為了物質拼殺的舞臺,而喪失了其酒神精神的依托。與此同時,由民族性引發的對立感則是十分鮮明的,正如《荷馬史詩》在西方文學中的重要地位,除卻因其涉及了古希臘歷史、地理、考古學和民俗學方面的重要知識,更因其詩中表現了西方文明在童年時期的國家與民族間的戰爭,這些戰爭的起承轉合或許披著神話外衣,但其核心依舊源于古希臘的民族精神。
(三)邊塞詩與戰爭的美學關系
一般來說,邊塞詩是以邊疆地區漢族軍民生活和自然風光為題材的詩,但其內核還是與戰爭本身有著更為直接的關系。戰爭作為創作背景在邊塞詩中往往以對戰場、兵戈和軍士三種對象的描繪加以體現。如王昌齡《塞下曲》中“飲馬度秋水,水寒風似刀”一句,其邊塞詩的性質主要是由詩中的“馬”“刀”等與戰爭有關的事物決定的。“馬”即是戰馬,“刀”即是戰刀,戰馬與戰刀這類兵戈之物隱喻了詩中的戰爭背景。雖然詩中亦展示著自然風光和時節氣候,但邊塞征戰的風貌寓于其中。而作為地理名稱的邊塞地于邊塞詩中的出現,也在強化著對戰場的側面刻畫。在王昌齡的《塞上曲》中有一句“從來幽并客,皆共塵沙老”,則展現了邊塞詩中戰場與兵士的形象。“幽”“并”二州為古來兵防要地,而那句“皆共塵沙老”意為衛國之軍人最終的結果都是要在戰場中老去。因此可以見得一隅,即邊塞詩中的美學意象往往需要通過戰場、兵戈與軍士來展現戰爭的嚴酷與殘烈。
筆者于《刀鋒之美:藝術媒介視域下的戰爭美學建構》一文中,曾經論述了戰爭與美學的一般性關系:戰爭與美,二者在實踐目的上并非殊途同歸,戰爭追求的是勝利,美則是“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4]。從這點來說,戰爭與美從功用性的追求上是存在出入的,但是不能單以此結論便否定戰爭與美學具有的聯系。從邊塞詩的美學表達中,不難發現邊塞詩描繪的戰爭是存在意境美的,如“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中體現出的壯美之情。這涉及中國古代文論及美學中“內心視象”的概念,張德林教授就“內心視象”的闡釋非常中肯,他認為,“視象,本來指客觀對象,主體用肉眼看得見的人和物,然而……只有用心靈的眼睛才能‘觀看得到,感覺得到”[5]。從這一點說,邊塞詩中所描繪的戰爭,已經與歷史上真正的戰爭屬于平行共存的狀態。由于戰爭的產生需要兩軍乃至多軍的持久對壘,而無論任何一方都有著各自對于戰爭的看法與執念,因此一場戰爭的客觀事實并不能成為邊塞詩歌創作時的唯一根據。在這種戰爭場域的調和下,詩人創作邊塞詩時完全存有個人的情感與看法,而這些情感與看法完全來自于詩人“內心視象”中的那場戰爭、那片戰場。但這種內心視象也絕非評論家不可捉摸的空中樓閣,因為文字是聯結“兩個戰爭”的最佳媒介,也因此張晶教授認為,“內心視象”存在于作品之中,是審美主體在意向性投射中產生于讀者腦海中的視覺影像[6]。
除卻帶有強烈寫實性質的邊塞詩,還有相當一部分邊塞詩中的戰爭不是真實的戰爭,而是審美主體的一種帶有美感的視覺成像,在這成像之中,戰爭追求的不再是單純的勝利。如柳宗元《唐鐃歌鼓吹曲十二篇》中,“烈烈旆其旗,熊虎雜龍蛇”一句便混淆了讀者內心視象中戰場的空間維度。此句描繪的并非戰場、兵戈乃至軍士,而是出征前我軍鋪張揮舞的旌旗,“烈烈”二字描繪了浩蕩揮舞的旌旗,卻沒有談及旌旗之下數以萬計的大軍,而“熊虎雜龍蛇”初一看會混淆其視象所對準的畫面,讓人誤認為是軍隊中雜糅了猛獸,而后畫面一轉,表明了其虎其蛇實乃軍旗上繡之圖案。以軍旗圖案這二維圖像,展示了三維之大軍,乃至保衛國家邊疆之戰必勝精神,可見邊塞詩中描繪的戰爭,完全是可以“境生于象外”的。
二、唐代邊塞詩的審美主體與其創作規律
如上所說,唐代邊塞詩的審美主體一般涉及戰場、兵戈與軍士,受中國古代詩歌的范式影響,邊塞詩中一般也蘊含著山水詩的清麗秀雅,但這也與創作者的具體心路歷程及其創作風格有關。鐘嶸于《詩品》序言中說道:“至于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7]鐘嶸的《詩品》較早對邊塞詩的創作內容及心路規律進行了概括,在他看來,詩人在面對戰爭,及戰爭帶來的一系列事物,如愛國、榮譽、死亡、媾和、親人故去等,其心靈被“感蕩”,其胸臆急需一個抒發的出口。而窺探這個出口,便能找出邊塞詩在美學上所形成的的一般創作規律。
唐代邊塞詩是一個多元交融的范疇,這種多元主要與唐朝這一時代由富足走向興盛、又從興盛走向衰亡有關。邊塞詩歌中的情懷對國家發展脈絡的走向感知更為細膩。一是國防安定是國家得以興盛的基礎,即便唐朝由盛轉衰的主要成因是安祿山、史思明的內亂,但唐朝在不同時期的邊防形勢亦不同;二是邊塞詩無論寫實還是寫意,詩人一定要將其創作融會于戰爭場域之中。
如著名的唐邊塞詩人岑參,在其早年隱居求學時作《高冠谷口招鄭鄠》,能有“澗花然暮雨,潭樹暖春云”這樣的生機盎然的詩句。但在從軍入邊后,這種盎然便成為了蕭然,如《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中的“瀚海闌干百丈冰,愁云慘淡萬里凝”,《磧中作》中的“今夜不知何處宿,平沙萬里絕人煙”,《經火山》中的“赤焰燒虜云,炎氛蒸塞空”,都與其早年詩作中的自然意象有所區別。岑參是一個細膩的詩人,也是一個真正到過邊塞的詩人,有過真實的軍旅經驗,便有了真實的心理感受。與中原相比,邊塞的風光更為雄奇壯美,但這種自然之壯美又何以與戰爭有著聯系?恰是岑參西行戍邊之職責,給了他在創作邊塞詩歌時一種更為形而上的精神。岑參戍邊之時,正是盛唐之際,那時的文人普遍具有建功立業的思想,而此時,西域特有的蕭然環境便成了其施展宏圖的沃土。更有甚者,如李益的《拂云堆》,更是將這種對戰爭必勝的自信與對敵人的藐視推向頂峰,“單于每近沙場獵。南望陰山哭始回”一句體現出了盛唐文人對于國家軍事實力的自信。
而“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安史之亂的爆發震碎了唐朝的統一進程,也瓦解了盛唐文人對于邊塞絕境的豪賞,與對外族無差別的不屑。如王建的《遼東行》,詩中“年年郡縣送征人,將與遼東作丘坂”便開始出現了“丘坂”(筆者注:在此指丘墓)這種隱喻著死亡的消極戰爭意象,說明邊塞的連年戰事已讓百姓叫苦,從而開始放棄對功名的追求,轉向對自身生命的憐惜。而王涯的《從軍行三首》(其三)中“白馬將軍頻破敵,黃龍戍卒幾時歸”便和前人王翰“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中表述的感情有所出入。在王翰的詩中,戰爭是與醉酒有關系的,醉酒而出戰,除卻一種盛世將士的瀟灑,更有著對于敵人和死亡的無懼,只因國力強盛,軍士出戰雖死而戰必勝,因此那時的戰死是有價值的。而王涯之時,累日的戰事已讓軍士看不到戰斗的意義與價值,因此將自身戍邊的孤苦之憤發泄到了自家將領身上,而非敵人。而常年戍邊的痛苦,也使得詩人將情愫逐漸由戰爭之事物轉移到了思鄉之上。如錢《春恨》中的“久戍臨洮報未歸,篋香銷盡別時衣”,而這種鄉思之上亦存中原之民在邊塞久未歸家后對農耕文化的眷戀,司馬扎《古邊卒思歸》中的“有田不得耕,身臥遼陽城”即是較為深刻的寫照。當這種對和平的向往到達一定程度后,對于戰爭的控訴也隨即而來,就如杜甫《前出塞九首》其六中的“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便闡述了戰爭即是當權者對于別人土地和財富的無休止覬覦和渴望,而一句“豈在多殺傷”便將邊塞詩中所存有的對戰爭的渴望進行了原罪式的剖析。
三、結語
綜上所言,邊塞詩在描述戰爭行為與意象時確有其審美價值,也存在一定的美學創作規律。但是這種規律與邊塞詩創作的時代盛衰、刻畫的戰爭的具體勝敗、與社會整體對于戍邊守塞的看法都有著一定的關系。由盛轉衰的唐代及其前后形成的邊塞詩便是這種情形最好的印證和寫照。只有當國家興盛、軍力強大,邊塞詩才能生出獨立的審美與豪邁的氣魄;一旦戰事吃緊,至國破家亡,邊塞詩中的精氣將急轉而下,直至對于戰爭本身的控訴和審判。在這里,可以看出,邊塞詩的產生與嬗變與中國古代詩歌中的“詩妖”理論是相契合的。而邊塞詩中的審美意象,尤其是那些與戰爭有關的審美意象,其隨時代的細微變化,也與一個國家的興衰與自信與否有著極為緊密的聯系。
參考文獻:
[1]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12.
[2]司馬遷.裴,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2105.
[3]李炳海,于雪棠.唐代邊塞詩傳[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2.
[4]張晶,石宕川.刀鋒之美:藝術媒介視域下的戰爭美學建構[M].現代傳播,2020(3):83-90.
[5]張德林.作家的內心視象與藝術創造[M].文學評論,1991(2):39-42.
[6]張晶.美學與詩學——張晶學術文選[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392.
[7]鐘嶸.曹旭,集注.詩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47.
作者簡介:石宕川,中國傳媒大學文藝學專業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