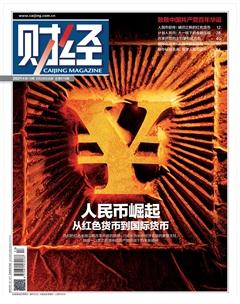中國經濟仍需“固本培元”
鐘正生 張璐
“固本培元”是今年4月3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對宏觀政策的新定調。中國經濟為何需要“固本培元”?在會議過去兩個月后,是否仍需“固本培元”?對這個問題的判斷決定著未來一段時間的宏觀政策走向,尤其是在美聯儲加息預期前移、并即將討論縮減QE的情況下,中國貨幣政策是否應該“搶跑”或者跟隨,在當前仍然存有爭議。
我們認為,當前中國經濟存有短板(制造業投資和消費),尤其產業鏈的下游表現得更明顯,仍然需要宏觀政策上的“固本培元”。在美聯儲政策動向備受矚目的情況下,中國的貨幣政策仍應“以我為主”,“搶跑”固然不必,是否跟隨亦需再行觀察。而聚焦中國經濟的短板,維持足夠程度的呵護,應該成為“以我為主”的最主要考量之一。
一、宏觀層面:經濟復蘇存在“高低腳”
從主要宏觀經濟數據來看,中國經濟復蘇的“高低腳”突出(圖1)。經濟復蘇的“長板”是出口和工業:今年前五個月,工業企業出口交貨值的兩年復合增速達到8.2%,而2019年疫情前增速僅1.3%;受出口帶動,工業增加值兩年復合增速也持續高于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前水平。經濟復蘇的穩定力量來自服務業、房地產投資和基建投資,其兩年復合增速已與疫情前相差不大。經濟復蘇的“短板”在于制造業投資和消費:前五個月餐飲收入的兩年復合增速仍未轉正,大幅低于疫情前接近10%的增速水平;商品零售從3月開始復蘇接近停滯,兩年復合增速4.8%仍顯著低于疫情前7.9%;制造業投資的恢復也較緩慢,相比疫情前3%左右的增速尚有明顯差距,尤其體現為民間投資復蘇亦顯乏力。
圖1:中國經濟復蘇的不均衡特征凸顯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公開資料整理。制圖:顏斌
可見,當前中國經濟復蘇的動能仍偏外向,而作為當前“穩定力量”的房地產和基建投資都處于嚴格監管之下,不太可能作為外需的有力承接。目前,政策層面已從房企(三條紅線)、金融機構(兩項房貸集中度政策)、地方政府(供地兩集中)和居民(限購)等層面形成合力,力圖減輕中國經濟與房地產的“捆綁”。在此形勢下,盡管目前房地產銷售仍保持較高景氣,但房屋新開工面積增速持續負增長,增速亦大幅低于疫情之前。這使得房地產投資增長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已開工項目的施工,其后勁和增長的穩定性都存在不確定性。基建投資則內嵌于地方政府隱性債務治理的大背景下,在清理規范地方融資平臺、堅決遏制隱性債務增量的嚴厲要求下,目前基建相關財政支出(包括城鄉社區事務、交通運輸、節能環保)兩年復合增速大幅負增長,地方專項債也出現發行進度緩慢的現象,后續基建投資的增長空間同樣受限。因此,面對外需改善不可長期持續,中國經濟必須進一步提振制造業投資和消費增長,才能保證有足夠的內生動能。

除了出口拉動的不平衡,消費的持續低迷也加重了下游產業鏈的壓力。盡管一季度中國居民收入進一步恢復增長,但消費復蘇仍然顯得步履維艱,居民消費傾向自2020 年顯著下挫以來,尚未有效回升。促進消費已成為中國面臨的一項中長期挑戰。圖/法新
二、中觀層面:產業鏈的下游短板明顯
在本輪疫后復蘇中,出口是終端需求的主要來源。2020年凈出口對中國GDP的貢獻率達到28%,是20年來最高。但本輪出口對中國產業鏈的拉動并不平衡,這與2017年上一輪出口高景氣時期有很大差別(圖2)。本輪出口拉動中,中游裝備制造類行業出口率先拉升,醫藥和汽車行業隨后,背后邏輯是發達國家生產受限,從中國進口了更多的工業制成品;今年以來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暴漲,加之發達國家工業生產恢復,帶動上游原材料行業出口加速反彈;但其他下游行業(除醫藥、汽車)出口持續負增長,與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前無異。
圖2:下游行業對制造業投資產生更大拖累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公開資料整理
圖3:本輪PPI從上游向下游傳導更加不暢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公開資料整理
與上述出口交貨值的情況相對應,截至2021年4月,除醫藥、汽車以外的下游工業行業工業增加值兩年復合增速普遍偏低,各行業平均增速為2.8%;而上游、中游各行業工業增加值的平均增速分別為5.6%和8.3%。
剔除工業品價格影響后,今年1月-4月(兩年復合)整體工業處于高營收增長、同時高庫存增長狀態,體現生產熱情較高、且工業品需求也較旺盛。但從中觀行業來看,庫存與營收的組合卻呈現出明顯分化:高庫存、高營收狀態在中游制造業行業中較為普遍,上游的黑色金屬、有色金屬、石油化工也呈現此種狀態,下游的汽車、煙草、農副食品亦然。但其他下游制造業普遍出現了較高庫存與較低營收的嚴重脫節(庫存增速處于歷史較高分位,而營收增速處于歷史較低分位)。出現類似狀況的還包括上游的非金屬礦物制品,中游的儀器儀表、通用設備、木材加工和造紙,但并不像下游行業那般突出。這種“高庫存、低營收”的組合,對于下游行業后續生產的持續性,以及擴張投資的可能性都會產生不利影響。
1994年初匯率并軌,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度后,按照主動、漸進、可控的“三性”原則,配合人民幣可兌換、國際化與資本賬戶開放進度,不斷提高人民幣匯率形成的市場化水平,加快培育和發展國內外匯市場。特別是2005年“7·21”匯改以來,人民幣匯率總體上呈現單邊升值走勢,并伴隨著人民幣多邊匯率升值。到2015年7月底,人民幣匯率較“7·21”匯改前夕累計升值35%,國際清算銀行編制的人民幣名義和實際有效匯率分別升值46%和57%。這表明“7·21”匯改后,參考籃子并非盯住籃子,外匯供求關系決定了人民幣匯率走勢。
到2015年7月底,中國外匯儲備余額3.65萬億美元,盡管比2014年6月底峰值低了3419億美元,卻仍遠高于2006年底的1.07萬億美元。而2006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做出了中國國際收支主要矛盾已經從外匯短缺轉為貿易順差過大、外匯儲備增長過快的重要判斷,提出要把促進國際收支平衡作為保持宏觀經濟穩定的重要任務。
2015年“8·11”匯改之初,人民幣遭遇階段性貶值壓力。人民幣匯率三次跌到7比1附近、遇“7”不過后,第四次于2019年8月應聲“破7”。此次“破7”不只是人民幣貶值,而是打開了匯率可上可下的空間,提高了匯率形成的市場化程度。因此,雖然“破7”不涉及中間價報價機制和匯率浮動區間的調整,卻仍被稱之為“不叫改革的改革”。
2017年,人民幣匯率和外匯儲備止跌回升,遏制了人民幣匯率單邊下跌走勢。自2018年起,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預期分化,央行基本退出了外匯市場常態干預。
這提高了國內貨幣政策的獨立性。2018年,在國內經濟下行、中美摩擦升級的背景下,中國頂住美聯儲四次加息并縮表的壓力,三次降準,引導市場利率走低,雖然當年底人民幣匯率再次跌到7附近。
這降低了對資本外匯管制手段的依賴。此后,不論人民幣升值貶值,都是外匯供求和國際金融市場變化的結果而非政策目標。
有關部門基本恪守了匯率政策中性,除了根據外匯形勢發展變化,退出或重啟部分跨境資本流動管理的宏觀審慎措施外,沒有采取新的資本外匯管制措施,相反還適時取消了QFII、RQFII額度限制,提高了QDII、QDLP審批額度。這促進了國際收支和外匯收支的自主平衡,加速了貿易投資便利化,增強了外國投資者信心,推進了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人民幣“破7”之后不久的2020年,受新冠疫情沖擊、國際金融動蕩、世界經濟停擺、大國政治博弈等因素影響,人民幣匯率呈現先抑后揚的走勢。到2021年5月底,較2020年5月底累計上漲12%,人民幣持續升值已一整年。
小結:人民幣匯率改革,機制比水平更重要。人民幣匯改的歷史就是一部中國經濟市場化、國際化的歷史。1994年匯率并軌以來,人民幣有管理浮動的匯率制度安排經歷了各種極端事件的考驗。特別是“破7”之后,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成為吸收內外部沖擊的“減震器”。這雄辯地證明,有管理浮動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匯率選擇。
由弱勢貨幣變為強勢貨幣
計劃經濟時期,人民幣匯率作為核算工具而非價格杠桿,其制定與進出口脫節,后期逐漸形成了高估。改革開放以來的轉軌經濟時期,直到1994年匯率并軌前夕,人民幣長期是一個弱勢貨幣。官方匯率從初期的1.50元人民幣對1美元,到1993年底跌至5.80元人民幣對1美元。1994年初,匯率并軌到了8.70元人民幣對1美元。故1994年之前,人民幣呈現螺旋式的貶值,市場看空人民幣的情緒強烈。當時,外匯是稀缺資源,甚至連個人持有外匯兌換券都成為身份的象征。
1994年并軌之初,市場主流觀點認為人民幣將“破九望十”。然而,并軌當年,人民幣匯率不僅沒有貶值反而升值2.9%,外匯儲備還翻了一番。到1997年底,人民幣匯率穩中趨升,累計升值5.1%,外匯儲備突破1000億美元。期間,人民幣也實現了從1994年之前完全不可兌換,到1994年初經常項目有條件可兌換,再到1996年底經常項目完全可兌換的飛躍。
1997年7月,泰銖失守引爆東南亞貨幣危機,到年底逐漸演變成席卷全球新興市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國重現資本外流、匯率貶值壓力。
1998年初,中國政府一方面實施積極的財政貨幣政策,擴內需、保增長,另一方面對外承諾人民幣不貶值,同時還要求增加外匯儲備。為此,在堅持經常項目可兌換原則下,強化經常項目用匯真實性審核,收緊資本項目購匯限制,加大外匯立法執法力度,成功兌現了人民幣不貶值承諾。
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在8.28元人民幣對1美元的水平,1998年至2000年間外匯儲備不降反增257億美元。直至2005年“7·21”匯改一次性升值2%,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參考一籃子貨幣調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危機時期,人民幣不貶值防止了危機進一步傳染,不僅支持了中國經濟金融穩定,也維護了亞洲乃至世界的經濟金融穩定,贏得了國際上的廣泛好評,奠定了人民幣新興世界強勢貨幣的地位。危機之后,人民幣在周邊流通和使用增加,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萌芽。
值得指出的是,改革開放以來,直至1994年之前,官方匯率的制定和發布主要依據都是國內企業的出口換匯成本。受企業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的影響,官方匯率的調整往往滯后于換匯成本,因此無論采用何種匯率制度安排,人民幣官方匯率均呈現出螺旋式貶值,人民幣匯率的弱勢特征明顯。相反,盡管1994年之前,中國外匯總體短缺,但自由浮動時期,外匯調劑市場仍呈現有漲有跌的震蕩走勢。
匯率并軌特別是2005年“7·21”匯改以來至2015年“8·11”匯改之前,人民幣匯率總體上呈現單邊升值走勢。僅有2008年底美國次貸危機演變成全球金融海嘯,中國遭遇了短暫的資本外流壓力,并主動收窄了人民幣匯率波幅,再度體現了負責任的大國風范。2009年底試行跨境貿易人民幣計價結算,宣告人民幣國際化正式啟航。
每逢人民幣升值,經常會遭遇各種爭議,如升值令出口部門承壓、升值吸引熱錢流入等等。“7·21”匯改前夕,曾有人預測,如果人民幣升值5%以上,國內出口行業將崩潰。但實際上,“7·21”匯改之后,人民幣最多升值了40%以上,中國出口不僅沒有崩盤,反而做成了全球第一,經常賬戶順差與GDP之比最高達到了10%。
為阻止人民幣匯率過快升值,在2014年之前,還采取了“控流入、擴流出”的措施。過去求之若渴的外匯流入尤其是熱錢流入,一度成為監管的重點,由“寬進嚴出”轉向“均衡管理”的跨境資本動態管理框架逐步建立。
正因為堅持市場化的匯率改革方向,才使得“擴內需、調結構、減順差、促平衡”的一攬子政策取得積極成效,促進了經濟內外均衡協調發展。現在,中國經常賬戶順差與GDP之比已降至2%以內,遠低于4%的國際警戒標準。從2016年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評估人民幣匯率水平符合經濟中長期基本面,既沒有高估也沒有低估。這支持中國抵制了“貨幣操縱”的不實指責。
小結:經濟強、貨幣強是強勢貨幣的內在基礎。過去20多年來人民幣由弱變強的歷史,正是中國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逐步變強的歷史。這也是亞洲金融危機和全球金融海嘯期間,做空人民幣無功而返的重要原因。2020年6月以來人民幣匯率震蕩走高,也是疫情防控好、經濟復蘇快、中美利差大、美元走勢弱等多重利好共振的影響。同時,以強勢人民幣為標志的匯改成功,增添了我們取消經常項目外匯收入強制結匯要求,實施個人年度便利化購售匯總額管理,有序推動金融雙向開放,穩慎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決心和勇氣。
(編輯:袁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