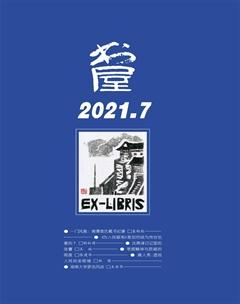陳獨(dú)秀的“饞”
熊少華
這些年來,談到前賢風(fēng)范、地方文化或者書法界的往事的時候,我會經(jīng)常說到陳獨(dú)秀這個名字,說到他暮年流寓重慶的一件小事。
抗戰(zhàn)時期,陳獨(dú)秀隨著內(nèi)遷避亂的逃難隊伍幾經(jīng)輾轉(zhuǎn),最后寄跡于重慶江津鄉(xiāng)下一個姓楊的人家。暮年的陳獨(dú)秀雖然貧病交加,但他倔強(qiáng)而又孤傲的性格至死不渝,寧可餓死也不受嗟來之食,頻頻拒絕各種利益的引誘和朋友的饋贈,以致他死后所遺物質(zhì)財富唯有土豆一堆。
一次年關(guān)將近,陳獨(dú)秀前往同時客居江津的佛學(xué)大家歐陽競無家中做客,偶然見到歐陽競無藏書中的《武榮碑》,頓時為其渾樸的氣象所吸引,以至于回家之后還念念不忘,旋即作詩一首記錄心跡:“貫休入蜀惟瓶缽,臥病山中生事微。歲暮家家足豚鴨,老饞獨(dú)羨武榮碑。”
唐代末年,畫僧貫休避亂入蜀,曾有詩句“一瓶一缽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自感身世。陳獨(dú)秀以貫休自喻其晚境凄涼,托足山野,貧病之余別無長物。歲末年初家家戶戶殺雞烹鴨籌備年貨,自己卻饑寒交加,但最讓他眼饞的卻不是這些,唯獨(dú)是那本點畫凝重、氣勢開張的漢碑拓片——《武榮碑》。
歐陽競無看到陳獨(dú)秀的詩作后,有感于心,隨即寶刀贈英雄,毫不含糊地將《武榮碑》送給了陳獨(dú)秀。
陳獨(dú)秀的書法恰似其人,筆法卓異,不尋常理,更無刻意安排雕飾,往往大起大落,隨緣任運(yùn)而神韻自見。其書法藝術(shù)的成就在名家輩出的民國時期也堪稱翹楚。由于他是新文化運(yùn)動的發(fā)起者、五四運(yùn)動的思想指導(dǎo)者、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者和中國共產(chǎn)黨創(chuàng)始人之一,其書法成就反被遮蔽,鮮為人知。近些年來,因為陳獨(dú)秀遺作的不斷面世和現(xiàn)當(dāng)代史料的逐漸厘清,越來越多的人方覺察出他獨(dú)絕的筆墨功力和深邃的藝術(shù)眼光。
據(jù)說還在北大時期,一次陳獨(dú)秀敲開了沈尹默家的門,開門見山就說:“我叫陳仲甫,昨天在劉三家看到你寫的詩,詩做得很好,字則其俗在骨。”劉三,即劉季平,與陳獨(dú)秀、沈尹默都是朋友。沈尹默這時不僅是中國新詩的先驅(qū)人物,還是書法界的大腕,面對陳獨(dú)秀的當(dāng)頭棒喝,他只好謙遜地說:“我的字受了南京仇淶之老先生的影響,用長鋒羊毫,至令不能提腕,所以寫不好。”陳、沈二人從此結(jié)為好友,爾后他們經(jīng)常“徜徉于湖山之間,相得甚歡”。
抗戰(zhàn)時期,陳獨(dú)秀與沈尹默同寓巴蜀,雖難見面,詩詞唱和亦復(fù)如舊。一次陳獨(dú)秀在給沈尹默學(xué)生臺靜農(nóng)的信中寫道:“尹默字素來工力甚深,非眼面朋友所可及,然其字外無字,視三十年前無大異也。”沈尹默對此已無以為意,他深知陳獨(dú)秀直率的為人,也深知自己藝術(shù)的取向,對書法的理解不同,見仁見智大異其趣,才導(dǎo)致了陳獨(dú)秀評價的偏執(zhí)吧。
陳獨(dú)秀天馬行空、不受約束的性格在他的書法中得到真實的反映,在《實庵自傳》中他回憶:“至于寫字,我喜歡臨碑帖,大哥總勸我學(xué)館閣體,我心里實在好笑,我已打定主意,只想考個舉人了事,決不愿意再上進(jìn),習(xí)那種討厭的館閣字做什么!”從這句話我們看出,陳獨(dú)秀不愿寫以“烏、方、光”為標(biāo)準(zhǔn)的館閣體,不愿以漂亮矯揉、甜俗光滑的書法姿態(tài)討好世人,他是一個頗具反骨的人,藝術(shù)上亦多有反叛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