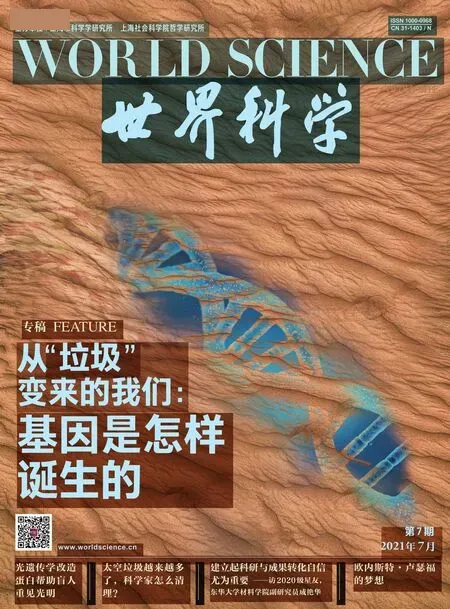越來越多國家希望“克隆”DARPA
編譯 李軍平

此前,使用信使核糖核酸(mRNA)技術生產疫苗的想法并未得到證實。但如果事實證明可行的話,這項技術將會給醫療行業帶來徹底改變,尤其是它可以保護人類防御各類傳染病與生物武器的侵害。于是,2013年,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應運而生。后來,DARPA向一家名為Moderna的小型新興公司提供了一筆高達2 500萬美元的撥款,資助其研發mRNA技術。八年后,在生產了超過1.75億劑疫苗后,Moderna研發的新冠肺炎疫苗與氣象衛星、全球定位系統、無人機、隱形技術、語音轉換技術、個人電腦和互聯網這些創新技術一樣,都被列入了最新的創新名單,這些技術的誕生都有DARPA的一份功勞。
可以說,DARPA塑造了現代世界,它的成功也催生了諸多效仿者。僅在美國,就有國土安全、情報、能源和國防這四個部門設立了高級研究計劃局。美國總統喬·拜登曾要求國會撥款65億美元建立一個衛生部高級研究計劃局,希望“終結我們所知的癌癥”。此外,拜登政府還計劃建立另一個專門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的高級研究計劃局。最近,德國也成立了兩個這樣的機構:一個是民間機構——聯邦破壞性創新局(SPRIN-D),另一個是軍事機構——網絡安全創新局。日本啟動的類似項目名稱為“登月型研發制度”(Moonshot R&D)。而在英國,議會則正在審核一項關于“高級研究與發明局”(UKARPA)的法案。
國家機構需設置類似DARPA的下屬機構
在經歷了40年的發展停滯后,發達國家政府紛紛開始加大研發領域投資,建立機構、開創未來(并在此過程中開拓巨大的產業)的想法便由此引發了他們濃厚的興趣,況且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的成功表明,這個想法并不僅僅只是美好的幻想。在許多國家,人們對資助體系中的官僚之風十分不滿,因此希望DARPA模式可以幫助他們規避這種作風。但正如許多人已經發現的那樣,效仿DARPA并非只是復制名字那般簡單。它們還需堅持奉行DARPA的各項原則,這些原則是其取得成功的關鍵,但也常常會讓政客們感到不安。
從理論層面看,這種方法非常簡單。但實際上,這就像是一場孤注一擲的賭博,因為其收益巨大,且贏得勝利在于少數人的努力。正如美國能源部高級研究計劃局(ARPA-E)第一任負責人阿倫·瑪朱姆達爾(Arun Majumdar)所說:“如果每個項目都可以取得成功,那么你將不會那么努力。”參與這場“賭博”的研究人員可能來自工業、學術界或其他行業,但無疑他們都站在了知識的前沿。瑪朱姆達爾對此表示:“只有站在前沿的人,才知道前沿知識是什么。”隨后,類似機構便會提供大量的資源,將這些優秀的研究人員聚集在一起,鼓勵他們為了共同的目標而奮斗,但同時也允許他們失敗。
結果便出現了許多“低仿版”的研發機構。例如,大多數這樣的機構專注于基礎研究,而DARPA則是專注于創造;前者傾向于使用同行評審報告和精挑細選的指標,而后者卻已經徹底消除了官僚主義(1965年,在一次僅為15分鐘的對話中,DARPA便決定投資100萬美元打造首個跨國計算機網絡,這也是互聯網的雛形);前者的所有工作均采取外包方式,而后者則會根據固定的短期合同雇傭一個負責人、幾個辦公室主任和不到100名的項目經理,且他們行事頗具風險資本家的作風,盡管其目的是產生具體的成果而非私人經濟回報。目前開展的項目包括模擬昆蟲的神經系統,以減少人工智能所需的計算,并研究如何保護士兵免受使用基因組編輯技術的敵人的傷害等。
新成立的高級研究計劃局面臨的第一個挑戰是,如何為這些實驗提供所需的自由空間。SPRIN-D的案例說明了這項挑戰的難度。在德國政府內閣批準了某個概念后,“聯邦審計院便會隨之出現”,SPRIN-D首席合伙人芭芭拉·迪爾(Barbara Diehl)嘆息道。在審計機構發布審計建議后,SPRIN-D便失去了對標準公共部門采購規則與薪資等級的豁免權,進而限制了其在人員雇傭、風險承擔方面的選擇。迪爾還說,現有的政府部門還會通過機構的董事會施加壓力,防止出現激進主義。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的前高級顧問多米尼克·卡明斯(Dominic Cummings)要求在英國設立代理處,作為他受雇的條件,并表示他對該機構立法中的部長監督規定頗感擔心。
如果總是受到政治干預,那么從事前沿的研究人員便無法充分發揮其冒險本能。最近,德國網絡安全創新局的行政與研究主管因政治干預而選擇了辭職。在美國,國土安全部高級研究計劃局雖然早在2002年就已成立,但由于國土安全部內部的權利斗爭,該機構一直未能做出成績。對此,一位觀察家如此說道:“它從未有過獨立決策的權利,也從未享受過獨立的預算。”關于拜登政府提議的衛生部高級研究計劃局(ARPA-H)“應當獨立存在,還是應當隸屬于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這個問題一直爭議不斷。雖然第二種方案面臨的立法挑戰較小,但可能會侵犯該機構的獨立性。
DARPA的2020年預算為36億美元,僅相當于NIH預算的8%。如果一切按計劃進行的話,ARPA-H的預算也大抵如此,而其他機構甚至無法獲得這一規模的資金支持(例如,ARPA-E去年的預算為4.25億美元,約等于DARPA一個辦公室獲得的資金支持)。由于這種模式是通過大量下注來實現少數的成功,因此,資金越少就意味著賭注越小,那么成功的機會也就越低,獲得持續政治支持的概率也就越小。鑒于在衡量該等機構的成果進展方面存在著諸多困難,因此這一點就顯得尤為重要。麻省理工學院的皮埃爾·阿祖萊(Pierre Azoulay)及其同事在一篇論文中指出:“從與政治決策相關的時間尺度上看,根本不可能準確衡量千分之一想法的成功率,更別說百萬分之一了。”
新成立的這些機構必須找到解決方案,將其創新成果帶出實驗室。DARPA與國防部之間保持著密切的關系,而后者就像是前者的客戶。但是,實際情況也并非總是這么簡單。例如,DARPA的官員不得不說服空軍了解隱形技術的潛力(因為隱形飛機的飛行速度慢且必須在夜晚飛行,所以后者并未被說服),且正如DARPA當初開展的半導體芯片工作一樣,許多突破性成果都先落入到民間機構手中。
但其他機構則完全缺乏這樣的“管道”。馬薩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的安娜·戈爾茨坦(Anna Goldstein)及其同事們開展的一項研究發現,盡管ARPA-E贊助的全新清潔技術公司較其他同類型公司獲得的專利更多,但其籌集風險資本,被更加大型的公司收購或上市的可能性極低。至少到目前為止,該類機構的創新成果都很難在現實中落地。
當ARPA-E在2009年成立時,人們希望風險資本家能對其創新成果加以利用。然而,事實證明他們不愿意如此。與風險投資家最愛投資的軟件技術相比,能源技術通常需要花費更久的時間才能進入市場。ARPA-E還曾為此調整了DARPA模式,增加了一個“技術-市場”團隊,為項目的產業化過程提供指導。去年,為了尋求發展,它還向此前的獲獎者發放了高達15萬美元的獎金。麻省理工學院的科學政策專家威廉·邦維利安(William Bonvillian)認為,這些項目離成功只缺少時間這一個要素而已,“互聯網誕生于1969年,但直到1991年或1992年才形成規模。所以我們需要花點時間,耐心等待”。
拜登政府提議成立的ARPA-H可能也會面臨同樣的難題。之所以提出該項建議,是因為NIH過于保守,且在生物學、化學和計算機科學幾大領域結合、誕生許多生命科學成果時,它仍然只關注生物學這一個學科。滑鐵盧大學的米科·帕克艾倫(Mikko Packalen)與斯坦福大學的杰伊·巴塔查里亞(Jay Bhattacharya)提供的支持性證據均表明,NIH對于最新前沿技術的投資力度已有所減小。ARPA-H的另一個目標是研發罕見疾病治療方法,但由于利潤空間有限,所以私營部門對此避之不及。與ARPA-E一樣,缺乏商業性可能會使創新成果轉化為實際應用的過程變得異常艱難。
奧巴馬政府前官員、ARPA-H倡導者邁克爾·斯特賓斯(Michael Stebbins)希望從DARPA招募一個人來領導這個全新的機構。復制DARPA自由文化的難度極大,即使DARPA自身也經歷過多次失敗。它在20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曾有過一段“休耕期”,很多人都認為它的野心在近幾十年有所削減——盡量避免失敗,但同時成功率也大大降低。此外,國防部設立此類機構還有一個內在優勢,即如果未能制造出厲害的武器,那么美國領導人也會很放心,因為他們的對手肯定也未能成功。
但如果未能成功治愈癌癥,便不會得到這樣的安慰了。但這也并不足以勸退美國、英國、德國和日本的政治家們。DARPA教會了我們,困難并不是退縮的理由,甚至可能成為堅持的理由。
資料來源 economis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