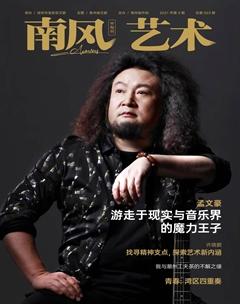淺談長篇歷史紀實文學的寫作


唐代詩人孟浩然在《與諸子登峴山》里說:“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實際上是說明了世間的人和事更替變化,暑往寒來,時間流逝,形成了從古到今的歷史。英國哲學家培根也說:“讀史使人明智,讀詩使人靈秀”,這些都說明了歷史對于人類的重要性。作為學者,要了解歷史,不外乎讀歷史文獻,走博物館,走訪或到遺址現場考察。但對于一般老百姓而言,如何讀到居廟堂之高的歷史知識,則比較難。故民國時期著名史學家和文學家蔡東潘說:“顧作史固難,讀史亦難”。如何讓歷史知識觀今鑒古,古人就做了很好的嘗試。其中尤以唐朝歷史傳奇、宋朝以歷史為背景的評書,直到明清時期的“歷史演義”,對歷史知識的普及起到很大的作用。但由于這些歷史演義,往往虛構成分比較多,史實不足的問題,所以蔡東潘說:“庸詎知其語出無稽,事多偽造,增人智識則不足,亂人心術且有余耶!”實際上是否定了許多演義性的所謂歷史小說對歷史真實性的偏差。筆者也認為不少冠以“歷史演義”的書籍,如果作為文學著作來讀還說得過去,但當做歷史來讀,不僅對普及歷史知識無任何意義,反而是一種對歷史的黑白顛倒,是一種知識毒害。就如我們許多民間把《三國演義》當做歷史來讀,殊不知,其和真實歷史的《三國志》已經相差甚遠。民間不少地方還篤信關羽有“過五關,斬六將”等能力,顯然是歷史演義對歷史知識“普及”的反面“功勞”。其他歷史演義對歷史人物、時間的張冠李戴,甚至對歷史的褻瀆更是不勝枚舉。
隨著歷史的發展,后面又有了幫助人們了解歷史更多的文學體裁,如歷史戲曲、歷史劇本。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又有了歷史電影、歷史電視劇走入人們的視線。然而讀史太難,讀小說容易誤導觀眾。看電影、電視劇既花費時間,又很難感受到文字的魅力。無疑,讀歷史紀實文學則可以避免讀史書的難度,又可以避免被小說情節的誤導,則可以算得上了解歷史和避免以上問題局限的一種折中。現在我就以這種同類題材的《穿越封鎖線——省港大營救始末》和《東縱戰士高漢如》(陳雪著,下同)、《喋血羅浮》和《羅浮曙光》(毛錦欽著,下同)、《東縱北撤》(牟國志著,下同)《開國將軍袁也烈》(周后運著,下同)作為例子分析,以饗讀者。我認為這類作品的主要特點有:
一是通過資料的引用和考究,來增強作品的可讀性和可信性。例如:《穿越封鎖線——省港大營救始末》中寫到當時我黨對文化的重視,就直接引用了《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即《整頓黨的作風》的原話。在這部書的第二章寫到1942年在日軍入侵香港,我黨港九大隊的武裝工作隊奉命插入新界抵抗日寇的主要人員也是采用了《港九獨立大隊史》的第10、13頁里“這支隊伍里有林沖、莫浩波、盧耀康、鄧華、李生、葉楚南、黃云生等十五六人。”《喋血羅浮》第二章《調兵遣將方陣亂》(第27頁)中直接引用了《蔣介石日記(1915-1949)》中的日寇由大亞灣登陸侵略中國華南時的內容,則更能真實地反應當時抗戰的情勢。《開國將軍袁也烈》在這本46萬多字的歷史紀實文學中光引用的書目就達到375種,這些資料的引用和參考無疑會更進一步增加其作品作為歷史紀實文學的可讀性和可信性。
二是其畫面感的敘事風格,可以增強故事的可讀性。《喋血羅浮》中的第一章《驚濤拍岸浪滔天》一開篇就寫到“南方十月,秋高氣爽,陽光明媚。然而,在廣東大亞灣,每當老人談起七十六年前的這一天,他們的表情大概都相同:搖頭,嘆氣。”再如毛錦欽同志的《羅浮曙光》中的第三篇第一章《困獸猶斗,敵軍圍困萬千重》中寫道:“1946年,從秋至冬,羅浮大地數月不下雨,河水枯竭,農田龜裂,旱災延綿數月……”這些無不用文字表現出強烈的畫面感。《東縱戰士高漢如》中的第一章第九節《棋高一著》中寫道:“天下著淅淅瀝瀝的小雨,雨水打在樹上簌簌有聲,樹葉上的雨滴掉落在茅屋頂上,在沿著稻草搭成的屋檐往下流,一串串地掉,滴答滴答地響個不停。”又如牟國志同志的《東縱北撤》第八章開頭寫道:“這天下午,夕陽透過紫荊樹碧綠的枝葉,斑駁地灑在沙面島蘇聯領事館樓宇的墻上、樓前的花圃上和濃蔭匝地的人行道上。”這里不僅通過強烈的畫面感展現了當時的地點和時間,也顯示了人物出場的背景。《開國將軍袁也烈》其開篇用“金秋十月,湖南省武岡縣黃橋鎮周圍的丘陵和山區,碩果累累的雪峰蜜橘滿山遍野,壓得青翠色的樹枝低下了頭。”一讀到此處,在讀者面前展現的剛好就是一幅屬于湘中的鄉村田野風光,其畫面感自不用說。
三是其對比的寫法可以增強閱讀的視覺效果。如《東縱北撤》第四章《狹路相逢看勇者 兩軍對壘有高人》,通過寫國民黨特務孫剛虎和曹萬齊等的陰險狡詐,不時地制造事端,與中共黨員、革命戰士方方、陳華等的鎮定、革命樂觀主義的對話等寫法,增強了視覺效果。
四是其場面的極力渲染,可以增強歷史紀實文學的厚度。《喋血羅浮》第三章《金戈鐵馬氣恢宏》寫到我們中國守軍抵抗日寇的場面就極為慘烈,第四章《山河破碎盡飄搖》更是把當時日寇鐵蹄蹂躪中華大地慘絕人寰的慘烈場面寫得不忍卒讀:“被毀的房屋的瓦礫中,埋了三十多具尸體,已挖出的凄涼地擱在路旁,從覆蓋的蘆葦席里看到那全是赤腳勞動者//一張破席子躺著兩名小孩的尸體,旁邊坐著他們的母親,滿身滿臉塵土,這種從未體驗過的痛苦經歷驚駭了她。好不容易從震塌的房屋里拖出重傷的丈夫,卻失去了兩個孩子//有人失去了頭顱,有人失去了雙腿,僅剩下一段肌肉在顫抖著……”這些場面的極力渲染,對表達主題而言,無疑是成功的。《東縱北撤》中的八十八章《百感交集慶勝利,萬人空巷迎親人》一開頭就用大量的詞匯描述了1946年7月5日,東縱北撤到山東煙臺的情景。通過其大氣和歡快的場面,極度渲染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軍人到達目的地的喜悅心情,同時也反映了中國人民對人民子弟兵由盼望到熱烈歡迎的場景。
當然,對于歷史紀實文學,站在受眾的立場來看,其需要注意的事項也是顯而易見的。在筆者讀過的幾十部歷史紀實文學作品中也發現了以下不足:
一是由于其是在歷史題材上的加工,大部分作者容易把作品寫成“歷史書”,而不是紀實文學。不少作者的作品往往很容易看到其創作過程中參考了哪些著作,有些作品甚至根本就沒有自己的新觀點。
二是繁雜的資料引用,往往會消弭讀者對文學的閱讀期待。在我讀過的不少這類題材作品中,不少作品對參考資料的引用超過了四分之一,有些極個別章節甚至達到三分之一的引用量。作為歷史紀實文學應該始終抱有作者本身的見解,而不是大量的引用,這是對新的歷史紀實文學最為嚴苛的要求之一。
三是“為了還原歷史”,作者往往很難把握作品的主題思想,淡化了人物的個性,缺乏作品個性。由于歷史紀實文學,除了作者的“新發現”“新觀點”和“新寫法”外,在主題思想上,往往也是作者較為棘手的問題,作為文學作品,哪怕是“春秋筆法”,也不失為一種主題的表達方式,也就是說一部好的歷史紀實文學作品,應該是有自己新的思想的,與之匹配的應該是人物也是有個性的。但許多作品往往容易臉譜化,就像京劇一樣,不少出場人物很快就被貼上了標簽。再加上由于涉獵歷史題材的作品太多,往往不少作者很難寫出自己的特色,更容易是前人作品思想的“復敘”。
四是由于面對重大歷史事件,大部分作者極易發表個人見解,導致議論太多,越俎代庖代替了讀者,導致讀者失去判斷的機會,降低了讀者的閱讀興趣。讀者為什么要去閱讀歷史紀實文學作品,首先應該是期待擁有閱讀的快感,其次就是想對歷史知識有所了解,而不至于太枯燥,否認他會先從讀歷史書開始的,當然對于專寫文藝評論的人來說自然要另當別論。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當代的歷史紀實文學,很需要克服上述缺點,否則也就失去了再創作新的歷史紀實文學的意義。
當然,歷史紀實文學從最初我國《戰國策》和《國語》作為這一類題材的濫觴,歷經唐代傳奇、宋代的話本,然后到明朝開始的歷史演義,再到現代的歷史紀實文學,可以說每一代作家和史學家都做了各類不同題材和風格的嘗試。這些作家們,往往也是人們極為敬重的作家之一。這類題材作品的創作,無論是對史學知識的傳播,還是對文學創作的發展和創新都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中國作為一個有著深厚文化歷史底蘊的國家和民族,這些作品終將在世界熠熠生輝。
李建毅,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惠州市散文與散文詩學會副會長,惠州大亞灣區作協主席,《大亞灣文藝》主編。出版有文學評論集《閱讀的維度》等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