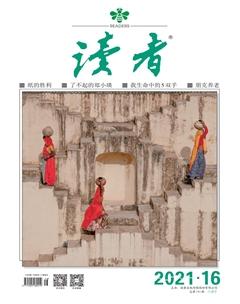不讀大學,人生會怎樣
崔東元 張杏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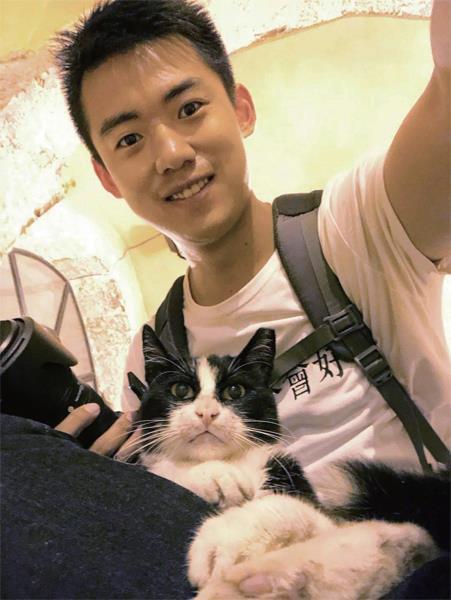
2008年夏天,燈光昏暗的房間里,16歲的于廣浩把一本臟兮兮的書扔到坐在沙發(fā)上的爺爺、奶奶和媽媽面前。“這本書叫《苔絲》,”他用小而清晰的聲音說,“它的故事很簡單,一個年輕人,被一群聲稱愛她的人毀了。”然后,他又補了一句:“你們應該好好看看。”
2020年,28歲的于廣浩對這個場景依舊印象深刻。爺爺抓起這本書,把它扔到他臉上,吼了一句:“于廣浩,你這輩子不會有什么出息!”而這位一向溫和的老人之所以暴怒,是因為于廣浩向家人提起了退學的想法。
“我在北京長大,但因為戶口在河北,便回到河北讀中學。教育環(huán)境的差異讓我難以忍受,2008年,我上初三的時候就想退學了,但為什么挨到高中才退呢?因為‘革命需要時間。”于廣浩笑言。
家人的強烈反對,沒有讓于廣浩后退半步。退學,是他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做出的選擇。
于廣浩習慣于把復雜的事情量化,他在決定是否要做一件事情之前會權衡事情本身的風險與收益。“我偏科嚴重,成績不好,如果我去參加高考,最多上一所三本院校,讓我用5年的時間換一張含金量不高的文憑,我覺得虧。假如風險、收益滿分都是100分,考大學在我眼里就是一件風險是10分、收益為20分的事情。”他認為與其接受家人給他安排好的路,不如趁著年輕,去嘗試走一條少有人走的路。
熱愛思考的天性讓他更關注一些與教科書無關的內容,在剩余的高中生活里,他儼然是一個游離于主流之外的人:如饑似渴地閱讀與課程無關的書,奔波在學生會、文學社之間,用紙和筆記錄下偶然迸發(fā)的靈感,寫了兩篇與題目要求無關的0分作文……在度過這段略顯瘋狂和失序的時光之后,他取得高中畢業(yè)證,邁入只屬于他的“大學”。
路上·大學
于廣浩的“大學生活”,從離家只有幾站地鐵的北京大學開始。他認為:“學可以不上,書還是得讀。”他想辦法混進北京大學的課堂,成為一名旁聽生。
他時常穿梭于教授政治、歷史、國際關系等課程的教室,往返于家和圖書館之間,他的身影也總是出現(xiàn)在學校的協(xié)會和社團中。在校園內扎根并瘋狂汲取營養(yǎng)的時光持續(xù)了一年半。這段時間里,他逐漸真切感受到自己掌握在手中的自由,內心對無數(shù)新奇事物也產生了愈來愈強烈的渴望。他如此形容游學時光最后半年里的自己:“比較躁動,書也讀不進去。”
在發(fā)現(xiàn)自己無法潛心學術之后,他偶然在某個論壇上看到一篇關于騎行的帖子。憑借著超強的行動力,于廣浩迅速弄來一輛車子和一些騎行裝備,在假期里繞著上海、無錫等長三角城市騎了一大圈,行程逾千里。
內心越燃越旺的火焰讓他不滿足于簡單的短距離騎行,兩個月的休息調整后,他索性踏上了跨越整個中國的征程。他從南京出發(fā),一路西行,用搭順風車的形式,歷經(jīng)28天,到達拉薩,在西藏繞著國境線轉了一大圈。后來,他又沿著中國南部的海岸線,繞著廣東、廣西等地轉了8000公里。
整整兩年,于廣浩就這樣一直行走在路上,他搭過600輛車,足跡幾乎遍布整個中國。他曾在北京寒冷的冬夜穿梭,在上海火車站一個人拉著拉桿箱興奮到顫抖,在太湖大橋上追逐太陽西下最后的光芒;他曾走過天山的牧場,穿行過察隅的森林,流連于九月的那拉提,徜徉在唐古拉的秋天,他看著禿鷲在頭頂盤旋,野驢在遠處嘶鳴……憶及此,于廣浩說:“那時的我,只有滿心的喜悅與感動。”
于廣浩的長途旅行,基本上是在父親不再給他提供經(jīng)濟支持的情況下進行的。“因為退學這件事情是他們絕對不可能認同的,他們覺得逼我回歸學校的最好方法就是不再給我提供經(jīng)濟支持。”
可就像于廣浩形容自己的那樣:“我是個硬骨頭,他們不給,我決不要,也決不低頭。”搭順風車本身可以省下一大筆路費,除此之外,于廣浩還通過與當?shù)鼐用裢浴⑼取⑼」?jié)省開支。

旅行途中的于廣浩(右)
于廣浩一路上不斷地與形形色色的人相遇,他在西藏認識了一位民間昆蟲科學家,于廣浩形容他為“真正追逐夢想的人”。這位狂熱的昆蟲愛好者,比于廣浩大10歲,在北歐攻讀醫(yī)學博士學位。他本可以拿著一份不菲的薪資,從事令人羨慕的工作,過上安逸的生活。但是出于對蝴蝶近乎癡狂的熱愛,在知道國內做蝴蝶研究收入頗微的情況下,他還是毅然放棄了其他的工作機會,全身心地投入蝴蝶研究領域。
于廣浩說:“我經(jīng)常想起他,他面臨選擇時壓力比我的壓力大多了,他要放棄的東西不知比我多了多少倍,但他還是遵從了自己的內心。”每當迷茫的時候,于廣浩總會反問自己一句:“人生這么短,我為什么不這樣做?”
在中國西南人跡罕至的原始森林里幫昆蟲學家抓了一年蝴蝶后,2014年,于廣浩結束了這段離經(jīng)叛道、恣意揮灑的“大學時光”,順利“畢業(yè)”了。
“成績是優(yōu)秀。”他說。
2014年2月16日,他在文章里正式寫下:“再見,我的大學。”
工作·創(chuàng)業(yè)
“于廣浩,你屈服啦?”
在決定要就業(yè)的那段時間,于廣浩經(jīng)常聽到這樣的聲音,但在他眼里,工作根本不是一件令人悲傷的事情。“就像我退學后依然堅持在大學里待了一年多一樣,反抗從來不是我的目的,更勇敢地生活才是。”于廣浩覺得,他已經(jīng)獲得生活給他的饋贈,下一步就是要帶著這些財富,走向人生的下一個階段,“這是很自然的事情,和屈不屈服沒有任何關系。”
由于個人經(jīng)歷豐富獨特,即便只有高中文憑,于廣浩也順利進入一家知名互聯(lián)網(wǎng)生鮮電商公司工作,擔任生鮮買手。憑借著一些機遇和出色的工作能力,他得到領導的賞識,從實習生做到采購經(jīng)理,只花了4個月。他說:“連升4級,火箭一樣的速度。22歲擔任采購經(jīng)理,我是整個集團有史以來最年輕的采購經(jīng)理。”缺乏挑戰(zhàn)性的日常工作讓于廣浩頗有才華被埋沒之感,也促使他一次次拷問自己的內心:“讀圣賢書,行萬里路,所為何事?”
不甘平淡的靈魂再一次躁動,這一次,內心熊熊燃燒的火焰使于廣浩對自己的個性有了更清晰的認識。“我對自己一直有很高的期許,喜歡挑戰(zhàn)。這是我的優(yōu)勢,我還年輕,應該去試試。”經(jīng)過幾年的積累與學習后,于廣浩開始了創(chuàng)業(yè)。
創(chuàng)業(yè)之路自然是坎坷崎嶇的,面臨著諸多風險與不確定。在成功創(chuàng)辦現(xiàn)在這家公司之前,于廣浩還經(jīng)歷過兩次創(chuàng)業(yè)失敗。兩次失敗的經(jīng)歷沒有讓于廣浩對創(chuàng)業(yè)望而卻步,反而令他迅速從失敗中汲取經(jīng)驗。他在腦海中快速復盤,更新,迭代。在謹慎評估后,他和伙伴一起創(chuàng)業(yè),做起了農業(yè)。“好多朋友知道我從互聯(lián)網(wǎng)大廠辭職去賣紅薯都覺得我瘋了,我說這有什么,創(chuàng)業(yè)是為了成事,想成事就要看趨勢、看市場,賺錢嘛,不丟人。”于廣浩笑著說。
愛好·星空
于廣浩自詡是“腳踏紅薯地,仰望星空”。他有著十分接地氣的職業(yè)——賣紅薯,和十分不接地氣的愛好——星空攝影。這頗具浪漫色彩的“月亮與六便士”的故事,還要從于廣浩20歲時被銀河的壯觀景象震撼開始說起。
那年他在青海玉樹做科考,正是5月,他借住在鄉(xiāng)間的一所小學里。某天半夜他出門上廁所時,偶然抬了一下頭,“一條橫亙天際的銀河就這么出現(xiàn)在我面前,我呆立半晌”。

永恒與毀滅。于廣浩攝
8年后的今天,再次憶起當夜,他仍然難以平靜。親眼所見的、壯麗璀璨的銀河,成為點燃他追“星”熱情的第一簇火焰。而當幾年后他架起天文望遠鏡,第一次清晰地看到月球上面的坑坑洼洼,第一次用鏡頭觸摸星體細微的紋理時,他甚至沒忍住哭了出來。
“星空的魅力到底在哪兒?”他回憶起當時所見的景象,眼里帶著沉醉。“你會感到自己是如此渺小,卻在和無限的宇宙對話。我要把這種美和感動記錄下來。”從那以后,于廣浩拿出相機,開始他的追“星”之旅。
星空攝影要求光污染少,因此于廣浩成了西部地區(qū)的常客。在輾轉新疆、青海、西藏和四川等地的旅途中,他留下了許多珍貴的回憶和作品。
“有一張拍攝雷暴的照片,是我早期的作品,我嘗試了很多次才拍出那個效果。”那是于廣浩第一次拍銀河,他至今還清楚地記得,他說:“當時在天山草原上,眼瞅著產生雷暴的積云飄過來,我嚇得腿軟,怕雷劈又不想跑。”各種念頭紛紛閃過,很快就只剩下了一個想法:不怕被雷劈,拍到片子就值了。
同時,對星空與宇宙的思考,也影響著他的許多作品。他自己非常喜歡的一幅作品是《永恒與毀滅》,里面有一只恐龍靜靜地站在星空下,一旁是C/2020 F3新智彗星。恐龍必然毀滅的命運、絕望的情緒和永恒的北斗七星形成巨大反差,這也正是他一直想表達的:生命有限,宇宙無垠。
“對于這張圖,我在拍攝之前只有一個很模糊的構思,為了能更加具體地找到我要表達的場景,我專門跑了2000多公里到黑龍江伊春的恐龍公園拍攝。”拍攝的那天正巧趕上黃昏,北斗七星也很亮,場景內能同時容下彗星、恐龍和北斗七星……于是就有了這張作品。
當然,星空攝影給于廣浩帶來的絕不只有愉悅,他也曾面臨很多絕望的時刻。2020年,為了拍攝日環(huán)食,于廣浩第8次進藏,一路遭遇的坎坷令他苦不堪言:汽車爆胎、水箱爆炸……在架起相機之后,天空依然陰云密布,倘若不是食甚時刻恰好飄來一個烏云云洞,他必然也會像先前的幾次一樣失望而歸。“所以很多人不能理解,你去看日食,跑那么遠干嗎?不確定性這么大,看電視轉播不好嗎?就算看到了,又有什么意義?”面對這樣的質疑,他不以為然,“你問我有什么意義,我在28歲那年跑一萬多公里對著太陽哭,這就是意義。”
“熱愛是我所有作品的底色。”這是于廣浩給自己的攝影作品寫下的注腳。可他從沒有給自己的人生做過注解,或許沒有注解就是對人生最好的解釋。退學10年,這個性格張揚的年輕人活出了自己的模樣,從游學到旅行,從科考到工作,從創(chuàng)業(yè)到追“星”……看似橫沖直撞的活法背后,是他從未變過的赤子之心,就像他在日記中所寫的那樣:“我只是在追求自己喜歡的生活。我最多只能告訴親愛的你,原來理想并非遙不可及,原來去追求理想并不會死在路上。”
這個28歲的年輕人,正懷揣著對這個世界、對生活、對人生最真摯的熱愛,奔赴一場場對他而言并不遙遠的未知。
(蟲兒飛摘自微信公眾號“中二病康復手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