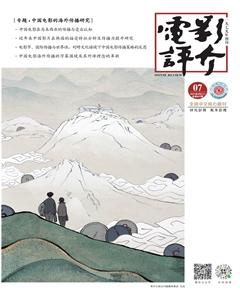中西視角對鑒,多元身份重置:英美華裔小說改編電影的跨文化敘事
董寧杰


在西方國家,文本小說和電影藝術互動的跨媒介改編,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文化現象。隨著英美華裔小說創作和研究熱潮的崛起,文化再造敘事模式已經實現了全面創新。英美華裔小說在視覺文化的影響和帶動下,電影改編的文化實踐已經成為時代發展的需要,同時,這一文化現象也感召社會歷史文化變遷的新生代創作思潮,成功實現了中西文化的雙向跨越。
一、英美華裔小說的發展歷程和多元語境特征
英美華裔小說的發軔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以美國華裔作家水仙花撰寫的《春香太太》為重要標志。之后,以湯婷婷等人為代表,英美華裔小說的創作逐步走向高峰,其不僅成為西方國家的主流文學,而且開始在國際文壇活躍,備受世界矚目。英美華裔文學的發展一共經歷了三個主要階段:第一個階段(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英美華裔文學創作,其內容和題材關注的范圍是中國社會,同時和西方國家的生活背景進行對照,敘事視角在中國和西方國家來回切換。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品主要有:湯婷婷的《女勇士》《中國佬》,徐忠雄的《天堂樹》,以及譚美英的《喜福會》;第二個階段(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英美華裔文學創作,其內容和題材漸漸從中國轉向西方國家,主要描述的是華人在西方社會的體驗和遭遇。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品主要有:湯婷婷創作的《孫行者》、任碧蓮創作的《典型的美國佬》等;第三個階段(21世紀以來)的英美華裔文學創作,其內容和題材關注范圍雖然中西兼而有之,但西方國家的敘述場有所淡化,作家們是以國際的視角范圍來審視作為故鄉的中國。作品中透露出一種雙重語境的文化色彩,他們在描摹中國社會現實時,也有了自己獨立的思考和認知,在書寫方式上也顯得更加獨特深刻。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品有:譚恩美創作的《拯救溺水魚》、鄺麗莎創作的《雪花秘扇》等。
英美華裔小說是世界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國際文壇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它不僅為世界文學的發展提供了新鮮養料、增添了奇異色彩,而且在促進中西方民族文化融合方面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近年來,英美華裔文學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態勢,顯現出前所未有的盎然生機,這些作品形象地再現了兩種不同文化、兩個不同種族的對立沖突,同時也將華人后裔的美好期盼寄托在作品中,體現了作者對中西文化融合的迫切渴望,希望藉此構建一個和諧共存的美好世界。以譚恩美的《喜福會》為例,這本書細致描繪了四對母女之間的文化代溝以及心理隔閡,深刻反映了華裔中國文化與西方異質文化的碰撞、交融過程。移民美國的華裔母親,她們有一種葉落歸根的懷舊情懷,但是由于她們長期生活在美國,因此在兩種文化沖突中經歷了艱難的心理掙扎。華裔母親們一直在考慮如何將中國文化言傳身教給自己的子女,從而守住中國文化之根。但幾個女兒們由于在美國長大,在美國白人主流社會的夾縫中生存,經常有一種文化迷失之感,后來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求得了心靈的解脫,她們這才明白:母親和祖國才是她們真正的“根”。
20世紀60年代以后,英美華裔小說作家漸漸興起了一種探索英美華人文化身份以及文化歸屬問題的熱潮。作品不僅側重于展現英美華人在西方國家的生存狀態以及奮斗歷程,同時還試圖刻畫全新的英美華人形象,塑造華人的群體性身份,即反映眾多的華人個體在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環境背景下內心的糾結、掙扎,試圖確立自己新的文化身份的過程,這個過程實際上體現了英美華人在異國他鄉不斷成熟成長的過程。以美國華裔作家趙健秀的作品《祭祀食品》為例,書中講述的是一個內心敏感的美裔華人青年藝術家約翰尼的故事。約翰尼的父親身患肺結核,疾病正在吞噬父親的健康,而且他們所生活的區域唐人街很多人也因為這種疾病的傳染相繼死去。對外約翰尼對父親的疾病是隱瞞的,一直當做一個秘密進行保護。約翰尼深深地感到唐人街這個地方太小了,他急迫地想離開這里,因為這里已經沒有他繼續生存發展的空間,他感到無比壓抑,他更希望走向更加廣闊的世界。然而他的內心也在猶豫,不知道自己離開唐人街后,是否真的能夠生存下去?實際上,這部小說所反饋出來的問題即約翰尼在成長過程中所遭遇的困惑,也是很多美國青少年面臨的主要困惑:唐人街作為美國傳統華人的一個主要社團,屬于一個相對比較封閉的圈子,這個圈子給華人提供的生存發展空間很小,再加上中國傳統文化存在的各種弊端,唐人街也像得了肺結核一樣在逐漸失去往昔的活力。因此,只有想辦法跳出這個圈子,確立自己新的坐標系,將華人文化和美國主流文化進行接軌,才能讓華人文化煥發新的光彩,讓美裔華人重獲新生。
二、英美華裔小說改編電影:從文字到光影的華麗變遷
隨著英美華裔文學小說作品的百花綻放,其已發展成為世界文學影視改編領域的重要成員。華裔美國文學是有著雙語文本的藝術作品,因此便有了雙文化的特殊背景。作為一種特殊文學范本,同時由于作者擁有中國與外國的雙重生活背景,華裔美國文學不管在內容方面,還是在創作風格甚至文字使用上,都具有雙重文化特色,這為世界影視的發展提供了全新譯本。20世紀30年代,英美華裔小說作品的影視改編開始萌芽,如賽珍珠榮獲普立茲獎的小說《大地》被改編成同名電影,成為較早走進好萊塢影院的東方題材電影代表。本片由維克托·弗萊明、西德尼·富蘭克林聯合導演,編劇為費利克斯·E。影片盡管表現的是中國農村一對夫婦的悲劇性故事,但劇中的主角卻都是由美國演員扮演。在風格方面,采取了西方古典主義電影風格,雖然影片講述的故事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有些老套,但影片制作嚴謹,拍攝技巧獨特,里面有很多特技表現。后來,演員路易絲.萊娜也憑借這部影片榮獲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大地》這部電影著力呈現中國農村樸實的生活面貌,它的誕生標志著美國流行文化電影這種藝術形式在對中國生活進行表達時有了明顯的進步。電影進行改編時,導演通過一定的美化策略對小說原著的部分情節進行了適當的修飾,去粗存精,細節化更強,一經上映便在好萊塢影壇取得了強烈反響,堪稱美國電影歷史上塑造中國形象的經典電影。
英美華裔小說的電影改編,不僅改變了中國人在外國人心目中的形象,而且還大大增加了英美華裔小說的國際影響力和文學地位,這對于傳播中國文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英美華裔小說的大量作品中,不僅有作家對祖輩歷史的深刻記憶,還有對時代變革的切實記錄,更有他們身處異鄉時對現實生活的直觀體驗和深刻思考。以美國為例,20世紀的美國社會,經歷了許多大事件:殘酷激烈的世界大戰、轟轟烈烈的民權運動和影響深遠的婦女解放運動,更有塵囂甚上的反文化運動、第三次文化浪潮等,對華裔文學創作產生了一定影響,同時也為影視改編帶來更多的靈感和素材。其實,不管是文學創作,還是各種類型的電影改編,都無法脫離社會現實和一定的時代背景。對英美華裔文學的電影改編而言,主要看重的是作家、作品的知名度或內容是否為中國故事等方面。知名作家、知名作品改編的影視作品容易形成一定的口碑和票房,反過來影視改編也可以從一定程度上推動英美華裔小說的發展創新,讓英美華裔文學漸漸擺脫邊緣性地位的現狀,躋身西方社會的主流文學圈。同時通過電影改編,不僅順利將文學作品過渡為影像,還可以實現文本到圖像的意義再生,重新激活原有的文本語言,拓展小說的闡釋空間,延伸文本的內涵。除了上文提到的賽珍珠及其作品《大地》外,黎錦揚也是英美華裔作家的重要代表。作為一名通過英文寫作闖進西方文壇的先鋒華人作家,黎錦揚創作的《花鼓歌》成為當時美國文壇頗受歡迎的小說,在美國主流文化圈也享有盛譽。還有華裔文學作家毛翔青的《酸甜》,被改編成影視作品上映后,在很大程度上擴大了英美華裔小說的影響力。這些作品不僅促進了原著的熱銷,而且很多專家學者也對其改編的影片進行了深入的解讀。
從另一個角度分析,英美華裔文學開始得到電影創作者的廣泛關注,并將很多作品成功推入影壇,這也是文化全球化的直觀體現。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快,文化的全球化也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同時,在諸多新興傳媒技術的推介下,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文化交流變得更加頻繁,不僅涌現出一大批英美華裔作家,作品數量越來越龐大,影響力越來越大,而且也得到廣大海外讀者和電影創作者的大力關注。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快,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和理解變得更加重要。由此可見,英美華裔文學作為一種多元化的文學形式而出現,不僅有助于各國跨文化交流,還為不同文化背景的受眾提供了一個了解他國文化的良好契機,從而發出不同的聲音。在西方發達國家看來,這是保證自己在激烈文化競爭、經濟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的重要手段,因此,以好萊塢為中心的影視機構不再局限于以往的電影改編角度和眼光,而是將一部分精力放在了對英美華裔文學作品的改編上來。英美華裔文學是以西方人所熟知的英語來展現中國元素,這樣的作品不僅改編起來相對容易,更具文化價值和歷史意義,而且容易引起西方世界的情感共鳴。
當今,中國的很多傳統文化之所以能夠被全世界所知曉,其中,對英美華裔文學的電影改編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對很多外國觀眾而言,和難以理解的文字篇章相比,電影對中國文化形式的呈現相對比較直觀,也便于吸收。同時,通過對英美華裔文學的電影改編,很多細致末節和零碎的故事情節,都被電影創作者進行了更進一步的修剪或弱化、集中,從而使故事中的矛盾沖突更加具有張力。
三、英美華裔小說改編電影的跨文化敘事分析
(一)從異域視角見證時代發展
電影改編從表面上看是通過電影形式將文字作品進行了二度傳達,而實際上是因為導演和編劇對原著作品有所觸動而進行的一種新形式的表現。所以在電影改編過程中,不僅要對原著的主題思想精確把握,對作品中透露出的哲理內涵有清醒認知,還要顯露電影創作者的獨特個性和另類視角,從而達到宣泄自我情感、提煉作品主旨的目的。不管是《大地》《雪花秘扇》還是《喜福會》,在電影改編過程中,創作者都融入了自己對原著小說的理解,并充分考慮到觀眾的接受程度和觀影口味,從而符合市場的需求。因此,這就要求創作者必須對原著小說內容進行一定程度的增刪,或者有選擇性的強化或者弱化,同時探索更加恰當的影視表現技巧,讓電影能順應時代發展的潮流。20世紀90年代前,很多英美華裔小說的改編電影,在情節的處理上采用的都是線性敘事方法,而且在鏡頭的拍攝上多半運用了蒙太奇的技巧。然而進入90年代后,英美華裔小說的電影改編中添加了諸多新的元素。在敘事手法上,從以往單一的線性敘事、第三敘事視角轉變為多重敘事,從而全方位、多樣化地展開故事情節。另外,影片還通過閃回、懸念等新的電影手段增加影片的觀賞性。如對小說《喜福會》的電影改編:原著中的敘事結構看似凌亂但卻錯落有致,而在電影改編過程中,主要是通過閃回的藝術方式來體現母親一代的故事。影片時而對母親的中國故事進行敘述,時而又切換到現實畫面中女兒所面臨的美國生活。通過這樣的手段,展現了兩代人在不同生活背景下的故事,也體現了不同文化之間的碰撞融合過程。影片還通過懸念預設的方式展現了美裔華人尋根之旅的圓滿,展現了片中主人公羅斯因為女性意識的覺醒從而達成圓滿的結局。
(二)借助華人視角傳播中國文化、建構西方社會形象
英美華裔文學的電影改編,不僅通過西方電影世界展現華人的生活經歷、描繪時代的發展變遷,還借助華人視角傳播中國文化、建構西方社會形象。在很多根據英美華裔小說改編的電影中,都涉及中國式愛情、友誼的話題,這從一定程度將中國忠誠、專一的道德觀念傳播給西方世界。另外,影片還展現了諸如女書、哭嫁、貼福字等中國傳統習俗,從而引起了很多西方人的濃厚興趣和關注。當然,這些改編電影除了展現中國的文化元素外,還順帶勾勒出西方國家的社會輪廓。以黎錦揚的《花鼓歌》為例。小說通過英語展現本國傳統文化的同時,也以華人的視角描繪了外國文化的地圖。書中雖然講述的是主人公王戚揚一家人在唐人街的生活狀況,而實際上把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的社會圖景也間接反映出來,記錄了當時華人在美國反華勢力的壓迫下艱難的生活環境和痛苦的內心掙扎。小說中塑造的王戚揚屬于一個典型的中國父親形象,他不僅有著根深蒂固的封建家長制傳統觀念,也存在難以改變的男權主義思想。他雖身在美國,卻依然堅守中國人的生存方式,而這正是引爆父子矛盾的導火索。但是在小說的結尾,王戚揚漸漸變得隨遇而安,并開始嘗試接受西方新鮮事物和異國文化。經過電影改編的《花鼓歌》,所塑造的王戚揚人物形象主要的作用是為了推動情節發展,他鼓勵兒子和李梅以美國方式自由戀愛,同時即便知道李梅是非法偷渡也對她和兒子的婚事表示大力支持。影片中所呈現的矛盾沖突也和小說有所差別,小說中反映的主要是不同生活環境和文化背景下,新老兩代人的身份認同過程和道德觀念差異、中西文化沖突和碰撞帶來的父子矛盾,而電影主要反映的則是父輩的教育苦惱、兒子對父輩管教表現出的無奈,呈現的僅僅是兩代人之間的心理隔閡和文化代溝,而非直接的父子矛盾。而且改編電影中重點表現的是王戚揚兒子和李梅的愛情故事,矛盾沖突以年輕人為中心和主線,同時在對華人形象的塑造上,他們對美國文化全盤吸收,這和小說中從排斥到緩慢接受的過程有所不同。總之,電影中主要展現的是華人被美國文化同化的生活狀況,對中國形象的展現則摻雜了西方人想象的成分,電影將華人形象作為一面折射鏡,從而凸顯西方文化和形象的“高大”。
(三)從全球背景描述個人成長
20世紀40年代至60年代,對英美華裔小說而言是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旅居國外的英美華人在歷經長時間的沉默后,發出了振聾發聵的吶喊。他們從一個幾乎被遺忘的群體,開始走進世界文化的洪流,找到了自己的立足之地。因此,對于這一時期的華裔中國人在英美國家的生活狀態,得到了很多英美華裔作家的重點關注和濃墨重彩的描繪。《飲碗茶》正是這一時期英美華裔小說的經典代表,它由美國華裔作家朱路易創作,記敘了20世紀40年代末在美國唐人街一群單身漢的社會生存狀態。書中的主人公王賓來是美國第二代華裔移民,他到中國結婚后,繼續回到唐人街生活,由于自己的性無能,其妻和光棍阿松發生奸情。王賓來的父親得知事情真相后,一氣之下割掉了阿松的耳朵。此事不僅引了起唐人街堂會的高度重視,而且也驚動了美國警方。后經二者的調解和處理,王賓來一家從唐人街搬到了舊金山,開啟了新的家庭生活。后來,《飲碗茶》這部小說被改編為電影,電影借鑒了后殖民主義的表現手法,生動形象地記錄了王賓來在美國成長的歷程,同時精細刻畫了美國唐人街另類的單身漢社會。在電影中,王賓來和他的妻子梅愛是作為父權壓迫之下的產物而存在的,他們缺乏主見,只是單純地依賴于父輩所做的決定。導演運用鏡像理論來表現人物的心路成長過程。影片中,當王賓來的父親割了阿松的耳朵后,王賓來為了避禍而逃走。王賓來走進父親的房間時,看到了自己小時候的照片,還有父親的很多照片。他又打開了衣櫥,衣櫥里露出一面鏡子,在鏡子中王賓來看見了真實的自己。他仿佛有所感悟:自己要成長,就必須擺脫對父親的依賴。鏡子這個道具雖然在電影中很小,甚至不值一提,但卻非常關鍵地引領著主人公的心理變化。從王賓來看到鏡子的那一刻起,他的內心就發生了轉變,他終于跨出了自我獨立的第一步,離開唐人街來到舊金山開啟新的生活旅程。而且他還原諒了妻子梅愛對自己的不忠。后來的王賓來慢慢變得事事有主見,他再也不是以前的自己,他開始成熟,擁有了新的生命。
結語
縱觀英美華裔小說的發展歷程,它幾經敘述視角的切換變遷,凸顯了中西文化碰撞交融、作者身份尋覓建構的漫長過程。隨著英美華裔小說的日趨成熟和文學地位的逐步提升,它以其多元化的語境特征成為電影改編領域一道獨特的風景。英美華裔文學的電影改編,不僅成功實現了小說從文字到光影的華麗變遷,還通過跨文化敘事模式勾勒出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時代的精神圖譜,為中國文化的傳播、西方社會形象的建構打開一個新的窗口,有力推動了東西方文化的雙向互動和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