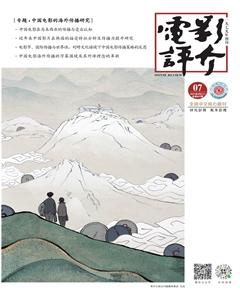主旋律元神:水華電影中的女性解放、革命激情與平等意識
孫萌
水華是中國電影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導演,盡管他的作品不是很多,只有《白毛女》(1950)、《土地》(1954)、《林家鋪子》(1959)、《革命家庭》(1961)、《烈火中永生》(1965)、《傷逝》(1981)、《藍色的花》(1984)等七部,但卻有著完整的體系和清晰的個人風格,是“詩言志”與“詩緣情”相融合的典范。水華導演在時代話語的裹挾中“化身神游”,探尋自我的存在,進而實現自我的完成。他的影片獨樹一幟,嚴謹細膩,形神兼備,深沉含蓄,洋溢著強烈的革命激情和濃郁的民族特色,每部作品都有獨特的美學追求,樸素淡雅,清逸雋永,詩意濃烈,受到觀眾的喜愛和電影界同行的贊賞與敬重,是中國第三代導演的杰出代表。
一、水華的創作特色與主旋律電影
水華(1916-1995)原名張毓藩,出生于江蘇南京一個小官吏家庭,幼時熟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對《紅樓夢》中的黛玉葬花、李清照的悲憫詩詞格外喜愛。1926年他在南京市立一中就讀時,開始受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在民族危亡之際,投身到左翼戲劇運動中,加入南京進步學生文藝團體“磨風劇社”和“南鐘劇社”,演出過《五奎橋》《放下你的鞭子》等進步話劇。1933年水華到復旦大學讀書,參加過奧尼爾的四幕話劇《天外》的演出。1934年,水華正式被吸收為左翼戲劇聯盟南京分盟成員,演出了易卜生的《娜拉》。1936年他東渡日本留學,觀摩研究了大量外國戲劇和電影作品。1937年4月回國,“七·七事變”后參加上海救亡演劇四隊與抗敵演劇二隊,輾轉多地積極參與各種抗日宣傳和戲劇演出活動。1939年曾在陶行知創辦的育才學校戲劇系擔任教員,這期間,他認真學習了毛澤東主席的文章,深入研究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人的著作。1940年春,水華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在魯迅藝術學院(以下簡稱為“魯藝”)戲劇系任教員并兼該院實驗劇團導演。1941年底,他與王濱聯合導演了蘇聯多幕劇《帶槍的人》。1942年5月,水華聆聽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他的藝術創作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延安整風運動期間,他導演過前蘇聯話劇《神手》,同時認真學習陜北方言,扶植民間演唱,以生活為根,搜集民歌,吸收秦腔、跑旱船等民間藝術的營養,編導了《夫妻逃難》《周子山》等秧歌劇以及話劇《糧食》、新歌劇《白毛女》。1946年至1948年間,水華在哈爾濱、佳木斯、沈陽一帶,建立東北魯迅藝術文學院,參加土改工作,培訓農村藝術干部,排演反映土地革命的戲劇。“這時的水華已是一個頭腦冷靜、經驗豐富的領導者,他的身份是土改工作團負責人、實驗劇團團長、青年們的老師、重大題材作品的掌控者。”[1]
延安是水華藝術與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轉折點,在魯藝這所現代主義藝術大本營里,他的階級立場、政治信仰與創作原則在此得以鑄就,他的“詩言志”與“詩緣情”相融、情志并舉的創作理念得以煉成。延安魯藝的革命履歷使他成為新中國文藝建設者中的主流人物。新中國建立后,他的作品有反映女性解放的《白毛女》《傷逝》;飽含革命激情的《烈火中永生》《革命家庭》《藍色的花》;富有平等意識的《林家鋪子》《土地》。水華電影的紅色基因與自身的藝術素養使他的作品先天擁有一種精神性與使命感,在具有功能性的同時追求形式上的美與永恒,有著藝術的精魂與生命力,讓人感覺超然又和藹可親,成為主旋律電影的元神,是中國主旋律電影創作中需要不斷回望的故鄉與精神支柱。
主旋律電影是指主流意識形態認可、國家政策倡導并體現主流文化價值觀,在情態表現上積極向上,表現歷史與現實的健康的電影創作。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征程為影視創作提供了無盡的源泉,是電影創作的寶貴財富,以黨史與紅色題材為主題的黨史電影也是主旋律電影。黨史電影可分為硬黨史電影與軟黨史電影,前者集中展示我黨波瀾壯闊的歷史與領袖人物的豐功偉績,以《建國大業》(2009)、《建黨偉業》(2011)、《建軍大業》(2017)等影片為代表;后者表現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如何貫徹到具體的人與生活中,如何為人民謀福利,讓人們感受到黨的先進性與優越性、擔當與使命,以水華導演的影片為代表。軟黨史電影并不軟,內核很硬,藍印花布里面包裹的是磁石。軟黨史電影是黨史電影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作為電影工作者如何把軟黨史的內容融入到創作中去,也是黨史電影創作中很重要的一環。
水華導演的每部作品都有他鮮明的藝術特點和風骨,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水華導演電影的文學性很高,在他那里,文學性和電影感渾然一體,具有非常強勁的造型意識;第二,對人物的刻畫深沉而又細膩,塑造了江姐、許云峰、喜兒等感動人心的人物形象,注重通過對人物的刻畫反映生活,反映時代面貌,揭示主題內涵;第三,在創作中講究虛實結合與意境美,追求藝術表現上的民族詩意,作品情真意切,質樸簡潔,形式典雅清正。深度采訪、化身神游與提煉(煉骨、煉肉、煉魂)是水華創作的獨特方式,[2]他把斯氏體系“演員自我修養”中的“神游”運用到導演構思中,當他熟悉了劇本內容、明確了作品的“最高任務”和“貫穿動作”之后,便進入了形象思維的“神游”階段,用采訪所得的大量生活素材和自己的全部知識經驗為基礎,憑借想象把人物所處的環境具體化,讓自己化身為電影中的喜兒、林老板、江姐或子君。
水華導演富有先鋒實驗精神,每部作品都有獨特的美學訴求,對藝術的探索絕不重復。《白毛女》解決的是新歌劇與電影藝術結合的問題,也就是寫意與寫實如何融合的問題;《林家鋪子》關注東方美學的詩意呈現與現實主義創作手法相結合,在中國電影史上做出了突出貢獻;介于二者之間拍攝的《土地》是電影民族史詩的一次嘗試;《革命家庭》突出了女性在革命道路上的成長與做出的貢獻、犧牲,成功塑造了周蓮這一感人至深的母親形象;《烈火中永生》在氛圍的營造與典型人物的塑造上頗有匠心,有著表現主義韻味;《傷逝》則轉向了徹底的心理劇,大膽運用意識流,注重內心探索;《藍色的花》是對黨的歷史的反思與忠誠,是對共產黨人不忘初心的影像呈現,反映了廣大人民是黨的源頭活水這一精神實質,人物身份的設定有著表意功能。
二、女性解放:從身體、心靈到經濟獨立
《白毛女》是水華的第一部電影作品,由水華和王濱聯合導演。影片根據1938年開始流傳于晉察冀地區的民間傳說“白毛仙姑”為題材來源,由同名歌劇改編而成。通過敘述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讓我們看到中國共產黨是如何在歷史中對女性解放起了決定性作用,讓人感受到“舊社會讓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這一主題。在這場從“舊社會”變為“新社會”的革命過程中,白毛女成為“苦難”的象征,女性的被損害與被蹂躪強化了革命的迫切感與必要性,郭沫若稱其為“受苦受難,有血有肉”的中國婦女與中國人民的“代表”。[3]
這部極具藝術價值的新中國早期電影,成為詮釋階級斗爭模式的經典樣板與引發民眾憶苦思甜的影像書寫。影片也成為水華從影后對自己革命生涯與藝術生涯的一次總結。影片藝術表達豐贍、質樸、淳真,運用比興手法,結合蒙太奇的活用、情緒的對照以及情節的呼應,獲得了強烈的藝術效果,有力地烘托了人物性格和命運。《白毛女》是第一部在新中國引起全國轟動的電影,上映時,國內首輪觀眾即達600余萬,創中外影片觀影人數最高紀錄。20世紀50年代,影片先后在30多個國家、地區上映。1951年榮獲第六屆卡羅維·發利國際電影節“特別榮譽獎”,捷克斯洛伐克的文化部長贊譽它:“不但充滿了詩意和優美的民歌,令人體會到中國悠久的文化藝術,并且巧妙地引用了民間傳奇,動人地體現出中國農民在封建制度壓迫下艱苦斗爭的史績。”[4]該片1957年還榮獲國家文化部1949—1955年優秀影片獎一等獎。
《傷逝》是水華的另一部有著強烈女性意識的電影,曾獲得文化部1981年優秀影片獎、1982年第二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攝影獎等獎項。影片表現了舊社會與人的自由的矛盾,對女性的困境進行了更深層次的剖析。《傷逝》根據魯迅的同名小說改編,影片以虛實相生的藝術手法營造詩化意境,畫面精致寫意,情景交融,一草一木盡顯國畫神韻。電影更多地借助話外音表現人物的心理活動,人物的潛意識與情緒流動滲透到客觀景物之中,透過詩意的鏡頭使得主人公的幻覺與想象得以延展和深化,達到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意境美。影片重在表現人物的內心世界和精神現實,展示了中國女性面臨的社會問題和心靈困境,有著現代電影的特質,很好地體現了原著的精神。子君是一個與傳統女性完全不同的女性形象,她深受易卜生、泰戈爾等人的影響,涓生和她談家庭專制,談打破舊的習慣,談男女平等。“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力。”子君的表白,是被禁錮在封建禮教牢籠里的中國婦女解放的宣言。她勇敢地向舊勢力挑戰,沖出封建家庭的樊籬,和涓生生活在一起。令人遺憾的是,他們之間的愛情由于時間的推移而變得極不合拍,生活又變得越來越艱難,子君的個性漸漸泯滅,她經常為做飯而出神,望著天空發呆,在涓生的眼里已經變成了另一個人。最終子君在愛情的幻滅中,在旁人賽過冰霜的冷眼下死去。子君的悲劇不僅是愛情的悲劇,也是社會的悲劇、人生的悲劇。“人必須生活著,愛才有所附麗”。子君這一形象比娜拉更具有歷史的深度和現實主義內涵。“她還必須更富有,提包里有準備,直白地說,就是要有錢。”[5]魯迅的答案具有超越時代的意義,女性要獲取真正的自由解放,必須以經濟權為標志,必須參與社會經濟制度的改革,否則即使已走出家門,也會以失敗而告終。婦女解放的當務之急不在于僅僅擺脫或推翻夫權專制及其男權中心的婚姻關系,而必須在心理上得到徹底解放,在經濟上爭取獨立的人格。
三、革命激情:追求內涵與意蘊的表達
于藍在《水華,再也聽不到你的聲音了》一文中曽動情地寫道:“你是一個不善辭令的藝術家,你是一個深鎖雙眉不停探索的藝術家,你更是一個滿懷革命激情的藝術家。你是把自己的一生都和時代與祖國緊密融為一體的藝術家。你的作品都飽含了為人民奉獻一切的時代內涵,這是人民藝術家最最珍貴的藝術之魂。”[6]水華自延安文藝整風后確立了“革命現實主義”文藝觀,“這種創作手法要求以革命傾向為判斷真實的依據和對人物加以褒貶的標準。”[7]現實主義的文藝作品要有深切的現實責任感與強烈的人文關懷,要求創作者高度關注現實人生,以溫情和敬畏之心,用尖銳犀利的筆觸對現實社會進行深度反映與思考,洞悉現實生活的內在本質。水華作品中的現實主義體現著他的革命精神與強大的信念,講求細節的真實,著力挖掘人物的內心世界,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這些特質充分體現在《烈火中永生》《革命家庭》與《藍色的花》幾部影片的創作中。
《烈火中永生》《革命家庭》與《藍色的花》均改編自文學作品。《烈火中永生》根據羅廣斌、楊益言、劉德彬所著革命經典小說《紅巖》改編,講述了解放前夕重慶最為黑暗的一段時期,共產黨人江姐和許云峰由于叛徒出賣被捕,在監獄中帶領難友同敵人頑強斗爭的故事。《革命家庭》展現了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一個共產黨員家庭進行對敵地下斗爭的故事,源于陶承的自傳體小說《我的一家》,女革命家陶承的丈夫與兩個兒子都是共產黨員,他們先后為革命而犧牲。《藍色的花》根據李國文的短篇小說《月食》改編而成,講述了抗日戰爭時期,小八路伊汝和首長結識了山區姑娘妞妞及其養母趙大娘,他與妞妞一家結下了深厚感情,后歷經坎坷與磨難,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他急切地回到村莊與家人團聚,在趙大娘墳前,妞妞正帶著他們的女兒心心等待著他的歸來。在這三部主旋律影片中,水華憑藉自己對生活理想、藝術理想真誠而執著的追求,竭力探尋思想內涵的深刻與藝術形式的美感。他扎根現實,將自己對普通民眾的真情實感注入影片,化入影片,基于藝術家敏銳的洞察力,巧妙地將想象力融入故事結構中,用各種藝術手法呈現“真實”的世界,創造現實,反映現實,以便抵達觀眾內心所認可的真實。
《烈火中永生》以江姐、許云峰的斗爭活動為中心,表現出當時艱苦卓絕的斗爭情景,以及身陷囹圄的共產黨人堅貞不屈的革命信念和獻身精神。水華以自己創作中的素樸、真情,天然規避了簡單枯燥的說教。他沒有通過煽情和夸張的方式來鋪展革命志士斗爭的過程,而是用細膩真實的鏡頭表現了他們的心理變化與性格特征,讓每個人物都具有獨特的辨識度和個性。例如甫志高誘騙江姐的那一場戲,水華使用了大量特寫鏡頭來描繪江姐從懷疑到確認甫志高叛變的表情變化,將江姐嫉惡如仇又敏銳機警的個性展現出來。影片中的江姐在敵人面前是鐵骨錚錚的堅強戰士,在丈夫面前是溫婉賢淑的妻子,在兒子面前是慈愛祥和的母親。于藍以樸實無華、清新自然與剛柔相濟的表演,成功地塑造了江姐這一感人至深的人物形象。江姐的光彩不僅來自她的寧死不屈,也在于于藍將女性的溫和細膩、從容淡定融入到人物的舉手投足之中。在于藍飾演的眾多銀幕角色中,江姐最為人們熟知和感佩。為了拍攝這部影片,她與水華用了兩年時間進行準備,到重慶采訪幸存革命者,搜集資料,到廣東邀請夏衍執筆創作劇本,邀請趙丹飾演許云峰。趙丹運用即興式的、真實自然的生活化表演,使許云峰既有內在的英雄氣概,又有一種平易近人的親切感,把共產黨人的忠勇、機智、堅定等氣質發揮到極致,與江姐的形象交相輝映,成為紅色經典電影的絕唱。對許云峰和江姐等正面人物塑造時,水華運用了許多仰拍鏡頭,通過這一視角將革命英雄的正氣凜然和堅強不屈在視覺觀感上凸顯了出來。于藍、趙丹的傾情演繹讓我們感受到共產黨人作為楷模的力量,讓我們相信英雄是真實存在的,這些英雄形象以他們的人格魅力影響了幾代人的理想和生活信念。
《革命家庭》中水華對原著進行了取舍與調整,將原來處于附屬地位的母親確立為主人公,變第一人稱回述為全景式描述,用旁白貫穿全劇,整部影片充滿人情味、詩情美與韻律感,影片榮獲1962年第1屆大眾電影百花獎“最佳編劇獎”。影片通過一個人的成長和一家人的變化反映時代風云,將一個家庭的命運同黨的命運、革命事業的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以簡潔凝煉、樸素清麗的鏡頭畫面,描述了兩代人在白色恐怖年代中默默為革命奉獻一切的動人故事,并以母親為軸心,抒發和渲染了夫妻、母子的摯愛親情。水華把母親的名字命名為“周蓮”是因為“周蓮”是“左聯”的諧音,導演想通過母親的形象紀念“左聯”時期的許多文藝先驅。影片注重用白描手段再現日常生活與人物心理的描摹,讓人物形象在生活細節中得以豐富、飽滿。于藍把一個不平凡女性的生命過程演繹得層次分明,質樸生動,清新感人,并以此片榮獲1961年第二屆莫斯科國際電影節最佳女演員獎。
《藍色的花》在體現我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宗旨的同時,將城鄉的二元性交織進歷史與當下的博弈中,表現了1949年以后黨的干部蛻化的社會現實問題。影片跳脫出常規的傷痕敘事框架,追求政治風雨侵蝕下永存的美好人性,創造出一種反思和內省的風格,凸顯了影片的現代性。這三部影片里面的共產黨人真正做到了為人民謀福利,為中華民族謀復興,讓人深受感動。我們需要《建國大業》《建黨偉業》等全景式群像式主旋律影片,也需要《烈火中永生》《革命家庭》《藍色的花》這樣具有英雄主義主題并能塑造普通共產黨人典型形象的作品。
四、平等意識:在情志并舉中體現
20世紀50年代,水華導演的《林家鋪子》與《土地》反映了土地與資源分配問題,以及社會不公現象,是體現平等意識的兩部電影。《土地》聚焦于農村,《林家鋪子》則集中展現中小城市的境況。
《林家鋪子》是水華的代表作,也是中國電影史上的一部經典佳作。影片改編自茅盾的同名小說,以1931年的中國江南某小鎮為背景,通過小工商業者的掙扎生存、最終倒閉和林老板一家的悲劇命運,展現了當時整個社會爾虞我詐、“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的黑暗現實。影片注重發揮電影表意和抒情功能,創造出很多有內涵有靈魂的畫面與場景,塑造出林老板、張寡婦等獨特而充滿生命力的人物形象,電影語言富有張力與意境,洋溢著民族詩情,被譽為中國的“詩電影”,曾獲得1983年第十二屆葡萄牙菲格拉達福茲國際電影節評委獎,1995年入選“紀念中國電影誕生90周年”十部優秀影片。
水華在這部影片中顯示出高超的影像表達技巧與場景調度能力。影片的開頭是一段流暢的影像敘事:鏡頭隨著烏篷船緩緩地搖進了一個江南小鎮,穿過狹窄的河道,進入那個特有的年代情境,水邊的墻壁上呈現出“攘外必先安內”的字樣,這時,一桶污水倒入平靜的河水中,污水沖擊河底,沉渣泛起,水面疊印出“1931年”的字幕。“污水”象征著在當時入侵中國的帝國主義列強,被污染的河水意指當時混亂不堪的中國社會現狀。這個隱喻蒙太奇段落含蓄而又形象地交代了多災多難的黑暗時代,表現出濃郁的地域特色,浸染出影片的悲劇底色。影片的結尾,水華繼續把隱喻表達寄托在和情節相關的場景中:畫外是張寡婦凄慘的呼喊,畫內是烏篷船上悲痛欲絕的林家父女,小船迷茫,在凄風苦雨中駛向遠方。影片體現了水華游心于“道”、情志并舉的創作宗旨。詩言志是一個詩學闡釋的命題,強調禮樂文化對情感的凈化與提升。詩緣情是一個基于創作立場的理論,是創作者對于創作機制的主動探尋,通過強調詩歌創作的動機“情”,確立情感對于詩歌創作與詩歌內容的主導地位。事實上,詩言志與詩緣情不是根本對立的兩個概念,而是相互生發、相互影響,并存于中國古代詩論中。在志與情和而不同的融合發展中,建立了既言政教之志又抒個人之情、情志并舉的詩性傳統,成為中華傳統美學中的精髓。程步高的《春蠶》(1933)、孫瑜的《大路》(1934)、蔡楚生的《一江春水向東流》(1947)、沈浮的《萬家燈火》(1948)、費穆的《小城之春》(1948)等影片,從電影創作層面印證著言志與緣情的有機結合,《林家鋪子》無疑也是這一詩性電影譜系的杰出代表。鄭洞天曾經這樣評價水華:“他在散文化方面做得較早,最成功,對后人影響也最大。如果第四、五代導演在散文化方面有所發展的話,是與《林家鋪子》這一類片子有淵源關系的。”[8]《林家鋪子》所傳達的中國古典美學神韻及其精湛的藝術水準,對社會的深刻洞察與對自由平等的心理訴求,使之成為中國詩意現實主義電影的典范之作。水華的學者型藝術家的個人氣質、真誠而又純粹的藝術個性,在這部影片中得到盡情展示。
《土地》創作的緣起是現實政治的需要,當時正在全國農村展開的土改運動如火如荼,需要一部影片把消滅封建土地所有制、實現“耕者有其田”的歷史進程記錄下來,宣傳土地改革的偉大意義。影片講述了1930年秋天,土地革命運動震動了竹林鄉,共產黨員謝友生領導當地貧苦農民打擊地主土豪、分田地,并建立了革命政權。他在這部遵命之作中追求視野的開闊與氣勢的雄渾,對黨的土改政策進行了影像化呈現,展示了土改運動的全過程,頗有史詩氣質。片中軟弱善良、膽小怕事最終覺醒的謝老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結語
水華的七部影片是新中國主流電影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在藝術服務于人民、服從于時代政治需要與實現藝術自我中輾轉騰挪,練就一種游心于“道”、情志并舉的藝術太極,給人一種獨特的審美體驗和生命體驗。他的電影彰顯了對自由、平等、美善的呼喚,為中國電影的藝術風格以及人性表現等方面的深化與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與法國導演相比,水華可以稱之為中國的“左岸派”,他的電影文學性很強,而且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具有藝術探索精神。與前蘇聯導演相比,水華可以稱之為中國的卡拉托佐夫,卡拉托佐夫的《雁南飛》(1957)、《我是古巴》(1964)等影片,在意識形態里面融入電影的詩性,所以才成為傳世之作。中國很多導演對水華贊賞有加、心服口服,水華導演的電影精神也影響著一代又一代電影人。
參考文獻:
[1]楊遠嬰.電影作者與文化再現[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5:103.
[2][8]馬德波.水華《神游》去了[ J ].大眾電影,1996(3):22.
[3]郭沫若.悲劇的解放——為《白毛女》演出而作[N].華商報(香港),1948-05-23.
[4]北京電影制片廠藝術研究室、中國電影出版社中國電影藝術編輯室合編.論水華[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2:10.
[5]魯迅.墳[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118.
[6]于藍等編選.水華集[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7:442.
[7]馬德波,戴光晰.導演創作記——論北影五大導演[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