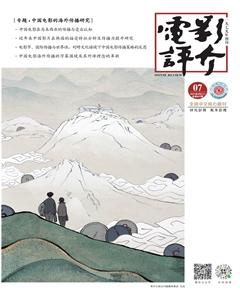中國奇幻動畫電影的本土原型開掘與全球文化交匯
米娜敏
中國奇幻動畫電影是中國動畫電影中的關鍵類型,也是中國動畫電影在全球文化與市場交流中最受歡迎的片種。近年來,《風語咒》(劉闊,2018)、《白蛇:緣起》(黃家康、趙霽,2019)、《西游記之大圣歸來》(田曉鵬,2015)等中國奇幻動畫電影調動了半個世紀以來自身的文化積淀,結合《大鬧天宮》(萬籟鳴、唐澄,1961)、《寶蓮燈》(常光希,1991)等一系列優秀奇幻動畫電影作品的經驗,在新的全球文化流動環境中尋找人類的普遍情感,挖掘文化本質與原型意象,整合全球文化資源,其內容受到全球觀眾的喜愛,在全球范圍內開拓了更大的市場與文化空間。
一、在奇幻之美中尋找人類普遍情感
提到中國奇幻動畫,觀眾往往會想到制作精美的英雄人物、雄奇浪漫的CG場景、充滿想象力的世界架構以及在精良的影像語言中收獲的審美體驗等,這也是中國奇幻動畫打動國內觀眾的原因所在。然而,許多制作精良、在中國市場深受觀眾喜愛的奇幻動畫作品,在國外的市場與票房卻不夠理想。相比之下,許多日本、歐美奇幻動畫電影并沒有如同中國作品內深厚的文化積淀,卻能夠在全世界傳播乃至在全球市場建立起市場霸權。中國奇幻動畫在世界電影市場立足的關鍵之一,在于如何在審美體驗的感染下傳達超越文化壁壘的深刻思想和情感,讓全球電影觀眾通過奇幻瑰美的視聽體驗,將注意力最終投注在對更深層次的精神內涵和價值剖析中,并在對中國奇幻與中國故事的展現中,呈現承載人類普遍情感的內容。
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中指出,我們所感知的一切現象,都以碎片化的空間與瞬時的時間形成的質料刺激形式,先驗地、直觀地進入我們感官之中。這些視聽感官的時空碎片通過純粹知性范疇的統攝被理解為具體的事物。這決定了我們對一個具體事物的兩種判斷方式:知識領域的概念判斷與感性領域的審美判斷。“奇幻”這一基本概念也是理論知識與審美判斷力相輔相成的理念。奇幻動畫電影中的人類普遍情感則產生于知性與想象力的和諧。[1]在知識領域,“奇幻”意味著與現實世界不同的架空世界,及其中種種想象力構筑的運行規則,能令現實世界形變出陌生感的人、景、事、物。如《風語咒》中上古四大兇獸為禍人間,被俠嵐用秘術“風語咒”封印,數千年后四大兇獸之一的饕餮蘇醒,為人間帶來危機的虛構設定;再例如《白蛇:緣起》中晚唐君主在國師的蒙蔽下命令天下百姓捕蛇修法,白蛇行刺國師卻被擊敗失憶,五百年后被許宣救起的設定等。這些以虛構卻精準的時間、地點與時間進行的背景設定是奇幻故事發展的重要基礎,它將一個個荒誕不經的“神話”“傳說”鉚定在特定的情景之中,潛在地賦予了主要角色以任務。《風語咒》中,兇獸饕餮即將出世,但能壓制饕餮的唯一方法“風語咒”已經失傳,男主角郎明的任務便自然而然地成為冒險找到“風語咒”,拯救人間于危難。《白蛇:緣起》中的女主角白蛇則在恢復記憶后要一邊與國師的爪牙戰斗周旋,一邊與誤會她叛逃的蛇族殺手闡明實情。在這些理解奇幻故事的知識內容產生之后,觀眾才能對奇幻的場景、風格、故事進行審美的判斷,產生審美的情感,例如對于少年朗明目盲的同情、對他執著尋求真相的感佩、為領悟“風語咒”作出的自我犧牲等。奇幻設定與奇幻美學共同指向美與善的先在理念,在審美領域內表現為美,在道德領域中則表現為善,是不同文化環境中的人類在審美判斷與道德判斷中共通的。
人類的普遍情感不是關乎個體經歷的,而是一種產生于各種情景之中的、恒久、普遍的共通情感,它在不同表象中的產生,與純粹的知性概念有關。純粹的知性概念即“賦予一個判斷中的各種不同表象以統一性的同一個機能,也賦予一個直觀中各種不同表象的單純綜合以統一性,這種統一性用普遍的方式來表達。”[2]具體到奇幻動畫中,“奇幻之美”的審美愉悅感產生于想象力世界與知性知識的結合,世界上不同地區的觀眾在憑借生活經驗與觀影經驗,自由地對影片的內容開啟認知的時候,自然生發出的純粹的知性概念就會在觀影中建立不同觀眾與影片的情感聯系,從而形成中國奇幻動畫電影的世界性表達方式。依然以上文中提到的兩部動畫為例。《風語咒》在CG動畫中以清新自然的色彩渲染出中國水墨山水的寫意感,靜謐清幽的森林夜晚、雄渾大氣的天井都頗具古典美學與視覺張力的影像表征。這些感性、知性形式的視覺內容建構起主線劇情中心懷理想的少年逐漸成長為英雄這一人類敘事藝術共通的主題,使《風語咒》跨越不同文化、地域,以強大的質料內容將其思想傳達給全世界觀眾。《白蛇:緣起》中白蛇與阿宣在小屋外一起欣賞日出、撐傘飛過云海、在山水間縱情放歌,二人間不離不棄、相濡以沫的愛情作為這些自然景觀的審美同構體,形成了建立在共通理性基礎上的感性體驗。即使國外的觀眾沒有見過煙雨濛濛的西湖、絢爛的山間朝霞,也會被一種對于審美普遍追求的認同所打動,這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先驗性感性情感,這種雄奇壯麗、美輪美奐的景觀形式,也喚起了國外觀眾對自然與情感之美的追求。
二、對文化本質與原型意象進行深度解析
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走向國際市場的中國奇幻動畫,選題或背景多出自中國傳統之中。在“西游宇宙”“封神宇宙”等一系列影片的世界架構中存在著許多基因優良的文化傳統,其敘事類型大多有著典型的奇幻性,較為適合改變為奇幻動畫電影。然而,中國的奇幻動畫電影在全球化時代的國際市場中,競爭力卻經常遜于一些傳遞普適價值觀的外國作品。對中國價值觀的輸出操之過急,反而難以達到預期。好萊塢商業動畫普遍將對親情的守護、對愛情的珍惜、對友情的堅持、對夢想的追求等普適主題隱藏在善惡對立中,而與這樣的處理方式相比,中國奇幻動畫更偏好以直接的方式與張揚的氣勢引出正方與反方的對立,在主要人物出場時就以一整套固定而扁平的描述方式,展現出鮮明的價值判斷立場。一些打著“奇幻”旗號的作品在預設好的故事套路與價值觀念下,缺乏個性與辨識度的主要角色與多元化主題表達發揮的空間,取而代之的是毫無成長弧光也無法引起觀眾同情的行動邏輯、陳腐無新意的世界觀與故事結構、大量毫無意義的冗余對話……這樣的處理方式不僅是對觀眾的不負責任,也體現了精神立場與價值取向的雙重缺失。即使對國內觀眾而言,套路化的故事與說教型的主題也極易引起觀影中的情感阻礙,對外國觀眾而言,這樣價值觀輸出優先于人物與主題表達的作品,在跨文化的傳播中還會遭遇文化壁壘,引起文化誤解,乃至對中國動畫與中國文化產生刻板印象。
盡管“奇幻”一詞的普遍使用在于當代文化工業發展成熟之后,奇幻小說、奇幻動畫、奇幻電影作為一種文化商品類型標簽的使用;但我國歷史悠久、豐富多元的文化脈絡中早已蘊含了“奇幻”的本質。當下的中國奇幻動畫電影應該在對民族化情感主題與價值概念的本質進行深化的基礎上,與全球文化中的主題表達求同存異,將講好中國奇幻故事作為國產奇幻動畫向海外延伸的首要出發點。以取材自《西游記》的《西游記之大圣歸來》為例,這部以孫悟空為核心人物的“西游宇宙”奇幻作品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對孫悟空形象的重寫。與之前幾部同類型同題材的“孫悟空”奇幻動畫相比,拍攝于1961年的《大鬧天宮》中的孫悟空自由不羈,在大鬧天宮的過程中威風凜凜,幾乎無往不勝,其中寄托了創作者對勞動人民反抗封建壓迫的贊美;1991年版《寶蓮燈》中的孫悟空以取得真經后蹉跎歲月的“斗戰勝佛”的形象出場,幫助了劈山救母的沉香,也在沉香的激勵下重新拿起金箍棒,找回了身為“齊天大圣”的光輝。《西游記之大圣歸來》中的孫悟空形象更加放肆顛覆,在這部動畫電影的世界觀中,孫悟空被降格為失去所有法術與力量的普通人,滿腹牢騷,無法面對自己,幾乎完全被現實擊倒而無能為力。在這樣的“孫悟空”故事中,孫悟空被剝奪了一切勇敢強大、自強不息、堅毅奉獻的固有情感內涵,成為一種英雄墮落的人物原型。其可以通過神話、宗教、夢境、幻想、傳說、文學敘事中不斷重復出現的原型意象顯現出來。“原始意象或原型是一種形象,或為妖魔,或為人,成為某種活動,他們在歷史過程中不斷重現,凡是創造性幻想得以自由表現的地方,就有它們的蹤影。”[3]原型意象是在所有個體化的自我意識出現之前,普遍而廣泛地存在于所有文化中的潛在心理過程和功能,它可以表現為反復出現的角色典型、敘事結構、描述性細節等;它的作用在于跨越文化壁壘,召喚出跨越時空的人類潛在心理,有超越個人、偶然和暫時的永恒藝術魅力。“原型的情景發生,我們會突然獲得一種不尋常的輕松感,仿佛被一種強大的力量運載或超度。在這一瞬間,我們不再是個人,而是整個族類,全人類的聲音一起在我們心中回響”[4]。《西游記之大圣歸來》剔除了孫悟空這一角色上的各種既有觀念,將其上升為更具人類普遍接受的原型意象,從而在無意識的原型心理的影響下,令孫悟空的故事不僅能反映本民族內涵,還能建構起世界普遍接受的共識形象:決戰時通過信念掙脫了佛祖的枷鎖,以磐石為盔甲、并幻化出鮮紅披風的孫悟空,無疑是中國觀眾熟悉的“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的孫悟空;而在五指山下蹉跎數百年后力量盡失、仍拼命保護弱小江流兒的孫悟空,則體現了跨越地域與文化的悠遠歷史中積累的、無數普通人呼喚的扶危濟困的平民英雄典型。在傳統的神魔敘事、歷史傳奇敘事的基礎上,奇幻動畫電影等當代奇幻作品作為宏大敘事衰落后的一種新的文化癥候出現。順應“互聯網哺育的一代青年人的消費需求”,并“在儒家傳統文化以及現實主義創作制約下的背景中產生”[5]。換言之,數字技術與互聯網技術的引進,催生了一種“無中生有”的內容生產與消費,這種以強大的想象力支持的內容生產與消費在文化意義上構成了中西方文化與亞文化的融合與創新。綜上觀之,對于文化的深層解讀應是今后中國奇幻動畫電影尋求突破的著力點。
三、在包容的文化認知中整合全球資源
當前的中國奇幻動畫電影正處于東方與西方、現實與幻想、過去與未來、原創或翻拍等多重范疇的交匯點。在這種多元文化交匯、異質特性雜糅的背景中,中國觀眾對社會、藝術、文化的認知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動。雷蒙德·威廉斯曾將“文化”闡釋為“一般社會過程中的一種特殊方式,是意義的給予和獲取,共通意義的緩慢發展,使社會獲得意義并反映它們的共通經驗”[6]。在電影創作的領域尊重不同文化的基本構成,對傳統文化資源進行符合當代價值的重構,對異質性資源基于文化均衡的原則,進行以求同存異為核心的通約整合,是增強國產奇幻動畫競爭力、拓展其全球生存空間的必經之路;也是對部分國家文化霸權,特別是對于西方中心主義的有效抗爭。在新的全球化文化認知中進行不同文化資源的通約整合,一方面在于將中華傳統文化轉化為現代媒介環境中的創作資源,將本土特有的文化資源向人類集體、普遍的生存的經驗與記憶轉化;另一方面,則要在人類永恒主題的表達基礎上,對全球多元文化中的共性加以開掘和豐富,尋找其中能夠引起不同地理區域觀眾強烈共鳴的人物、故事與情感。全球文化資源的再創作與跨媒介、跨地域轉化是一個反復、多面向的過程。
以《羅小黑戰記》(木頭,2019)為例。這部動畫電影虛構了人類世界與妖精共同生活的現實,一只名為羅小黑的黑貓盜取天明珠失敗,重傷而逃,在家園被破壞開始了它的流浪之旅。這部動畫的導演及主要創作人員都是年輕一代日本動畫的愛好者,在羅小黑的冒險之旅中,多次出現了國外作品中的元素:《龍珠》里的云澤比特高地、《海賊王》里的九蛇島、《鋼之煉金術師》的生命之樹與賢者之石、《魔神英雄傳》里的創界山……導演木頭在采訪中也坦言受到《聰明的一休》《恐龍特急克塞號》《龍珠》《機器貓》等作品的影響。如在《羅小黑戰記》一幕中出現了妖精洛竹以上半身眼中前傾的姿勢急速奔跑的畫面,這樣夸張的動作明顯不符合現實重力的原則,在真人電影中也很少出現,但它卻是許多二維動畫繪制動作場景時的慣用方式。例如《懸崖上的金魚姬》(宮崎駿,2008)中宗介向海中的波妞跑去時,為了強調速度快將宗介的身體畫得極度傾斜,在連續的活動畫面中,這樣不具備平衡感卻頗具動態感的效果給手繪的奔跑動作帶來了生機勃勃之感。在對藝術形式的借鑒之外,《羅小黑戰記》中也充滿了跨文化的人文氣息與時代內涵,在對民族文化的自覺、自信中呈現出了對普適情感與多元文化的深層認知與凝練表達。例如主人公羅小黑的角色設計。在影片開頭時羅小黑失去家園,在尋找新家的途中結識了風息并被他收留,開始把風息當做家人。整部影片以羅小黑的視角展開,因此采用了非常多的仰角鏡頭,以模擬小貓(與變身后兒童)的低視角。這一主要角色的設置方式本身不帶偏見,純真可愛、以赤誠之心待人的小黑在出場之處純潔如同白紙,是一個亟待故事情節豐滿的人物;羅小黑的旅途則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倫精神、對溫馨家園與安定生活的渴望及信任他人、集體意識等不帶有地域特征的共同情感。故事中的風息、洛竹、虛淮、天虎等因為家園遭到人類破壞而流離失所。一開始,他們因為討厭人類聚集在一起,計劃自行創造一個沒有人類存在的領域。但羅小黑的出現,卻使他們消解了對異族的恐懼與憎惡,他們將羅小黑與同伴視為比沒有人的領域更為重要的家人,從而最終接受了與人類共同生存的事實。“一個人的藝術審美心理易于和表現他所屬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藝術作品共鳴,同時由于求奇、求新和渴望了解陌生這一系列心理因素制約,也愿意接受他種地城、異族文化形成的藝術作品,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越是民族的,越是容易走向世界”[7]。《羅小黑戰記》中對情感的升華與對異質文化的包容,也許正是當前中國奇幻動畫作品乃至國產文化工業走出國門、走向海外的過程中需要借鑒的根本要義。影片結尾處,妖精鳩老和小仙哪吒討論風息留下的森林會怎樣處理,鳩老想到自己曾有一座洞府被人類占有收起了門票,因此風息的森林也可能被改造成公園收門票,而哪吒卻認為會被人類砍掉當木材。這段既世俗又超脫,既帶有遺憾又不失溫情與幽默的對話治愈了人類與妖怪之間爭斗帶來的創傷,也以普適性的內容消弭了當今世界上不同文化之間的裂痕,體現了和諧融通、謙虛內斂的包容性認知。這可能也是《羅小黑戰記》可以開辟“海外同步長線上映”的全新海外發行模式,并創造了中國動畫電影海外發行票房紀錄的原因所在。
結語
中國奇幻動畫電影經常需要從國內外的成功作品中汲取經驗,探尋本土文化蘊含的價值核心與世界文化資源的交匯點,深度挖掘人性內涵與對生命價值的認知,繼而在自身的技術水平與市場經驗基礎上積極探索存在的不足,最后以共同的人性表達與情感判斷為跨文化傳播的基礎進入海外市場。
參考文獻:
[1][2][德]康德.判斷力批判[M].鄧曉芒,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0,73.
[3][4]葉舒憲.神話:原型批評[M].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150,17.
[5]陳旭光,陸川,張頤武,尹鴻.想象力的挑戰與中國奇幻類電影的探索[ J ].創作與評論,2016(04):124.
[6][英]雷蒙·威廉斯.文化與社會[M].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11:315.
[7]尹鴻,唐建英.走得出去才能站得起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電影軟實力[ J ].當代電影,2008(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