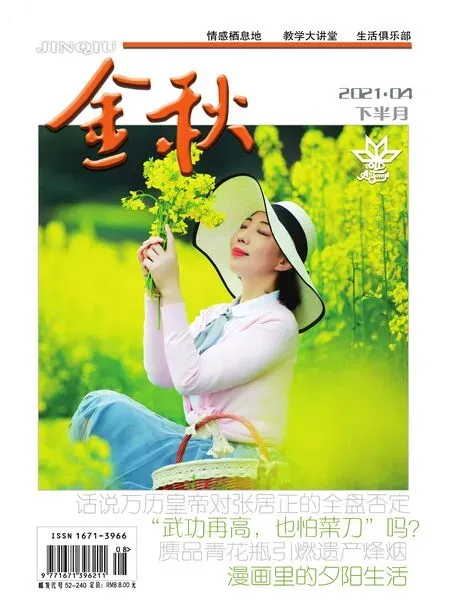曾國藩論詩 酷似林黛玉
◎文/廣東·劉黎平

林黛玉是《紅樓夢》中的文學形象,一輩子除了曾在揚州和金陵之間來回過一兩次之外,大部分時間不曾走出深閨大院,主要是待在大觀園里,在怡紅院、瀟湘館、蘅蕪苑之間走動,是一位大家閨秀,柔弱女子,無驚天動地的舉動,她能和曾國藩有什么共同點呢?曾國藩是晚清重臣,一生南北征戰,先是征討太平軍,其發跡也源于此,后來又和捻軍作戰,功敗垂成。他還是洋務運動的發起者,一生不管爭議如何,確實是個實實在在有重大影響的歷史人物,這個人怎么能和小說中虛構的貴族小姐有共同點呢?
然而,凡是古代中國有文化的人物,都是愛好詩歌的,盡管有時候兩個人物八竿子都打不著,但在詩歌這個領域,卻可能有著驚人的相似性。林黛玉與曾國藩亦如此。
學習寫詩,必須先熟讀作品
俗話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說的是中國傳統的寫詩之道,強調先要熟悉優秀作品,熟讀文本,然后才能有感性積累,從而從事文學創作。而且詩歌必須含蓄,講究意蘊,切忌直露淺俗,這些也必須建立在詳熟前輩大師作品的基礎上。
再說林黛玉,在賈府女性當中絕對是詩詞高手,如果拍合影,恐怕應該坐在第一排,只憑“冷月葬花魂”就能獨步《紅樓夢》。薛寶釵雖然有詩才,但和黛玉比起來,不免俗了一分。黛玉作為詩人已經是高手,而作為老師呢?在《紅樓夢》第四十八回,就有個香菱學詩的故事,通過香菱的請教,林黛玉的指教,道出了學詩必須先熟悉優秀作品的道理,同時晚清重臣曾國藩關于讀詩寫詩的見解,也和林黛玉有異曲同工之妙。
薛家的丫鬟香菱,也就是《紅樓夢》中甄士隱的女兒,被拐賣為婢女,雖然遭遇悲慘,但文藝青年無論在什么環境里都不會放棄追求藝術和美好的夢想,一旦和林黛玉親近,馬上就提出要跟林黛玉學詩。香菱并不是沒有基礎,她也私下里學過一些詩歌,這也不奇怪,早在《唐詩三百首》問世之前,《千家詩》已經影響千家萬戶,《紅樓夢》里的女性聚會,也以千家詩為口令。香菱跟黛玉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只愛陸放翁的詩,‘重簾不卷留香久,古硯微凹聚墨多’。”說明香菱在這個領域并非一無所知。
黛玉首先排除了香菱的畏難心理,她將詩歌創作之道總結起來,使其顯得很簡單。她說寫詩算什么難事,也值得你辛辛苦苦去學,“不過是起承轉合,當中承轉是兩副對子,平聲對仄聲,虛的對‘虛’的,實的對‘實’的。若是果有了奇句,連平仄虛實不對都使得的”。增強了香菱的信心之后,黛玉老師就告訴香菱的學習之道,要細讀王維的五言律詩一百首,“細心揣摩熟透了”,然后是細讀杜甫的詩一二百首,李白的七言絕句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了這三個人作了底子”。說完了這些話,然后就將王維的五言律詩送給香菱,叫她去苦讀熟讀。香菱領了這份家庭作業,果然覺都不睡,通宵點燈讀詩,“諸事不顧,只向燈下一首一首的讀起來”。
林黛玉教香菱如此讀書,而《紅樓夢》問世百來年后的曾國藩是怎樣教導子弟讀詩歌的呢?我們來看他的書信記錄。
在咸豐八年(1858年)八月二十日寫給曾紀澤的信中,他要求曾紀澤“須熟讀五古七古各數十首”,所謂五古七古,就是指五言古體詩和七言古體詩,而且還有儀式感,要讀出感情,要讀出氣場,“先之以高聲朗誦,以昌其氣”,先高聲朗誦之后,還得持續下去,用比較低的聲音密密地吟詠,先前如同春雷,后來如同細雨,“以玩其味”,在氣勢上和玩味上齊頭并進,然后古人寫詩的情境和氣勢,才能涌上心來,與之合而為一。香菱在燈下專心讀王維之詩,估計也是高低聲相間地用功。
再往前推,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三月初五日寫給弟弟們的信件中,他說“學詩無別法,但須看一家之專集,不可讀選本”。曾國藩生怕弟弟們不能領會,強調了一句:“至要至要。”
要讀哪些專集呢,從曾國藩自己編輯的詩歌書籍就可以看出一二,他閑暇時間所編輯的《十八家詩鈔》,就大量收集了李白、杜甫、王維的詩歌,動輒幾百首,每一種體裁的詩歌都集中在一起,這和林黛玉要求集中精力在王維的詩歌上用功如出一轍。林黛玉在王維的詩歌專集上畫了一個個紅圈圈,要求香菱重點誦讀和學習,其實也相當于臨時編了一本教材,這種教材和曾國藩的《十八家詩鈔》的相同之處在于,不零碎選作品,而是大量同類型的詩歌集中在一起,讓學生“高聲朗誦”和“密詠恬吟”。
向最牛詩人的老師學習
林黛玉老師和香菱同學第一次上課交流時,香菱說喜歡陸游的詩歌,誰知道黛玉馬上糾偏:“你們因不知詩,所以見了這淺近的就愛,一入了了這個格局,再學出不來的。”
看到這里,不免有些驚奇,令人錯愕,連陸游的詩都不算上乘嗎?那要誰才能入你的法眼呢?其實,黛玉的這番話,也正是宋明清時期文化人的共識:要學好詩,必須以《詩經》《楚辭》、漢樂府、古詩十九首、盛唐詩為范本,這樣才能走上正道。盛唐之后的詩歌雖好,但不足以取法。這種觀點不管科學與否,在當時確實是主流。
例如《滄浪詩話》就認為,想要學好詩,就得從先秦兩漢和魏晉詩歌、李杜入手,“皆須熟讀”,這樣才“不失正路”。晚清的曾國藩也如此認為,在同治元年正月十四日寫給兒子曾紀澤的信中這樣寫:“爾要讀古詩,漢魏六朝,取余所選曹、阮、陶、謝、鮑六家,專心讀之。”這些詩人,就是指三國魏晉時期的三曹、阮籍、陶淵明、謝靈運、鮑照等,其詩古樸高簡,可以打好寫詩的底子。而黛玉教導香菱的又如何呢?我們且看,黛玉認為,在熟悉了李白、杜甫、王維三家之后,“然后再把陶淵明、應、謝、阮、庾、鮑等人的一看”,其中的應是指東漢詩人應玚,劉應該是指建安七子中的劉楨,或者東晉的劉琨,庾則是南北朝時期的庾信,杜甫夸他“文章老來成”。

曾國藩
兩相對比一看,曾國藩開的書單和林黛玉開的書單幾乎如出一轍,尤其是十分重視漢魏六朝的詩歌,是不是曾國藩看了《紅樓夢》受到啟發了呢?難道林黛玉是曾國藩間接的老師?其實也未必,在曾國藩的日記、筆記和書信里,似乎找不到他愛看《紅樓夢》的記錄,但這并不妨礙他和林黛玉的觀點趨同,其實也就是說他和曹雪芹的觀點趨同,曹雪芹只不過是通過林黛玉的口,以林黛玉立言,講出了自己的詩歌主張。
我們今天的人喜歡唐詩,而唐代那些大詩人,他們的老師又是誰呢?最直接的老師就是魏晉南北朝時候的詩人,例如陶淵明,建安七子,三曹,竹林七賢等等。李白就屢次表達了自己對那個時代詩人的崇拜,例如“中間小謝又清發”“令人長憶謝玄暉”,杜甫、王維他們都是如此。想想看,李白、杜甫等人已經是中國古代最牛詩人,而他們強大的能量,直接來源于魏晉南北朝這些師傅,牛人的師傅,后人當然也得膜拜和學習。這就是為什么歷代學詩的人都強調漢魏古詩的原因。不是曾國藩師法林黛玉,而是英雄所見略同。
講究詩在功夫之外
香菱之所以能悟到詩歌的妙處,還在于生活經歷。她在接觸王維的山水風景詩之前,由于坎坷的生活經歷,就已經對于詩中所涉及的自然風光有了感性的認知,等到一用功讀古人的詩歌,所見與所讀結合起來,油然就產生意會的妙處,小姑娘打了一個很恰當的比方,“念在嘴里倒像有幾千斤重的一個橄欖”。原來,當她讀到“渡頭余落日,墟里上孤煙”時,想起某年進京的時候,泊舟江上,看到碧青的煙連云直上,于是意識到了這兩句詩的妙處。
讀詩要和生活相結合,才能有感悟,曾國藩也講過:“作詩文……然必須平日積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源,其所言之理”,所謂的“積理至富”,就是說平日的積累,諸如生活體驗積累,達到了一定的豐富程度,則自然于詩有感悟,說的不就是香菱對于“渡頭余落日,墟里上孤煙”的體會嗎?
如此說來我們就會明白一個道理,今天的家長教孩子學古詩,未必能有立竿見影之用,但是現在熟悉了,在將來的經歷當中,遇到類似詩中的情景,一下子就會噴發出來,將詩與生活融為一體,提升人生的藝術修養。林黛玉的感悟,香菱的感悟,曾國藩的感悟,和我們就會融合貫通,長流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