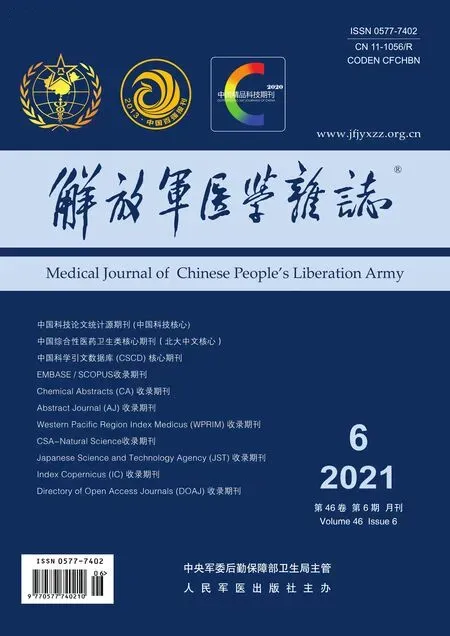高密度脂蛋白在動脈粥樣硬化免疫反應中的作用機制研究進展
潘杭雨,劉丹,郎吉萍,戴秋月,郭志剛
南方醫科大學南方醫院心血管內科,廣州 510515
心腦血管疾病是人類健康的第一大殺手,而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是心血管疾病的首要病因[1]。2016年,全球1/3死亡者的病因是心血管疾病,其中超過75%發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給這些國家帶來了巨大的經濟負擔[2]。降低危險因素、提高保護因素是預防和治療動脈粥樣硬化的重要措施。高密度脂蛋白(high density lipoprotein,HDL)作為一種血清蛋白,一直以來被認為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保護因素之一。流行病學研究表明,血漿低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igh density lipoprotein-cholesterol,HDL-C)和高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ow density lipoproteincholesterol,LDL-C)是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therosclerot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ASCVD)的主要危險因素[3]。Boden等[4]發現,血漿中HDL-C每升高10 mg/L,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風險可降低2%~3%。目前一致認為,膽固醇逆轉運(reverse cholesterol transport,RCT),即膽固醇從外周組織及細胞中流出轉運至肝臟經膽道排泄是降低ASCVD風險的主要機制,而膽固醇通過HDL從巨噬細胞中流出是RCT的關鍵步驟[5]。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提示動脈粥樣硬化與免疫反應也存在密切聯系。在動脈粥樣硬化形成過程中,單核細胞來源的巨噬細胞吞噬脂質后形成泡沫細胞是動脈粥樣硬化斑塊發生的一個重要環節,而且在斑塊病灶中還可發現樹突細胞,以及與其共定位的T淋巴細胞。HDL促進膽固醇外流的作用也調控了參與動脈粥樣硬化的免疫細胞的一系列反應,包括單核-巨噬細胞、B淋巴細胞和T淋巴細胞等[6]。因此,HDL可通過影響免疫反應而對動脈粥樣硬化的發生發展過程產生影響,從而發揮抗動脈粥樣硬化的作用。本文以HDL為重點,結合多項文獻研究闡述其與免疫反應的相互作用關系,以期為動脈粥樣硬化的防治提供新的策略。
1 HDL概述
HDL是脂質與蛋白質的非共價準球形復合物,其水合密度為1063~1210 g/L[7]。HDL顆粒的基本結構包括酯化的膽固醇核心和由磷脂、游離膽固醇(free cholesterol,FC)、載脂蛋白組成的單層結構外殼[8]。HDL顆粒具有不同比例的不同脂質:三酰甘油(triglycerides,TG)、膽固醇酯(cholesterol ester,CE)、FC及磷脂。部分HDL顆粒缺乏脂質或無脂質[9]。隨著對HDL研究的深入,鑒定出了幾種特定的HDL,約70%的HDL由載脂蛋白A-Ⅰ(ApoA-Ⅰ)組成,而由ApoA-Ⅱ組成者占15%~20%[7]。缺乏脂質的ApoA-Ⅰ主要在肝臟和小腸中合成,分泌入血漿后與三磷酸腺苷結合盒轉運體A1(ATPbinding cassette transporter A1,ABCA1)相互作用產生前體β-HDL[10]。ABCA1將細胞內的FC轉運至細胞膜,并流出至缺乏脂質的ApoA-Ⅰ形成盤形HDL。卵磷脂膽固醇脂酰轉移酶(lecithin-cholesterol acyltransferase,LCAT)可酯化HDL表面的FC,使HDL形態由盤形轉變為球形,成為成熟的HDL。在人類H D L 中的C E 可通過膽固醇酯轉移蛋白(cholesteryl ester transfer protein,CETP)轉移至富含TG的脂蛋白,間接通過LDL受體在肝臟中清除,或直接通過選擇性攝取作為HDL中CE肝受體的B類Ⅰ型清道夫受體(scavenger receptor class B type Ⅰ,SR-BⅠ),而在肝臟中清除[9]。
如前所述,HDL最為人所熟知的功能是通過促進膽固醇從巨噬細胞中流出而促進RCT。HDL還具有抗炎、抗氧化、抗凋亡及促進一氧化氮(nitric oxid,NO)產生等作用[11]。一項在冠心病患者中進行的研究發現,穩定型冠心病或急性冠脈綜合征(acute coronary syndrome,ACS)患者的HDL無法刺激內皮細胞一氧化氮合酶激活途徑及NO的產生,從而導致HDL的內皮抗炎及修復作用受損[12]。因此,HDL促進NO的產生可能在抗動脈粥樣硬化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此外,胰島β細胞內脂質水平失衡被認為是胰島β細胞衰竭的重要原因。HDL可通過降低胰島β細胞內膽固醇的含量,改善其分泌胰島素的功能,從而在血糖調節及緩解2型糖尿病中發揮作用[13]。
2 HDL與免疫反應
人體免疫反應主要分為兩大部分:獲得免疫和固有免疫。獲得免疫是機體應對特異性抗原時產生的免疫反應,通過抗原遞呈細胞(antigen presenting cell,APC)加工抗原并產生大量的T淋巴細胞或B淋巴細胞受體和免疫球蛋白來識別抗原;固有免疫是出生后即具備的天然防御系統,參與的免疫成分主要有吞噬細胞、NK細胞、溶菌酶和補體等,對外來抗原起到非特異性防御作用。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證實,獲得免疫和固有免疫中的一些成分參與了動脈粥樣硬化的發生發展過程,后續內容將主要針對目前已有較多基礎或臨床研究證明的與HDL和動脈粥樣硬化炎癥反應相關的免疫機制進行闡述。
2.1 HDL與獲得免疫 在動脈粥樣硬化斑塊中發現的多種APC提示獲得性免疫反應可發生于斑塊病灶中[14]。大量研究發現,多種獲得免疫中的關鍵因素參與了動脈粥樣硬化的發生發展過程,如定位于細胞膜上的脂筏,可促進炎癥反應的鞘氨醇-1-磷酸(spinghosine-1-phosphate,S1P),以及在高膽固醇血癥小鼠中發現的產生促炎因子γ-干擾素和腫瘤壞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的輔助性T細胞1(helper T cell 1,Th1)均可發揮促動脈粥樣硬化作用[14-16]。而三磷酸腺苷結合盒轉運體G1(ATPbinding cassette transporter G1,ABCG1)及ABCA1在巨噬細胞、樹突細胞中表達也證實了HDL和ApoA-Ⅰ可參與APC調節膽固醇內穩態的過程[17]。
2.1.1 HDL與脂筏 脂筏是含有高濃度膽固醇、鞘磷脂和與多種生物學過程相關的蛋白質的細胞膜微結構域,目前認為其參與調節了LDL的轉胞吞作用、血管壁細胞的凋亡、免疫細胞的激活與炎癥反應、蛋白酶的激活以及斑塊的穩定性等一系列與動脈粥樣硬化相關的關鍵事件。定位于APC脂筏中的主要組織相容性復合體Ⅱ(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 Ⅱ,MHC Ⅱ)類分子,在抗原遞呈和信號轉導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7]。脂筏能將MHC Ⅱ肽復合物聚集于APC表面,減少活化T細胞所需的抗原量,因此,破壞APC表面的脂筏結構可抑制MHCⅡ介導的低濃度抗原遞呈[18]。脂筏的功能與其含有的脂質成分息息相關,增加或減少細胞膜中膽固醇的含量會改變脂筏的結構,進一步導致脂筏依賴的信號通路發生改變[19]。HDL和ApoA-Ⅰ可促進膽固醇從細胞中流出,使脂筏中膽固醇的含量發生變化,導致巨噬細胞及其他APC的功能發生重要改變,并對抗原遞呈產生影響,抑制了APC激活T細胞的功能[16-17](圖1),而ApoA-Ⅰ與ABCA1結合激活的信號通路在該效應中可能起主要作用[14]。有研究證實,當巨噬細胞、單核細胞、中性粒細胞、內皮細胞和脂肪細胞暴露于HDL或ApoA-Ⅰ時,可導致脂筏豐度降低,從而廣泛抑制多種脂筏依賴的炎癥反應[20]。CD40及其配體CD40L可激活多條炎癥信號通路,從而促進動脈粥樣硬化病灶的發生發展。CD40通過募集它的適配蛋白TNF受體相關因子(TNF receptor-associated factor,TRAF)形成蛋白復合物,進一步激活下游促炎信號通路,而TRAF-6在被配體激活后主要定位于脂筏中。ApoA-Ⅰ可通過ABCA1依賴的膽固醇外流調節TRAF-6進入脂筏,從而抑制內皮細胞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 kappa-B,NF-κB)的活化,減輕CD40L誘導的巨噬細胞炎癥反應[21]。總之,HDL和ApoA-Ⅰ可通過調節膽固醇的外流改變脂筏的功能進而影響免疫細胞,從而對動脈粥樣硬化產生影響。

圖1 HDL調節脂筏膽固醇含量對抗原遞呈細胞功能的影響Fig. 1 Influence of HDL regulating cholesterol content of lipid rafts on the function of antigen presenting cells
2.1.2 HDL與鞘氨醇-1-磷酸 脂筏中的鞘脂產生鞘氨醇,再被鞘氨醇激酶磷酸化后產生S1P。游離的或與白蛋白結合的S1P均容易被降解,而與HDL結合的S1P較穩定,提示HDL-S1P可能是發揮生物學功能的主要形式[16]。在巨噬細胞中,有S1P受體1(S1P receptor 1,S1PR1)和S1P受體2(S1P receptor 2,S1PR2)兩種受體,S1P可通過S1PR1抑制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介導的促炎細胞因子的產生,且可使促炎的M1巨噬細胞亞型向抗炎的M2亞型轉變;還可通過S1PR2抑制巨噬細胞的遷移和向炎癥部位的聚集[14]。正常情況下S1PR2在內皮細胞中幾乎不表達,當發生炎癥時,S1PR2的表達增加,且其過表達可激活NF-κB依賴的黏附分子的產生[22],因此S1P在動脈粥樣硬化進程中的作用具有兩面性:一方面,S1P具有抗細胞凋亡、抗炎、舒張血管、維持內皮細胞屏障功能的作用,且可降低血管細胞黏附分子(VCAM)的表達;另一方面,S1P能夠促進淋巴細胞的激活,并促進血栓形成[23]。最近有研究表明,在LDL-R-/-的小鼠中,移植缺乏鞘氨醇激酶2的骨髓可使得內源性S1P水平升高1.5~2.0倍,與野生型小鼠相比,實驗組小鼠的病灶絕對大小、壞死核心區域面積和斑塊管腔比均明顯降低[24]。S1P可能是HDL發揮心血管保護作用的基礎,且有研究認為HDL是與載脂蛋白M結合的S1P的主要載體[25]。Lee等[26]發現,HDL相關S1P可通過刺激S1PR1和SR-BⅠ受體蛋白的分子間相互作用來影響S1P介導的細胞代謝改變,如可引起細胞內鈣離子濃度的升高。Keul等[22]發現,在冠狀動脈疾病患者中,由于S1P缺陷可使HDL-S1P水平較健康人低20%(P<0.05),導致HDL功能障礙進而引起NO依賴的動脈血管舒張功能受損;而在健康人中,HDL能夠依賴HDL-S1P有效地抑制TNF-α介導的炎癥反應。除冠狀動脈疾病外,HDL-S1P含量減少還可導致一系列疾病,如2型糖尿病、慢性腎病,提示HDL-S1P可作為HDL的一種重要組分影響HDL的正常功能,并可在疾病中發生改變[22]。
2.2 HDL與固有免疫 蛋白質組學分析顯示,HDL顆粒存在56種蛋白質,包括載脂蛋白和免疫調節蛋白,因此HDL可能參與了固有免疫并介導抗炎和抗感染效應[27-28]。HDL可抑制內皮細胞黏附分子的表達,包括細胞間黏附分子-1、VCAM-1及E-選擇素。此外,HDL還可抑制促炎細胞因子和化學因子的表達[29-30]。Taborda等[31]分析了HDL對膽固醇結晶和其他天然免疫激活物的免疫調節活性的影響,發現HDL能夠在不影響免疫細胞表面模式識別受體表達的情況下,通過Toll樣受體(Toll-like receptor,TLR)和炎癥小體介導對天然免疫刺激化合物的免疫抑制作用,導致白細胞介素-1β(Interleukin-1β,IL-1β)和IL-6的產生減少,提示HDL可調節不同天然免疫激活物誘導的免疫應答,從而影響炎癥反應。炎癥小體、炎癥反應中產生的急相蛋白及外源性病原體的產物等均可誘導炎性因子的產生,進而引發機體固有免疫反應,并對免疫細胞產生影響,促進動脈粥樣硬化病變的發展。HDL可抑制與動脈粥樣硬化有關的炎癥相關成分,從而發揮抗動脈粥樣硬化作用。
2.2.1 HDL與核苷酸寡聚化結構域(NOD)樣受體(NLR)蛋白3炎癥小體 NLR是炎癥反應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共發現了5種NLR炎癥小體,其中NOD樣受體蛋白3(NOD-like receptor protein 3,NLRP3)炎癥小體與多種自身炎癥疾病相關,包括痛風和動脈粥樣硬化[31]。NLRP3炎癥小體可能是連接脂蛋白代謝異常與動脈粥樣硬化的關鍵環節。抑制巨噬細胞中NLRP3炎癥小體的關鍵成分可完全阻滯膽固醇結晶介導的IL-1β的產生[32]。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ox-LDL)、氧化型高密度脂蛋白(ox-HDL)和HDL對NLRP3及其下游[如含半胱氨酸的天冬氨酸蛋白水解酶-1(caspase-1)、IL-1β、IL-18]的表達具有調控作用,其中ox-LDL和ox-HDL可增加NLRP3的表達,并激活NLRP3下游細胞因子和caspase-1,進一步誘導IL-1β和IL-18的分泌;而在HDL的作用下,NLRP3及其下游炎性細胞因子的表達降低[32]。Thacker等[33]發現,用重組HDL制劑(reconstituted HDL,rHDL)處理單核細胞和原代巨噬細胞可降低膽固醇結晶誘導的IL-1β的產生(P<0.01);分別用rHDL和天然HDL處理單核細胞,與未經處理的對照組相比,IL-1β的分泌分別降低70%和60%(P<0.001),提示rHDL和天然HDL均可通過減少IL-1β和NLRP3等炎癥小體關鍵基因的表達而發揮對IL-1β分泌的抑制效應。由于HDL和ApoA-Ⅰ分別通過ABCG1和ABCA1介導膽固醇的外流,因此在缺乏ABCA1或ABCG1的樹突細胞中,ApoA-Ⅰ和HDL介導的膽固醇外流減少,導致膽固醇積累的小鼠表現出NLRP3炎癥小體激活,但其活化機制尚未確定[34]。上述研究正向或反向地說明了HDL可減少NLRP3的表達與激活,并進一步抑制炎性因子的產生及炎癥反應。
2.2.2 HDL與血清淀粉樣蛋白 血清淀粉樣蛋白(serum amyloid A,SAA)是急性時相血清中HDL的載脂蛋白[35]。在急性炎癥反應中,SAA急劇升高,而在動脈粥樣硬化等慢性炎癥中,其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高于基線水平。在炎癥過程中,肝臟產生的急性時相蛋白可取代HDL中的ApoA-Ⅰ、ApoA-Ⅱ和其他酶等,產生富含SAA和血清磷脂酶A2(serum phospholipase A2,sPLA2)的缺乏保護作用的功能障礙型HDL[16](圖2)。SAA激活的巨噬細胞刺激IL-8和單核細胞趨化蛋白-1的釋放,其功能是分別募集中性粒細胞和單核細胞至炎癥部位。其他一些已知與動脈粥樣硬化相關的細胞因子的分泌也增加,而HDL可減弱此炎癥效應,可能是由于隔絕了具有促炎效應的不與脂質結合的SAA[36-37]。在心臟組織中,SAA誘導VCAM-1、NF-κB、TNF-α和促凝組織因子的mRNA表達明顯上調,而在動脈粥樣硬化模型ApoE-/-小鼠中,與單用SAA處理的小鼠比較,使用HDL預處理的小鼠血管動脈粥樣硬化和脂質氧化損傷程度更輕,表明HDL可降低SAA介導的血管內皮損傷[38]。SAA可通過NLRP3介導的caspase-1刺激巨噬細胞分泌IL-1β,而HDL能夠抑制巨噬細胞中SAA介導的IL-1β的轉錄和分泌[39]。目前關于SAA對HDL功能的影響尚存在爭議,有學者認為,在炎癥時HDL與SAA的相互作用增強,可導致HDL與脂肪細胞表面的蛋白多糖結合,從而限制HDL與細胞膜的相互作用,并抑制其促進膽固醇外流的能力[40];而另有研究報道,在SAA水平較高的患者中,HDL具有更強的抗氧化能力[41]。總之,SAA作為一種急性時相蛋白在促進動脈粥樣硬化病變的慢性炎癥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而HDL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其帶來的炎癥效應。

圖2 功能型HDL向功能障礙型HDL的轉變機制Fig.2 Mechanism of transition from functional HDL to dysfunctional HDL
2.2.3 HDL與LPS LPS通過分泌衰老相關因子(如NF-κB)介導的炎癥反應與多種老年退行性疾病密切相關[42]。研究發現,LPS可誘導衰老巨噬細胞的產生,而衰老巨噬細胞可沉積于血管內皮下,并促進彈性纖維的降解,使斑塊纖維帽變薄,降低其穩定性,最終促進了動脈粥樣硬化病變的發展[43-44]。HDL能夠與LPS和其他細菌產物結合并中和毒力,是HDL抑制炎癥反應的一個主要機制。HDL可促進LPS與LPS結合蛋白(LPS-binding protein,LBP)的相互作用,有助于LPS的清除;高濃度LBP可抑制白細胞對LPS的反應,而HDL可抑制高濃度LBP的抑制活性,維持白細胞對LPS的敏感性,從而誘導對革蘭陰性菌的早期炎癥反應[45]。另外,HDL可促進HDL受體SR-BⅠ與HDL-LPS復合物結合并介導復合物的清除[14,45]。有學者在小鼠體內預注射rHDL使其血漿HDL-C水平升高2倍,然后再給小鼠注射LPS,結果顯示,HDL-C升高小鼠的血漿TNF-α濃度-時間曲線下面積為(194±132) U/(ml.h),僅為對照組小鼠[(1126±582) U/(ml.h)]的17%(P<0.03),且存活時間明顯延長(P<0.05)[46]。相反,在ApoA-Ⅰ敲除小鼠的膿毒血癥模型中,由于HDL-C水平較低,中和LPS毒性的能力受損,從而促進了炎性細胞因子的產生[14]。與HDL緊密相連的ApoA-Ⅰ主要通過上調一種能夠促進炎癥基因mRNA衰減的RNA結合蛋白——tristetraprolin而抑制巨噬細胞中LPS誘導的炎癥反應[21]。TLR在動脈粥樣硬化病變過程中可啟動NLRP3炎癥小體,使后者被膽固醇結晶激活,產生IL-1β[47]。LPS是TLR4的一個主要配體,由于TLR定位在脂筏中,因此,當HDL和ApoA-Ⅰ引起脂筏的結構及功能發生改變時,可抑制LPS介導的細胞活化[6]。
3 HDL作為動脈粥樣硬化的治療靶點
目前,治療動脈粥樣硬化的經典藥物主要有他汀類、貝特類、煙酸等,近幾年也出現了一些針對新靶點的藥物如CETP抑制劑、過氧化物酶體增殖物激活受體激動劑、內皮酯酶抑制劑、LCAT調節子等[3]。HDL是降低ASCVD患病風險的主要因素之一,且具有調節免疫的作用,因此,將HDL作為ASCVD的治療靶點也是研究的一大熱點。考慮到HDL的保護作用,如提高循環中的HDL含量可增強其促進RCT及免疫調節的功能,從而減輕動脈粥樣硬化中的免疫反應。如前所述,HDL可通過細胞膜上的脂筏實現對免疫細胞的調節,因此,當HDL含量增加時,由于脂筏的作用可抑制免疫細胞的活化,從而減輕炎癥反應。
靜脈輸注HDL是最符合人體生理的一種直接升高HDL水平的治療方法。rHDL是來源于ApoA-Ⅰ并從血漿中純化得到的試劑,不僅可以快速升高循環中HDL的水平,而且其中的ApoA-Ⅰ還能夠與不同的磷脂重組,而這些磷脂可能產生特定的生物學作用[48]。ApoA-Ⅰ Milano(AIM)是目前知名度最高的rHDL,是載脂蛋白的一種變體,最早在米蘭鄉村的一小部分人群中發現。2006年,Nicholls等[49]納入47例30~75歲的ACS患者,隨機分組接受安慰劑(n=11)與AIM(n=36)治療,并使用血管內超聲檢測血管變化,結果發現AIM組外彈性膜體積與基線相比縮小4.8%[基線時為(343.8±92.5)×10-6L,隨訪時為(324.5±97.3)×10-6L,P=0.006],粥瘤的體積縮小10.9%[基線時為(163.4±54.3)×10-6L,隨訪時為(145.6±46.9)×10-6L,P<0.0001],且二者呈正相關關系(r=0.62,P<0.0001),但由于粥樣硬化的消退伴隨著外彈性膜的逆向重構,導致管腔大小無明顯改變[基線時為(180.1±68.3)×10-6L,隨訪時為(178.9±76.6)×10-6L,P=0.59]。另一種rHDL——CSL111是由人血漿ApoA-Ⅰ和大豆磷脂酰膽堿結合而成,在化學和生物學上與天然HDL相似[50]。Tardif等[50]通過隨機對照研究納入183例患者,并使用血管內超聲評估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斑塊,發現短期的CSL111輸注并未明顯降低動脈粥樣硬化斑塊體積(安慰劑組為158.3×10-6L,實驗組為151.0×10-6L,P=0.48),但斑塊特征指數及冠狀動脈積分卻明顯改善(P=0.01,P=0.03)。近年來,CSL111的替代物——CSL112的臨床Ⅱa期試驗結果表明,穩定的ASCVD患者單次輸注CSL112具有明確的安全性,并能夠增強RCT早期階段關鍵生物標志物的表達[48]。在一項納入44例動脈粥樣硬化疾病患者的隨機雙盲對照試驗中,CSL112與標準雙聯抗血小板療法聯用對血小板的聚集無明顯影響,因此認為CSL112不會影響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標準雙聯抗血小板治療的止血效果或增加心肌梗死后亞急性期出血的風險[51]。
然而,并非所有臨床研究都能得出理想的陽性結果。Nicholls等[52]開展的MILANO-PILOT研究對122例使用他汀類藥物治療的ACS患者每周靜脈注射MDCO-216(一種新型HDL類似物)或生理鹽水安慰劑,6周后通過血管內超聲評估動脈粥樣硬化斑塊情況。結果發現,MDCO-216治療后斑塊減少0.21%,而對照組斑塊減少0.94%(P=0.07,95%CI -0.07~1.52);MDCO-216組標準化總動脈粥瘤體積減少6.4×10-6L,而對照組減少7.9×10-6L(P=0.67,95%CI -5.6~8.7)。從檢測的各項指標可以看出,在他汀藥治療的背景下,MDCO-216并不能明顯增加動脈粥樣硬化斑塊的消退。該團隊的另一項研究(CARAT研究),通過對比CER-001(含有重組人ApoA-Ⅰ與鞘磷脂的rHDL制劑)與安慰劑在ACS患者中的療效,發現CER-001并未減輕動脈粥樣硬化病變[53]。因此,對于不同種類rHDL制劑的效果應當保持中立客觀的態度。
4 總結與展望
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證實,HDL對動脈粥樣硬化的發生發展起著重要的負向調節作用,其促進RCT、抗氧化、抗血栓形成等效應均為降低ASCVD患病風險的作用機制,而HDL對免疫炎癥反應的抑制是其中的一個重要部分。目前的動物及體外實驗表明HDL可通過多種機制,如影響獲得免疫中的脂筏、S1P等,以及影響固有免疫中的NLRP3、SAA、LPS等來發揮其抗炎作用,并顯示出較好的效果。但目前仍缺乏通過這些機制發揮作用的臨床藥物,因此,將基礎研究真正運用于臨床也是研究的另一大方向。同時,對于HDL的免疫調節作用有許多方面仍處于探索階段,需要開展更多的研究加以闡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