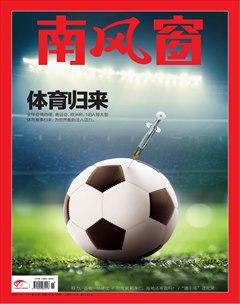拜登經濟學可能推高通脹
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
美國總統(tǒng)拜登準備效仿小羅斯福大手筆支出,而這是后者在二戰(zhàn)前一直避免做的事情。這有可能引發(fā)上世紀70年代讓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功敗垂成”的那種通貨膨脹。
自今年1月以來,拜登政府已支出或承諾支出1.9萬億美元用于直接的新冠救濟,2.7萬億美元用于投資和商業(yè)支持,1.8萬億美元用于福利和教育。這些加起來有6.4萬億美元,占美國GDP的近30%。
支出將主要通過美聯儲購買債券來融資,隨后還將增稅。但它是二戰(zhàn)以來美國最大的公共投資動員,還是通脹性揮霍?
我們還不知道,因為我們沒有準確的方法來衡量產出缺口—實際產出和潛在產出之間的差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到今年年底,美國經濟的增長將超過潛力,歐洲經濟將接近潛力。這標志著未來將發(fā)生通貨膨脹,必須扭轉赤字融資模式。
與這種靜態(tài)觀點相反,很多人相信政府投資計劃會增加美國經濟的潛在產出,從而實現更快的非通脹性增長。
拜登經濟學的大部分內容,是通過教育和培訓提高勞動力的生產率。但這是一個長期的計劃。從短期來看,所謂的供給方“瓶頸”可能會推高通脹。因此,過于宏大的議程顯然是危險的—可能發(fā)生政策突然轉向、衰退卷土重來,以及預期幻滅。
可以走更穩(wěn)定之路,但拜登政府忽略了兩個可以讓自己輕松很多的積極建議。首先是“聯邦就業(yè)保障”計劃。簡言之,政府應該保證在私營部門找不到工作的人都有飯碗,其固定小時工資不低于國家最低工資。“聯邦就業(yè)保障”的目標,不是未來的產出需求,而是目前的勞動力需求。
“聯邦就業(yè)保障”作為勞動力市場的緩沖器,會隨著商業(yè)周期自動擴展和收縮。1978年美國《漢弗萊—霍金斯法案》從未實施,該法案“授權”聯邦政府建立“公共就業(yè)儲備”,以平衡私人支出的波動。這些儲備會隨著私營經濟的榮枯而消耗和補充,從而產生比失業(yè)保險更強大的自動穩(wěn)定作用。
第二個積極的想法,是經濟學家弗拉基米爾·馬施的“有償自由貿易”計劃。進入新千年以來,美國已經損失了數百萬個制造業(yè)工作崗位,主要原因是生產被外包給了更便宜的亞洲勞動力市場。與此相對應的是,美國經常賬戶赤字平均約占GDP的5%。
拜登政府的主要目標之一,是重建美國的制造能力。雖然新冠讓所有去工業(yè)化國家都接受了一個傳統(tǒng)觀點,即它們應該為國內制造商保留“必要的”采購,而拜登的“美國制造”措施與前總統(tǒng)特朗普的“美國優(yōu)先”方針相呼應,但拜登實現美國貿易再平衡的計劃,是通過對國內生產商、貿易協(xié)議和國際協(xié)定的稅收補貼,而不是通過關稅和侮辱。
拜登的計劃是模糊和無法令人信服的。在一個充滿了次優(yōu)選擇的世界里,馬施計劃為拜登提供了最快捷、最優(yōu)雅的方式,確保他想要的平衡貿易。基本原理很簡單:任何有能力這樣做的政府,都應該單方面對其總貿易逆差設定上限,并相應地限制允許從每個貿易伙伴進口的商品的價值。
馬施認為,有償自由貿易“將刺激離岸企業(yè)和工作崗位重返美國”。它還將自動防止貿易戰(zhàn),因為“順差國家試圖降低從美國進口的價值,都會自動降低其被允許出口的價值”。
尋求刺激經濟的政策制定者,必須比過去的凱恩斯主義者更加注意避免通貨膨脹,并確保國內創(chuàng)造的就業(yè)不會被生產能力的流失抵消掉。拜登政府別無選擇,只能吸取這些教訓。如果明智的話,它將避免緊縮和不受約束的貿易,轉而支持充分就業(yè)和實現這一目標所需的生產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