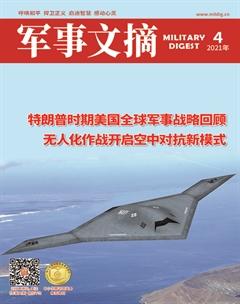特朗普時期美國中東戰略回顧
丁工

中東作為控三洲、連四海的戰略要地,歷來就是各種勢力輪番登場、角力爭斗的競技場,世界大國也多以稱雄中東來奠定強國偉業和宣示帝國霸業。因此,自二戰后美國勢力開始染指中東以來,美國各屆政府都高度重視中東事務。特朗普執政時期美國的首要戰略關切雖然是亞太方向,但依然對中東地區投注大量精力和資源。
特朗普執政時期美國
中東戰略的特點
綜合來說,特朗普時期美國在中東的戰略舉措既有延續又有調整,繼續保有美國霸權,維護美國主導、對美有利地區秩序的基本目標沒有變,并依循奧巴馬時期削減部署美軍整建制作戰力量,注重發揮地區盟友和親美勢力的作用,加緊扶植庫爾德武裝等新崛起力量,以維持中東地區各方勢力大致平衡的既有方針。但同時,與奧巴馬政府時期相比,特朗普中東政策中袒護以色列和遏制伊朗的成分則更加濃烈。
袒護以色列??巴以爭端延宕70多年,是導致中東地區安全形勢動蕩不斷的根源性問題之一。對巴以爭端,美國歷任政府盡管具體措施各有側重,但基本都是延續和奉行在壓制巴方、袒護以色列前提下,促進雙方建國的固有政策。但特朗普政府卻完全跳出美國在此問題上的既定框架,對以色列方面不遺余力地給予支持,包括承認以色列對戈蘭高地擁有主權、接受猶太人吞并定居點以及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等。應該說,特朗普對巴以問題的政策,不僅與美國政府的傳統立場相左,也偏離了國際社會以兩國方案為基礎,和平解決巴以爭端的主流路線。同時,在美國的默許和配合下,以色列介入敘利亞局勢的頻次不斷增加,多次對敘利亞境內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軍火庫和指揮所進行精確打擊。特朗普政府的袒護使以色列在地區格局中處于更加強勢的地位,結果助長了以色列在處理與周邊國家矛盾時選取軍事手段和武力解決的傾向。

西方勢力的介入,造成中東地區安全形勢動蕩不斷
遏制伊朗??2001和2003年,美國發動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推翻了伊朗的兩大敵人——塔利班和薩達姆政權,伊朗戰略環境獲得極大改善,顯露強勢崛起的端倪。自那時起,聯合埃及、沙特、約旦、阿聯酋和以色列等地區盟友,打壓和圍堵伊朗就成為美國軍事部署和地區布局的工作重心,中東地緣政治版圖也隨之形成華盛頓-利雅得-安曼-開羅與德黑蘭-巴格達-大馬士革兩大陣營對峙博弈的格局。但在奧巴馬執政時期,美國對伊朗的態度是更傾向采取懷柔和安撫政策,干涉伊朗事務和雙邊地緣政治博弈的烈度有所下降。尤其是2014年6月,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宣布建國后,聯合打擊“伊斯蘭國”這一共同敵人的迫切需求,又進一步拉緊了兩國利益融合借重的紐帶。
而2015年7月,全面核協議的簽訂,更讓美伊關系步入一段蜜月期。與此同時,奧巴馬對伊政策卻導致美國和地區盟國的矛盾加劇,沙特、以色列、埃及等“親美反伊”國家開始重新評估與美國的關系,沙特甚至在地區事務和國際問題上多次公開與美方唱反調,并嚴厲“提示”美國在伊朗核問題上“松綁解套”,將對地區局勢產生不可預知的災難性結局。
2017年,特朗普上臺后,美國新政府認為奧巴馬的地區政策存在嚴重失誤,對伊朗太過放縱和寬容,不僅失去了中東盟友的信任,還使伊朗的地區野心不斷膨脹。基于此,特朗普一改前任政府對伊朗的綏靖政策,再度恢復對伊朗的強硬和敵視立場,對核問題的態度也由“友善規勸”轉向“極限施壓”,并重拾“以伊劃線”區分敵我的傳統思路。2017年5月,訪問沙特期間,特朗普對穆斯林領袖發表演講,專門選擇伊朗作為抨擊對象,稱伊朗助燃“教派間沖突和恐怖的火焰”,并呼吁海灣國家“驅趕恐怖分子和極端主義分子”。2018年5月,美國宣布單方面退出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緊接著便重啟一系列對伊朗的制裁,雙方對峙態勢也隨之一再升溫。
2018年7月,美國試圖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為藍本,聯合沙特、埃及、約旦和海灣國家組建“阿拉伯版北約”,以牽制伊朗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2019年,美國又采取懸賞收集有關伊方地下金融渠道的情報信息、宣布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為“恐怖組織”和取消8個伊朗原油進口方制裁豁免等措施,進一步加大對伊朗遏制和封堵的力度。2020年1月,美軍擊殺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名將蘇萊曼尼,更是將美伊本已緊張的關系推升到一個新高度,從而也把伊朗核協議當事國前期積累的成果消耗殆盡。
特朗普執政時期美國中東戰略的影響
概括來說,特朗普執政時期美國中東戰略對地區的影響主要體現為激化固有矛盾、惡化安全環境,繼續扮演攪動中東利益格局持續震蕩的推手角色。
誘發中東產生核擴散的多米諾效應。美國持續施壓和加碼制裁促使伊朗不安全感增加,導致伊朗在核問題上采取極端措施,屆時“擁核”的伊朗將會打破中東原有的戰略生態,也將從地區層面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有分析人士認為,美國對伊方實施“長臂管轄”“極限施壓”不僅讓伊朗經濟陷入困境,也可能迫使伊方采取激進策略,反向刺激伊朗加快核研發的進度。
2019年7月,伊朗原子能組織發言人貝赫魯茲·卡邁勒萬表示:“伊朗已經突破伊核協議關于3.67%濃縮鈾生產豐度的限制,如果伊核協議其他簽署方無法保證伊朗在協議中的權益,伊朗將在下一步實現20%豐度濃縮鈾生產。”同時,隨著伊朗在核技術方面不斷獲得新突破,以色列和部分國家對伊朗安全威脅的擔憂和疑慮加劇,而這又促使他們開始尋求核路線以平衡伊朗核能力的提升。例如,以沙特為首的阿拉伯國家和伊朗是勢均力敵的競爭對手,雙方對立既有民族矛盾、教派紛爭的因素,也有地緣政治博弈的成分。一旦伊朗在核計劃上取得重大進展,阿拉伯國家必然想要發展核能力,以確保與伊朗形成核力量上的總體均勢。

2018年05月14日,美國駐以大使館搬遷至耶路撒冷
強化對立態勢,加劇沖突風險。美國在搬遷美國駐以大使館至耶路撒冷,關閉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駐華盛頓辦事處,停止資助聯合國巴勒斯坦難民救濟機構以及猶太人擴建定居點等問題上的“變臉”引來相關各方惡評如潮,激起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世界的憤怒情緒,也引爆以色列與巴勒斯坦方面新一輪的尖銳交鋒和激烈沖突。
2018年3月,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人舉行持續數月的“回歸大游行”抗議示威活動,以色列防暴警察動用高壓水槍、催淚瓦斯、胡椒噴劑試圖驅散示威人群,而抗議的巴方民眾則以焚燒公共設施、投擲石塊的方式反擊。同時,以色列還以保護平民百姓的生命和財產安全為由,多次出動戰機對加沙地帶的哈馬斯武裝及其所屬實體進行空襲轟炸,成為自2014年7月以色列實施“護刃行動”以來,巴以之間最大規模的武裝交火。
毫無疑問,巴勒斯坦是特朗普“中東和平新計劃”的最大受害者,而以色列則是最大受益者,這種建立在偏袒和不公基礎上的方案,不但無助于促進巴以之間的全面和解,相反卻會加速擰緊巴以之間“以牙還牙”“以血還血”的無解死結。另外,美國原本是想通過刺殺蘇萊曼尼的方式削弱伊朗對外行動能力,但是從現實情況看并未取得預期效果,“圣城旅”戰斗力不僅沒有受到影響,反倒是美軍在多股敵人“交叉火力”的攻擊之下,遭受襲擊的次數成幾何倍數增長。因此,特朗普究竟是一招妙棋還是一記敗招尚難斷定,但美國試圖以武力手段脅迫伊朗政府,滿足其政治和經濟訴求的夢想終將破滅,而且還會激起伊朗同仇敵愾的抵抗意志,致使美伊關系轉圜的空間被進一步壓縮。

伊朗原子能組織發言人貝赫魯茲·卡邁勒萬在接受采訪時稱,伊核協議和伊朗自身國防建設不可能被拿來談判

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帶邊境舉行“回歸大游行”紀念活動
綜上所述,在特朗普執政時期美國在巴以問題上陷入全面僵化,與以色列盟友關系得到空前強化,與伊朗關系更加惡化,不僅把巴以和談推向絕路,還使本已趨穩向好的伊朗核問題復歸激烈對抗的老路。總的來看,特朗普中東政策過于偏激,雖然通過制造地區緊張局勢、夸大安全威脅,達到借機傾銷大量軍火以及重新團結和凝聚盟國人心的目的,卻也給本已緊張的地區安全局勢火上澆油,使其繼任者拜登政府面臨更加復雜的現實挑戰。
因此,對美國拜登政府來說,號準地區局勢發展的脈搏和律動,重回尋求政治方式、開展包容性對話的傳統道路,找到符合地區實際、兼顧各方利益的解決方案,對美國在地區秩序中完成“復出歸位”的目標至關重要。
責任編輯:陳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