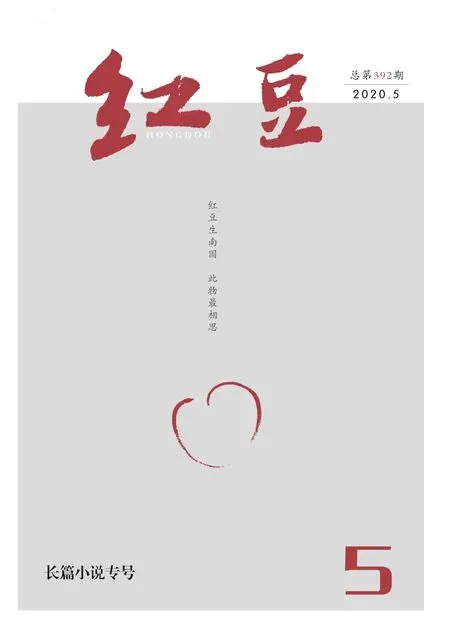在心靈深處的沉思與憂傷
鄭姿靚
不忘記昨天,才能更清晰地認知人類的今天,展望明天。在國富民強的新時代,一些有思想有膽識的作家,將敏銳的目光投向迷霧繚繞的歷史,重審“歷史的新聞”,挖掘那些被歷史大潮攜卷甚至逐漸湮沒的人和事,以新的歷史觀重新書寫,給予現代理性下的觀照與判斷。這是我讀著名作家衣向東老師《身份》的一點感想。
一
一九二七年,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在嚴峻的形勢下,為有效打擊敵人、嚴懲叛徒,開展有力的對敵斗爭,保衛中央領導機關的安全,收集掌握情報,營救被捕同志和建立秘密電臺,周恩來一手創建和領導了中央特科,開創了中國共產黨情報和政治保衛工作的先河。
長篇小說《身份》講述了在土地革命時期大時代背景下,在中共地下組織與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艱難斗爭中,由“雙槍俠”龔瀚文為隊長的上海中央特科打狗隊憑借高超的武力與周密的謀略,多次成功刺殺中共叛徒,打擊了敵人的囂張氣焰,保護中共地下組織工作順利展開。事實上,根據已披露的文獻史料,龔瀚文及其領導的打狗隊在歷史上確有真實原型。中央特科下的“紅隊”,俗稱打狗隊,是中央特科中執行各項任務的重要力量。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江蘇省委在原工人糾察隊的基礎上,選拔一些政治堅定立場、槍打得準、對上海情況熟悉的工人,組成一支小隊伍,擔負起鏟除特務、叛徒、內奸的任務。 《檔案春秋》二〇一二年三月刊發黎霞的署名文章《鄺惠安與中國特科“打狗隊”》,采用新近公開的國民檔案,披露了關于三十年代中央特科“打狗隊”一些鮮為人知的內情。同年十月刊上,另有《〈鄺惠安與中央特科“打狗隊”〉補遺》發表,擴充了部分史料細節。
通過對資料的搜集、分析,可以確認長篇小說《身份》中的主人公龔瀚文的歷史原型正是化名為鄺惠安的中央特科“打狗隊”隊長龔昌榮。據史料記載,鄺惠安是廣東江門新會籍人,練就一身過硬本領,雙手使槍,百發百中。一九三〇年七月在香港受命負責保衛中共廣東省委機關和香港黨組織的安全。同年十月受周恩來重托,鄺惠安來到上海擔任中央特科的“打狗隊”隊長。他善于化裝和變換口音,即便他的手下,對他的描述也五花八門。打狗隊成員遍布各行各業,他們的身份是菜販、廚師、紗廠工人、小商人。他們一面隱蔽于各自的職業身份背后,一面又在鄺惠安的訓練下脫胎換骨,成為一群令特務們聞風喪膽的“打狗勇士”。《鄺惠安與中國特科“打狗隊”》(《檔案春秋》二〇一二年第三期)中記述了打狗隊刺殺叛徒曹伯謙、暗殺特務頭腦馬紹武以及追殺熊國華的事跡。而在研究中央特科史的專家馬振犢的《國民黨特務活動史》一書中,記敘了打狗隊的被捕與罹難:國民黨特工總部上海行動區滬西分區主任蘇成德偶遇了已失蹤近一個月的“細胞”張阿四,據說他被中共滬西區委撥到“打狗隊”,蘇成德當即決定讓張阿四繼續潛回“打狗隊”,他則派出特務進行蹲點守候。很快,上海區總部就掌握了趙軒、孟華亭、鄺惠安等人的秘密住處。鄺惠安等人承受了酷刑審訊,并拒絕了徐恩曾的勸降,于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三日被執行絞刑處決。在他們犧牲五個月后,中央特科完成了歷史使命,“打狗隊”隊員撤離上海,奔赴新的征程。
在梳理相關史料后可確定,長篇小說《身份》并非一般的革命歷史題材小說。早期的革命歷史小說的作者,大都是所敘述的情境、事件的親歷者,通過追憶歷史表達個體經驗,并參與革命敘事在當代的經典化進程。因而這種敘事會在真實性上受到格外的關注甚至指摘。近年來,虛構性作為小說文體的重要藝術手段,為創作革命歷史題材小說的當代作家提供了重審、重構歷史的合法性。與那段歷史拉開越遠的距離,作家們逐漸開始不再苛求絕對地還原歷史現場,而是以回溯的視角表達對歷史的再認識。
長篇小說《身份》中的龔瀚文無論是哪里的話,他只要聽了,就能模仿出來。不僅有語言天賦,還會變身術,稍微搗鼓一下,立即變成另一個模樣,比如戴上一副牙套,立即改變了面部形象。這是對史料記載中的鄺惠安特工天賦的還原。除此之外,小說中龔瀚文最隱秘的藏身地“法租界巨賴達路鳳翔銀樓的二樓的住所”,以及熊國樺被擊斃的“仁濟醫院”,甚至打狗隊被處以絞刑的日期,都與已披露的史料信息相吻合。應該說,小說體現出了“實體化寫實”,依賴于材料和結構的真實。作者將歷史上這一富有新聞性的事件及事件參與者、經歷者的主要言行、思想、情緒等作為小說的框架和內容,同時以文學的虛構手法進行心理描寫、場景描寫和細節描寫等。關鍵是作者以新聞的敘事立場和觀點完成了小說的主體敘事——以敏銳的新聞眼光發掘題材,以客觀且不乏創造性的思維方式與表現能力展示題材。小說采取“零聚焦”的全知敘述方式,敘述聲音像鏡頭般平穩滑動,客觀地展示了參與事件的各個不同立場的人物角色的行動和心理狀態。
二
長篇小說《身份》雖具有明顯的“實體化寫實”的特點,但其概念本身就一直于爭議中生存。一九八〇年代中期,這類小說作為一種新型的文學樣式,曾引起過熱烈的反響和爭鳴。一些評論家充分肯定了這一文體的創新實驗意義和審美價值。 有部分學者認為“紀實”與小說文體的“虛構”手段,本身蘊含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對立,因此這種結合是一種“時時處于傾斜狀態的悖謬存在” 。著名紀實文學家葉永烈就不承認紀實小說,他說:“紀實小說這概念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紀實是真實的,小說是虛構的,怎么能把紀實跟小說糅合在一起?”
本篇暫不討論紀實小說這個稱謂的合法性,但可以肯定的是長篇小說《身份》中,既有對史實的忠實還原,也有作者的藝術虛構。紀實與虛構兩種元素在小說中融合呈現,但并未形成虛構中夾在真人真事的“不倫不類的文學怪胎”。
“歷史是一個任人涂抹的小姑娘”,后人無論如何努力都很難毫無差錯地復原歷史上的某一分秒。因而哪怕作者進行了大量史料搜集和考證工作,盡量在小說中還原事件的主要參與者,甚至事件發生的時間和地點,也很難確保復原這段歷史時信息的絕對真實。這也正是“紀實”與“虛構”這一對矛盾概念在小說創作中互補甚至融合統一的原因。在類似歷史題材小說的實際創作中,哪怕作者懷有紀實的目的,抱有還原歷史現場的宏愿,但后人對歷史的認知本身就是“虛構”的,絕對真實才是無法抵達的悖謬。允許“虛構”對“紀實”的補充,才能使人物有真實的血肉,情節有恰當的邏輯;允許“紀實”對“虛構”的入侵,則使小說具有完整的可信度。
小說在敘述刺殺行動時,盡力將行動的前因后果,包括過程中的曲折性、復雜性敘述清晰,將細節設計真實。如刺殺上海公安局督查科副科長錢藝時,因情況緊急,龔瀚文只能單獨行動,在除夕夜人流如織的城隍廟完成刺殺。“城隍廟門口走出一群人,龔瀚文開始迎著這群人走去。他走得很慢,而且東張西望,像是看風景的行人。等到這群人接近看煙火的人群時,龔瀚文加快了步伐。他看到這群人身后,有三五個警察護衛著,警察的注意力都在天空的煙火上,邊走便仰頭看著。龔瀚文越來越接近錢藝了,他已經看到錢藝臉上的笑容和眼鏡片上被煙火映照出的彩光。他沉穩地向前走著,還有五步的距離就是最佳射擊點,他心里數著一、二、三、四、五,刷的一下掏出雙槍,啪啪兩聲。錢藝身后的警察,聽到兩聲槍響,以為有煙火在頭頂炸響,都慌亂地朝天空看去。錢藝身邊的男女發出驚叫,警察這才看到有人躺在地上。”這是小說中較為順利的一次刺殺行動,因此篇幅雖短,且語言不飾文采,簡潔平實,但傳神的神態和動作描寫,使龔瀚文的形象躍然紙上。對刺殺叛徒曹時言的講述卻與已披露發表的史料有些許出入。據資料記載,鄺惠安得知曹伯謙秘密居住于上海斯文里某處,但可惜不知曹具體的門牌號碼,在弄堂里誤殺了與曹面容酷似的世界紅十字會上海總辦事處的辦事員周翰。第一次執行任務失敗后,鄺惠安通過另一名打入公安局的內線湯杰才打聽消息,得知曹伯謙住在斯文里1040號,于是重新調整策略,完成刺殺任務。但在小說《身份》中,龔瀚文第一次刺殺行動發生在閘北一個特務秘密辦事處,但卻是誤殺了一個面容酷似曹時言的特務。第二次借曹時言被邀請到法院勸降被捕的中共地下黨員的機會,龔瀚文帶領隊員提前在法院附近埋伏,將其擊斃于法院門口。小說在這一情節中體現出了“紀實”與“虛構”的延宕。它所希望體現的是叛徒的狡詐以及鋤奸行動給予敵人的震懾,因此在“曹伯謙被刺殺兩次方才伏法”的史實上進行再創造,“中央特科‘打狗隊竟然在大白天,將叛徒處決于法院門口,太有諷刺意味了”,所產生的震懾效果也為后文的推進埋下引線——“這一槍幾乎把上海的天空打了一個窟窿,讓一時沉悶的上海地下黨歡欣鼓舞,士氣倍增”。
既然敘事內容真實(或言素材真實)是無法完全實現的,那么《身份》所追求的致真效應是指什么呢?《身份》并非是單純的作者個體經驗表達,也是作者向讀者的鋪陳展示。因此,讓讀者在文本范圍內相信事件的真實性,并對此形成認知和判斷,便是《身份》的所謂真實性追求。作者選擇以這種實驗性文體書寫《身份》的意義,也正是將中共早期開展地下工作的艱難斗爭、痛苦與犧牲展示給未曾親歷歷史的后代,讓他們能夠觸摸歷史脈搏中的斑駁血淚。
而喚起讀者閱讀真實感的關鍵,不僅在于“寫什么”,更在于“怎樣寫”。小說以新聞性的眼光,盡力祛除敘述語言的修飾、削弱敘述過程的起伏,使其像日常口語所講述的一段客觀存在的歷史。在小說的敘事過程中,作者盡力遮蔽了自我存在感,主動放棄了作者的部分“權利”,盡量避免隱含作者的情緒和觀點介入作品中,使得小說成為一個細節生動且向讀者完全敞開的場域,以追求讀者在還原的歷史生態圖景中的閱讀真實感。更由于其敘述語言的平實、簡潔和口語化,降低了讀者的閱讀難度,易于讀者的理解和接受。
三
為了發揮《身份》的文體功能,作者把“虛構”作為一種藝術手段進行創作。筆者認為,“虛構”的參與不僅沒有破壞作者對真實性的追求,反而保護了讀者的閱讀真實感。
小說以一對年輕男女在刑場完成婚禮開頭,被處決的中共地下黨員與女學生在生命盡頭的悲壯之戀,卻被“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十幾名記者爭搶著跑到墻根下,瘋狂拍照”。而這張血泊中的照片卻與被香港媒體吹捧為“緝共”高手謝成安淺笑的照片擺在一處,形成一樁泣血的諷刺。報紙與新聞是小說中不斷出現的符號,它代表一種客觀發生的陳述聲音。它以零度的情感記錄犧牲、記錄勝利、記錄歷史的殘酷真相,以鋪陳開后人回溯歷史的全部素材。小說中的新聞報紙,代表的正是一種紀實的姿態。換言之,是歷史留給后人供以指認和想象的遺產。
那恐怕是在那個風云詭譎的時代,在所有的爾虞我詐和偽裝欺瞞背后,對家國明天的赤誠信仰與對“小家”的虧欠、愧疚,纏繞交織的矛盾情感。
小說《身份》的情節按時間線索推進,而每個情節高潮都伴隨著主人公龔瀚文的一次身份轉換。龔瀚文在香港暗殺尤廣仁和謝成安初顯特工天賦,于是組織將其派往上海中央特科成立打狗隊,他擁有了第一個假身份——陳皮店老板祁廣輝。在成功完成幾次鋤奸任務后,中央特科二號人物華老板叛變,中共地下組織遭到毀滅性打擊。龔瀚文協助完成將中央機關重要領導人轉移出上海的任務后,為了進一步隱蔽身份,身份轉變為舊家具店老板鄺惠安。之后,因打狗隊隊員陳一石與女學生江月相戀,被特務以戀人相要挾,最終出賣了打狗隊五名隊員。打狗隊在這一災難性打擊下幾乎全軍覆沒。為在更艱難且危險的境況下重建打狗隊,龔瀚文又化名裁縫鋪老板“方柏全”。龔瀚文最終犧牲時,他的敵人甚至下屬都不知曉他的真實姓名。
龔瀚文高超的特工天賦使他能夠扮演好變換的不同身份,一次次出色地完成組織任務。但在“身份”背后,他有真正的父母、妻兒,有真實的愛恨,有活生生的血肉。“看完張秀芳和女兒的照片后,真的很想跟陳銘聊天,聊什么都無所謂,就是想跟他說說話。在十里洋場的上海,盡管人流熙熙攘攘,但他一直有種孤獨感,從他身邊走過的人如此陌生,以至于讓他感覺整個城市只有他一個人在街道上穿行。他是誰,家在哪里,沒人知道,甚至連他自己都不知道。在偌大的城市里,真正知道自己叫龔瀚文的只有陳銘,他能夠喚醒自己的記憶,能夠證實他的存在,因為他知道自己的過去,甚至預知自己的未來。”這時小說中的龔瀚文用祁廣輝的身份工作不久,獄中的妻兒與在戰場前線廝殺的記憶仍纏繞著他的神經,謹小慎微的偽裝時常將他拖入對自我身份的迷茫中。“其實龔瀚文也有過這種幻想,如果不參加共產黨,他可以跟張秀芳在上海開個陳皮店,專賣家鄉新會的陳皮,劉小光可以作為合伙人,說不定能成為陳皮行業的大鱷。想著想著,又會嘆息,他知道自己沒有選擇,為推翻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建立一個沒有剝削和壓迫的新社會,他必須做“黑屋子里的點燈人”,哪怕獻出生命,都不足惜。”作者對此時龔瀚文心理狀態的虛構和想象的延展,使其成為一個真正有血肉感的形象,而非一個“打狗戰士”的身份符號。
小說中寫到龔瀚文轉變身份為鄺惠安時,“他特意把寫著‘鄺惠安的紙條看了幾遍,心里默誦‘鄺惠安三個字”。這是龔瀚文內心的一次自我蛻變。若陳皮店老板祁廣輝的身份仍能讓他從中尋得與做陳皮生意的父親遙遠的心理聯通,使得他偶爾回到原本的龔瀚文,遙寄過去“小家”的安定生活,那么鄺惠安則是刺激了他“徹底扮演別人”的思想覺悟。而在遭遇了打狗隊五名隊員被捕,妻兒也再次入獄的打擊后,為了隱蔽,龔瀚文迎來了第三個假身份。他夢囈一般說:“冉小姐,你看我像個裁縫嗎?”身份的轉變不僅是小說情節發展的線索,也推進著龔瀚文心理成長的脈絡。
“你是誰,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活著。忘掉你是誰,記住誰是你。”這是小說最殘酷的主旨所在。對于龔瀚文這樣游走在不同身份遮蔽下的特工來說,最痛苦的并非是在艱險的敵人統治轄區中執行任務,而是放棄了自己原本的身份甚至與之相連的一切羈絆。于是后文中龔瀚文不能與大街上被特務跟蹤、淪落到討飯境地的妻兒相認,也無法將為引他出現而被特務驅趕到街上流浪乞討的親生兒女收養。面對與自己假扮夫妻以逃避特務搜查的進步女青年冉墨宣,他也無法坦誠自己的身份。他戴著假面具被裝在套子里,活在他親自經營出的真空中。而小說中的陳銘作為龔瀚文的入黨介紹人,實際上是一個比龔瀚文更早加入中共黨組織,更早從事地下工作,以致對自身命運有更為現實的預見性的角色。這種對自身命運的殘酷關照,使他對個體身份和性命的讓渡有一種幾近悲憫的平靜,而這亦是有堅定信仰的中共黨員們共同的路徑與命運的投射。陳銘與龔瀚文的對照,正是一個背負沉重使命活在人間的中共黨員,與為了理想與信仰犧牲生命的英勇戰士的對照。又或者,前者是后者的生命續曲。
“我是誰”的問題在特工英雄的一次次身份轉換中,終歸成為消散在歷史曠野中的遙遠回音,直到犧牲,打狗隊隊長都無法再做回龔瀚文。而在龔瀚文所處的時代中,由于工作身份的特殊性,“他是誰”也幾乎無人知曉,于戰友、于國家,甚至于敵人,他都只是暗夜中匆忙隱蔽的背影。而今,作家們只能從歷史的夾縫中挖掘史料遺跡,加以想象性虛構補充,盡力還原歷史的真實血淚。先烈的面貌雖已模糊,但精神依舊真實深刻。現如今,終于回應了他的理想,也回答了他的身份。
責任編輯? ?侯建軍 謝蓉
特邀編輯? ?張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