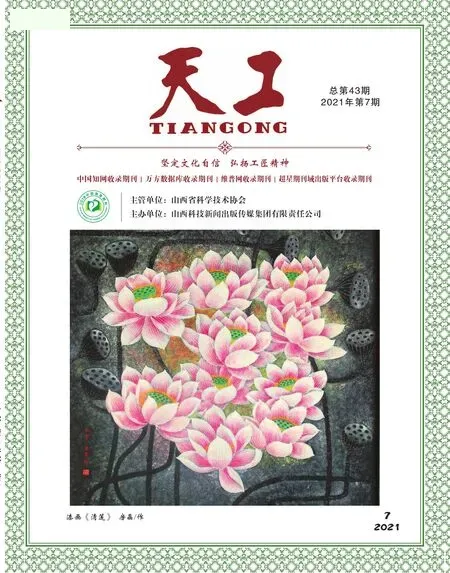陶瓷3D打印技術藝術實踐研究
吳辰博 佛山職業技術學院電子信息學院
3D打印技術也稱增材制造技術(Addit ive Manufacturing,AM),出現于20世紀80年代末期。而本文主要討論的則是利用陶瓷材料進行陶瓷藝術品制作的3D打印技術。
在國內陶瓷工藝的大環境中,掌握3D打印技術的商業公司和陶藝創作者之間缺乏相互了解,是導致該技術無法在藝術創作領域中得到大面積普及的原因之一。
筆者希望通過自身的創作實踐,探索陶瓷3D打印技術應用于藝術創作領域的方向。
一、陶瓷3D打印技術的發展
自第一臺3D打印機面世以來,至今發展了30年左右。隨著技術的革新與相關材料的研究愈加豐富,3D打印行業的市場規模日益增長。
作為3D打印行業的龍頭企業,德國EOS集團的市值經過2016年到2018年短短兩年的時間,就從93億人民幣增長到了約180億人民幣。
在同一時間里,中國的企業也緊追其后,西安鉑力特、北京鑫精合、湖南華曙高科、杭州先臨三維、上海聯泰科技、深圳光華偉業等從事3D打印技術服務的企業先后上市,市值估價都在10億~30億人民幣左右①數據源于南極熊3D打印網。。
3DSystems、EOS集團和普立得(Stratasys)公司作為全球3D打印行業的三巨頭,也持續進行陶瓷材料方面的研究。
因工作原理、適用的材料和產品的使用目的的不同,3D打印技術的種類分為LOM、DLP、FFF、EMB、Polyjet等。而目前可以適用于陶瓷材料的3D打印技術主要有噴嘴擠壓成型(FDM)、選擇性激光燒結或熔融成型(SLS)、立體光刻成型(SLA)以及黏合劑噴射成型(3DP)四種。
本文的實踐創作部分所使用的技術類型,屬于上述中的FDM技術。
二、陶瓷3D打印技術藝術創作探索
3D打印技術的工作原理有多種形式,但追根溯源,所有3D打印品的初始狀態都是由電腦提供的一份三維數據。通過數據的分析,3D打印機才可以自動形成最終造型。
由于3D打印技術具有利用電子數據進行可視化呈現的特征,在本文的研究來看,仍然存在一種方式,可以更充分地利用這點特殊屬性,從而開辟出陶藝創作的可能性方向。
(一)處于“電子時代”的3D打印陶藝創作
20世紀50年代,第一臺電子計算機被發明,從此人類逐步邁入了“電子時代”。隨著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進行,電子技術迅猛發展,其最大的特點便是允許一切信息都可以通過電子技術進行數據化,并加以收集、傳遞、處理。3D打印技術正是基于電子技術的發展才得以發明的。
Joachim-Morineau Studio設計的“滴水機”使用Arduino編程的方式,進而干預3D打印機硬件的運轉;邁克爾·伊甸和伯納特·屈尼通過三維建模的方式制作打印數據,從而進行3D打印。這其中都涉及電子數據的使用,都是由數據決定最終視覺呈現效果的創作方式。
但也正如上文中所提到的那樣,在陶藝創作中仍然看到了許多傳統工藝的影子。對于使用陶瓷材料的3D打印技術,我們完全可以用一種獨屬于“電子時代”的思考邏輯。
喬納森·基普的《噪音形態》系列作品通過對噪音數據的收集,再使用Processing編程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對數據進行干預,并形成最終的三維數據。這樣的創作流程,幾乎將“數據決定視覺呈現效果”這種方式使用到了極致,將數據的事情完全交給了數據,真正做到了用數據進行藝術創作,是一種十分具有“電子時代”屬性的創作方式。
(二)3D打印陶藝創作的個人探索
《噪音形態》系列作品的創作流程可以總結為:從自然中收集數據→主觀改造數據→將數據可視化處理→通過3D打印實體化呈現。這條邏輯鏈完整且極具“電子時代”屬性。但這條邏輯鏈是否可以繼續深挖,使其“電子時代”屬性更加強烈呢?
筆者將目光轉移到主題的選擇以及數據的收集來源上。
當我們站在“電子時代”的語境中思考3D打印藝術創作時,數據的來源尤為重要,甚至直接決定了作品的風格。而對于數據而言,電子計算機無疑是世界上最具有發言權的載體。
本文的實踐研究就將數據的收集源放在電子計算機上,通過對計算機語言的數據收集,再重新構建“數據收集→數據改造→數據可視化處理→3D打印實體化呈現”的創作流程。
三、《人工智能之詩》對3D打印陶藝創作的實踐分析
前期研究的準備階段,筆者對與陶瓷3D打印技術相關的資料進行了收集、整理及分析。上文提到,該技術的誕生本就受益于“電子時代”的發展,也因此具備“電子時代”對數據的依賴屬性。這種屬性明確了該技術的本質:3D打印技術是一種將數據可視化呈現的技術手段。
針對本文的創作實踐作品《人工智能之詩》,創作者使用Processing編程軟件對收集來的數據進行可視化處理,輸出陶瓷3D打印機可識別的三維數據文件,并最終生成視覺造型。這樣的創作手法和邏輯已經完全脫離傳統陶瓷手工業的制成范疇,更像是新媒體作品的創作。
正是因為電子科技的發展,才使得新媒體藝術這種將電子數據作為創作材料的藝術形式變為可能。而當我們使用陶瓷3D打印技術進行藝術創作時,實際上也就是在使用三維電子數據進行藝術創作。這也是《人工智能之詩》試圖為陶瓷3D打印技術應用于藝術創作上進行方向性探索,即利用新媒體藝術使用電子數據的創作邏輯,通過對電子數據的收集、處理、重構進行三維數據的視覺化創作,再使用陶瓷3D打印生成最終成品。
四、結語
史蒂芬·霍斯金斯(Stephen Hoskins)①史蒂芬·霍斯金斯是惠普公司精細打印研究專家兼英國布里斯托爾市西英格蘭大學精細打印研究中心(CFPR)主任。在其著作《3D打印:藝術家、設計師和制造商》②(英)史蒂芬·霍斯金斯:《3D打印:藝術家、設計師和制造商》,鷺江出版社,2016。一書中曾預言,他堅信3D打印技術在視覺藝術方面的巨大潛能,在不久的將來,該技術將會成為各界創作者所使用的主流技術,并在15年后,3D打印陶瓷將成為商業現實。
陶瓷3D打印技術在國內的相關研究雖然遠不及國際上的發展成熟,但對于藝術創作而言,國內廠商現有的技術完全可以作為豐富陶瓷藝術創作手段的工具,在陶瓷藝術創作向外延拓展的方向上起到積極作用。

圖1 2019年廣州美術學院研究生畢業展現場展示效果(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對于絕大多數藝術工作者而言,技術的使用只是形式語言的一部分。筆者認為,陶瓷3D打印技術的介入,將會為陶瓷藝術帶來另一種面貌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是寶貴的,在使用創新技術時,多考慮其固有的屬性特征,才能使陶瓷3D打印技術在藝術創作中的應用方向更具探索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