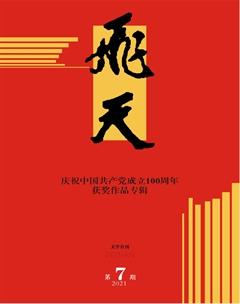紅都物語
范劍鳴

棉花:試驗的種子
我看過新疆的棉花地,無邊無際,像豪華的盛宴,鋪展在祖國的西部。收獲季節,天上的云朵也會走到大地上,在陽光中與棉花熱烈交談。
這是新中國的棉花,由于眾多而熱烈。
但我也看過蘇區的棉花地,細小得像一粒種子。有時還不如天上的一朵云彩那么大,就像蘇區自身,在南方的群山之中,在蜿蜒的阡陌之中,嘗試著,探索著,孜孜不倦,星火燎原,努力讓一種純凈的白鋪展在紅土地,溫暖而又美好。
這是共和國搖籃里的棉花,由于稀少而熱烈。
這是神奇的土地。如果你來到瑞金一個叫葉坪的村子,至今能在一個古老的祠堂里,看到先輩們留下的旗幟和口號。1931年11月7日,一朵白云透過密集的香樟林,聽到那句響亮的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了!關于土地,關于棉花,關于秋天,關于溫暖,那時一群人有了自己的理解。
我所看到的棉花,是蘇區的棉花。現在,我的家鄉瑞金并不種棉花,這只是一種久遠的記憶。在一個春天的上午,在葉坪革命舊址群的展館上,我看到了這種源于歷史深處的記憶。我看到了蘇區的棉花,由于稀少而熱烈,由于稀少而讓蘇區怦然心動!由于稀少而珍貴,由于珍貴而讓一群蘇區的科技工作者怦然心動!
那是一種叫“農事試驗場”的土地,它源于“二蘇大會”的報告,源于瑞金沙洲壩剛剛建起的大禮堂,源于1934的春風,源于一口濃重的湘音:“為著促進農業的目的,而在每鄉每區組織一個小范圍的蘇維埃農事試驗場,并且設立農業研究學校與農產品展覽所,同是迫切的需要。”這就樣,一群散亂的土地被團結起來,一畝、十畝、百畝,集中接納了異鄉的種子,棉花的種子。
然而,沒有科學的精神,又怎能種好蘇區的棉花?正如沒有探索的精神,又怎能在瑞金這個小盆地上,用蘇維埃的辦法來定國安邦?一切都在試驗之中。那時的蘇區,棉花就是蘇維埃,棉花就是一種理想和主義,棉花就是一種精神和信仰。我曾經在一份舊報紙上,看到過這種棉花,帶著理想的色彩,樸素得讓人感動:“熱烈進行植棉運動,保障明年每人都有一件新衣新褲穿!”
我看到了蘇區的棉花,最初是一些種子。最初在中央土地部,收藏著,分發著,來到蘇區細小的土地上。我幾乎能感受到種子的溫度,我幾乎能感受到捧著種子的手微微顫抖,我幾乎知道蘇區的歌謠為此而唱:“撒下了種子,介支個紅了天”。如果我是《紅色中華》的記者,如果我在1934年4月走進了蘇區的土地,我也會迅速寫下一個個標題:《植棉選種試驗成功》,《熱烈進行中的瑞金植棉運動》……
這就是蘇區的棉花。在“農事試驗場”,帶著初生的喜悅,帶著開創的興奮。多少年了,棉花長到了新疆,棉花離開了瑞金,但有一種精神仍然深深地根植在紅色故都。
硝鹽:泥土的味道
硝鹽究竟是不是鹽?這是一個化學問題,也是一個語文問題,同時還是個歷史問題。在硝煙彌漫的年代,如果你從一份中央政府的機關報里,看到一則《熬硝鹽的方法》,你會不會吃驚?正如在餐盤中看到一粒過剩的、多余的鹽粒,你會不會吃驚?
當然有一些吃驚。為此,我曾仔細探究過熬制的辦法,看到硝鹽有著何等卑微的身世。“以前放過鹽的地方,多年的老屋,和堆過糞便的墻上,只要里面的泥土有點咸味,(取土少許放在舌頭上一嘗便知),都可以熬鹽。”在蘇區,在中央政府的報紙上,這些高貴的硝鹽,這些受到尊寵的物品,一點也不掩飾自己的出生之地。
還有更低賤的出處嗎?來自泥土的硝鹽,甚至有著比泥土更加不潔的身份。我少年時看過這種泥墻,白花花的鹽霜,像苦澀的大地吐出了自己的舌頭。蘇區的硝鹽,就像蘇維埃的主人們一樣,來自底層,來自角落。為此,這樣的報紙,這樣的中央政府,這樣的硝鹽,又如何能不熱愛泥土的味道?“糞土之墻不可圬也”,如今,糞土之墻卻可以放到舌頭上舔嘗,為了大眾最急迫的需要。
作為政黨的喉舌,報紙已辦到了第205期。蘇維埃已建設多年,但艱難困苦仍然圍剿著蘇區。只有懂得編輯的良苦用心,你才能深深地理解蘇區。《熬硝鹽的方法》,確實要讓更多的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人,掌握了這種熬硝鹽的方法?究竟有多少人,走到糞土之墻,挖出了那些帶著白霜的泥土,帶著咸味的泥土?這種土辦法早已過時,但我就是忍不住探究,就像重新替李紳構思那首唐朝的憫農詩。
碎土,挖池。開溝二尺許,略深于放土之池。挖來的墻土,不可太虛,不可太實,不漏,不透。培土,加水,續水,濾土,換土。得含鹽之水,進鍋熬制……如此循環。天工開物,人工造物,皆道法自然。這是最古老的方子,千百年來反復使用。這是最偉大的發明,火藥便沿著這個方子走到人間。硝和鹽,最終合而為一。硝鹽,終于從歷史的幽暗之處,亮出白花花的身子,閃耀著歲月的光芒。
在和平的年代,制作煙花焰火的硝,安慰舌頭味蕾的鹽,從來不愿意混在一起。為此在這個春天,在瑞金的革命舊址群里,我曾經向講解員打聽:硝鹽究竟是不是鹽?我沒有得到答案。因為這不僅是歷史問題,還是化學和語文一起制造的腦筋急轉彎。
硝鹽,并不是硝和鹽。但確實是硝和鹽。在蘇區時期,硝和鹽,就像硝煙與炊煙,就像戰爭與和平,就像革命與建設,既是對立的,又是統一的,既是分割的,又是融合的。我必須告訴你,關于食鹽,中央蘇區信奉的是“有鹽同咸,無鹽同淡”。我必須告訴你,硝鹽并不是氯化鈉。它給舌頭的不只是咸和淡,而是深深的苦澀,以及泥土的氣息。
同樣讓我吃驚的,是一則短短的新聞:《瑞金合龍區建立硝鹽廠》。作為重大的喜訊,它卻如此簡短。“每天能夠出鹽十八斤,足夠供給全部群眾的需要,并且東西也好,(硝又為我們軍事上的需要品)。”這些年,我曾一次次走進這個叫合龍的地方,把西瓜基地、蔬菜大棚、合作社搬進新聞里。八十多年后的今天,再也沒有人知道硝鹽廠,但這里的家園,仍然有泥土的味道。
燈草:光明的重量
在城市的書房里,我幾乎會忽略燈盞的存在,因為把夜晚變成白天,似乎過于容易。如果不是瞻仰舊居,如果不是認識一種叫燈草的事物,我幾乎會忘掉八十多年前,人們跟黑暗作斗爭的樣子。
一張書桌上,必定會有一支筆和幾頁紙。一張藤椅前,必定會有一支燈盞。作為寫作者,多么渴望有一只燈盞,把白天的光明延續下來。我理解這種奮筆疾書的心情。但我沒有體驗過一邊文思泉涌、一邊撩撥燈火的場景。現在,舊居的擺設還原了成八十年前的情景。我認識做成燈盞的竹筒,認識盛放油料的金屬,但我不認識燃燒過的燈芯。
灰白,短小,像一條歷史的臍帶。
講解員說,這是一種草,南方的草,名字就叫燈心草。講解員說,這種燈草非常輕,在方言中,燈草就用來形容輕。為燈火而生長的草,當然來自野外。作為一種野草,它們能像蘇區的棉花一樣珍貴,能像蘇區的食鹽一樣稀奇嗎?當然不是。但講解員告訴我,當年的蘇區,就連燈草的使用,也制定了標準:一個晚上,只能用三根燈草。就像一個白天,只能有三次用餐。
三根燈草,每一根,不會超過一尺。三根燈草,必須從黑夜堅持到黎明。三根燈草,在蘇區的土地上,從生長到采割,從晾曬到截取,從泥土到燈盞,需要一個春秋,就是一個四季輪回。草是青草,燈是油燈。用草撐住的光明,有多么艱難?如果不是這個制約,如果不是這個標準,我承認,我不會對這種草產生更深的興趣。
在蘇區的土地上,稻子收割了,秋天快到了,人們就會來到野外的潮地,走進一片片青草,為制造光明做好準備。燈心草,像縮小的翠竹,實心,直立生長。草莖上,帶著淡淡的黃或白,到了夏天,小巧的花朵從梢上鼓出來。收割季節,有的像席草那么綿長,有的像稻草那么短小。人們割取草莖,曬干,取出莖髓,理直,扎成小把。
在蘇區,在這間舊居里,分發的三根燈草,可能來自同一根燈草,也可能取自三根不同的燈草。三根燈草,捧著節制的光明,在黑夜出現,在黑夜消逝。但講解員的故事,重點并不是三根燈草,而是一根燈草。就在這間舊居里,作為領袖,它熱愛的寫作剛剛開始,而燈盞的火苗一再壓低。為了節約燈油,為了節約燈草,他決定用最微弱的燈光,照亮自己最磅礴的書寫。
有什么樣的意志,用一根燈草就可以戰勝黑暗?一根燈草,又一根燈草,是什么樣的書寫,讓那些細小的火苗,擁有了光明的重量?我看了看那張書桌。上面擺放著當年的著作,《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和《我們的經濟政策》。我讀過里面的文字,關于蘇維埃,關于國家,關于革命,關于勝利。那些密集的漢字,仿佛就是來自燈草,并和燈草一起發出了堅定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