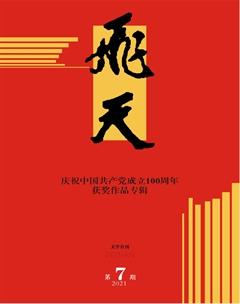哈達鋪的一束燈光
王軍紅
一
11月9日,我們從天水出發,去三百公里之外的宕昌縣哈達鋪鎮。一夜的雨淅淅瀝瀝下個不停,早上啟程時,雨點更加密集,立冬后的寒意陣陣襲來,不由讓人裹緊了衣服。行至武山,云收雨歇,大陽出來了,天公作美!五個小時后,我們終于到達哈達鋪鎮。
哈達鋪鎮位于宕昌縣西北35公里處,是紅軍長征經過的重要集鎮。我們此行的目的地正是被譽為“紅軍長征加油站”——宕昌哈達鋪紅軍長征紀念館。隔著自動門,遠遠看見哈達鋪紅軍長征紀念碑,代表紅一、紅二、紅四方面軍的三支巨筆直挺天際,似乎在蒼穹和大地之間書寫那段波瀾壯闊、艱苦卓絕的長征歷史。紀念館門口的行道樹,葉子全部已變紅,鮮活飽滿的紅葉迎風抖動,像是給前來虔誠瞻仰的人訴說著八十年前這里發生的一個個激昂悲壯的故事。
紀念館大廳,是開國元勛們的群體塑像。行完鞠躬禮,我們跟著講解員慢慢移動,在她飽含深情的講述中,我們與遠去的歷史又一次重逢。恍惚中,那鋪天蓋地的吶喊聲、沖鋒聲、槍炮聲、風聲雨聲……交匯在一起,那段不平凡的崢嶸歲月一幕幕浮現于眼前。
二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紅一方面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失利,最后被迫退出中央蘇區開始戰略轉移,輾轉途中大戰、惡戰、激戰、苦戰無數。
1934年11月血戰湘江。1935年1月四渡赤水,同年5月強渡大渡河,5月底飛奪瀘定橋,9月17日激戰臘子口,9月18日,黨中央率領紅一方面軍突破天險臘子口,占領哈達鋪。
1935年9月20日下午,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到達哈達鋪,從當地郵政代辦所得到《大公報》《中央日報》《民國日報》等報紙,報紙上刊登著徐海東率領紅軍和陜北紅軍會合的消息,還有陜北革命根據地“匪區”略圖。這無疑是個天大的好消息,根據這些消息,22日,黨中央在毛澤東同志住處(原哈達鋪“義和昌”藥鋪)召開中央領導會議,作出了落腳陜北、建立新蘇區的決定。又在“關帝廟”召開團以上干部會議,宣布了中央的決定,并正式改編紅一方面軍為陜甘支隊。
到陜北去!在哈達鋪會議上第一次被明確提出。
我又一次想起哈達鋪“義和昌”藥鋪后面瓦房里的一束燈光,這束燈光伴隨著毛澤東的身影出現在每一個夜晚。燈光下,一位領袖運籌了到陜北去的重大決策;燈光下,一位詩人欣然寫下了“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后盡開顏”的恢宏詩篇;燈光下,紅軍長征千萬里行程的目的地也被照亮。
三
在哈達鋪紀念館的展廳頂部,貼著當年發現的幾份報紙,貼在頭頂,寓意便是“喜從天降”。
圣潔吉祥的哈達鋪以富庶豐饒的物資滋養著身體極度疲憊的紅軍戰士,哈達鋪自古就是甘川道上的一個商貿重鎮,物資豐富,商業活躍,以出產著名藥材當歸而吸引了全國各地的客商來這里經營藥材。據統計,宕昌人民為1935年9月北上的紅一方面軍和1936年10月北上的紅二、紅四方面軍積極籌集了數十萬斤糧秣和大批軍用物資,使經過雪山草地和長時間行軍作戰的紅軍將士的身體得到恢復,被譽為長征途中的“加油站”。
走出紀念館,很快便步入“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第一街”。這里地勢開闊,街道平坦,店鋪林立,交易紅火,依然一派繁榮景象。“義和昌”藥鋪、“郵政代辦所”、“同善社”、“關帝廟”、“張家大院”等紅軍長征舊址原貌得以修護,并保存完整。
順著指示牌走進“義和昌”藥鋪,后院平房便是毛澤東與張聞天同志的住所,院內房子屬土木結構,黛瓦粉墻,木格窗欞,青磚鋪地,古樸寧靜。初冬時節,不時有樹葉簌簌而下,落滿房頂,樹葉與瓦松相映成趣,煞是好看。院子里有五人塑像在同看一張《大公報》。同心樹前,合影留念的人很多,而我想,看報紙的五人才是同心同德,齊心合力。
在周恩來住所,院子里也有一組雕塑,重現哈達鋪老中醫前來為周恩來看病的情景。當年過草地時,周恩來的身體極其虛弱,最后是靠擔架抬出草地的。在哈達鋪,醫術精湛的老先生主動上門問診,想必是被紅軍大公無私的品格和秋毫無犯的紀律深深打動,軍民之間有了魚水般的情誼。
我們圍在“郵政代辦所”郵筒前,這是一只多么神奇的郵筒呀!它胖鼓鼓的肚子裝載著多少份來自全國各地的報紙,正是這些報紙相互佐證,為中國革命找到了一條出路。
在長街上漫溯,清一色的仿古臨街店鋪,紅彤彤的國旗一字排開,哈達鋪似乎沉浸在一片紅色的海洋里。這是一片紅色的土地,也是一片深情的土地,只有深愛這片土地的兒女才會為她拋頭顱,灑熱血,雖九死而猶未悔!
四
參觀完哈達鋪紀念館后,我們前往甘南州迭部縣臘子口戰役紀念館。
奪取臘子口,就打通了紅軍北上通道。當時紅軍面臨的形勢非常嚴峻,左側有卓尼楊土司的騎兵,右側有胡宗南的主力,后側有從四川跟來的劉文輝的川軍側翼,如不能很快突破臘子口,就會面臨被敵人四面合圍的危險,打贏這場戰役的重要性可想而知。臘子口這個“天險”將如何被攻破?當講解員講到一名叫“云貴川”的小戰士主動請纓,借助一個鐵鉤攀爬上懸崖絕壁,又在身上綁滿手榴彈從懸崖跳入敵人碉堡,玉石俱焚時,我的眼里噙滿了淚水。
小戰士17歲,多么美好的年華,如果在現在,他才是一名高中生,調皮又狡黠,單純又善良,也許,他正背著雙肩包走在上學的路上。可當年的“云貴川”小戰士已經走遍了云南、貴州、四川三省,又跟隨大部隊到了甘肅境內,在資歷上算是“老戰士”了。現在,我們無法揣測他跳入敵人碉堡時的內心想法。試問,誰不戀生,誰無親人,誰不想好好活著?但是,“云貴川”卻把生留給了戰友,把死留給了自己,或者,他根本就沒多想,完成任務,讓戰友們減少傷亡是他唯一的心愿。
我們前往臘子口實地察看,沿途絕壁,真是“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援”。當年激戰的硝煙早已飄散,被攻下的碉堡遺址還在,臘子河水依然川流不息。站在溫煦的陽光里,倚著木橋護欄,我舉目張望,哪一塊巖壁上曾留下紅軍小戰士身上的溫熱,哪一塊巖石曾留下他奮力攀爬的足跡,哪一朵浪花曾照見他從天而降的身影?一時間,四周寂寂,風不吹了,時間也靜止了。許久,聽見旁邊有人說:“他一定是天上的神仙,看到紅軍有難,就來相助,然后羽化而去,否則,怎么連名字都沒有呢?”
那一刻,我覺得,他們說的是真的。
五
從臘子口往南幾百米,便是臘子口戰役紀念碑,由楊成武將軍題字,紀念在此戰役中犧牲的烈士,也包括17歲的紅軍小戰士“云貴川”。
紀念碑寬2.5米,象征兩萬五千里長征,高9.16米,寓意1935年9月16日攻破天險臘子口。望著高聳的紀念碑,讓人感慨萬千。可不可以這樣理解呢?兩萬五千里長征,從1934年10月算起,在無數次戰役中犧牲的烈士,包括那些沒有走出雪山的,被茫茫草地吞噬的,被滾滾河水卷走的,也包括宕昌二千多名參軍戰士,他們在岷洮西固戰役和成徽兩康戰役中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默默無聞地長眠在異地他鄉。
天地間需要一座座豐碑來銘記英雄們的大德與功績!
聶榮臻在回憶錄中寫道:“臘子口一打開,全盤棋都走活了。”
是的,9月23日,陜甘支隊離開哈達鋪,9月27日到達通渭縣榜羅鎮,10月5日翻越六盤山,10月19日,勝利到達陜甘根據地吳起鎮。至此,中國工農紅軍歷時一年,縱橫11個省,長驅兩萬五千里的長征勝利結束,從而完成了堅苦卓絕的戰略轉移任務。
六
返程的時候,我們從陽光明媚的下午一直走到天黑,漆黑的夜,零星的燈光,滿天的星星......我知道,我們此刻行走的路,在當年,是紅軍戰士用雙腳丈量過,是他們一步一步走過來的。在這么黑的夜里趕路是需要燈光指引的。我又想起哈達鋪“義和昌”藥鋪的一束燈光,這束燈光,它曾照亮歷史,也照亮現實;照亮過去,也照亮未來,我們今天所擁有的和平、幸福的生活里,一定有那束光的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