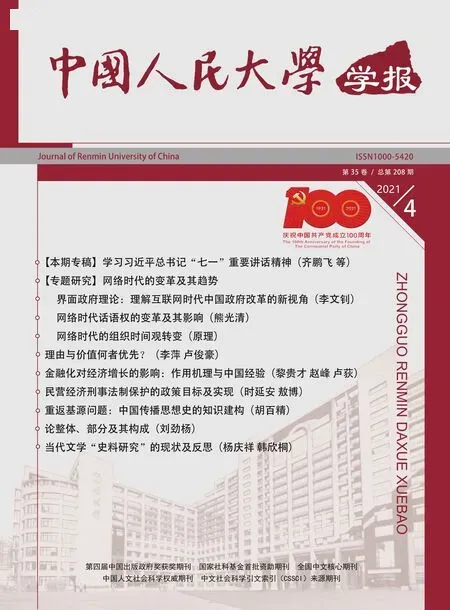網絡時代的組織時間觀轉變
原 理
時間是人們與自然和技術世界發生聯系的重要介質,人們靠技術和物質來感受、測量時間,同時,人們也受制于自己創造的物質和技術。時間作為一種社會建構,在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得到了截然不同的構想,它被行為、社會習慣和人際習慣所鞏固,并形成共識,最終對人類行為進行規制。科學理解方面的變化往往會引起其所屬時代的整個文化結構的變化,從而影響著人們對時間的理解和體驗,“一直以來,社會思想中有一個穩固的前提,即特定歷史時期的主導技術定義了時間組織以及對它的文化理解”(1)N.Green.“On the Move:Technology,Mobility,and the Mediation of Social Time and Space”.The Information Society,2002,18(4):283.,隨著技術的進步,人們的時間觀念和體驗也在改變。
馬克·泰勒在《為什么速度越快,時間越少》中描述道:“呼叫等待……無休止的電話會議……完全不顧時間地點的強制性視頻會議……睡覺時床頭也得放著一臺iphone……整晚整晚地刷郵件……坐在出租車上正準備與朋友約個晚飯時又因為收到郵件而返回辦公室……”(2)馬克·泰勒:《為什么速度越快,時間越少》, 1頁,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8。,這反映了互聯網時代的普通人正在經歷的真實生活。信息和網絡技術的快速發展帶給了人們前所未有的時間體驗,全球各地的人們建立了實時聯系,取消了地域和時間的限制,這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工作方式,同時也給人們帶來了一系列壓力和困擾。當我們在討論時間觀念的時候,實際上是在討論如何理解時間對于人的意義以及如何把握時間的節奏,它涉及生活方式的選擇和自我價值的探索。現代社會的人們在各種各樣的組織中工作,組織時間的要求和規范深刻影響著人們的行動方式和人格認知。對比工業時代和網絡時代的組織時間觀,在當下進行反思,極有必要。
一、工業時代的組織時間觀
20世紀60年代, 英國歷史學家湯普森一篇題為《時間、工作規制和工業資本主義》(3)E.P.Thompson.“Time,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Past and Present,1967,38(1):56-97.的論文,在學界引起了熱烈討論。湯普森提出了一個問題——鐘表時間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工人對時間的內在理解,它如何影響和重塑了工業社會的工作習慣。湯普森指出,時鐘式的時間規制產生之前,也就是農業社會中的人們所依靠的是“自然”的工作節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農民遵循四季的變化,漁民遵循海洋的規律,牧民遵循動物的習性。這種形式的勞作是“任務導向” (task orientation)的,在今天的農村仍然保留了這種類型的工作。任務導向型工作的特點是盡可能少地區分“工作”和“生活”,傾向于根據任務來確定工作日的延長或縮短,并且在“工作”和“打發時間”之間沒有很大的沖突感。由于農業工作必須緊密結合自然條件,這種工作規制是獨立于嚴格的時鐘標準之外的。比如,在農業社會,一個農民收割玉米的效率,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玉米的生長情況和農民自身的經驗,不同品質的玉米對應著不同的收割和處理手段,時間本身并不足以衡量這個農民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質量。農業社會的勞動分工主要是基于家庭,因此“任務導向型”的工作雇用關系是一種家庭式的關系,有關工作的規制實際上也是一種家庭式的紀律和管制模式。
工業社會的大規模制造需要系統化的管理制度和標準化的生產,而這種標準化基于生產技術的進步和勞動管理的變革。工業化不僅改變了生產和商品,以及產品的分配系統,同時它也給身體和心靈強加了新的規訓措施。隨著商業企業的日益發展,時間開始作為商品進行買賣,并作為衡量工作績效的重要標尺。傳統的任務導向型工作對于工業社會的管理機制來說,是浪費和消磨時間。工業社會制造系統的標準化和效率要求依賴于時鐘時間來管理工人,并使之內化為新的工作習慣。
在英國管理史學家斯圖爾特·克雷納的著作《管理百年》中,科學管理思想的創始人泰勒被稱為“拿著秒表的復興英雄”(4)斯圖爾特·克雷納:《管理百年》, 20、25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泰勒坦言,自己最痛恨的就是當時普遍存在的工人“磨洋工”的現象,即有意識地在工作時間里慢慢干、少干活,也就是浪費“工作時間”。泰勒認為,人力方面的低效率和浪費對于社會造成的損失是巨大的,會直接影響到企業的產量和國民整體的富裕。(5)F.W.泰勒:《科學管理原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為了弄清楚工人們真正的工作效率,泰勒把每項工作都拆分成最基本的動作,用秒表詳細計量工人工作的每一個環節所需要的時間,以確定一種效率最高的工作方式,作為科學管理的工作標準。科學管理的目的就是要通過科學的管理手段使工人以最快的速度達到最高的效率,泰勒試圖證明,這實際上與工人的最佳利益一致。
雖然泰勒的管理原則和建議在今天看來大部分已經成為管理常識,然而在當時卻意味著重大的思想變革。克雷納指出,泰勒的秒表之所以意義重大,是因為他改變了人們的時間意識。在此之前,各地的時間觀念是本土化的,人們按照自己的時間概念行事。泰勒的管理哲學影響了全世界,科學管理成為第一套國際化的管理理論,從此,“時間不再由太陽的升起或教堂的鐘聲來宣告,而是以工廠的警笛或時鐘作準。從那時起,時間由管理者衡量和宣告了”(6)斯圖爾特·克雷納:《管理百年》, 20、25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
時鐘作為主要的測量工具,使時間可以被衡量、被分割、被買賣,它以某種時間單位的形式來衡量一個人出賣的勞動量。作為勞動報酬的重要衡量單位,時間可以被轉化為金錢。“時間就是金錢”的假定支撐并統治著組織管理的理論和實踐。工作時間,就是個人“出售”給組織可以用于工作的時間,這種關于時間的經濟理念導致在現代組織管理中,收益與對工作時間的利用率掛鉤,工人的工作時間利用得越充分,管理效率就越高。由于工作時間和私人時間之間的清晰劃分,雇員在工作的時候,要確保工作時間沒有被“浪費”。任何不能被轉化為金錢的時間,比如家庭時間、休閑時間等,就是與占統治地位的工作時間相沖突的。
亨利·福特開創的生產線管理是機器時代主流的企業形象,他相信,生產速度帶來競爭優勢。雖然福特和泰勒的理念類似,但福特更強調節約成本,而不是關注工人個體的工作內容。福特制采取的大規模生產流水線系統,極大地提高了生產效率,它通過創造一系列復雜的生產系統,來確保零件、組件和裝配能在合適的時間運送到裝配線上,在此過程中,工人要嚴格配合流水線上的傳送機皮帶。福特曾表示:“我們希望工人們按照吩咐行事。組織高度分工,環環相扣,絕不可能允許工人自行其是。”(7)斯圖爾特·克雷納:《管理百年》,54、254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在福特的眼中,流水線上沒有“完整”的人,對工作進行分類之后,“我們發現有670項可以由沒有腿的人干,有2 360項可由只有一條腿的人干,有2項可以由沒有手臂的人干,有715項可以由只有一條手臂的人干,有10項能由盲人來干”(8)亨利·福特:《亨利·福特財富筆記:汽車大王的創業箴言》, 212頁,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3。。卓別林主演的電影《摩登時代》對福特制的濫用做出了最精彩的反諷,通過對工作時間的精確控制和分割,人的思想、情感和個體化需要被遺忘在機械循環的流水線上,人成了時間規制的奴隸。
20世紀末,效率仍然是組織管理的魔咒。為了提高效率和獲取競爭優勢,時間在管理過程中被精密地安排和測算,比如,設備的使用、勞動工資的支付、采購保存原料和儲存產品的花費、運輸和上架等各個方面,都要被科學地計算,以減少不必要的時間浪費。時間控制就是企業工作的邏輯基礎。美國管理學家邁克爾·哈默和詹姆斯·錢皮在20世紀90年代引領了一個管理風尚——“流程再造”:從根本上重新思考企業的關鍵流程,以實現成本、質量、服務和速度等績效關鍵指標的大幅提升。(9)邁克爾·哈默、詹姆斯·錢皮:《企業再造》,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企業再造概念包括了全面質量管理、即時生產方式(Just In Time)、時間競爭(Time-based Competition)和精益生產等思想,其中時間壓縮成為管理競爭的有力工具。在整個生產流程中,時間控制要求縮短每個操作環節的時間,優化組織結構并加速資源的流通,整個流程要比行業競爭對手更快,所有和組織生產無關的時間要壓縮到最小。在此過程中,人成了企業再造最大的絆腳石,對于管理者而言,精益流程比人更為關鍵,員工無非是執行流程的機器,而“拋棄人性就是提高效率的途徑”(10)斯圖爾特·克雷納:《管理百年》,54、254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為了使企業的核心流程更為精簡和高效,企業的流程再造理論在真實的實踐中,似乎成了裁員和縮小規模的幌子。
自工業革命以來,人和時間的關系發生了重大的改變,從一種以事件和產物為本的經濟模式過渡到了一種以時間為本的經濟模式,在這種模式下,管理者希望工人在工作時間內能夠生產出盡可能多的價值,確保公司能從雇員的工作時間里得到最多的回報。時間是商品,可以被使用、被浪費、被賺取、被壓縮、被重塑、被優化……這種“工作時間”與“私人時間”的區分在傳統的資本主義制度中,被認為是資本家剝削工人的一種手段。(11)K.Starkey.“Time and Work Organization: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In M.Young,and T.Schuller (eds.).The Rhythms of Society.London:Routledge,1988,pp.95-117.“工作時間”與“私人時間”的二元對立在工作場所體現在勞資雙方為爭奪時間控制權而進行的曠日持久的斗爭:管理者要延長工人的工時,而工人則要縮短工時。在“工作時間”和“私人時間”之間具有清晰的界限,超出規定的“工作時間”就是“加班”,如果管理者不付出額外的代價,個人有權拒絕工作更長的時間。8小時工作制最早由社會主義者羅伯特·歐文于1817年提出,他主張“八小時勞動,八小時休閑,八小時休息”。1919年,8小時工作制被國際勞工會議所承認,爾后各國從法律上確認了休閑和休息對于人們的重要性,然而,這種工作時間的限制和區分在今天的網絡時代悄然發生了變化。
二、網絡時代的組織時間觀變化和趨勢
20世紀后半葉和21世紀頭20年間,可以收集、存儲和處理信息的超高速電腦,以及個人電腦、便攜式平板電腦和手機的出現,帶來了時間觀念的變革以及組織管理的巨變。即時通信技術的發展讓時間不能再簡單地被看作是固定的、可以被物理分割的系統,鐘表時間也不再是具有絕對統治地位的時間工具,因為傳統的對于“工作時間”與“私人時間”的區分已經在失去意義——網絡時代的工作時間不僅僅限于在工作場所工作的時間,移動通信設備的使用使得員工的工作超越了工作場所的有形邊界,花在工作上的時間溢出了它原本的物理框架,變得難以計算和把握。在互聯網時代,時間觀在組織管理中出現了以下三個變化和趨勢。
(一)越來越快,時間成為更稀缺的資源
古典經濟學理論認為,這個世界上的資源總是稀缺的,商業和經濟管理的作用就是在各種需求之間通過競爭的方式分配有限的資源。然而,有些經濟學家,比如加爾布雷斯就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在西方的經濟體中,稀缺已經不是決定性的特征了。(12)J.K.Galbraith.The Affluent Society.Boston,and New York:A Mariner Books,1998.如今,對于許多國家和地區來說,食物和住所等基礎資源充足,商業企業提供的商品很大一部分都不屬于生活必需品。后現代思想家鮑德里亞曾指出,消費社會中,商品的重要性僅被當作一個符號而不是有用的東西。(13)J.Baudrillard.The Mirror of Production.St.Louis,Mo.:Telos Press,1975.商業企業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要看起來更“時尚”、更“個性化”、更“舒適”、更“便利”……才能吸引更多的消費者。因此,人們在今天所購買的不僅僅是必要的生活物品,而是“品牌”“體驗”“創意”“身份”“認同”,等等。但是,如果稀缺可以被消除,或已經被消除,為什么我們的經濟體并沒有發生實質的變化呢?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和約翰·博伊德提供了一種可能的答案:“這些有形的資源的確已經變得非常豐富,但另一種不被留意的資源——時間,卻變得越來越稀缺了。”(14)菲利普·津巴多、約翰·博伊德:《時間的悖論:關于時間觀的科學》,306、305頁,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1912年在《經濟發展理論》(15)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中,從經濟學的角度闡述創新理論,產生了“資本主義的創造性破壞”這句名言。他發現,大概每50年左右,由企業家主導的創新浪潮就會席卷整個社會,在創新技術摧毀舊的行業的同時,它也會為新的浪潮埋下伏筆。1960年,美國領導力大師沃倫·本尼斯和社會學家菲利普·斯萊特在《臨時社會》一書中提出,世界改變的速度會持續加快,直到所有事情都變成暫時性的。(16)W.Bennis, and P.E.Elaster.The Temporary Society.San Francisco:Jossey-Bass,1998.今天,我們正在真切地體驗著這種加速度。在互聯網發達的社會里,那些在過去平均50年左右才會發生一次的顯著性創新和變革,在今天的商業社會里每時每刻都在發生。熊彼特所描述的創新浪潮,那種巨大的改變,在互聯網社會已經變成一種常態。熊彼特保守估計的50年商業周期現在看起來漫長得讓人無法理解,因為企業被要求無時無刻地要思考如何改變、如何創新,而不僅僅是適應現有的環境。
因此,互聯網時間和傳統的鐘表時間是完全不同的:由于全球互聯,在商業領域,世界上所有國家和社會的時間高度統一,達成了一致的標準,那就是——沒有絕對的時間標準;不再強調白天和黑夜的區分,不再強調時區和時差的不同,每一個時刻、分分秒秒都是企業要關注的,因為,對今天的企業來說,時間不只意味著金錢,它更意味著“可能性”,意味著“生存”與“死亡”。實時或接近實時更新的信息要求企業比其對手要更敏銳,對于企業的管理者而言,“時間是問題,時間是團隊的一部分,時間是對手,時間是促成變革的普遍性力量”(17)菲利普·津巴多、約翰·博伊德:《時間的悖論:關于時間觀的科學》,306、305頁,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與傳統企業所強調的產品的生產速度相比,今天的企業更看重的是創意和想法轉化為現實的速度。產品和服務更新換代日益頻繁,“慢”就意味著被競爭對手打敗,被市場淘汰,被消費者遺忘。一個創新的想法,它必須盡快被實施,投資人可以給企業有形的資源,但他們無法給企業更多的時間,因而“效率”仍然是今天管理所關注的核心,并且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它遠比工業社會更重要:一個企業如果想生存,它必須全力奔跑。速度,是中小企業得以生存的基本考驗,也是大型企業得以維系和發展的首要任務。即便是在搜索市場上占據統治地位的谷歌,也不能滿足于擁有指數級增長的數據,“他們的工程師正在全天候的工作,以提高搜索的效率和速度”(18)馬克·泰勒:《為什么速度越快,時間越少》, 203頁,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8。。可是,追趕和爭奪時間讓企業的發展由“馬拉松”變成了“百米沖刺”,從全球來看,企業的壽命周期在急劇縮短(19)杰格迪什·N.謝斯:《為什么企業的壽命越來越短》,載《IT時代周刊》,2011(9)。,在日本,2018年度有465家百年以上的老牌企業倒閉,刷新了2000年以來的最高紀錄。(20)黃琨:《2018年,日本在365天里倒閉了465家“百年老店”》,https://t.qianzhan.com/caijing/detail/190730-d1a04baa. html。
(二)越來越久,無邊界的工作時間
過去,私人時間和工作時間的界限之所以清晰,是由于傳統工業的工作性質導致的。在傳統的工業社會里,工廠車間中普通員工的工作對象大多是“物”,生產的成果往往也是由看得見、摸得著的產品(或部分產品)呈現出來,所以,“理想的工業生產就是一切要標準化,標準化的生產體系是嵌入在標準化的時間節奏之中的,這意味著要設計好每天的節奏以保證運作的最高效率”(21)B.Adam.Timescapes of Modernity:The Environment and Invisible Hazards.London:Routledge,1998 ,p.140.。這也就是為什么泰勒在《科學管理原理》中強調要反復通過對工人的工作動作進行實驗,由此來確定一個最為“科學的”、最“有效率的”工時設定。
然而,和傳統的工業社會所面對的工作對象相比,信息社會的企業,特別是知識型企業,所面對的工作對象要復雜得多。知識型員工(22)德魯克在《21世紀的管理挑戰》中提出了“知識型員工”(Knowledge worker)的概念,用以指稱那些利用知識或信息工作的人,與傳統的體力勞動者相區分。的工作內容主要是關乎人或事件“任務”或者圍繞某個目標主題展開的“項目”,是被人為定義和詮釋的,不能夠像“物”那樣被清晰表達和認知。并且,處理“任務”和“項目”所涉及因素的復雜性要遠超過處理“物”的復雜性。比如,一個廣告活動策劃團隊要完成一個活動項目,不僅僅要受到自身的工作效率、態度、理解、創意、團隊默契程度等因素的影響,也必須符合委托方的理念,受到委托方的認可。在反復溝通商議的基礎上,項目才可以得以展開,而且項目在開展過程中隨時有各種突發的情況發生導致項目細節的變化或者項目目標的轉變。在此過程中,“人”的因素,特別是有關價值觀、知識儲備、思考方式、創新思維、審美取向、技術能力等方面的因素,是影響事件發展和進程的重要因素。如果說泰勒的秒表可以分割、測量和標準化工廠工人的動作和工時的話,知識型員工的工作很難如法炮制進行測算。并且,許多組織創新和知識創新的成果都是團隊的共同合作,員工個人的工作時間經常被包裹在整個團隊的工作時間之內。因此,受其所包含的各種復雜因素限制,在今天,處理一項“事件”或者完成某個“項目”所要花費的時間無法標準化,也難以預測和控制。
在所有移動網絡設備中,手機具有最為顯著的“隨時隨地”的效果。以手機為代表的移動網絡設備的普遍化使工作場所從原本的物理場所延展開來,進入由網絡信號支持的、移動傳播設備所構筑的更大范圍的空間之中。傳統意義上工作場所之外的家庭場所、咖啡館、地鐵、商場、甚至行走著的街道、正在駕駛中的汽車內……都可以成為新的辦公場所。對于知識型員工來說,工作不再受到任何具體有形的物理限制,工作內容的處理和完成更依賴于如何對信息進行處理。由于員工的工作內容是待處理的復雜事件,而非廠房內的“物”,他們在工作之外的時間也必須隨時“在線”,管理中理想的“全天候工人(the accessible worker)”成為現實(23)E.Bell,and A.Tuckman.“Hanging on the Telephone:Temporal Flexibility and the Accessible Worker”.In R.Whipp, et al.(eds.).Making Time:Time and Management in Modern Organizatio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17.。來自全球不斷涌現和接收到的新的信息讓公司必須全天候處于工作和等待任務的狀態,普及的空調機和供暖設備儼然已經消除了自然季節的變換,于是“每一個單位時間的工作都變得跟其他單位時間別無二致”(24)Daniel Boorstin.The Americans:The Democratic Experience.New York:Vintage,1974,p.362.。
鐘表時間不再作為對工人進行工作規制的統治性工具,越來越多的企業采取“彈性工作制”,即員工可以靈活地選擇工作的具體時間安排,以代替統一、固定的上下班時間制度。這是否意味著組織員工在今天的工作中擁有更多自由呢?由于人們隨時能夠上網,管理者傾向于認為員工隨時都向工作開放,也就是說,工作可以在任何時間進行。互聯網和信息技術為管理者控制工作場所和工作時間之外的員工提供了越來越可靠的工具,比如說,視頻會議、微信工作群、電話、各種辦公軟件,等等,都可以隨時監測員工的狀態以及對工作的跟進程度。 石井認為,“一方面,環境中的‘移動性’能讓手機使用者們自己控制來電,因而為他們提供了更多的自由”,“另一方面,如果使用者們不能通過隨心所欲地關掉手機或是忽略一些通話來自由地控制來電,那么手機只能限制他們的自由”(25)K.Ishii.“Implications of Mobility:The Uses of Personal Communication Media in Everyday Life”.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6,56 (2):346-365.。事實上,在企業中,組織成員并沒有太多的自由去選擇在工作時間之外是否關閉手機,極為可能,員工被要求24小時保持手機狀態的通暢,許多工作的正式合同中就明確規定員工要在正常工作之外能夠處理任何突發的情況。而管理者們更是要時時刻刻通過移動設備來保證管理信息下達、傳播、交流的有效性。傳統的工作時間規制基于“朝九晚五”的時間安排,但是今天,由于工作對象的待完成要求,以及員工的持續“在線”狀態,使得星期天和星期一也不再有太多區別。
(三)越來越碎片化,時間就是當下
由于互聯網的發展模糊了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的邊界,組織管理者對員工在工作時間、工作地點和他們愿意接收的工作范圍等方面都具有更強的彈性和適應性,也使得同時處理多項工作成為可能。以前,人們一次做一件事,而現在,組織成員往往是幾件事一起做。信息和通信技術讓人們能夠同時參與不同來源的若干任務。任務隨時隨地通過各種形式傳送到員工那里,被期望盡快處理。和傳統的一次只做一項工作的傳統模式相比,今天的員工除了接受任務之外,還必須能夠迅速地對這些任務做出判斷、排序和選擇,并分別予以回應,“沒有最快,只有更快,所有的事情都必須在當下這一刻完成”(26)馬克·泰勒:《為什么速度越快,時間越少》,314頁,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8。。時間是碎片化的,從碎片化的時間中,我們所獲得的信息也是碎片化的,這導致工作中注意力的缺失。大量依賴基于移動互聯網設備和網絡辦公軟件的工作被迫多次間斷,注意力反復地被各種入侵的郵件、通知、短信、語音等信息打擾,員工幾乎不可能集中精神并維持一種專注的狀態。
移動互聯網的發展讓一些不曾被重視或浪費掉的時間得以充分地利用。對于知識型員工來說,靈感和創意可以發生在工作以外的任何時間和場合。那些等待地鐵或公交車的時間、排隊買票的時間、乘坐火車或飛機的時間、電視節目間歇的廣告時間,等等,在從前被認為是“被浪費的”和“經濟上無產出”的而今天卻可以被轉化為可以用于生產的、能夠產生經濟效益的時間。(27)M.Perry,et al.“Dealing with Mobility:Understanding Access Anytime,Anywhere”.Transactions on Computer HumanInteraction,2001,8(4):323-347.甚至,傳統的休閑場域也變成了工作場所,比如某些品牌的床墊設計了內置電源插座,以支持人們利用睡前時間來辦公,其廣告將床鋪描繪成“見面地點,工作場所,夫婦的舒適區”(28)馬克·泰勒:《為什么速度越快,時間越少》, 314頁,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8。。手機和平板電腦讓人們隨時隨地對信息敞開,從一個界面迅速跳到另一個界面,從一個文本迅速跳到另一個文本,從一個任務跳到另一個任務,每一個細小的時刻都有可能創造新的績效,也有可能決定工作項目的成敗。
林瑞奇提出了“微觀協調”(micro-coordination)的概念,意指移動網絡設備對日常活動精確的調節。(29)R.Ling.“We Will be Reached:The Use of Mobile Telephony among Norwegian Youth”.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eople,2000,13(2):102-120.在工作中,人們可以依賴移動網絡設備來進行這種工作上的“微觀協調”,實現事務安排和調整的即時化,這樣,人們在工作中對事件的處理方式更加靈活,事先的計劃可以根據過程的變化而不斷進行調整。這意味著我們應該從根本上重構傳統管理中核心的要素——“計劃”的意義,它不再擁有事先預測的神奇能力,以充當組織運行的控制器,幫助組織排除惱人的變化因素。傳統“計劃”的重要性開始慢慢減弱,人們在充滿復雜性和可變性的工作情境中,可以憑借信息傳播的流動性即刻修正和調節預先的計劃和安排。不再有什么一勞永逸的“有效的”具體計劃,對“實時信息”的捕捉是組織應對瞬時變化的關鍵。然而,計劃的“失靈”也同時意味著組織拋棄了長期的目標,當長遠的投資和規劃瓦解為短期行為,所謂實時性就會使組織著眼于當下。
碎片化的工作時間帶來的不僅僅是對個人注意力的過度侵擾,也造成了人意識的割裂和自我的分裂。18世紀末,德國哲學家席勒指出:“人永遠被束縛在整體的一個孤零零的小碎片上,人自己也只好把自己造就為一個碎片……他不是把人性印在他的天性上,而是僅僅變成他的職業和他專門知識的標志。”(30)Friedrich Schiller.O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Man in a Series of Letter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p.35.他認為,現代社會的經濟理性不僅導致了社會的“碎片化”,更導致了人的“碎片化”。人的“碎片化”與“人是目的”這一啟蒙道德規劃的根本原則是完全背離的,席勒也預料不到網絡時代的人和社會將會破碎成什么樣子。
三、總結與反思
農業社會的工作時間以“任務”為導向,以自然晝夜的交替、四季的更迭為時間的衡量標準,然而由于農作物的生產有地域性的差異,人們對時間的理解是地方性的。工業社會中,“鐘表時間”樹立了一個獨立于物體和事件之外的客觀的、可測量的標準,鐘表時間是現代企業控制管理過程的一個重要工具,在管理中,時間和利潤緊密聯系,利潤最大化通過時間的最小化取得,通過節約時間,可以節約生產成本。同時,時間也意味著生產力,當一個組織能夠縮短完成一定數量的工作所需要的時間時,該組織就被認為是更有效率或更有生產力的組織。因此,工業社會的組織時間觀是以“效率”為導向、以鐘表時間為標準的。
互聯網時代,企業除了考慮生產效率之外,更要追求快到極致的“速度”,這表現在迅速的決策、快速的產品迭代、加速的創新和改變以及及時對市場變化做出反應等。“效率”在今天仍然是組織生存和發展的關鍵,只是含義比工業社會更豐富,對企業的要求更嚴苛。并且,組織時間的標準由“鐘表時間”變為“當下時間”,即時間就是現在!這與全球化和信息網絡化對組織所帶來的機遇和挑戰密切相關。移動互聯網絡消弭了晝夜的界限、地域的界限、私人時間和工作時間的界限……時時刻刻,都可以是組織時間(見表1)。

表1 組織時間觀對比
基于鐘表的時間規制影響了從泰勒起始的絕大多數管理思想和實踐,它是傳統組織管理所依賴的基本假設,它幫助管理者極大地提高了組織的生產效率。管理學家彼得·德魯克曾經指出,過去的一百年里,管理學最大的成就,是把體力勞動者的生產力提高了50倍,但是,21世紀的最大挑戰是提高知識型工人的生產力。(31)彼得·德魯克:《21世紀的管理挑戰》,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6。互聯網時代是科技理性和經濟理性高度發展的結果,隨著電腦、手機、電子郵件等通信工具的發展和普及,和體力勞動者相比,知識型員工的工作并沒有更輕松。和工業時代的工人一樣,今天的知識型員工仍然難以擺脫自己作為“工具”的命運,他們的精神壓力更大,對外界的變化反應更為敏感,工作任務無處不在,私人生活空間不斷被隨時發生的工作擠占。調查表明,IT化程度越高的企業,工作范圍越廣,工作量就會越大,工作速度也越快。(32)森岡孝二:《過勞時代》,北京,新星出版社,2019。工業時代那種集中式、自上而下的組織系統結構隨著網絡時代去中心化的分布式技術而逐漸失去了嚴格的形式和邊界。通過信息的獲取、利用來應對情境的復雜性和無處不在的變化成為組織管理的真正優勢,搶占時間成為企業競爭的核心。對速度和同時性的膜拜對組織管理和組織中的人帶來了諸多的副作用,如組織長期規劃的消失、組織成員自我意識的消解和認知能力的碎片化、組織成員過度的勞動,等等。
(一)關注當下,組織策略愈加“短期主義”
近年來,組織管理的“短期主義”(short-termism)成了一個廣受關注的話題。“短期主義”強調管理者通過短期主義的行為實現了強化短期業績而有損于企業的長期價值。一方面,資本市場本身的短期導向,即雅各布所說的“不耐煩的資本”(impatient capital)(33)M.T.Jacob.Short-term America:The Causes and Cures of Our Business Myopia.Boston,MA: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91.導致了管理者的短視。盡管投資市場看重長期投資,但相當多的證據表明,資本并不喜歡看起來收益堪憂的投資,當一定時期內收益不足,投資方就會縮減資金。因此,許多學者批評目前的管理方法的一個主要缺點就是過于強調賬本盈虧和短期利潤(34)P.B.Voos.“Managerial Perceptions of the Economic Impact of Labor Relations Programs”.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1987,40(2):195-208.,并且有很多管理策略往往因為它們不能帶來利潤最大化而被否定。一項研究表明,許多西方管理者并不考慮12個月以后的事情。(35)D.C.Wilson.A Strategy of Change,Concepts and Controversies in the Management of Change.London:Routledge,1992.另一方面,互聯網和其他通信技術加速了全球化的進程,世界各個國家、地區之間的經濟聯系在空間和時間上都更加緊密。所有的企業、組織為了生存下去,必須銳意進取,不斷改革創新、削減成本、增加附加價值,提供更好、更快的新產品和服務。對于速度的迫切要求使得企業不得不關注當下,通過日益加快的速度處理信息,集中解決眼前的問題,無暇顧及對未來的整體規劃。對于管理者在這種朝著實時軌道加速的全球化環境中的決策能力,珀瑟表示并不樂觀。他指出,管理者在信息實時傳送的情況下被迫立即做出反應,可是這種即時反應所依靠的仍然是熟悉的討論和無意識的認知偏見。這種短暫的決策使未來更加充滿了不可知的因素,而且管理者處理不斷變化的現實情況的能力并沒有提高,因為他們的即時回應總是會落入連續的即時重復,每一次決策都只是在追求更快的反應速度和效率,“‘加速—下滑—再加速’的模式是一個惡性因果循環,使本來有限的關注范圍更被縮小”(36)。當行動和反應實現了同步,那么毫無疑問,管理決策所包含的深度思考微乎其微。即時性超越了未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去歷史性的、去空間化的、去時間化的現在。這樣,組織管理的時間導向被簡化為現在,在這種當下的時間維度中,“不再有歷史或未來——沒有時間可被用于嚴肅的思考或創造性的想象”(37)羅納德·E.珀瑟:《有爭議的當下:對于“實時”管理的批判觀點》,載理查德·惠普等編:《建構時間:現代組織中的時間與管理》,205、204頁,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二)組織成員過度的勞動
1930年,經濟學家凱恩斯在其論文《我們后代的經濟前景》中,曾提出過一個著名的猜測,認為資本主義的成功將帶來一個休閑的時代,到2030年,人們每周只需要工作15個小時就能滿足他們的需要,發愁如何消磨時間。(38)J.M.Keynes.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Essays in Persuasion.New York:Papamoa Press,2019,p.185.然而凱恩斯有關工作時間的預言卻沒有發生。我們曾經期望技術可以改變生活,移動和無線設備會減少工作,增加休閑時間,但實際上,網絡時代的工作日已經延長到時時刻刻。對于那些掛在手機和平板電腦上工作的人來說,“八小時工作、八小時休閑和八小時休息”的模式已經成為往昔美好的回憶。
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全球化導致了日益激烈的競爭環境,在就業市場中,員工必須和其他國家的工人在工資和工作時間上進行競爭,因而只能放棄休閑時間,工作更長時間。網絡時代,信息技術突破了社會的物理空間約束,模糊了工作和家庭的邊界,工作時間和個人時間的連接在提升工作效率的同時,也使得以時間為核心的工作競爭更加激烈。并且,“攀比性消費”(competitive consumption)是另一個工作時間增加的重要原因。基本的生活需要是相對容易滿足的,而欲望是無休止的。人們在滿足了基本的生活需要之后仍然努力工作,是因為攀比的欲望沒有盡頭,人們希望用錢來換取更舒適的生活、更高的社會地位,這意味著人們愿意用更多的錢來換更少的時間。
“過勞”的概念來自日語“karoshi”(過勞死),如今它成為一個在全世界蔓延的普遍現象。關于過勞死和過勞導致各種心理和生理問題的媒體報道在增加,過度勞動也逐漸成為學術界關注的問題。據2009年調查數據,城市白領亞健康比例達76%,處于“過勞”狀態接近六成(39)孟續鐸、肖鵬燕:《過勞研究在中國》,載《人力資源開發》,2012(10)。;2014年,一項對我國31個一級行政區域的1 176名企業員工“過勞”狀況的抽樣調查發現,總體“過勞”的人員比例達58.2%,接近2/3的企業員工存在“過勞”現象。(40)孟續鐸、王欣:《企業員工“過勞”現狀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基于“推—拉”模型的分析》,載《人口與經濟》,2014(3)。2019年,中國的程序員們率先在網上抵制互聯網公司的“996”工作制,中國白領尤其是互聯網行業的員工,加班現象嚴重。馬蜂窩旅行網發布的《中國上班族旅行方式研究報告》顯示,除了在工作場所加班,我國白領在旅行中處理工作的人數比例高達88%。(41)劉佳:《中國上班族旅行方式研究報告:超八成人旅行時會工作》,http://news.cnwest.com/content/2017-09/12/content_15373694.htm?from=pc。過長的勞動時間給員工帶來了嚴重傷害,有研究報告顯示,高強度、高壓力的工作環境導致我國過勞死案例激增,甚至有超越日本的趨勢。(42)潘晨光、王憲磊:《人才藍皮書:中國人才發展報告No.3》,403-405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三)組織成員認知的碎片化和自我意識的消解
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中,時間一直是國家、組織進行紀律規訓和權力控制的重要手段。以往由于標準化的管理,在流水線上,工人不得不沉浸于無休止的重復性動作,一個個零碎的瞬間讓他們無法思考整個生產過程是怎樣的。今天,網絡本身隨時隨地的開放性,使得同時進行多項工作成為可能。當多重任務成為一種生活方式,伴隨失去的閑暇時間,人們會失去與那些真正重要的事物的聯系,比如家庭、朋友和獨處時的思考。每一個時間都是當下,過去和未來經常崩潰為瞬間的碎片,人們來不及回憶過去,也沒時間去展望未來,“我們走得越快,我們忘記的越多,我們忘記的越多,我們就越不知道我們是誰,該去哪里”(43)馬克·泰勒:《為什么速度越快,時間越少》, 352頁,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8。。
在工業時代,機器為工業生產和贏利提供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可用性,同時,作為機器的附件,工人必須放棄自我來適應機械。工業化革命期間,這種適應曾經讓工人痛苦不堪。根據湯普森的描述,當時英國的產業工人砸爛高懸在工廠入口的時鐘(而不是工廠的機器)時,他們的憤怒指向了這個記錄時間的恐怖又可怕的標準,因為他們被迫加速的產出量是由它來監控的。(44)E.P.Thompson.“Time,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Past and Present,1967,38(1) :56-97.“8小時工作制”是一百多年前全世界的工人通過無數次的罷工和斗爭而爭取來的結果,而今天這種工人與工作時間之間的博弈變得更加艱難。如果說工業時代的工人的工作時間主要依附于機器生產的要求,那么今天員工的工作時間則主要聽從于處理快速變化的信息的要求;如果說工業時代的工人起碼還有8小時工作以外的個人時間的話,那么今天的人們則被期待上交所有的個人時間。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人們對多重任務的接受,如今變成了一種自發的行為,幾乎不再需要監督,已經脫離了過去工業時代的強制工作模式。一方面,這是由于“現代人格顯示出生活加速是對好的生活的一種自愿‘承諾’”(45)伍麟:《社會焦慮的時間視角》,載《哲學研究》,2013(5)。,當社會制度化的穩定機制日趨衰微,職業代際傳承消失,工作崗位變動日益頻繁,知識需要不斷的迭代更新……一系列新的社會與職場變化使員工擔心跟不上時代的速度而被拋棄,從而自愿接受生活的加速和工作的要求。并且,工作內容和任務早已不能用量化的時間來規定,彈性的、自主工作時間看似給予人們更多的自主權,但并不能消除不斷增加的未完成的工作任務。另一方面,網絡改變了人的生活方式,手機已經不再是人的用具,而是成為一個外置器官。(46)汪民安:《論家用電器》,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5。今天,人們總是會不自覺地查看手機短信,不斷刷新郵件和信息。由此,莫爾斯(Morse)從福柯的《規訓與懲罰》中獲得啟發,提出了“實時技術的規訓”(47)Morse.Virtualities:Television,Media Art,and Cybercultur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8,p.118.,來描述人們在不知不覺中已經用移動網絡設備為自己心甘情愿地套上了枷鎖。珀瑟指出,一個人越傾向于體現服從時鐘時間的機械或數字節拍,就越能感覺到在時間中自我意識的喪失。(48)羅納德·E.珀瑟:《有爭議的當下:對于“實時”管理的批判觀點》,載理查德·惠普等編:《建構時間:現代組織中的時間與管理》, 214頁,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在工業時代,為了配合機器生產的要求,“守時”成為參與工作生活的全體成員的一個自律要求,而在網絡時代,不只是“守時”,“即時反饋”也成為一種普遍性的要求,或者說,成為一種職業道德的衡量標準,即無論何時何地,都應該對工作信息做出快速的回應。
綜上所述,和傳統的工業社會的“鐘表時間”相比,組織在互聯網時代的“當下時間”模糊了時間的物理限制,模糊了個人時間與工作時間,強調對變化的快速反應。“時間就是金錢”這個論斷在今天仍然成立,只不過時間即金錢不再僅僅存在于機器與人的配合中,而是存在于一個廣泛分布的、多層交叉的、錯綜復雜的全球市場的網絡化競爭之中。時間也不再僅僅是金錢,對組織來說意味著生存和失敗,對組織中的人來說意味著優勝劣汰。“當下時間”讓全球組織競爭的方式發生了極大的改變,快速和即時性反應是這個時代對于組織發展的基本要求,然而對于時間破碎成的一連串“當下”和“現在”,無時無刻的工作,快速滿足的欲望,人們同時面臨著諸如深度思考、注意力和想象力的匱乏危機,也收到了來自過度壓力和疲勞的健康警示。
因此,互聯網的發展極大地改變了人們對于工作時間的理解以及社會生活的節奏,每個人都享受更快的網絡、更快的物流、更快的產品更新、更快的交易等所帶來的便捷和高效,卻又被不斷加速和蔓延的工作時間所束縛,其中隱藏著一種現代人的悖論,即馬克斯·韋伯所描述的理性的“鐵籠”。理性的計算、紀律的訓練和技術的革新所實現的高效率是以人的自由為代價的,網絡社會組織工作的動態性、開放性和彈性使“鐵籠”以一種更加隱蔽的面目呈現。關于“996”工作制的抗議和抵制是值得重視的,但如果僅把縮減工時所產生的沖突和艱難的談判看作是對以往工作時間斗爭的延伸,而沒有意識到組織工作時間、工作的內在要求、互聯網技術發展以及社會整體對于效率的追求之間內在聯系的話,那么單純要求免除“加班制”的提議就沒有切中要害,畢竟工作任務存在于每一個當下,每個人都或被動或主動地卷入社會加速器之中。
不管我們如何希望通過法律或道德準則來限制組織中員工的工作時間,但由于網絡技術的影響,人們的工作內容和工作方式早已發生了改變,傳統的對于工作效果和效率的評估方式也已發生轉變,僅僅靠縮短組織內的工作時間來提升人們個人休閑時間的美好愿望看起來要落空。當然,短期內組織工作時間的改善性措施是必要的,但它不足以應付全球加速發展的問題;更深層次的改善則需要尼采所說的“重估一切價值”,我們迫切地需要反思那些在組織管理中占據核心位置的價值觀,比如效率、效用、速度、競爭、消費、理性,等等,思考它們在現在及未來到底意味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