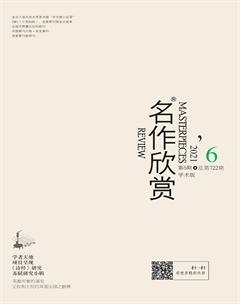烏拉特民間故事中的生命意識
摘 要:人類在漫長的進化過程中逐漸擁有了自我認知,產生了生命意識。作為烏拉特蒙古人生命符號的呈現,烏拉特民間故事反映了蒙古族人的生命活動、生命意識和生命思想。通過對烏拉特民間故事的分析和解讀,探究烏拉特民間故事中所蘊含的烏拉特蒙古人的生命意識。
關鍵詞:烏拉特 民間故事 生命意識
一、生命意識概念
現今的科學研究認為,在人類漫長的進化過程中,對于時間和死亡的認知,是人類進化過程中的一次飛躍,對于生命存亡的認知,成為人類認知自身的肇始,是人類自我意識形成的一個標志。雅思貝爾斯認為,史前階段是一個緩慢而又巨大的過程,所有的事物都在無意識當中實施。人盡管己經發展為人,但是依然和自然緊密聯系。這種依附關系表現為生命意識原型。人和自然、社會融為一體的生存記憶與體驗,借助古代文明階段的集體記憶通過漫長的歷史發展時期,最終積淀為“生命意識原型”a。無論是中國傳統哲學從外宇宙層面解讀“我”與“物”的關系,還是西方哲學從內宇宙層面探討生命本身,人類試圖通過對于生命的探索,實現自我的定義與定位。人類于生命認知中確證了自身的存在,在此基礎上發現生命主體,內省自我價值,重構生命歷程。從整體上看,生命意識作為人類最為原始的一種意識形態,是個體生命對自身存在價值與意義的自我認知,在關注人類生存與命運的過程中產生了生命關懷與生死體驗。
二、烏拉特民間故事中的生命意識
蘇珊·朗格認為:“如果要想使得某種創造出來的符合(一個藝術品)激發人們的美感,它就必須以情感的形式展示出來:也就是說,她必須使自己作為一個生命活動的投影或符號呈現出來,必須使自己成為一個與生命的基本形式相類似的邏輯。”b烏拉特民間故事正是烏拉特蒙古族人生命活動的符號呈現。它反映了烏拉特蒙古族人的生命活動、生命意識和生命思想。
(一)體魄與力量——野性生命力的彰顯
人類在最初確證自身存在之時,是從確證自己的自然身體形式的存在開始的。按照傳統社會學的理論來看,人類社會從狩獵采集出發,經過牧業(園耕)社會,過渡到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而在進入到工業社會之前,尤其是在狩獵采集以及牧業(園耕)社會時期,由于社會生產力低下,人是最重要的生產力。原始人類面對惡劣環境的時候,在與自然的對抗中,人處于被壓制狀態,那些為了生存、擺脫對自然依附性的生存競爭最終也成為凌駕于其他生物,充滿了血腥、野蠻氣息的集體生活記憶,并慢慢積淀,最終成為“獸性原型”。作為人類最直接的力量來源,強悍的身體可以增加人的生存概率和財富產出,在這種情況下,健康、強壯、富有生命活力的自然身體形式本身受到推崇。古希臘時期,希臘人們就十分注重對于體魄的鍛煉。“青年人大半時間都在練身場上角斗,跳躍、拳擊,賽跑、擲鐵餅,把赤裸的肌肉練得又強壯又柔軟,目的是要練成一個最結實、最輕靈、最健美的身體。”c
這一點在烏拉特民間故事中也表現得較為突出,烏拉特草原生命呈現出粗獷的姿態,他們高大威猛、強壯有力,迸發出蓬勃的野性生命力,這種充滿力量的野性生命力在烏拉特人看來就是生的希望的象征。
烏拉特民間故事塑造了許多這樣的形象。丹增扎西喇嘛身板好、力氣大,一次舉三百斤毫不費力。欽達瑪身高八尺,腰圓臂粗,有健壯的前胸,他不僅身強而且力壯,“欽達瑪到工具房挑了一個山斧,把小甕那么粗的木墩子放在地上輕輕一打劈成兩瓣兒。”即使如鋼絲一般的弓弦他只要用力咬幾下也會砰地一聲斷了。而傳奇搏克手布和呼日金也是“一副好身板,到十八歲時,人長到一米九,力大無比”。靠著這樣的身板兒,這把力氣,似乎沒有什么能難住布和呼日金的。“布和呼日金騎駱駝回家,把小蒙古包馱在駱駝上,上面讓母親坐上,走到半路地,駱駝發脾氣,臥下后怎么也起不來。布和呼日金這時候拿出繩索,捆好駱駝的四肢,連駝帶貨背到目的地。”“到了近處才發現一個人背著一塊大石頭過來了。那個背石頭的人正是昨日想喝水而沒有喝成的那個小伙子。背上的石頭有蒙古包那么大。來者直直走到那口水井旁邊把那磐石正好甩在井口上。人們當時嚇愣了,天下還有這么大力氣的人。”
在烏拉特草原上,不僅小伙子身強體壯,連姑娘們也是腰圓臀寬,在力量方面比起后生們也是不遑多讓。“有一位大個子姑娘站在水井臺上為駝群飲水。姑娘用的是整塊牛皮做的水斗子,大約能裝三百斤水,她提這個大水斗就像提擠奶桶那樣輕松。”馴馬高手色日瑪也是五大三粗、臂力驚人,她徒步套馬可以站在原地不動就能把馬拉到跟前。這種對于身體本身與力量夸張的描述,折射出的是烏拉特人對于力量的崇拜。世界上的每個民族在原始狀態時期,都會崇拜一種力量,具體表述為崇拜圖騰。圖騰雖然千差萬別,但都有一個共性,擁有比人類遠遠強大的力量,并具有一定的神秘感。對圖騰的崇拜,實質是對強大力量的敬仰,希望神靈能夠庇護自己,以獲得征服自然的能力。而烏拉特人將這種希望寄予了人類自身。在嚴酷自然帶來的生存困難中,他們相信源于草原的人,不僅有著蓬勃的野性生命力,更擁有不屈的意志和搏斗精神,烏拉特蒙古人相信擁有這些的草原人終將支配草原命運。
(二)意志與勇氣——對生命的守護
廣袤的烏拉特草原的是烏拉特蒙古人賴以生存的家園,但草原上亦是危機四伏,生存環境亦十分艱難。烏拉特人面對生存危機之時,并不逃避亦不妥協,而是努力自救。在艱難生存環境中求生的烏拉特蒙古人養成了粗獷而又強悍的性格,同時他們也具備了極強的生命力量與意志。無論是面對強大自然的力量還是生活的困境和磨難時,盡管人類顯得如此卑微與渺小,但是烏拉特蒙古人從來不會自怨自艾,更加沒有失去對于生活的勇氣與信心,對生命的珍視使他們從未選擇放棄。
當人處于極度殘酷的環境中,對生的渴望,會激發出人的潛能。恩泰為了逃避追蹤者只能徒步在高山密林中穿梭,在嚴重缺水極度疲累的情況下恩泰被困在山洞之中,洞口守著十幾只狼,恩泰卻只有一根粗樹枝和一把腰刀。“它們用爪子刨,用身體撞,周圍嚎叫成一團,要是膽子小的人,嚇都嚇死了。”而恩泰毫無畏懼,守著洞口,以樹枝和腰刀殺退狼群的一次又一次進攻,直到天亮,狼群退去。之后恩泰翻過了一座又一座高山,三天后,又饑又渴,卻走到了懸崖邊上,唯一的出路就是跳崖。“他果斷用長袍包好頭部,把身子縮成一團,閉住呼吸,用力往前一竄,飛出山崖。”墜崖后的恩泰失去了知覺,等他恢復意識的時候,渾身都疼,嘴里全是血腥味兒,左髖部分已經沒有了知覺。求生的意志戰勝了身體的痛苦,恩泰掙扎著向東走去,他認定那是一條起死回生的陽光大道。恩泰這一路的遭遇可謂九死一生,他在這樣極度嚴酷的生存環境去中,因對生的渴望,迸發出強烈的生命意志, 為他走出困境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力量,最終贏得了生存的機會。
烏拉特蒙古人在面對生活困境時,即使生活再困苦,也從不怨天尤人和憤世嫉俗,而是直面這些困難,對于生命給予了足夠的敬重以及渴望。“臺吉”那木噶的家鄉,好的草場都被王爺府占了,再加上大量開墾種地,導致沒有辦法放牧,到那木噶40歲的時候,他變成了“三無臺吉”(指沒有子女、沒有財產、沒有奴隸的貴族)。家里的羊群也沒了,糧食也沒有了,秋收后只能在莊稼地里拾些麥穗、谷穗熬過一冬一春。那木噶和他的妻子甚至只有一條褲子,一個人出門了,另一個人只能躺被窩里。這種情況下,那木噶在寒冬臘月,單衣縮食出門謀生。為了生存,他可以放棄貴族的尊嚴,給一個平民當上門女婿,找了個脾氣不好、嬌生慣養、嫁不出去的丑姑娘。在生活穩定下來之后,那木噶回家鄉接大老婆才知道“臺吉夫人”已然成了乞丐,不知所蹤。而這位由貴族成為乞丐的夫人,也沒有輕易放棄自己、放棄生活,她一路靠乞討和幫人做工,最終和丈夫團圓。而那木噶也經過自己的努力變成了“三有臺吉”。
烏拉特蒙古人對生命的珍視,不僅體現在對自己生命的看重,也體現在對別人生命的維護上。他們有艱難求生的勇氣,也有勇于犧牲的勇氣,為了他人的生命得以延續、為了草原上的人們更好地生存,烏拉特蒙古人愿意為此獻出生命,他們奮不顧身、義無反顧。勃哈力將軍偶遇被魔鬼莽古斯搶來的少女,為了救她與魔鬼搏斗重傷,被魔鬼封死在小石頭敖包中,化成了巍峨的山;十八歲的香寶來為了好的草場放牧,不必倒場,挺身而出單槍匹馬與“有蒙古包那么粗”的巨蟒搏斗,為草原鏟除了危害。雅格拉代只身一人取鳳羽、擒巨蟒、鎮可汗,使草原人民過上了安居樂業的生活。人與人之間的關愛與扶持、奉獻與犧牲,這種人性的溫情也是對生命的珍惜。
烏拉特民間故事中所反映出的烏拉特蒙古人的生命意識非常鮮明。在嚴酷自然環境和生活困境夾縫中努力生存的烏拉特蒙古人堅信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救贖者”。他們勇猛剽悍,崇尚力量,呈現出生機勃勃的野性生命力;他們不屈不撓,負重前行,迸發出堅忍頑強的生命意志;他們相互扶持、勇于奉獻,流露著溫情脈脈的生命關懷。
a朱欣、謝冬平:《對雅思貝爾斯存在主義教育哲學之闡述》,《學術流》2012年第2期,第195—199頁。
b蘇珊·朗格:《藝術問題》,滕守堯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24頁。
c〔法〕泰納:《藝術哲學》,傅雷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版,第43頁。
參考文獻:
[1]葉舒憲.原型批評的理論與方法[M].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總社,2018.
[2]蘇珊·朗格.藝術問題[M].滕守堯譯.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3]尤西林.美學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基金項目: 本文系烏拉特民間故事的文化價值觀研究(項目編號:HYSQ201811)
作 者: 曹媛,文學碩士,河套學院講師,研究方向:文藝學。
編 輯:曹曉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