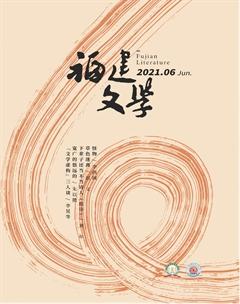真實與虛構
李晁
由“我”到他人,由現實到真實,是小說創作的一條路徑,這一切是怎么發生的,它的落腳點在什么地方?我認為是虛構。這幾乎和人類說謊的天性有些關系。我們知道,生活里的一部分謊言無傷大雅,它只是一個人借此表達對不可能的生活和欲望的適當想象,而為了規避責任或追逐利益的謊言則屬于另一類。這兩種類型(甚至更多類型)的謊言正充斥著我們的生活,而文學虛構則屬于系統化的光明正大的“謊言”創造活動。
謊言天生就要吸引人,這是它的屬性,又因述說者帶著的特殊激情,所以它的誕生就必然帶有表演性,這自然也屬于創造,而謊言的最大的舞臺無疑屬于權力。遠古人類在面對不可解的自然現象時需要做出解釋,這解釋就同時帶有安撫和震懾的作用,并由此導入鬼神或神話的世界。這也可視作虛構,一種偉大的虛構,后世的人們都接受了這由先人虛構出來的不可觸摸的那一部分世界,它的偉大在于擴展了我們對世界或表象之外的世界的認知,是想象力的集大成表現,因它完成了體系,并自洽。
等到文學的出現,這一力量便堂而皇之成為我們接受其影響的方式。當神話變為歷史,當人類開始無比嚴肅地像對待科學一樣對待虛構,虛構的嚴肅性和正當性就得以確立,可一旦確立,就又產生了相應的隔膜,即我們要一次次自然地面對這不自然的結果。
在小說里更是如此,看上去除了作者之外,我們不知道虛構與現實與“我”的界限到底在什么地方,這一分割線只有作者心知肚明,所以約翰·塞爾說:“一部作品是不是文學是由讀者決定的,至于是不是虛構則由作者決定。”(摘自伊格爾頓《文學事件》)這有一定道理。小說生產中的虛構環節就天然地帶有神秘性,虛構成分的多少,它在一個作品中占有多少的配比,是難以被量化的,就像作者的寫作意圖與讀者的接受可能南轅北轍一樣。所以J.O.厄姆森說:“如果一部作品中的主要角色取材自真實生活就不成為虛構。”(摘自伊格爾頓《文學事件》)這就是個很片面的看法。但還有一個觀點認為,某件事可以同時是事實和虛構,“你可能要在戲里打一個噴嚏,當你真的打了一個噴嚏時就權當它是表演,因此你真打了一個虛構的噴嚏”。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發現,來自伊格爾頓的設想。當然,這也是一個極端的例子,概率可能比中雙色球還要小,但概率小也可能存在。我們寫小說也有這樣的幻覺,一個發生的事件被我們寫出來就如同它從來沒有發生過,就是說,是你制造了這樣的事實,而非事實影響了你。
我傾向于認為不論小說取材的真實程度占比多少,一旦它變形,沿著自我的軌跡發展,即為虛構,也就是說虛構與真實并非對立,而是彼此包容。甚至可以武斷地認為,虛構正因為材料或來源(諸如環境)的真實而變得更加牢固。反過來講,我們以為的真實(生活),某種程度上也來源于虛構(主觀的感知)。比如我們猜測一個人的想法,借助我們對他的了解或信息掌握乃至僅僅憑借感覺(感覺的發生也可以視作一次微小而又瞬間的虛構)做出判斷,我們無比想要靠近他的想法,并一次次得出自我的想象結果,這一并非由他得出的結論,很可能得出重疊的信息,就是說我們猜對了。當兩者達成一致時,便說明了事物可以同時是虛構和真實的,而不必在戲里碰巧打一個真實的噴嚏,它有更廣泛的基礎。
說回文學,虛構的來源與配比,自然是一個小說家的秘密配方,是他依據熟悉世界的材料做出的具體選擇。我們看《局外人》,加繆的隨筆和手記為我們探索《局外人》提供了有力的幫助。《局外人》的核心情節,開篇即出現,默爾索在母親的葬禮上沒有哭,這是在庭審部分主人公備受攻擊的一點,這條線索的來源在哪里?在大學畢業論文中,加繆著重寫到了奧古斯丁,而奧古斯丁在《懺悔錄》里就寫過,“安葬前(依照當地習俗)將遺體停放在墓穴旁邊,為她進行了祈禱儀式,誦讀為我們贖罪的祈禱詞,甚至在這過程中,我都完全沒有哭泣。”可以看出奧古斯汀雖為母親的死感到傷心難過,但他沒有在母親的葬禮上哭泣,這就可以看作加繆虛構默爾索這一核心表現的來源。小說的葬禮,乃至葬禮的地點馬朗戈,構成了小說開篇的重頭場景,這也來自加繆的親身經歷,加繆的嫂子就把自己的母親送進了馬朗戈的養老院,也是一個郊外的小鎮,這位祖母死后,加繆去參加了葬禮,這是作者的確鑿經歷,甚至那個跟隨送葬隊伍的小老頭、死去老太太的未婚夫的角色都是真實的。而小說第二部分,涉及庭審,更與加繆的記者生涯有關,他參加了數不清的法庭審判,做過不少深入報道。好玩的是,我們在庭審時發現的與默爾索照面的那個記者,難道不是加繆的客串演出?
在參加完嫂子母親的葬禮后,加繆在1938年秋天寫下了一條重要手記:
今天,媽媽死了。也許是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養老院的一封電報,說:“母死。明日葬。專此通知。”這說明不了什么。可能是昨天死的。(據郭宏安譯本)
這一段沒有任何其他說明文字的文字在幾年后正式成為文學史上最經典的開頭之一,且沒有改動,完全照搬。
即便通過如此粗略地分析,我們也能夠看到文學虛構與作家真實經歷之間的關系,正因為這種種因素,加繆才會寫出這樣的《局外人》,而不是別的版本。虛構的來源與背景,我們大體清晰了,可小說最重要的精神內核卻仍沒有解決,尤其對默爾索這個人物而言,這些都是外在的條件。比如陽光,海灘上的陽光,在默爾索殺人的時刻,那陽光的反復出現,都讓我們都不得不思考一個問題,即人物心理,這心理與虛構又有著怎樣的關聯?這一部分的存在,我覺得才是虛構的最迷人之處,因為它跳開了對外部環境與作者的自我經歷的取舍與加工,而進入了虛構的核心部分,即沿著某些真實線索而獨立發展的部分,是它塑造了人物、影響了命運,從而完整表達出作者意圖。不論出于荒誕還是真實,也不論讀者理不理解,這都是讀者借虛構取得共情,由共情而得出結論的過程。
這一切也是漸進的,如果說外部環境是小說人物依托的來源,是他的生涯的潛移默化的諸種影響之一,而等他真正成為那個“他”,就要靠作者的大膽探索和進一步虛構了。這才是虛構最為有力的部分,也是最為困難的部分,它既要求人物與環境融為一體,讓環境暗示人物,又要讓人物發出自己的聲音,不斷適應虛構的進程,而人物最終的聲音或許會脫離他或作家所依托的環境,上升為一個全新的存在。這就是虛構的目的——離開源點,越遠越好。
我們為什么需要虛構?難道現實還不夠生動還不夠震撼嗎?現實可是一個不斷循環而又變化的整體,它的優勢是天然或者說自然,虛構能達到這一程度嗎?我想說,能。小說的任務并非描摹世界,而是以有限的篇幅延伸出一個完整的運行的世界,它有自己的獨立性。打個比方,你永遠無法觸摸到鏡中的自己,你的觸感是由你的指頭和鏡面共同生成的,而非鏡面中的那個人真的和你擊掌。那個鏡中的世界也不因你的離開而發生偏移,這就如同文本世界,我們恰可以通過有限的文本去感受文本所依托的更為深邃的空間,這就是小說的魔力和魅力。
如果只看局部事件,也是這樣。一個我們道聽途說來的事件,我們是沒有參與度可言的,它的出現只是一個結果的呈現,但這樣的結果或者說事實是由我們看到的這個材料決定的。事實上,我們完全無法把握那一事件進程中各方面的關系及其表現,這就會影響我們的判斷和情感的投入,因為我們的大腦只對我們接受的部分做出反應,這是殘缺不全的,甚至我們會因為講述人的立場與角度的不同而受到牽引和誤導。當下的許多事件為什么常常反轉?就是因為材料和角度的更替,因為一個人有一個人的角度,一個集團有一個集團的立場,這是阻止我們深入了解的障礙。那么還有一種情況,如果是我本人經歷的又如何?我自己的經歷該有說服力了吧?也不一定,當事人處于事件之中,他也有自己的立場和利益,而由這樣的立場和利益出發,當發生了與自己相關聯的事件時,我們的感受難道就是完整的就是絕對的?不一定吧,因為事件并非只是我的事件,同時肯定也是他人的事件,而一旦涉及他人,難道我們就像了解自己那樣了解別人?這里面的偶然性要考慮,情感的理智度要考量,更別說來自其他方面的影響與遮蔽,這都會左右我們看待一個事物,而虛構恰恰是打破這種混亂處境的途徑,是讓我們擺脫現實桎梏的有力手段,如同“上帝不響,像一切全由我定”。我定,就是一部虛構作品的全部來源與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