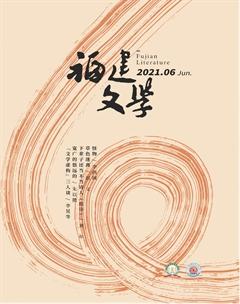一花一世界
陳潤庭
可信的不可能之事比不可信的可能之事更為可取。
——亞里士多德《詩學》
在虛構小說幾乎成為文學代名詞的今天,談論文學虛構意義自不待言。將文學虛構作為視點,讓我們得以同時管窺當代文學內部與外部危機的癥候。作家余華接受采訪時坦言,“發生在身邊和新聞中的事情不需要收集就會跑到跟前,而這些現實比小說更荒誕。”在一個文學邊緣化的時代,敘事小說不再是社會與文化評論的工具,自媒體與新聞媒體每天都在生產各種更加離奇且“真實”的故事。這種情勢迫使文學回答虛構存在的價值所在。依靠資本與科技的力量,團隊作戰的電影工業可以呈現出高度奇觀化的世界圖景,IP開發把文學語言的虛構,變成電影生產環節中有待圖像化加工的原礦石。而在文學的內部,一種名為“非虛構”的寫作自美國舶來,成為當代文學擺脫“失聲”的良藥。
危機之下,文學虛構已非文學之長,而成了文學之短嗎?
2010年,《人民文學》率先設置“非虛構”欄目,推出了梁鴻《梁莊在中國》等一系列“非虛構”作品;五年后白俄羅斯作家阿列克謝耶維奇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將“非虛構”推向新的高潮。一連串的文學現象,似乎在告訴小說作者們,我們賴以為生的虛構,正面臨著合法性的危機。比起林林總總的虛構文學,當下的讀者更樂意閱讀“非虛構”,相信個人口吻帶來的“真實”。
當前國內“非虛構”寫作的主要作者,除了數量龐大但常曇花一現的作者之外,就是原本的文學創作與研究的從業人員以及特稿記者。可以說,“非虛構”作家主要由文學界和媒體界人士構成。這與“非虛構”寫作的起源與文體特征不無關系。“非虛構”寫作起源自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代表作家杜魯門·卡波特與諾曼·梅勒以新聞報道體的方式寫小說,被稱為“新新聞體”或“新新聞主義”。
在誕生伊始,“非虛構”就是新聞與文學的混血兒。“非虛構”取材往往來自創作主體的個人經驗,或是對真實新聞的深度挖掘;文體則介于自敘傳與特稿之間。文體的交雜讓“非虛構”擁有了更多的敘事自由,可以突破傳統新聞為保持新聞倫理設置的諸多禁令,如按自然時序敘事、語言簡潔、一般不使用具有情感色彩的形容詞、不對人物做文學性的描摹等。與此同時,“非虛構”的命名本身即在暗指自身的真實性,比文學虛構擁有更高更直接的真實性。但實際上,有些“非虛構”作者甚至聲稱自己會根據某些需要,改動所描寫事件的人物、時間及地點。如果說,虛構無法完全避免,敘事必然帶有一定的虛構,那么問題仍在詩學的范疇。但借“非虛構”之名公然造假,卻是寫作倫理的問題。
“非虛構”的敘事,也必然會有虛構。虛構本身并不構成問題。構成問題的是,“非虛構”號稱更真實,卻難免虛構。正如海登·懷特所言,“敘事本身本質上已被證明是虛構的”。也就是說,虛構是敘事本質的屬性。敘事開始之時,虛構也相伴而行。而文學敘事中的虛構,自然概莫能外。而既然虛構伴隨敘事而生,虛構便不可能單單存活在文學的畛域,一定是見諸人類以口傳言、提筆作文的諸多領域之內。
文學的疆域,也并非自古以來就邊界清晰。事實上,到今天也未清晰過。我們今天通用的文學概念,很大程度上是歐洲19世紀現代學科建立時代的產物。“被作為文學研讀的作品過去并不是一種專門的類型,而是被作為運用語言和修辭的經典學習的。”因而,歐洲現代意義上的文學概念,是通過對“19世紀修辭學的抑制”得以建立的。至此,修辭學被貶斥為關于語言技藝與實用的學科。與此同時,歷史學在科學的焦慮下,對敘事的虛構屬性避之不及,急于拋棄,以便自立門戶。文學由此才得以變成關乎純美的語言藝術。唯美主義的雙手將文學從社會生活之中輕輕捧起,用夢幻與神秘包裹起來。既然文學寫作的技藝與敏感的體質,都近似于靈感與天賦,那么虛構自然也難以習得、無法教授。當我們談論文學虛構時,既假定了在其他語言領域中存在形態迥異的虛構,也暗示了存在一種單單屬于文學的虛構。
回溯現代文學的生成,不是為了讓虛構與文學重新分家,或是七零八碎地肢解概念,而是在歷史語境的回顧中,重新辨清虛構作為敘事技藝的面貌,提出更有當代性的文學問題:為什么我們仍然需要文學虛構?
我們都知道,唯一的真相既已發生,難以靠后來的語言敘事捕獲。在喧嘩騷動之中,真相往往沉陷于“竹林中”無法復得。“非虛構”所造就的“真實”,實際上是文本敘事產生的效果,是確鑿的修辭問題,或者說,是文學技藝的問題。“非虛構”幾乎自覺摒棄了現代主義文學以來發展出的敘事技巧(意識流是其中少數的例外),轉而以相當有限的現實主義文學的方式進行敘事與描摹。為了獲得一種真實的文本效果,“非虛構”在此與現代史學采取了相似的話語策略。而現代文學也正是在現代主義上形成了一座高峰。隨著現代主義文學的誕生,文學敘事的技藝也迎來大爆炸的時期。現代主義文學發展出琳瑯滿目的敘事技藝,讓虛構與真實走出簡單對立、重新拋光,也讓作家有了更銳利的手術刀去解剖日益復雜的社會現實,抵達真實的更深處。
在現代文學產生以來,“虛構—真實”契約日漸失效的今天,文學的危機是真實的,也是正在發生的,甚至是日益深重的,但企圖依靠商業主義的“非虛構”為文學開出藥方卻是虛妄的。以“非虛構”之名與之實,通過拋棄現代主義文學留下的敘事遺產和審美,拉近文學與當代讀者的距離,讓文學重回社會生活的領域,我認為得不償失。布洛赫說,“發現小說才能發現的,這是小說存在的唯一理由。” 我想借用赫爾曼·布洛赫這句話的邏輯。發現文學虛構才能發現的,這是文學虛構存在的唯一理由。
法國哲學家甘丹·梅亞蘇在《形而上學與科學外世界的虛構》中重新審視了休謨與康德那場著名的論爭。讓我們回顧一下這場論爭。休謨基于反經驗主義的立場,提出關于桌球的想象:即便條件不變,為什么我們擊出的桌球就一定要采用我們能預料到的路線運動呢?由此,休謨提出了關于物理恒定、因果關系必然性的懷疑論。而康德則以“朱砂之喻”相對。如果朱砂時而是輕的,時而是重的,時而是綠色的,時而是塊狀的,這種現實假如存在,那么一切也只是多元的混沌。在這種情況之下,首先坍塌的是我們的感知。人類的感知力無法認識與承受這樣完全混沌的世界。梅亞蘇批駁了康德先驗式的邏輯推演,認為其觀點建立在“蓋然性”的假定之上。簡而言之,是以非黑即白的邏輯進行的推演。
那么,有沒有一個可能世界,存在于絕對非理性與絕對理性之間的灰色地帶呢?
對此,梅亞蘇給予了肯定的答案。他認為,無論科幻小說虛構的未來再怎么千變萬化,科學卻不能缺少。科學是理性在小說中的代言人。而在梅亞蘇所描繪的可能世界里,有兩條法則必須遵從。首先,在那里發生的事件不能被任何真實的或現象的邏輯所解釋;其次,科學的問題在那里是存在的,盡管是否定式的。而如阿西莫夫《桌球》等一些以這樣的可能世界為背景的虛構作品,長期被納入“科幻小說”類別之中。但在梅亞蘇眼里,這些作品應該被稱為“科幻外小說”。
危機下的文學虛構何為?梅亞蘇給予了“或然性”的啟示。在今天,文學虛構的出路在于構建“或然性”的可能世界。正如多勒澤爾所言,“可能世界的疆界隨著人類的世界建構活動不斷擴張和變化,而文學虛構是世界建構事業最為活躍的實驗室”。與電影的越來越高超的呈現技術相比,現代主義文學以來文學的“向內轉”策略,仍然發揮著作用,保持了文學虛構書寫內心世界的優勢。而在電子游戲的互動性與代入感面前,“向內轉”的策略是否仍然奏效,已成問題。但無論電影還是游戲,都形成了各自工業化的生產模式,其發展有賴于資本的大量投入。與之相比,文學虛構單槍匹馬,卻反而自由。一個鍵盤就可以造出一個世界。正是在文學虛構極端的個人性之中,藏著虛構最內核的秘密,也藏著它免受異己之強權染指的潛能。一個文本的可能世界誕生的時刻,也即是一個個體的白日夢現于人前的瞬間。白日夢并非毫無意義的無稽之談。借助文學虛構的力量,白日夢的可能世界與現實世界并肩而立,將現實的邊界拓展。文學虛構就是讓世界看見花,看見一花一世界。
責任編輯林東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