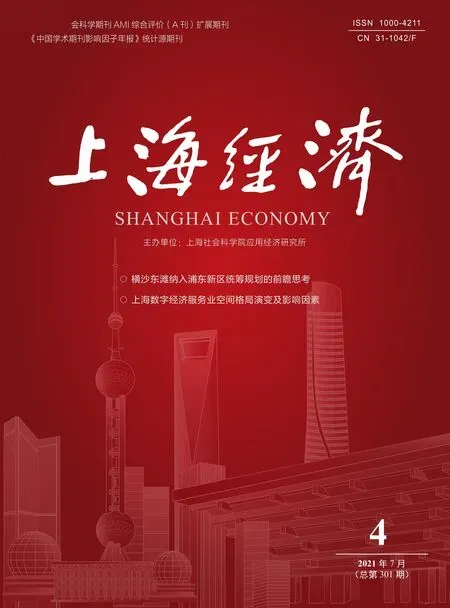上海數字經濟服務業空間格局演變及影響因素
康江江 汪明峰
(1.上海社會科學院應用經濟研究所,上海 200020;2.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200062;3.華東師范大學城市與區域科學學院,上海200241)
一、引言
當前,以信息技術為引領的產業新業態方興未艾,在加快信息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催生了一種全新的經濟形態——數字經濟。從全球來看,中美正在引領數字經濟。2015年數字經濟的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在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進一步強調了要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2019年中國數字經濟增加值的規模達到35.8億元,占GDP比重36.2%(數據源于《數字中國建設發展進程報告(2019年)》),更是凸顯了數字經濟對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引領作用。可以發現,中國作為數字經濟大國,數字經濟逐漸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增長動力,成為我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依托(趙濤等,2020)。更進一步,數字經濟作為驅動經濟發展的關鍵生產要素,對于我國主要城市的經濟發展的作用也愈發重要,對于推動城市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就上海而言,2019年數字經濟產值規模已經超過了50%(數據源于《2021上海市數字經濟發展研究報告》),表明數字經濟已經成為引領上海經濟繼續增長的引擎。為進一步促進數字經濟發展,2019年出臺的《上海加快發展數字經濟推動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實施意見》,指出要持續增強新時代上海數字經濟發展新優勢,加快提升數字經濟規模和質量。2020年出臺的《上海市推進新型基礎設施建設行動方案(2020-2022年)》更是指出,通過一系列數字經濟基礎設施的建設來構建上海新興產業技術創新發展的支撐體系。然而,數字經濟的發展不僅要關注產值規模的提升,還應該注重發展質量的提升。尤其是在全國數字經濟百家齊放的大環境下,聚焦上海數字經濟發展重點領域。全力打造數字經濟發展新亮點,持續增強新時代上海數字經濟發展新優勢,促進上海數字經濟的更高質量發展。
二、文獻綜述
從已有的研究成果來看,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數字經濟的產生及其內涵。英國新經濟學家Tapscott(1996)首次提出“數字經濟”,隨后各國政府紛紛采取措施將數字經濟作為推動經濟增長的新動能。數字經濟在范圍上涵蓋電子商務、信息技術、相應的信息通信技術(ICT)基礎設施、IT行業本身、商品和服務的數字傳輸及IT所支撐的有形商品的零售銷售(Malecki & Moriset,2008)。其中,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包括電子信息制造業、電信業、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互聯網行業等,與ICT產業具有較強的重疊性(趙義懷,2020;徐麗梅,2020)。不過,2021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經濟及核心產業分類(2021)》中,將數字經濟確定為數字產品制造業、數字產品服務業、數字技術應用業、數字要素驅動業、數字效率提升業這五個類別。相比原先的ICT產業,主要增加了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的融合的相關產業。第二,影響數字經濟空間格局的要素機理分析。首先,傳統區位理論認為,產業分布受制于地方發展條件與區位優勢(韓峰和李玉雙,2019)。通過介入比較優勢的構建,政府部門能通過地方發展策略的實施,推動產業的地方性集聚發展(Bai等,2004)。其次,城市發展理論指出,集聚是城市發展的本質,城市發展要素的空間集中的向心力會促進產業在城市空間的集聚。數字經濟產業作為城市產業發展的新業態,只有大城市才能獲得技術支持、市場保證和經濟效益。因此,數字經濟產業中外資企業主要集中在城市化發展水平較高地區(康江江等,2019)。第三,數字經濟發展的政策研究。其一為國外數字經濟政策研究,隨著許多發達國家對產業政策的興趣復蘇,各地政府都對發掘更強大、更具“競爭力”的數字經濟有著濃厚的政策興趣。例如,英國的科技城計劃、美國的區域創新集群、歐盟的“智能專業化”政策(Foray,2015)和歐美“銹帶”轉型“智帶”的智能轉型(阿格塔米爾和巴克,2017)。其二為國內關于全國、上海及長三角其他地區推進數經濟發展的政策建議。上海數字經濟基礎較好,在全國數字經濟指數中的占據領先地位(劉軍等,2020)。從突破數字經濟核心產業關鍵技術、提升數字經濟規模等級、數字經濟產業集聚效應以及建設數字經濟產業聯盟等等方面提升上海數字經濟的發展水平(袁偉等,2020)。將上海打造成為具有影響力的數據中心、數字技術創新策源地、數字經濟貿易國家樞紐港以及面向未來的數字之城(趙義懷,2020)。此外,浙江省啟動“數字浙江”建設(方申國,2019);江蘇省著力推進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提檔升級,大力提升數字基礎設施(南磊,2018);安徽省發布《支持數字經濟發展若干政策》,組建安徽工業互聯網產業聯盟等(范琦娟,2018)。可以發現全國主要省份都提出了數字經濟的發展政策與方略,特別是2021年國家統計局專門公布了數字經濟核心產業的行業類型、分類和具體代碼,更是為指導全國推進數字經濟發展、統計以及區域比較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基礎,同時也會進一步推動數字經濟的發展。
總結而言,國外研究起步較早,在數字經濟的空間效應及其對產業、社會的影響方面研究較多,對其在地方發展中實際作用的研究稍顯薄弱。國內研究近幾年進展較快,但研究的主要局限性和急需解決問題是,研究內容較為籠統與分散,較少明確聚焦地方產業發展需求,進行深入的針對性實證研究,地方指導意義較弱。為展開這一研究,需要首先明晰數字經濟服務業企業的空間區位選擇特征與分布規律,分析這些企業在進行區位選擇時主要關注的影響因素,進而提出未來促進本地數字經濟服務業的發展提供相關的對策建議。因此,本文基于2008—2018年上海數字經濟服務業企業相關數據,分析上海數字經濟服務業企業的空間變化特征,并利用負二項回歸分析方法對其影響因素進行實證檢驗,以期深入掌握上海數字經濟服務業發展空間規律與驅動因素,為上海進一步推動全市數字經濟發展以及內部不同區級單元協同發展提供支持。
三、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一)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來源主要包括上海市統計局第二(2008年)、第三次(2013年)國民經濟普查數據中的數字經濟企業數據,以及2018年上海市的工商注冊的數字經濟服務業企業數據。獲取的數字經濟企業數量分別為2008年3832家、2013年10068家、2018年35825家。其中,2008和2013年企業信息字段包括企業名稱、企業地址、行業類型、注冊資本、營業收入、法人、成立時間、行政區劃、經營范圍等。基于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字經濟及其核心產業統計分類(2021)》指南,主要選擇數字經濟核心產業中的服務業行業進行研究。因此,本文的數字經濟服務業產業主要涵蓋電信、廣播電視和衛星傳輸服務業、互聯網及相關服務、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文化數字內容及其服務業等具體門類。此外,在模型實證中,本文還用到城市層面的數據,主要來源于《上海統計年鑒》、上海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2015年上海1%人口抽樣調查資料等,以及上海道路、地鐵站點、大型綜合商城POI數據等。
(二)研究方法
負二項回歸分析方法。由于分布在每個鄉鎮的數字經濟服務業企業存在一定的不連續特征,即某些鄉鎮擁有的企業數量相對較多,有的城市分布的數量很少甚至為零,這就說明數字經濟服務業企業在空間上的分布可能存在較為明顯的離散特征,不符合泊松回歸模型的假設。同時,通過檢驗因變量的方差與均值,發現方差明顯大于均值,說明存在“過度分散”,需要用負二項模型來進行實證檢驗(陳強,2014)。

是的估計參數,服從泊松分布:

在公式(2-3)式中:i表示縣域單元,t表示時間,K為超離散程度,服從均值為0、方差為α的伽馬分布。α越大,表明超離散程度越強。
四、上海數字經濟服務業空間特征演變
(一)總體空間特征
1.區級尺度下“中心—外圍”狀空間分異格局逐漸演變為“多中心—外圍”特征
通過計算16個區的企業分布密度(利用數字經濟企業數量/區行政區劃面積計算所得,用來表示各個區數字經濟服務業企業集中程度的高低),結果見圖1。

圖1 2008—2018年上海區級尺度數字經濟服務業分布趨勢
通過觀察企業在不同市區的分布密度圖可以發現,上海數字經濟服務業的空間分布大致呈現出較強的“中心—外圍”狀分布特征,即中心市區如黃浦、徐匯等區企業分布密度相對較高,而外圍市區如金山、奉賢等市區的數字經濟服務業企業則分布密度較低。然而,上海各個區的發展狀況存在一定差異,整體空間格局也處于不斷的變化當中,多中心趨勢開始凸顯。具體看來,2008年上海數字經濟服務業呈現出非常顯著的中心高,外圍低的空間分布差異。其中,黃浦、靜安、徐匯、長寧是四大核心集聚中心,是上海數字經濟服務業分布密度最高的區域,同時鄰近的普陀、虹口兩區的數字經濟服務業也呈現出較高的集聚度;然而,位于遠郊區的金山、松江、崇明等區的數字經濟服務業企業分布密度較低,表明這些地區的數字經濟服務業的發展水平相對較低;雖然2013年中心市區的數字經濟服務業集聚程度較高,但是近郊區的浦東、寶山和嘉定等有所發展,且這些區的數字經濟服務業集聚程度有所提升;到2018年,仍舊呈現出以中心市區為主,近郊區和遠郊區為外圍的空間分布格局,但是開始出現多中心分布特征,主要是近郊區有所發展,而崇明和金山、奉賢等區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較低。
2.鎮級尺度下多中心狀空間分布格局逐步形成
基于上海各個鄉鎮街道單元的數字經濟服務業企業數量,按照企業分布數量多少進行統一分類,劃分為5個等級,結果見表1。從鄉鎮尺度的企業空間分布變化中發現,數字經濟服務業企業的空間分布主要呈現出較強的多中心空間分布特征,即主要以少數鎮或街道為主要的集中分布區,這些區域并不僅僅集中于主要的中心市區,而且在一些近郊區和遠郊區的鄉鎮也集聚了大量數字經濟服務業企業。具體看來,主要以浦東新區的張江科技園區、陸家嘴街道、徐匯的楓林路街道以及黃浦的外灘街道,逐漸演變為張江、臨港、五角場為核心的空間格局。同時,一些中心市區的街道和鎮則不再具有集聚優勢,同時數字經濟服務業企業進一步向少量中心鎮或園區進行集聚,尤其是非中心市區的城鎮成長迅速。具體而言,張江、五角場街道、陸家嘴街道等一直是數字經濟服務業企業集中分布區,張江成為上海數字經濟服務業分布的超級集聚中心,臨港新城、南翔鎮、唐鎮等郊區強鎮逐漸也逐漸成為地方性的集聚中心。總之,2008—2018年上海數字經濟服務業主要以浦東新區的鎮為主要的集聚中心,中心市區的少許鎮或街道也集聚了大量的數字經濟服務業但地位在不斷下降,而郊區的部分中心鎮成長為本區重要的數字經濟服務業企業集聚中心。

表1 2008—2018年鄉鎮尺度數字經濟服務業企業分布趨勢
五、影響因素分析
(一)變量選取與描述性統計
企業的區位選擇可能受多個要素的影響,已有研究針對影響因子的選擇已經做了大量的相關性研究(蔣海兵等,2015;公維民和張志斌等,2021;徐禎等,2021)。這些研究均認為地區的交通便利程度(交通可達性)、所處的地理區位、產業發展基礎(包括地方化經濟、城市化經濟以及核心配套產業的發展水平等)、經濟發展水平、區域發展環境等是影響企業進行區位選擇的主要因素。基于此,本文主要利用2018年企業在鄉鎮尺度的空間分布數量作為因變量,主要從交通要素、區位要素、產業基礎要素以及經濟基礎要素四個方面進行實證分析。
其中,交通要素指標主要選擇以下三個具體的指標,即是否有高速公路通過(Highway)、地鐵站點的數量(Subway)、有無快速公路通過(F-Road)三個指標進行表示。這是因為數字經濟服務業企業在進行區位的空間選擇時,會綜合考慮本地的交通通達性,距離高速路、快速路以及地鐵交通方便的地方,方便出行和對外聯系,有利于企業快速與客戶進行對接,同時也有利于企業員工的上下班通勤,可以較低企業運營的交通成本。
區位因素不僅是指企業所在的區的地理位置,同時也關注地方自身的一些商務設施的輔助。主要選擇以下幾個指標進行具體分析,即利用鄉鎮距離人民廣場的歐式距離(D-Center)反映本地與市中心的聯系緊密程度;選擇鄉鎮所在的區是否位于中心市區來表示地方的絕對位置,更進一步,將上海16個區按照張凡等(2010)的研究成果劃分為中心市區、近中心市區、近郊區以及遠郊區四類,按照鄉鎮所在區進行虛擬變量的設置。同時,數字經濟服務業企業對大型商城也有一定的依賴程度,選擇2018年大型商城的數量(Mall)進行表示。一方面大型商場可以為數字經濟服務業企業提供一定的生活和工作便利,另一方面也會提升區域的地價和房價,提升企業的運營成本。
產業發展基礎是企業區位選擇的重要影響因素,尤其是當地數字經濟服務業的發展基礎,會對后進企業的區位選擇產生較大的影響。這是因為地方化經濟效應的影響導致同類產業趨向于集聚在一起,這就會促使越來越多的同類產業進入本地,以獲得勞動力共享、技術溢出和中間投入等;同時,城市化經濟也會對企業的區位選擇產生影響,多樣化經濟效應的存在會提供多樣化的勞動力、服務和產業發展要素,吸引企業進行區位選擇。數字經濟服務業屬于技術密集型服務業,對先進生產性服務業的需求也比較高,需要先進生產性服務業為其提供必要的金融、商務服務和技術服務。因此,選擇相關性產業基礎、城市化經濟、先進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水平三個變量來刻畫產業基礎要素的影響。其中,相關性產業基礎(L-economy),主要用2013年各個鄉鎮數字經濟服務業企業數量表示;城市化經濟(U-economy),主要用2010年各鄉鎮的常住人口規模表示;先進服務業發展水平(S-APS),用2015年各個鄉鎮金融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以及科技服務業三個行業占總就業人數的比重來表示。
最后,數字經濟服務業的區位選擇也會受到本地經濟發展水平(Pgdp)的影響,因為這些產業屬于現代化經濟,更加傾向于在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進行區位選擇,由于鄉鎮尺度的數據缺乏,所以用各個區的人均GDP進行表示。
(二)模型結果分析
通過對模型進行檢驗,結果發現樣本方差遠大于樣本均值,而且 Alpha 的置信區間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過度分散”參數“Alpha=0”的原假設,即說明應該使用負二項回歸模型進行估計,同時 Vuong 統計量在[-1.96, 1.96]的區間范圍內,表明不適合使用零膨脹負二項回歸模型,因此本文采用標準負二項回歸模型進行結果的估計。表2展示了模型的回歸結果,通過分別將交通要素變量、區位因素變量、產業基礎變量、經濟基礎變量放入模型中,得到的結果如表2中的模型1、2、3、4所示,然后將所有變量均放入模型中,得到最終的模型5結果,可以發現大多數變量的估計結果都比較穩定。

表2 變量基本屬性與描述性統計

相關性產業發展基礎 L-economy利用第四次經濟普查數據,計算2013年上海各個鄉鎮數字經濟服務業企業的數量,作為測度各個鄉鎮單元的數字經濟服務業發展基礎的代理變量487 0 59.3產業基礎城市化經濟 U-economy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利用各個鄉鎮2010年的人口規模進行測度,取對數 12.95 3.56 11.26高級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基礎 S-APS利用2015年上海市人口抽樣調查數據,計算2015年上海各個區金融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以及科技服務業三個行業占總就業人數的比重,作為測度各個鄉鎮單元的高級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基礎的代理變量。0.2 0.03 0.11經濟基礎 區域經濟水平 Pgdp 利用各個區的人均GDP進行測度,取對數 12.76 10.84 11.66
交通要素變量的模型結果(模型1)和整個模型(模型5)的估計結果中,除了快速公路便利性變量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以外,另外兩個高速公路便捷性和地鐵交通便捷性變量均通過了顯著性水平檢驗。這也均證實了交通便利性會對數字經濟服務業企業的進入布局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說明區域的交通越便利,越會吸引數字經濟服務業企業在本地區進行區位選擇(蔣海兵等,2015)。具體而言,高速公路通過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高速公路的通過率越高,越會吸引數字經濟服務業企業在此進行區位選擇和布局。同時,地鐵站點變量結果顯著為正,表明地鐵站點數量的增加會促進數字經濟服務業企業在該區域進行區位選擇。已有研究均發現良好的交通條件會吸引企業進行區位選擇(公維民和張志斌等,2021;徐禎等,2021)。這是因為交通便利性是影響數字經濟服務業企業選址布局的重要因素,這些企業需要經常會見客戶,及時的與客戶、政府之間進行溝通與交流,因此對交通的便利性要求較高(羅雙雙等,2012)。
反映區位因素的變量在分模型(模型2)和整個模型(模型5)的估計結果相對穩定,除大型商城變量顯著為負之外,距離市中心的變量和地理位置變量均未能通過顯著性檢驗。其中,模型2發現近郊區的中心鎮級單元是數字經濟服務業企業的重要選擇區位目的地,這是因為很多數字經濟服務業企業位于浦東地區,尤其是浦東的張江是上海電子信息產業的發展重鎮,電子信息制造和服務業均比較發達,因此吸引了大量的數字經濟服務業企業進入。另外,反映區位因素的另一個變量大型商場會對數字經濟服務業企業的區位選擇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這與一些相關的研究結果有所不同(徐禎等,2021)。雖然大型商城的布局會對提升整個地區的服務設施配套水平,會為數字經濟服務業企業提供相對便利的生活服務設施,服務這些企業的公司員工。然而,一個不爭的事實便是大型商場的進入會顯著提升區域的用地成本,抬升本地的房價、地價,同時其也會通過市場競租對辦公樓的空間產生一定的擠壓作用,從而提升數字經濟服務業的辦公成本,從而不利于數字經濟服務業在該區域進行區位選擇。
從反映產業發展基礎變量的模型3和整個模型結果(模型5)來看,反映地方產業基礎的地方化經濟、城市化經濟以及配套產業三個變量的結果都顯著為正,表明區域的產業基礎會對數字經濟服務業企業的區位選擇產生顯著的正向作用。具體而言,反映本地化經濟的變量顯著為正,說明企業進行空間區位選擇時,會考慮本地原有的相關性產業基礎。由于本地化經濟的存在,可以提供專業化勞動力、技術溢出以及中間投入,進而會促進該產業發展水平的提升,進而吸引更多的專業化企業進入該地(羅雙雙,2012;林娟等2017)。同時,模型的估計結果展現出城市化經濟也會對數字經濟服務業企業的空間選擇產生正向的影響。這是因為城市化經濟效應的存在,結果會為數字經濟服務業的發展提供產業發展的市場、多樣化勞動力以及產業發展配套設施,進而改善區域的發展環境。尤其是對于數字經濟服務業企業而言,屬于現代化經濟中最具發展潛力的產業,需要較高的人口規模來提供較大的市場,進而吸引數字經濟企業的進入(李佳洺等,2018)。數字經濟服務業的發展需要相關的服務業進行配套,尤其是金融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以及科技服務業等高級生產性服務業,可以為數字經濟企業的發展提供金融支持、商務服務以及科技服務等,對數字經濟服務業的發展能夠提供必要的經濟和技術支持,從而吸引更多的數字經濟服務業進行區位選擇(方遠平等,2020)。最后,反映區域經濟發展基礎的人均GDP變量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
總結而言,模型估計結果展現出數字經濟服務業企業的空間區位選擇是區域交通條件、區位條件以及產業基礎三者綜合作用的結果,地理區位的便捷性和已有的專業化產業、相關性產業以及城市化經濟等均會對數字經濟服務業區位選擇產生正向的促進作用,而區位條件中的大型商城等競爭性產業的發展會對數字經濟服務業企業的區位選擇產生一定的不利作用。

表3 負二項回歸模型估計結果

注::括號內為標準誤,***,p < 0.01;**,p < 0.05;*,p < 0.1。
六、結論與對策
(一)主要結論
本文利用2008—2018年近10年的上海市數字經濟服務業企業的地理區位數據,從區級尺度和鄉鎮單元尺度分析了企業具體的空間分布特征與總體變化趨勢,然后利用負二項回歸模型方法,從交通要素、區位要素、產業要素以及經濟要素四個方面來實證檢驗了這4個要素對數字經濟服務業企業在空間區位選擇的具體影響,得到以下主要結論:
第一,上海數字經濟服務業主要以“中心—外圍”的趨勢逐漸演變為“多中心—外圍”狀空間分布特征。即雖然中心市區的數字經濟服務業集聚程度相對較高,但是一些近郊區的數字經濟服務業也處于不斷的發展當中,尤其是浦東新區的數字經濟服務業發展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其余如崇明、金山、青浦等區數字經濟服務業整體集聚水平相對較低。
第二,從鄉鎮尺度的空間分布變化中發現,數字經濟服務業企業的空間分布主要呈現出較強的局部空間集聚特征,并且呈現出多中心空間集聚趨勢。即從主要以浦東新區的張江科技園區、陸家嘴街道以及中心市區的外灘街道、徐家匯街道為主要集聚中心,逐漸演變為張江、臨港、五角場為核心的多中心空間分布格局,而中心市區的多數街道和鎮則不再具有集聚優勢,表明數字經濟服務業企業進一步向少量中心鎮或園區進行集聚。浦東新區的張江成為上海數字經濟服務業企業分布最集中的區域,成為整個市域范圍內的超級集聚中心。雖然中心市區的一些鎮域單元仍舊集聚了一些的數字經濟服務業企業,但是相比張江高科技園區而言,其區域集聚程度還相對較低。
第三,區域交通條件、區位條件以及產業基礎是影響數字經濟服務業企業的空間區位選擇的重要因素。其中,地理區位的便捷性,尤其是高速公路和地鐵交通的便利程度的提升,會顯著提升數字經濟服務業企業進行區位選擇。同時,數字經濟服務業企業在進行區位選擇時,地方的產業基礎對數字經濟服務業企業的選擇也具有重要的正向作用,尤其是本地已有的數字經濟發展基礎是數字經濟企業會對區位選擇產生重要影響,同時城市化經濟也會產生重要的正向影響。數字經濟服務業的發展離不開與之緊密配套的先進生產性服務業,對其空間布局的區位選擇會產生非常大的影響;最后,與以往研究不同的是,論文發現大型綜合商城會擠壓數字經濟服務業的發展,大型商場的進入會顯著提升區域的用地成本,抬升本地的房價、地價,同時其也會通過市場競租對辦公樓的空間產生一定的擠壓作用,大型購物商城的產業競爭會對數字經濟服務業企業的區位選擇產生一定的不利作用。
(二)主要建議
隨著上海不斷加快數字化轉型及數字經濟的發展,上海各個市區也都在推進本區數字經濟的發展,助力上海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同時,由于上海數字經濟服務業空間分布特征的多中心發展趨勢,需要在推動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同時,繼續促進上海各個區在數字經濟規模上有所提升,加快數字化多中心趨勢發展,主要建議如下:
1.強化數字經濟空間格局的多中心趨勢。隨著上海數字經濟服務業空間分布的多中心發展趨勢越發顯著,應該繼續強化以張江、臨港、五角場為核心的數字經濟強鎮的中心帶動作用,推動張江科技園和張江鎮與唐鎮、金橋鎮等鄰近鎮域單元實現聯動發展,提升地方核心引領水平;同時,推動臨港新城鎮與泥城鎮、書院鎮、萬祥鎮等區域內鄰近數字經濟強鎮的聯動發展,形成區域性組團發展集聚中心,提升該區域數字經濟的集聚發展水平與區域競爭力;推動五角場街道與周邊鄰近長海路街道、新江灣城街道、高境鎮等實現數字經濟發展的區域聯動發展,強化區域集聚中心地位。最后,進一步推動提籃橋街道、香花橋街道、南翔鎮等地方性強鎮數字經濟服務業的發展,形成地方性集聚小中心。
2.推動鄉鎮街道的配套發展。數字經濟服務業的發展離不開發達的交通基礎設施,尤其是高速公路和地鐵的便利性,對于數字經濟服務業的布局有重要的影響。因此,需要完善數字經濟強鎮的交通基礎配套設施,進一步提升這些地方的快速市內交通運輸能力,方便數字經濟服務業企業的對外聯系。同時,在產業配套上,強化先進生產性服務業為數字經濟發展的服務能力,促進先進生產性服務業與數字經濟服務業企業融合發展和協同發展,實現數字經濟服務業與先進生產性服務業之間的互動發展;最后,合理協調數字經濟服務業發展用地與大型購物商城用地之間的發展關系與配比關系,實現本區域數字經濟與其他產業之間的協調發展。
本文主要從企業區位選擇視角,利用上海數字經濟服務業企業的位置數據進行分析,由于缺乏連續企業的屬性數據,如從業人口、產值等,可能忽略了企業屬性特征影響下的數字經濟服務業空間格局,同時數字經濟是近年來上海提出的新的經濟發展動能,未來的研究需要將研究的時間序列放在更長的時間段內分析其空間分異特征與變化規律。同時,未來需要結合相關的數據分析與企業調研,進一步驗證數字經濟服務業企業在區位選擇中關注的核心要素,強化本研究的現實指導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