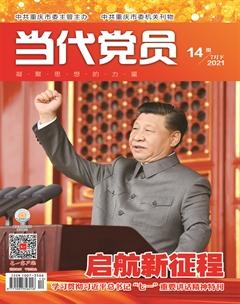“如今政策就是好,我要努力往前跑”
許幼飛
作為石柱土家族自治縣中益鄉華溪村黨支部書記,王祥生總是忙到“來無影去無蹤”,似乎這一刻不牢牢地抓住他,下一刻他就會因為村里的事情不見人影。
事實也的確如此。
在同王祥生交流的近3個小時里,他接了不下10通電話,還有很多人前來找他。
“王書記總是把村里的事放在第一位,就連休息時也在心里琢磨呢。”中益鄉黨委組織委員胥方貴稱。
傳承
6月16日,中益鄉華溪村。
青山綠水間,一棟棟漂亮的新房錯落有致,磚木混合結構搭配青瓦黃墻,盡顯地方特色;不少民居門前,鄉親們自種的花草果木在瓦缽和瓷盆里長勢喜人,一切顯得愜意而美好。
然而,在幾年前,華溪村還是十里八鄉都有名的窮山溝。
“那時候交通不便,去最近的鄉鎮需要翻過一座座大山。”作為土生土長的華溪村人,王祥生曾深切感受過這里的貧瘠,“村里有的人一輩子沒有趕過場,有的人一輩子住著漏雨房,有的人一輩子生了病只能靠硬扛。”
1978年,初中畢業的王祥生外出做起了生意。他最開心的是自己的第一單生意就賺了40元,“那時候,父母在家忙碌一整天,也掙不了什么錢”。
可就在生意蒸蒸日上之時,父親王宗武的一席話卻將王祥生勸回了華溪村。
“祥生,你如果回來把全村人都帶富了,那才是真本事。”時任華溪村黨支部書記的王宗武語重心長地說。眼見自己的年紀越來越大,村里的貧困卻不見好轉,王宗武很發愁,他把希望寄托到正值壯年的兒子身上。
起初,王祥生曾數次拒絕回鄉,但看著父親日漸佝僂的背影,他決定接過“接力棒”。2003年,為了兌現向父親許下的承諾,王祥生回到華溪村。
回村后,從修路到架橋,從帶領鄉親們養豬到解決鄰里間雞毛蒜皮的小事,王祥生總是竭盡全力、不計回報。
破局
“過去村里有什么?說白了就是洋芋、紅苕、包谷‘三大坨。”56歲的花仁叔對過去的生活記憶猶新。
三頂“帽子”——支柱產業“空白村”、集體經濟“空殼村”、老人兒童“留守村”,多年來壓得鄉親們喘不過氣。
“我一直想改變這種狀況,但那時候村里一是缺人,二是缺錢,什么都發展不起來。”王祥生很無奈。
2017年,在脫貧攻堅工作中,中益鄉被精準識別為全市深度貧困鄉。
此刻的王祥生除了感覺責任重大外,他還敏銳地意識到“改變華溪村的機會來了”。
為了做好發展規劃,王祥生同駐村工作隊的隊員們走遍華溪村的每個角落;為了做好產業布局,他常利用晚上休息的時間思考謀劃。
2017年12月,華溪村成為全市首批38個“三變”改革試點村之一。
借著這股東風,王祥生建立起企業、村集體經濟組織、村民“三方共贏”的利益聯結機制。在機制的作用下,沉睡的資源被慢慢喚醒,空中有蜂飛、地上飄果香、土里藏黃精。就這樣,一張立體農業布局的藍圖,在華溪村逐漸變為現實。
這股東風不僅給鄉親們指明了致富路,還讓在外的游子看到了家鄉的發展希望,紛紛返鄉創業。
花仁叔常年在外務工的女兒女婿回到村里,和她一起將自家房屋改造后,辦起了農家樂。
“現在一個月的收入是以前的三四倍,一家人還能團團圓圓的。”花仁叔很是滿意。
2019年,華溪村戶均增收4000余元,實現了整村脫貧。2020年,村集體經濟收入突破200萬元。
傾情
陳朋曾是華溪村遠近聞名的“酒鬼”,因為嗜酒成性,一家人的生活貧困潦倒。
“那時,陳朋一天到晚醉醺醺的。”王祥生回憶道,“跟他說話總是一股酒味撲面而來。”
2016年,陳朋一家被確認為建檔立卡貧困戶。
即使這樣,陳朋還是沒有醒悟,每日抱著酒壺不肯撒手,就連村里送的“脫貧豬”都被他賣了換酒喝。
這樣的行為不僅惹惱了妻子譚明蘭,也讓陳朋自己成為王祥生的重點關注對象。王祥生開始三天兩頭上門給他做思想工作。
“現在政策這么好,這個家還得靠你撐起來。”
“老母親還要靠你養老,你要給兩個娃作表率。”
……
在王祥生的不斷努力下,陳朋的思想得到了很大轉變。他將豬又贖了回來,悉心飼養。后來,在王祥生的帶動下,他還嘗試種了兩畝辣椒。
“那一年,陳朋的辣椒賣了8000多元,我從他的臉上終于看到了笑容。”王祥生說。
這8000多元的收益徹底點亮了陳朋的希望,慢慢地,村里人發現陳朋變了——他戒了酒,還流轉了5畝中藥材地做管護。
2020年,陳朋家年收入超過5萬元,日子越過越紅火。
“他現在可是村民學習的標桿呢。”王祥生很欣慰,“除了新建、改造硬件設施,我們還要激發鄉親們的內生動力,不讓任何一個人在小康路上掉隊。大家共同努力,才能讓華溪村變得更好。”
付出
“讓華溪村變得更好”成了王祥生的執念,也讓他在家庭面前顯得有幾分不近人情。
王祥生和妻子相處的時間,遠低于他撲在工作上的時間。有段時間,兩個兒子只有在晚上才能見到風塵仆仆歸來的父親,就連節假日也不例外。
“節假日正是我最忙碌的時候。其他人可以休息,但事情總要解決。”王祥生也不惱,在華溪村工作近20年的時間里,他早已習慣這種工作強度。但在他心底還是有著一份深深的愧疚——那是對病危住院,去世前自己都未曾陪伴過的老父親。
2018年6月初,王宗武病重,住進了縣人民醫院。
當時正值華溪村農房改造,王祥生實在脫不了身。不得已,他聘請了專職護工照顧父親,匆忙交代兩句就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沒承想,這一走竟是永別。
即便如此,治喪期間,王祥生也未曾休息半天。他說:“父親的喪事,有我家屬打主力。村里事情多,工作不能緩。”于是,他晚上為父親守夜,白天到村里工作,一天都沒落下。
也正是這份忘我的付出,換來了華溪村今日的巨變。
一天傍晚,天空還飄著細雨。看著嶄新的華溪村,王祥生頓感心潮澎湃。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他快步朝父親墓地走去。
在父親的墓碑前,王祥生蹲下來一邊用手輕輕擦拭著父親的名字,一邊說:“爸爸,這幾年華溪村的變化可以稱得上是翻天覆地。您要是健在,看到這樣的變化一定高興得不得了。現在政策好,我更要努力向前跑。”說話間,他的眼里已經噙滿淚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