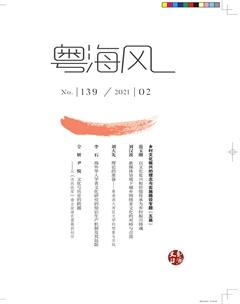生存,還是死亡
曹祎娜
電影的發行機制,是一個隨電影技術不斷發展變化的過程。直到今天,這個過程可以說還在不斷地發展和調適當中。總體而言,在過去120多年的時間進程中,電影的發行方式和傳播方式基本上都是以傳播介質——銀幕為核心的銀幕中心制。可以說,銀幕在哪里,電影就在哪里。銀幕在哪里?這個問題的答案一直漂浮不定。作為當代觀眾,我們理所當然地認為銀幕就在電影院里——我們會不假思索地把電影和電影院聯系起來,就好像提到黃金,第一反應就是將它作為貨幣。其實,檢索電影史,就會發現電影和電影院的關系并非天生,而是電影技術發展到一定階段時才出現的依存關系。
電影自發明之初,再到登堂入室踏入劇院一樣的電影院,經過了將近30年的摸索。一般認為,直到1927年《爵士歌手》在首次使用光學音效之后,電影在影院的吸引力才算穩固建立[1]。此前,“早期電影”只是馬戲團棚子里用來招攬馬戲觀眾的玩意兒。當電影首次遷入影院時,影院往往要以音樂、歌舞、雜耍及其他各種現場表演的方式來支撐電影放映。有聲電影出現之后,這種“支持性表演”才退出舞臺,電影院成為專門放映電影的場所,至此,人們開始把電影和電影院相提并論。但電影院的地位并非固若金湯,它一直處在不斷被爭奪威脅的過程中,電影院和其背后的制片公司,一直在試圖通過技術革新,鞏固電影院對電影發行的壟斷位置,以票房收入獲取電影最大的商業價值。新技術的“攻”和電影院的“防”,這一臺對手戲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就拉鋸戰似的持續了70年。
2020年,肆虐全球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給全球經濟帶來了海嘯般的沖擊,旅游、娛樂、航空等行業相繼遭受重創,全球電影業同樣瀕臨絕境。在美國(截至3月16日),AMC宣布關閉全球所有的1000多家影院,已然面臨倒閉的境地[2]。在中國,據《經濟日報》等媒體報道,2020年第一季度就有5328家影視公司倒閉,2200家電影院關門[3]。疫情對電影業的沖擊可以說是電影自誕生之日至今120多年來最慘烈的一次。因為疫情,愛好電影的人在長達半年多的時間里無法進入影院,他們不得不選擇各種替代方式來觀影——這一變化在未來或許會牽動電影業,特別是發行放映環節的巨大變革,即電影“走出”電影院的革新。在討論這場可能的革新之前,我們先簡略地回顧一下院線電影在過去120多年里經歷過的數次危機和轉機。
一、技術:一直在為影院留住觀眾的
賽場上狂奔
電影的商業放映始于法國,穩步發展于美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國電影產量已經占到世界電影總產量的85%,占美國市場的98%。伴隨著美國電影公司的擴展和壟斷,電影行業逐漸出現了縱向一體化[4] 的結構變化。在這種機制下,像華納電影公司這種規模較小的競爭者,由于被排除在制片廠制度之外,最終做出了為電影增加聲音的一系列決策,通過聲音技術,確定了自己的競爭地位。聲音的加入,不僅豐富了電影的表現手段,也讓觀眾獲得了更好的觀影體驗,從而吸引更多的人走進影院,結果就是——影院的運營成本大幅下降,盈利能力空前加強,并強化了好萊塢對世界電影的掌控力。可以說,在電影中加入的這一新技術元素,促使電影業市場格局發生了轉變。
然而,一度向好的電影產業很快就遇到了巨大的挑戰,那就是——電視的出現。1953年,幾乎一半的美國家庭都擁有一臺電視機,美國的觀影人次也下降到1946年的一半。對此,電影產業采取了兩種策略應對電視帶來的威脅:一是資本慣常采用的策略,“如果我不能戰勝你,我就收購你”。于是,一些大型傳媒集團開始收購電視頻道和電視制作公司,并專門制作為電視播放的電視電影,從而開拓出一個嶄新的市場;另一個策略就是通過技術的突破來實現對電視的超越。也許是受先前有聲電影技術使電影市場實現爆發式增長的歷史先例的啟發,電影業界先后將一系列新技術帶入電影的制作與發行放映環節。這些技術包括:全景電影,寬銀幕電影,立體電影,香味電影,彩色電影,等等。直至21世紀,大量介入的CG技術一度造成了超級巨片的奇觀現象。所有這些技術的介入,就是電影業設法通過各種手段來鞏固影院放映的魅力,持續吸引電影觀眾到電影院觀影,并且讓觀眾相信只有在電影院才能欣賞到如此這般的電影奇觀。這類電影確實創造了奇幻的觀影體驗,使觀影樂趣超越了家庭錄像及其他娛樂形式。然而,電影的制作成本也隨之不斷攀升,而觀眾對所謂視覺奇觀的熱情卻開始減弱,技術革新創造了諸如《泰坦尼克號》《阿凡達》這樣的票房神話,但對大多數電影來說,在技術方面的巨資投入,未必能夠保證足夠的票房收入和市場影響力。
在這場用新技術捍衛影院魔力的馬拉松賽事上,電影院贏得非常不易。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電影業與電影院不斷地遭遇著各類競爭對手,黑白電視、彩色電視、錄像機(帶)到了20世紀90年代,在個人多媒體電腦全面普及后,DVD、電腦屏幕以及家庭影院再度給影院放映帶來重創。隨著網絡時代和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到來,智能手機又全面介入人類生活,手機屏幕、平板電腦又成為電影放映的界面。近年來,VR眼鏡和AR眼鏡技術不斷提高,它們結合高速移動互聯網成為新型電影播映界面之后,就開始蠶食起影院的版圖。如果說電視、電腦和手機、平板電腦在和影院競爭過程中,的確沒法在畫面寬闊度、畫質明亮細膩、3D效果以及環繞音效等方面和影院競爭,但VR進入后,觀眾在那個虛擬的眼鏡里,確實可以看到和IMAX與巨幕不分軒輊的觀看效果。
由此可見,放映電影的媒介載體隨技術的發展也不斷地遷移和變化著,今天,“銀幕”已經不再固化于電影院了。電影的發行、放映與觀眾的欣賞、接受,這個需要在影院完成的環節以及影院本身,不僅持續遭遇著技術的嚴峻挑戰,更是在2020年全球性新冠疫情的重創下,面臨即將被推下懸崖的命運。如果電影只能依賴影院放映才能存在,那接下來,電影也將被終結。然而,電影會被終結嗎?顯然不會。根據調查,疫情期間,由于人們長期隔離在封閉的家中,人們看電影不是少了,而是比平時看得更多了。以國內為例,《人民日報》援引騰訊視頻,愛奇藝和阿里巴巴優酷網的數據,僅在2020年第一季度,就有14部電影的網絡票房收入超過1000萬元,而2019年全年只有15部互聯網電影實現了這一目標。這說明觀眾正大面積向線上轉移,以網絡觀看作為替代模式。電影和電影院這種依存關系,被疫情再一次打破。
疫情后,影院是否能夠繼續生存下去,成了所有熱愛電影、關心電影的人們關切的問題。目前,有兩種相反的觀點并存:一種觀點認為,不管疫情是否結束,電影院的這種發行放映模式,都將必然走向衰落和式微,就像那些曾經引發萬人空巷,今天卻只能走向小眾,勉強存在的話劇院、歌劇院一樣,未來的影院也將成為一種小眾的電影消費模式。除一些具備視覺奇觀或加入了特別體驗的電影才需要在電影院特別體驗之外,其他大量的電影消費將通過網絡轉移到其他介質或其他空間形態上來。持相反觀點的人則堅信,只要電影還存在,電影院就會永遠存在,而且會永遠像現在這樣紅火。這種堅信,來自那些對影院觀影習慣具有執念的觀眾,他們對傳統電影有著深厚的情感、對影院觀影方式極度迷戀。他們認為,在電影院的觀影體驗是其他任何媒介形式無法提供的。與此同時,他們還特別強調,電影院具有其他任何媒介形式所不具備的特殊的社交功能。人們走進影院看電影,從某種意義上講,不僅是一種特殊情調的現代生活方式,當全球數以百萬人在同一時間走入影院觀看一部電影時,還會有一種特殊的儀式感,這是用電腦、電視、VR觀看無法營造的。可以說,他們已經將電影院和某種生活方式連接在一起,并且單方面地希望電影院能永遠地存在和延續下去。
但是,電影院能夠延續下去嗎?生存還是死亡,這是一個需要考慮的問題。如果我們承認以下事實的話,就會再次深刻理解新技術的沖擊力是多么的巨大:電燈替代了蠟燭,火車、汽車、飛機替代了馬車,數字影像技術替代了膠片,手機打敗了有線電話,互聯網幾乎消滅了電報和傳真,并且進一步攻城掠地般地繼續蠶食著報紙、雜志、電視臺。雖然“蠟燭”類前輩的身影還在,但充滿技術力量的后者不可否認地大幅度取代了它們。技術既能為電影和電影院提供生命力,也能破壞和毀滅這兩者的存在,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對此,我們必須坦然面對。
二、商業:影院的經濟屬性反噬電影藝術的發展
在回顧電影發行和放映的歷史之后,我們看到,最早的電影放映是在馬戲團的大棚里完成的,是正式演出馬戲之前,一個用來招攬觀眾的前置娛樂。當時的電影無論從文化、藝術甚至經濟方面,都還沒有完全形成自己獨立的形態和主體。在經過一系列的“技術”和“藝術”的努力之后,電影才有了更加豐富的表現力和美學形式,形成了今天的電影形態和產業格局。如今,電影已經不再是一種簡單的娛樂產品與文化商品,它是用視聽語言書寫的一種文化,是人類多元文化格局下的一種文化現象。
如果我們把鏡頭拉開來看的話,電影的發行放映也不一定非得發生在專業的電影院里。專業電影院線存在的理由,其主要原因并非是電影藝術和電影文化本身的要求,而是經濟上的規模效益所需要的。一本書印刷量太少就會賠錢,一份報紙發行量太少也會賠錢,而一部電影,作為一個文化產品的時候,其盈虧平衡也需要達到最低的觀眾數量。總的觀眾數量太少,制片方會賠錢;單一場次觀眾數量太少,影院會賠錢。在數字電影出現之前,電影的制作、發行和放映均通過拷貝,以及一系列專業的機器和專業的人員來完成,這一切都合計為相當高的運營成本。而一部影片拷貝的使用次數是有限的,在每一次的放映過程中,觀眾的數量決定了這個拷貝的價值實現,如何最大限度地將觀眾招攬在一起,就成了電影發行放映最關鍵的問題。在制作電影這一環,由于投入成本相當高,如果沒有足夠的發行放映市場,沒有足夠的觀眾,必然就會賠錢——這意味著,電影的再生產不可持續。
從影院的商業投資邏輯講,傳統的電影放映模式借鑒的是傳統的劇院模式,讓眾多的觀眾在同一時間聚集在同一空間,看同一場電影。這種模式是按照經濟學上的規模效應來制定的。電影院是由資本控制的一種商業形態,逐利是資本的天性,資本總是希望收益的最大化。因此,從20世紀第二個十年中期開始,美國的電影公司開始投入豪華宮殿般的影院建設,這就導致了電影只有最賣座的影片才能獲利。一些小規模、小成本的文藝片,根本不可能進入電影院系統與觀眾見面。今天,這種趨勢變得更加明顯:電影院成了大片、巨片逐鹿票房的主戰場;一些優秀的中小成本電影,甚至需要出品人下跪,才能在院線上與觀眾見面。從這個意義上講,影院系統已經異化為電影藝術創新的直接殺手,已經成為一種阻礙電影發展的落后機制。
從經濟上講,現行的電影院發行模式并非理想。以中國為例,雖然2019年國內院線總票房達到640多億元,但事實上,常年在電影院觀看電影的觀眾也就是那固定的1億多一點兒。14億人當中的另外十多億人,幾乎從來不進電影院。對于電影這種追求最大觀眾規模的產業而言,成了一個非常尷尬的現實。如何把其余十幾億人的視線拉到電影前面來呢?傳統的影院模式顯然是做不到。因為,一個人選擇到影院去看電影,需要在訂票、去影院的途中,以及等待影片放映等環節花費大量的時間及潛在的額外消費(諸如吃飯或者爆米花),在觀看的時候可能還要忍受鄰座觀眾的喧嚷和打擾……如果繼續使用傳統的電影院模式,另外的十幾億人永遠不會走進電影院消費,電影的市場規模也就永遠只能在一個天花板下反復的震蕩。從文化上講,影院模式還是一種基于傳統社會的中心主義,中心集權的一對多的大眾傳播媒介形式,它是反個性和反多元性的,是一種單向的文化傳播,與網絡社會中人和人之間的鏈接以點對點的網狀結構、離散結構格格不入;和網生一代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格格不入,而當下和未來的電影觀眾恰好是成長于網絡時代的年輕群體。
電影本質上是一種影像藝術,觀眾在觀看電影的時候,是通過觀看光影投射在銀幕上或者其他介質上形成的影像和聲音聯合創造的虛擬空間里面發生的事件,以及事件中的人物生命歷程、情感歷程從而獲得觀影體驗和審美愉悅。所以,我們看電影,看的是電影的影像,而不是看影院里的銀幕。影院的銀幕經歷了早期的幕布,后來的白墻,到后來的金屬幕等多種形式。無論是白墻還是金屬幕,其實質僅僅是一個反射光影的平面。影院中,空置狀態下的銀幕就像一張白紙,沒有任何內容,沒有故事,沒有情感,沒有個性,沒有任何美感。只有將影像投射在銀幕上的時候,一切才開始發生。在這個意義上講,電影并非先驗地、必然地和電影院連接在一起。電影和電影院的關系,只是一種技術和商業的權宜之計。在沒有更好的形式或手段可以替代之前,制片公司為了追求更大的經濟利益,會想盡一切辦法固化和強化這種聯系,將觀眾拉近影院并留在影院,這些手段包括但不限于將影院變得更加的多功能化(盈利模式多元化)——冷飲店、咖啡廳、書店、玩具店等和影院聚集在一起,都是為了豐富影院的消費場景,強化其觀影之外的各種附加功能。這些功能和電影本身不相干,但商家通過電影吸引了人流,賣出更多的爆米花、冰激淋、汽水、可樂、面包、玩具等快消品,獲取更多的商業銷售以及利潤。由于影院建設所需要的巨大投資和維持影院運行的巨大投入,需要快速回收資本,在當今的影院經營中,電影的票房收入和這些周邊消費品的收入早就平分秋色,甚至超過電影票的收入。如果電影本身不再是電影院的主要銷售收入,這似乎又回到了馬戲團大棚里用電影招攬更多觀眾買票看馬戲的原點?
三、線上數字影院:一種新的電影業態
除了前面提到的電影業人士在技術上不斷做出吸引觀眾進入影院的努力之外,面對電影從銀幕蔓延到各種電子顯示設備的范圍越來越寬,觀眾從銀幕前分流越來越嚴重的現實,電影院也通過技術手段和經營策略與新媒介爭奪觀眾,比如增加銀幕數量,增加影廳數量,實現銀幕的超大化,提高影院座椅的舒適度……這一切,看上去是一個電影業態在發展和進步,本質上卻是傳統的電影發行模式在和新技術爭奪觀眾。然而,從世界各國的票房收入來看,顯然都遭逢了瓶頸。以美國為例,它已經進入到某種天花板的狀態,年維持在500億到600億美元的水準已經多年循環不前。中國市場的電影票房收入在經歷了近10年的狂飆之后,從2017年起,增長曲線也已明顯放緩。
是看電影的觀眾人數下降了嗎?顯然不是。反觀網絡,就會發現看電影的絕對人數并沒有減少,反而是增加了。2019年6月,愛奇藝公布了其最新會員規模數據,截至6月22日凌晨5點13分,愛奇藝會員數量突破1億;同期,騰訊視頻的注冊用戶也突破了1個多億[5]。除幾家主流視頻網站之外,各個廣播電視網絡公司,在他們所開設的網絡院線里,也配備了大量的電影。觀眾只需要付一塊錢到五塊錢不等就可以看到一部好萊塢的大片。借助尺寸越來越大(65寸以上),畫質達到4K,音響還原效果越來越好的彩色電視,在20平方米空間里的觀影效果與影院相比,差別越來越小。上述多種觀影途徑新增加的電影觀眾,在國內,至少有4個億,是影院觀眾的4倍。他們看電影,但不進電影院。
線上數字院線的蓬勃發展和線下影院的艱苦維持,在今年疫情期間,矛盾更加突出,一些原本是為影院拍攝的電影,在疫情期間紛紛改為網絡發行,這對行業造成的長期沖擊遠比幾部電影的影響要大[6]。因為新片供應是線下影院最大的優勢,但這個優勢也正在流失。近期,網上流傳了這樣一段視頻:在海外市場已經翹首期盼了半年之久的《花木蘭》(迪士尼公司出品)因為疫情影響,放棄在院線上映,而將版權賣給了網絡放映平臺Netflix。一位法國影院老板獲知消息,憤怒地將已經布置好的宣傳物料砸毀,以表達心中的失望和不滿。有人評述這個視頻說:這段視頻像一個寓言,一個象征,是影院時代走向衰落的一個象征。
線下影院是否很快走向衰落,也許還不能簡單定論。但網絡院線對實體電影院線的沖擊,是電影經濟形態在新技術條件下的必然轉型,也是數字時代、網絡時代人們生活方式和電影文化的轉型。在傳統的電影院里面,觀眾只是觀眾;在互聯網時代,觀眾變成了用戶。作為觀眾的觀影人群,他們永遠是被動的,他們必須走幾公里的路,坐各種交通工具,到電影院去。而電影院放什么影片,是由影院來決定的,觀眾并沒有自主選擇權。但在網絡院線,電影變成了一種服務內容——觀眾變成了網絡用戶,而用戶是上帝。新技術帶來新經濟,新經濟滋生新業態。傳統影院和線上院線的動能轉換,這是自電影發明以來,電影文化領域發生的最大的一次格局轉換。
結語
追求自由,追求自我解放,是根植于人類靈魂和精神深處最本能的一種需求,是人類發展一切技術、經濟和社會的根本目標所在。電影從電影院走出,轉向網絡傳播,也可以看成是對人們渴求自由的呼應。這種自由包括,自由地選擇觀看電影的內容、觀看形式、在自己決定的時間和空間里觀看電影。網絡電影的傳播方式,順應著人們對自由的追求。展望未來的電影生態,或許可能會引發這樣一些新變化:院線大片的“窗口期”或會保留,但周期縮短,從影院到網絡平臺的時間差可能要減少;網絡觀影這種方式可能和影院觀影并行,更多缺少“視聽奇觀”的電影會直接選擇網絡播放,網絡付費點擊分成和影院票房共同構成影片收益的主回收渠道;“影院電影”則會更加注重視覺奇觀、視聽震撼效果。電影院也將由單純的“觀影”轉向視聽娛樂與美食、社交、親子等相結合的多重消費功能場所。
敘事,是人類文明存在、延續和發展的重要手段,也是人類自身的一種天然欲望,電影作為人類使用影像語言進行敘事的一種形態,將永遠伴隨著人類一直存在下去。但是,電影的傳播模式,將隨著技術的發展不斷更新迭代,數字技術和5G技術,將會對很多傳統行業造成顛覆性變革,它已經和電影發生了遭遇,和電影院這種經濟模式發生了接觸,它對影院電影或者說電影院線產生顛覆性的影響也是題中之義。無論是作為電影從業者,還是普通的電影觀眾,接納技術革命帶來的電影傳播形式的變化,并且擁抱這個變化,才是不二之選。
(作者單位:北京電影學院)
注釋:
[1] [澳] 格雷姆·特納 著:《電影作為社會實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1頁。
[2] https://www.91700.net.cn/remen/2875917.html。
[3] http://k.sina.com.cn/article_1810477860_6be9b32400100okn8.html?
[4] 20世紀20年代,以派拉蒙、福克斯等公司操持的擴張整合計劃使一家公司能夠同時制作、發行和放映自己的影片,以確保對產業的控制,這一行為被稱之為電影業的“縱向一體化”(Vertical Intergration)架構。
[5] 在美國,以Netflix、YouTube為基礎的網絡數字電影發行也在不斷發展。根據報道,Netflix公司2020年1月至3月付費用戶增加了1580萬,全球用戶總數超過1.82億。
[6] 電影《囧媽》原定檔于2020年春節期間在院線上映,在各大院線都已經做好全面安排之后,出品方單方面撕毀合約,以6億元的價格將版權賣給網絡公司,這是一個在院線需要18億元的票房才能夠獲得的收益。在海外市場,迪士尼公司出品的《花木蘭》最近也放棄了在院線上映的計劃,將版權賣給網絡放映平臺Netfl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