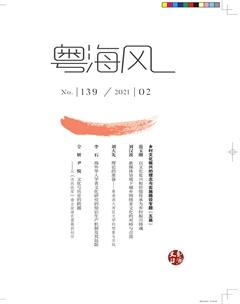懷念吳定宇
殷國明
我會經常想起吳定宇,這時他那仁厚天真的面龐就會浮現在我的眼前。他有時候喜歡抱胸而立,眼中充滿對于這個世界的敬畏和愛意。而對于我來說,這就是永恒。
結識吳定宇是一種緣分,甚至凝結著幾代學人的深情大義。我1984年研究生畢業,未得恩師錢谷融先生應許就跑到了暨南大學,先生頗為擔心,就把我托付給了兩位老友吳宏聰先生和陳則光先生。吳宏聰先生與錢先生交誼深厚,在此之前曾到上海探望錢先生,席間當面就提出要我到中山大學,錢先生也當即笑而未許,沒有想到我后來會自己去了暨南大學。為此吳宏聰先生多次說過此事。而陳則光先生與錢先生同是南京中央大學校友,在思想方面頗有默契。我到廣東后得到這兩位老先生多方面的照應,使我有可能在嶺南文壇有所作為。當時凡屬文學和學術活動,吳宏聰先生總是不會漏掉我,而且每次都為我站臺打氣:“讓小殷談談,他思想開放,總有新的見解。”自然,也有很多時候,兩位老先生不能不為我遮風擋雨,使我免于遭受一些無妄之災。記得有一年,兩位老先生去北京開會,提名我為中國現代文學會理事,結果被否定,兩位老先生都很不高興。吳宏聰先生曾多次用“莫名其妙”說到這件事,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影響。還發現,在那個時代幾位老先生都習慣用“莫名其妙”這個詞,來對應當時經常發生的莫名其妙的事。
其實,我已經記不清是何時認識吳定宇的,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從一開始我就被吳定宇對待老先生的態度打動了。他不僅人前事后畢恭畢敬,而且非常關心老先生的生活,不時來問安和看顧。而自此之后,我到暨南大學任教的生活有了很大變化,我經常會騎著單車,從天河崗頂越過海珠大橋到中山大學去。通常我會先到定宇家,然后一起去拜訪吳宏聰先生。因為吳先生年事較高,所以一般一起吃飯也可能不行,這要看情況而定。后來比較多的情況是,我們一起去看望黃修己老師,若方便還會去見見住在近旁的艾曉明,每次大家都是無話不談,親近暢快。黃修己先生是非常爽快之人,夫人更是大方心細,每次必定做東請客吃飯,最后大家一定盡興才歸。
我還記得,在一個風雨將即來臨的傍晚,他還帶我去看望了黃天驥教授,暢言臺上臺下戲劇性的時代變遷;而程文超教授舉家從美國回來,吳定宇則為其生活排憂解難,忙前忙后;不久,我們一起在文超家中聚會,如一家親朋互相囑托。后來,文超榮獲“德藝雙星”稱號,在廣東文壇風生水起,卻不幸得了喉癌,非常痛苦;又是定宇經常去看他,陪他散步,予以安慰。一次程文超實在苦痛難忍,竟高舉雙手朝天呼叫:“上帝啊!我犯了什么大罪,讓我遭受如此痛苦和厄運啊!”定宇每逢語此都黯然神傷,充滿人性厚誼。
這是一種別樣的美麗生活。
當然,作為定宇家的常客,很多時候我都會在定宇家吃飯。而自從我贊美定宇愛人戴月所燒的地道的四川麻辣豆腐之后,定宇總是讓愛人為我準備這道菜,實在讓我感動,因為他愛人工作也相當忙。晚飯后,我并不會急急回家,而是一起在中山大學校園散步。我們會走過中山堂,圍繞前面草地轉轉,然后繞到綠蔭深處,走到陳寅恪住過的地方。一路上,基本上都是定宇在說話,從天南海北到故情熱腸;從自己經歷過的種種遭遇,到學術界的種種人情世故,時而金剛怒目,時而幽默風生,時而拊掌自得,時而悲嘆惋惜,完全撇開了日常謙順、拘謹、少語、甚至有點遷迂的樣子,而表現出一種落拓無忌、盡善盡美的情懷。而我永遠難忘的,是他那開懷爽朗的大笑,那笑聲驚動了綠蔭中棲息的小鳥,會在樹叢之間引起一陣陣跳躍的回聲,無止無息,我想會永遠回蕩在中山大學夜色之中。
可以說。對我來說,定宇不僅是知己,而且一直是一種心靈支撐。
由于向往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的氣息,研究生畢業后我就去了廣東。一是因為自己當時年盛氣高,天性不羈,更由于修養薄淺,不知中國文化的山高水深;二是由于得到諸多廣東同仁的鼓勵支持,感動之余亦有得意忘形之時,所以在一些學術交流場合亦多有慷慨放言,以圖一時之快。而每次如有定宇在座,總會得到他的贊許。當時饒芃子教授曾稱我是一個騎著黑馬來的哥薩克,而定宇曾私下對我說:“聽你所講,我總是覺得我們倆心性相通,但是你有叛逆的狼性,而我更多的是羊性,膽小順從慣了。”我聽后很是感動。其實,定宇和我都是屬猴,他整整大我一輪,他的閱歷和見識都比我豐富、深層得多。
感動的不僅是定宇的真誠和理解,而且還有他的一以貫之的情深義重。
記得1989年北京大學與現代文學研究會召開了全國性的“紀念五四運動70周年學術討論會”,規模隆重。經過論文篩選,吳定宇和我作為廣東代表參會。我本來就是想去北京玩玩,見見朋友,沒想到提交的論文《“五四”功績與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受到了某種過度的關注。開完會我就急急忙忙回廣東了,然而,隨著時間推進,文壇傳出了一些對我不利的消息。這時,我突然發現朋友似乎一下子少了許多,人也感到孤獨了許多。而就在此時,定宇來了,請我去他家吃飯,還說戴月專門為你燒了麻辣豆腐。
這又是一次難忘的晚餐,完后又是一次令我感動的散步。我們談了很多,聊到后來我的眼眶濕了。還好,此時中大的月亮躲到云彩中去了,定宇看不到我的表情。
我相信定宇,他是一個不食言的真君子。他比我大一輪,他知道我表面堅強下面的內心的脆弱。其實,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也漸漸淡出學界,很少參加、甚至接到邀請不去參加學術會議。但是還時不時會聽到一些不知從何而來、為何而傳的、莫名其妙的說法。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作為我的好友,定宇總是直言對我進行維護和申言。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況且定宇!
我想,我們對于文學的信心,除了大自然賦予的靈秀之外,就是人本身所具有的魅力,它來自千千萬萬優美的人生,來自我們周圍很多像吳定宇這樣的人,他們使我們感到真誠和愛。
自20世紀90年代之后,定宇轉向了陳寅恪研究,我們見面交談也越來越多涉及這個話題。在這期間,定宇漸漸仿佛變了一個人,精神和氣色也與以前大有不同。在一段很長的時間內,他都沉浸在對于陳寅恪生平資料研讀之中,在用整個身心感受、接受和理解陳寅恪的人生及其選擇,也把自己深深帶入到對于中國整個學術史和文化史的反思之中。我每次去,他都會把近期有所發現的點點滴滴講給我聽,充滿醍醐灌頂的感悟和驚喜,不僅在學術議題和見解方面有諸多奪人之見,而且有一種喜獲精神救贖和棲息之地的喜悅和自信,表現出一種仁厚、博大的文化情懷。而我,作為定宇的朋友,也作為一個心靈的聆聽和陪伴者,也從這種心靈的歷史力量的觸動和感動中獲取了很多教益。
我一直記得那些日子。
我想,這對于定宇的學術生涯乃至生命歷程來說,也是一次巨大的觸動和轉變。定宇在郭沫若和巴金研究中都曾有所用心,亦有不小的成就,但是都不能與陳寅恪研究相提并論。接觸和發現陳寅恪,對于吳定宇來說,不僅完全打開了他的視野和心窗,而且融進了自己的靈魂,為自己的心靈找到了歸宿和棲息地,由此研究對于他不止于一種思想和學問的探尋,而且是一種世紀性的精神對話,與其說他從眾多資料中發現了陳寅恪,不如說他從陳寅恪身上發現了自己,他從此獲得了一個真正的知己,一掃其時代遭遇在其內心置放和淤積的種種思想余悸和意識障礙,使自己獲得了從未有過的解脫和解放,從此他的心靈也不再孤獨和惆悵,一個大寫的“我”開始在著述中凸顯出來。這一點,從1996年出版《學人魂:陳寅恪傳》(共284頁),到2014年推出《守望:陳寅恪往事》(共502頁),像一條不斷跳動的生命紅線飆升在字里行間,昭示著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雖歷經風雨,但是在跨越世紀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依然文氣相通,血脈相傳。
從某種程度上說,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之路是風雨兼程,那么,90年代則是一次再出發,是中國文心的一次再自覺;不過這次所“雕”不是“龍”,而是文人自己的靈魂、品相和精神。所以,盡管權位名位誘惑和拉走了很多曾經敢為天下先的作家和學者,但是鍛造了文化的精魂,留下了一批真正的、堅定不移的追尋者和守望者。
吳定宇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兩本書就貫穿著這種歷史追尋,而定宇也總是在出版后第一時間寄給我。不過,此時我已經重返上海華東師大教書,我每每想起定宇時,也不時翻閱一二,心想寫點什么,但是我卻一直未曾開筆,寫下只言片語。至今每次想想都會感到非常內疚,因為,我知道如果我能寫點什么,定宇一定會很高興的,盡管他從來沒有提出過此類的要求。
其實,自從我離開廣東,一種不吉祥的影子就一直追隨著我。其中一件事就是定宇的身體,他先后多次住院,最后做了換腎手術。這是一段令人心焦的日子,愛莫能助的我只能在異地默默祈禱。好在換腎手術比較成功,定宇的身體也慢慢有所康復。我回上海后,實際上很少有機會回廣東。那一年,我返回廣州,專門去探望了定宇全家。照舊,盡管定宇身體虛弱了許多,但是晚飯后我們還是一起在中大校園溜了一圈。那天的天氣不錯,一路上話題很多,而且,定宇不時會在一個地方停下來說:“你還記得嗎?這里過去還有幾棵樹,現在沒有了。”諸如此類。到了最后,話題又回到了陳寅恪,定宇這次又講起“文革”期間吳宓從四川趕來探望陳寅恪的事情,他說得投入,我聽得細膩。說到動情處,我們兩人都站住了,在月光下定宇潸然淚下,對我說:“你知道我為什么又說起這件事嗎?”我也淚目了,說:“知道。因為你和我。”
這是我最后一次到定宇家去,也是最后一次在中大一起散步。回到上海后,定宇和我偶爾也會通通電話,記得有一次他告訴我,他現在發現了新的散步去處,就是中大后面的珠江江畔,非常美,我們過去一直沒有去過。他還說,你下次來,我們一定一起去散步。
是啊,多美啊!水波蕩漾,微微江風吹拂,美麗的珠江游船彩燈輝煌,緩緩從江心駛過。我和定宇兄一起并肩而立,矚目遠望,共同面對和感受這一去不復返的歲月滔滔。
當然,還有戴翊,我們相互念念不忘的老友,此時他已經早走一步。
沒想到定宇突然走了。
定宇千古。
(作者單位: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