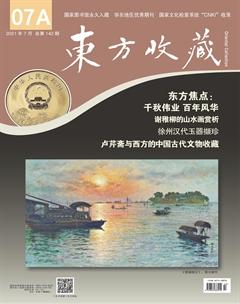承襲或流變:夏文彥《圖繪寶鑒》對中日鑒藏創作的影響
摘要:元人夏文彥的《圖繪寶鑒》成書后,便以其內容的豐富性,受到了當時的鑒藏界、文化界的歡迎且經久不衰。該書不僅對前朝畫史的體例內容有所繼承,同時也體現出夏文彥本人對書畫的認識水平以及元朝的繪畫美學思想。并且,畫史著錄的使用作為鑒藏活動的環節之一,其作用是不可小覷的。本文通過對夏文彥《圖繪寶鑒》傳播的時代因素、版本源流、內容傳承等方面進行分析,從而體現出其對中國與日本鑒藏創作的影響。
關鍵詞:夏文彥;中日交流;藝術收藏;《圖繪寶鑒》
中國的古代書畫有著十分悠久的歷史,作為我國極具特色的傳統文化,無論是名家技法的傳承欣賞亦或是史料方面的佐證研究,其各方面的價值可謂毋庸置疑。直到今天,我們仍然可以在博物館、美術館中觀賞到一大批優秀的前人翰墨。這些古代書畫作品之所以流傳至今,一方面,與古人的鑒藏活動有關。早在東漢末年,已有“漢武創置秘閣,以聚圖書”;再到隋煬帝時期,《隋書·經籍志一》中曰:“又聚魏已來古跡名畫,于殿后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古跡;西曰寶跡臺,藏古畫”;唐太宗李世民則“實行了非常優厚的書畫征集政策,所以法書名畫不斷進入內府”;宋徽宗朝所創的宣和內府,搜攬天下名跡;元文宗圖帖睦爾的奎章閣,所藏之物在元朝更是首屈一指;直到清代乾隆帝,其對書畫的收藏亦是如癡如醉。除了公家收藏,私人收藏家在歷代同樣比比皆是,如米芾、趙孟頫、項元汴、安岐等。正是他們對于書畫鑒藏的喜愛,才使得一部分古代書畫得以保存。另一方面,對于古代公私收藏起到記錄、引導作用的各類著錄、畫論,同樣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使收藏者們有史可證、有跡可循,是書畫作品流傳有序的部分證明。此類著錄、畫論,有南齊謝赫的《古畫品錄》、唐代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宋代郭熙的《林泉高致》、郭若虛的《圖畫見聞志》等,而在元代,一部繪畫史論的集大成之作,由夏文彥所整理編纂的《圖繪寶鑒》,我們可以借之以一窺著錄的基本內容,同時分析它在中日鑒藏方面的影響。
一、夏文彥與其編纂的《圖繪寶鑒》
夏文彥,生卒年不詳,“字士良,號蘭渚生,元末松江府華亭人,先祖為吳興人”,是元代末年的鑒藏家、史論家、畫家。《圖繪寶鑒》是夏文彥遍覽家藏又四處瀏覽文獻從而匯編而成的,該書以內容的豐富性,一經刊刻,便在當時受到了極大的歡迎,從十四世紀中期,流傳至今。相較于之前朝代的著錄、畫論書籍,該書在內容的收集與編纂上呈現出了更高程度上的“完整性”。夏文彥的《圖繪寶鑒》“一書共五卷,又補遺一卷”。陶宗儀在《南村輟耕錄》中認為《圖繪寶鑒》取材于《歷代名畫記》《圖畫見聞志》《畫繼》《續畫記》等書,并參照《宣和畫譜》《南渡七朝畫史》,以及齊、梁、魏、陳、唐、宋以來歷代的諸家畫錄、傳記、雜說等各種類型的文獻書籍再結合他個人的理解等編輯成書。書中的卷一部分,包括“六法三品、三病、六要、六長、制作楷模、古今優劣、粉本、賞鑒、裝褫書畫定式、敘歷代能畫人名”,該部分為畫論及與鑒賞相關的知識;而從卷二到卷五,夏文彥則列出了歷代畫史人物的傳記與基本資料,共記錄了約一千五百位歷朝歷代畫家,對這些畫家的姓名、籍貫、官職、所擅長之畫科、師承做了簡單介紹。
二、中國古代鑒藏史中的《圖繪寶鑒》
夏文彥所編纂的《圖繪寶鑒》,“于至正二十五年(1365)成書”。成書年代處于元朝末期,回溯元朝整體的鑒藏條件及風氣,元內府的收藏到了元文宗統治的天歷、至順年間,已十分可觀;而私家收藏方面,亦有如趙孟頫、喬簣成、柯九思這樣的大藏家。整體氛圍的營造,以及家境的優渥、家藏的傳承,使得夏文彥能夠接觸到一定的書畫作品。并且,他受父親的影響,也很愛好古玩和書畫,“蓄書萬卷外,古名流跡墨,舍金購之弗吝。于文人才士之圖寫,尤所珍重”。除此之外,夏文彥本人也具備繪畫的能力。各方面的因由,都對《圖繪寶鑒》的編纂起到了萌芽乃至推動的作用。到了明代,公私收藏的風氣不輸前朝;宮廷書畫的收藏,在歷經宣宗、憲宗、孝宗三朝后,“內府收藏數目之富,其盛況不亞于宋代宣和與紹興兩朝”,明內府收藏至此,呈現出鼎盛的局面。然而,“由于宮廷內庫管理上的紊亂,無賬目可稽,致使太監中盜竊者有之,以贗充真者有之,在明人的筆記中均有所涉及。隆慶(1567—1572)、萬歷(1573—1620)間,國庫空虛,以庋藏歷代名書畫折俸,于是從宮中源源散出之名跡流入私家之手,從而鑒藏之風因此抬頭,相應的鑒賞水平隨之提高,有后來居上之勢”。明代內府收藏的流失,從側面擴大了私家收藏的規模。伴隨著私家收藏風氣的炙盛,明代私人藏家們在挑選心儀的藏品之時,所面對無外乎書畫價值及真偽等問題,而判斷以上問題的標準或依據,除了私人收藏家的個人品位、鑒藏水平外,還需要相關的文獻、著錄在一定程度上進行佐證;如此的情況不僅使得歷代書畫論著在其中廣泛地運用,也催生出大量的品鑒著述,為《圖繪寶鑒》的后世傳播及應用提供了條件。以上是對《圖繪寶鑒》在中國古代鑒藏史中成書及流傳的時代特點所做的分析,而通過歷代各種版本的《圖繪寶鑒》則更能說明它流傳之久;除了至正二十五年的五卷本外,還有“至正二十六年(1366)刊本、借綠草堂刊本、康熙三年(1664)武林傳經堂刊《增廣圖繪寶鑒》本、《四庫全書》本、同治十三年(1874)復元刊本等”,增補頻次之高、版本之多、跨越年代之久,足見《圖繪寶鑒》的受歡迎程度。其次,從夏文彥《圖繪寶鑒》的體例以及內容取材來看,多引前朝畫史著錄,元人陶宗儀在《南村輟耕錄》中對此就有所提及。而根據近現代和當代學者的研究,還有北宋劉道醇的《圣朝名畫評》、元代湯后垕的《畫鑒》等。取材的程度、順序眾說紛紜,但可以肯定的是,《圖繪寶鑒》采眾家之長匯編而成,對歷代著錄的各方面有所繼承。同時《圖繪寶鑒》對古代文獻內容還起到了保護作用。相關研究提到“夏文彥所根據的是業已散失的《南渡七朝畫史》等著作。既然原作已不復存在,《圖繪寶鑒》所收錄保存下來的這部分資料也就很值得寶貴。特別是南宋部分,至今仍是我們研究南宋繪畫史必不可少的參考文獻”。明清時期,明代的韓昂就受人囑托而沿承《圖繪寶鑒》的體例編成《圖繪寶鑒續編》,增補了明代部分。清代的毛大倫、藍瑛、謝彬、馮仙湜,“以上四人,先后纂《增廣圖繪寶鑒》后三卷及補充”,將內容續編至清朝初期。不僅如此,《圖繪寶鑒》的內容廣為后世著錄所引用。明代僧人蓮儒編纂的《畫禪》,“全文篇幅少,約一千五百字左右,內容主要來自前代王世貞所輯《畫苑》、夏文彥《圖繪寶鑒》”;明代茅一相所作的《欣賞繪妙》書中多個部分均有引用,“再核茅氏書,實源自于《圖繪寶鑒》。按,《圖繪寶鑒》卷首有論畫九則,《欣賞繪妙》論畫十三則,多出夏氏《圖繪寶鑒》。畫家小傳,亦多就《圖繪寶鑒》直事鈔錄而略加損益”。書畫著錄作為鑒藏活動中的一環,向來為收藏家與書畫史家大量地使用、參考。夏文彥的《圖繪寶鑒》當然也不例外,其在中國古代鑒藏史中的影響力,可見一斑。
三、流入日本后的《圖繪寶鑒》所帶來的影響
《圖繪寶鑒》刊刻之后,在中國的鑒藏界廣為流傳。對我國古代的書畫鑒藏活動以及畫史著錄的編寫均有不俗的影響,它的傳播甚至對與我國隔海相望的日本產生了影響。關于《圖繪寶鑒》傳入日本的時間,從日本僧侶岐陽方秀參照《圖繪寶鑒》所寫的《中峰廣錄不二鈔》可知,“《中峰廣錄不二鈔》記應永二十七年(1420),因此得知當時在日本早已流傳了《圖繪寶鑒》,從而《圖繪寶鑒》傳到日本的時期可以追溯到更加早期”,故可判斷出,《圖繪寶鑒》在十五世紀早期乃至更早時期已傳入日本。而考究年代,15世紀的日本處于室町時代。日本進入室町時代與我國明朝的建立年代相差不遠。14世紀末期,日本國內動蕩分裂、南北朝權勢對立,無暇顧及與明朝的外交。同時伴隨著長久以來,倭寇對中國的騷擾問題,在“1387年(明洪武二十年,日本南朝元中四年),寧波衛指揮林賢借日兵助胡惟庸謀反事件被揭露,明太祖遂絕日本貿易,嚴海禁,譴將剿御倭寇”。直到足利義滿統一南北朝后,日本才逐漸想要緩和與明朝的關系,恢復邦交。在應永十一年,明日雙方締結了《永樂堪合貿易條約》。隨后的中日交流過程中,“自應永八年(1401)至天文十六年(1547)約150年的時間里,日本共派遣了19批遣明船。進行朝貢貿易的‘堪合船始發于應永十一年(1404),共17批、84艘船”。可以確定的是,“堪合貿易”的開始時間為十五世紀初,與上文所推斷的《圖繪寶鑒》傳入日本的大概時間相吻合,因此通過“堪合貿易”是《圖繪寶鑒》流入日本的時間節點之一;并且,伴隨著“堪合船”的流通、日本僧侶與商人赴華,更是為《圖繪寶鑒》在日本的傳播創造了條件。《圖繪寶鑒》傳入日本后,其受歡迎程度不亞于中國,“在鐮倉·室町時代(從13世紀到16世紀)的日本被認為理解中國繪畫的基本資料。這些從中國來的早期版本,在日本被認為是一種貴重品。到17世紀初的江戶時代前期,開始出版五冊本之后,又從京都的吉野屋權兵衛出版三冊本,在承應元年(1652)又從同一原版出版三冊本。寬政年間(1789—1801)又被大阪河內屋喜兵衛出版。從以上的事實可以證明它在日本非常流行”。除了在日本長時間地出版及再版,《圖繪寶鑒》還影響了一批日本美術文獻的寫作。如室町時代的《君臺觀左右帳記》,該書由足利義政時期的同朋眾能阿彌、藝阿彌以及相阿彌共同編寫。“平凡社《大百科事典》在解釋《君臺觀左右帳記》此書時,也有‘畫家傳記受夏文彥《圖繪寶鑒》影響一說,經過對兩書內容的對照,發現相似度很高,有理由相信《圖繪寶鑒》與《君臺觀左右帳記》這兩個文本之間確實有著影響關系”。日本學者近藤秀實同樣認為“室町時代為將軍府鑒定書畫的能阿彌和相阿彌所編的有關中國繪畫和工藝品的《君臺觀左右帳記》中就有參照《圖繪寶鑒》的痕跡。”不僅如此,其他美術文獻亦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圖繪寶鑒》的影響,“林守篤《畫筌》[正德二年(1712)自序,享保六年(1721)刊]是狩野派的畫學啟蒙書,其中,《圖繪寶鑒》被列舉為引用書。從桑山玉洲《繪事鄙言》[寬政十一年(1799)刊]、安西云煙《近世名家書畫談》[嘉永五年(1852)刊]、森島長志《槃礴脞話》開始,江戶時代的日本畫論頻繁地引用《圖繪寶鑒》,另外現在發行的美術辭典也多引用《圖繪寶鑒》的記事。”可見,《圖繪寶鑒》作為“媒介”,將其所繼承、引用的歷代畫史著錄的內容在日本再一次實現了文化的承續。除此之外,《圖繪寶鑒》還對室町時代中國繪畫的收藏,起到了某種程度上的引導作用。學者石守謙在他的著作《移動的桃花源》中對這一時期的中日書畫交易關系這樣寫道“當這些來華日人開始在寧波、杭州或北京等城市中尋找‘高級(相對于寺院中儀式所需的宗教繪畫而言)的繪畫作品時,他們也進入了當地的藝術市場運作之中。面對各種作品/商品充斥的這個藝術市場,買賣雙方都需要有一些輔助工具讓交易能夠盡快地在‘高級品的共識基礎上進行,對于來自外國的買方而言,更有如此需求。《圖繪寶鑒》應該就是其中的重要工具。它一方面是賣方向那些外國買家介紹作者、提高價值感的依據,另一方面也是日本買方在交易中認識、選擇作者,判斷作品價值,甚至是在赴華之前接受委托,在中國市場中尋找收藏作品之憑借。如果說《圖繪寶鑒》在日本僧侶/商人在中國購買高級繪畫作品的交易行為中,為雙方扮演一個‘指南式的中介角色,可說一點也不為過。”除了在收藏趣味的方面,《圖繪寶鑒》亦對日本繪畫的創作具有一定的影響,如室町時代的水墨山水畫創作以及畫家雪舟等楊的風格取材等,石守謙書中對此也有過相關的研究。由此可見,《圖繪寶鑒》傳入日本后,同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四、總結
通過上文的分析,夏文彥的《圖繪寶鑒》對中國與日本的鑒藏創作方面的確起到了一定的影響。對中國古代的鑒藏活動,特別是用以佐證書畫作品真偽及來源的畫史著錄而言,《圖繪寶鑒》有著承前啟后的作用;所謂承前,即《圖繪寶鑒》對前朝畫史文獻如《歷代名畫記》《宣和畫譜》等進行取材,并在體例、內容方面有所繼承,體現出文化的傳承與發展。除此之外,對于一些現已失傳的文獻書籍,《圖繪寶鑒》對其內容的引用同時,還起到了保護的作用。而所謂啟后,如明代韓昂在之前的基礎上所增補出的《圖繪寶鑒續編》以及其他一些明清時期的書畫著錄書籍對《圖繪寶鑒》不同程度上的借鑒,體現出的則是《圖繪寶鑒》對后世書畫論著的編寫起到的啟發作用。而對日本而言,它的影響不僅僅表現在對當時日本收藏中國繪畫的方向引導,并且,《圖繪寶鑒》作為一種“載體”將其所繼承、引用的中國傳統畫史內容在日本再一次實現了文化的承續,指導著一大批日本美術文獻的寫作;不僅如此,室町時代日本的水墨山水畫的創作風格取向,同樣與《圖繪寶鑒》不無關系。
在《圖繪寶鑒》的自序中,夏文彥寫道“僕性鄙僻,六藝之外,他無所好,獨嘗嗜畫,遇所適,輒終日諦玩,殆忘寢食。”可知,正是出于對書畫如此的喜好與偏愛,甚至到達一種上癮的地步,夏文彥才能有如此的動力與毅力將此書編纂完成。并且,具備這樣的精神所作成的書,絕非常人所及。盡管此書存在著如剽奪之嫌、畫家時代編次混亂或內容失實等問題,但這并不能扼殺《圖繪寶鑒》在一定程度上對中國古代鑒藏以及中日文化交流上所作出的貢獻。
(作者簡介:孫啟,上海戲劇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古代繪畫史、中日美術交流)
參考文獻
1. 楊仁愷《中國書畫》[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P129。
2.元代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一八》[M],中華書局,1958:P220。
3.陳高華《夏文彥和<圖繪寶鑒>》[J],《美術研究》,1981(04):P80-82+75。
4.楊仁愷《中國書畫鑒定學稿》[M],遼海出版社,2000:P24。
5.謝巍《中國畫學著作考錄》[M],上海書畫出版社,1998:P263。
6.耿明松《明代繪畫專史研究》[J],《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美術與設計)》,2018(02):P13-16+209。
7.張同標《明末書畫文獻著述得失的個案研究——以<欣賞繪妙>與<艷雪齋畫苑>為例》[J],《中國美術研究》,2012(03):P17-28。
8.石冢美津子《從君臺觀左右帳記看宋代花鳥畫與日本狩野派》[D],中國美術學院,2008。
9.吳廷璆《日本史》[M],南開大學出版社,1994:P165。
10.馮瑋《日本通史》[M],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2:P252。
11.近藤秀實《日本的中國繪畫史研究與俞劍華》[J],《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美術與設計版)》,2009(02):P28-29+161。
12.壽舒舒《日本畫論<君臺觀左右帳記>中唐代畫家之考察研究》[J],《開封教育學院學報》,2018,38(09):P270-272+279。
13.近藤秀實、何慶先《<圖繪寶鑒>校刊與研究》[M],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P308。
14.石守謙《移動的桃花源》[M],三聯書店,2016:P190。
15.元代夏文彥《圖繪寶鑒》[M],商務印書館,1930: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