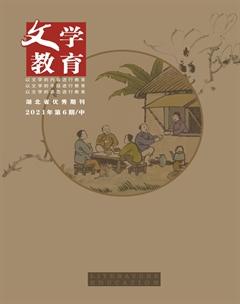鄭敏《金黃的稻束》的藝術(shù)呈現(xiàn)
李潔
內(nèi)容摘要:鄭敏《金黃的稻束》既是一曲人生沉潛之婉曲,也是一首大地之頌歌。“金黃的稻束”是個(gè)人生命的象征之物,象征站在曠野之中的思想者,詩(shī)人鄭敏借以“金黃的稻束”呈現(xiàn)其對(duì)個(gè)人生命體驗(yàn)與社會(huì)歷史哲思的情感表達(dá)。《金黃的稻束》中情景交融,其思想內(nèi)容與藝術(shù)形式相互融合,思想內(nèi)容賦予了藝術(shù)形式生命力與情感性,藝術(shù)形式為思想內(nèi)容的表現(xiàn)提供了審美空間與情感空間。
關(guān)鍵詞:《金黃的稻束》 生命感覺 歷史哲思 藝術(shù)呈現(xiàn)
鄭敏以“金黃的稻束”作為詩(shī)的題目,“金黃的稻束”具有多重的象征意蘊(yùn)。單純從題目著眼,“稻束”的“金黃”色彩表明了時(shí)節(jié),為整首詩(shī)的基本情感提供了一個(gè)大致大方向。在普通人眼里,“稻束”只不過是豐收之后脫落谷穗的一束束稻草,它們被擱放在田野里,等待被焚燒的命運(yùn)。而在詩(shī)人眼里,它們是富有生命力的思想者,即便是靜默地佇立著,也能彰顯出其生命里的深邃。孫玉石是這樣評(píng)價(jià)鄭敏的,“她總是把自己生命的體驗(yàn)和哲理沉思,有機(jī)而巧妙地滲進(jìn)各種自然或生活的物象,這些物象不是被重新發(fā)現(xiàn),就是被藝術(shù)變形,賦予了詩(shī)人富于個(gè)性的思考和情感,成為一個(gè)有深刻蘊(yùn)涵的藝術(shù)本體,自然以及詩(shī)人筆下的客觀物,與詩(shī)人的哲理思考融成一個(gè)美的結(jié)晶體了。”[1]詩(shī)人是以詩(shī)性、哲理的眼光看世界,在鄭敏想象的世界里,“金黃的稻束”不是等待被處理的事物,而是具有生命、具有情感的思想者。在“金黃的稻束”的思想里可窺見的不僅是個(gè)人生命的感覺,更是社會(huì)歷史哲思的呈現(xiàn)。
《金黃的稻束》整體上呈現(xiàn)出優(yōu)美簡(jiǎn)約的語(yǔ)言風(fēng)格,詩(shī)人鄭敏不刻意追求辭藻上的華麗,不刻意渲染濃厚的氛圍以達(dá)到感化讀者的目的,而是以一種平靜溫和的態(tài)度訴說(shuō)著一個(gè)關(guān)于生命的故事。詩(shī)人鄭敏以“金黃的稻束”為主要抒情對(duì)象,將生命力全部?jī)A注于“金黃的稻束”身上,“金黃的稻束”象征著個(gè)人生命,而在這個(gè)人生命的背后彰顯的是社會(huì)歷史的哲思。“金黃的稻束站在/割過的秋天的田里”,“秋天”是一個(gè)適合生命沉思的季節(jié),在果實(shí)豐收與生命凋零的過程中進(jìn)行自我生命的沉潛與反思。單一個(gè)“站”字將“金黃的稻束”的生命力凸顯得淋漓盡致,試想一下,在喜悅與凄涼并存的季節(jié),站在秋風(fēng)微起的曠野之中,“金黃的稻束”將會(huì)呈現(xiàn)出何種姿態(tài)?“我想起無(wú)數(shù)個(gè)疲倦的母親,/黃昏的路上我看見了那皺了的美麗的臉”,“金黃的稻束”喚起了“我”對(duì)母親的記憶,“金黃的稻束”與“母親”在某個(gè)情感層面上是相通的,“金黃的稻束”在最好的時(shí)光里貢獻(xiàn)了它全部的果實(shí),“母親”在最美的年華里奉獻(xiàn)了她所有的愛。時(shí)間的刻痕在兩者身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記,此處,詩(shī)人將“母親”身上濃厚的情感傾注于“金黃的稻束”身上,其所表達(dá)的不僅是對(duì)時(shí)光易逝的感嘆,更重要的是為了傳遞對(duì)生命之美麗與生命之堅(jiān)忍的贊頌。“黃昏”本意指生命消逝之時(shí),詩(shī)中描寫“我”走在“黃昏的路上”,“黃昏”的色彩與“金黃”交相輝映,營(yíng)造了出優(yōu)美、朦朧的意境,才能使“那皺了的美麗的臉”有詩(shī)性的呈現(xiàn)。“收獲日的滿月在/高聳的樹巔上,/暮色里,遠(yuǎn)山/圍著我們的心邊”,詩(shī)人心中的月亮不是清冷憂傷的代表,而是盛滿了陽(yáng)光的溫暖的滿月,滿月溫暖的光亮從高處灑向大地,與暮色融合在著天地之間。此處詩(shī)人重在以一種遙遠(yuǎn)的姿態(tài)在遼闊的空間里描繪出一幅情感充盈、意境悠遠(yuǎn)的水墨畫。“圍著”是一種保護(hù)的姿態(tài),在溫暖的空間里,“我們”的心靈是被守護(hù)著的。“沒有一個(gè)雕像能比這更靜默。”在詩(shī)人看來(lái)羅丹的雕塑作品《思想者》也比不上這“金黃的稻束”的“靜默”,羅丹的雕塑作品《思想者》有低頭頷首、托頜沉思的動(dòng)作,“金黃的稻束”只有靜默之中的更靜默,在這“靜默”之中凝聚著無(wú)限的生命力量。
“我們需要詩(shī)歌來(lái)與科學(xué)互補(bǔ),因?yàn)樵?shī)歌能使情感、并通過情感能使態(tài)度得到日常的宣泄;科學(xué)企圖壓制情感和態(tài)度,以便不受干擾地描繪客觀世界。”[2]與科學(xué)家對(duì)待客觀的世界不同,詩(shī)人鄭敏通過詩(shī)歌來(lái)抒發(fā)自我內(nèi)心的情感、表現(xiàn)自己的人生態(tài)度。詩(shī)人既在“金黃的稻束”的“靜默”中探尋個(gè)人生命的真實(shí)與美好,也在這“靜默”中挖掘關(guān)于社會(huì)歷史的哲理問題。“肩荷著那偉大的疲倦,你們/在這伸向遠(yuǎn)遠(yuǎn)的一片/秋天的田里低首沉思”,鄭敏以“偉大”來(lái)修飾“疲倦”,這與前面“我想起無(wú)數(shù)個(gè)疲倦的母親”中的“疲倦”相呼應(yīng),“疲倦”背后的真相是“金黃的稻束”以自身的軀體為這靜謐的秋天積累喜悅。完成自己一生的使命后,“金黃的稻束”在遼闊的曠野里與秋天進(jìn)行無(wú)聲的對(duì)話,這場(chǎng)無(wú)聲的對(duì)話是“金黃的稻束”與自我內(nèi)在心靈的溝通,是在靜默之中釋放靈魂的前奏。“秋天”是詩(shī)人筆下浩瀚無(wú)垠的宇宙的代名詞,“我”“我們”以及“金黃的稻束”“你們”與變幻莫測(cè)的宇宙進(jìn)行一場(chǎng)無(wú)聲的對(duì)話,對(duì)話的結(jié)果是對(duì)自我內(nèi)心的探尋與對(duì)社會(huì)歷史的重新審視。“靜默。靜默。歷史也只不是/腳下一條流去的小河”,在面對(duì)深不可測(cè)的宇宙及自我至純的內(nèi)心之時(shí),社會(huì)歷史的全部也只不過是曾經(jīng)流逝過的歲月而已,它隨著時(shí)間的腳步或許在記憶中消失不見,或許被塵封在記憶的某個(gè)角落。在靜默的沉思之中,不必困擾于社會(huì)歷史中的浮華世事,只需以最真摯最純潔態(tài)度進(jìn)行自我生命的凝神觀照。“而你們,站在那兒,/將成了人類的一個(gè)思想。”詩(shī)人將“金黃的稻束”比喻為“人類的一個(gè)思想”,一個(gè)什么樣思想?一個(gè)關(guān)于人類生命感覺的思想,一個(gè)關(guān)于社會(huì)歷史的哲學(xué)思想。在詩(shī)篇結(jié)尾,“金黃的稻束”是站在秋天的曠野之中的思想者,它是個(gè)人生命的思想者,它是社會(huì)歷史的思想者,它的話語(yǔ)權(quán)是被放置于整個(gè)浩瀚的宇宙之中來(lái)評(píng)判的。
《金黃的稻束》在思想內(nèi)容與藝術(shù)形式上達(dá)到了凝合的高度,詩(shī)作中的藝術(shù)形式不單單只具有審美的效果,更是將詩(shī)中思想內(nèi)蘊(yùn)的呈現(xiàn)推向了更高的藝術(shù)層次。“在理解想象的隱喻的時(shí)候,常要求我們考慮的不是B(喻體vehicle)如何說(shuō)明A(喻旨tenor),而是當(dāng)兩者被放在一起相互對(duì)照、相互說(shuō)明時(shí)能產(chǎn)生什么意義。”[3]《金黃的稻束》整首詩(shī)的表現(xiàn)方式為隱喻與象征,其所表現(xiàn)出的隱喻意義與象征意義是詩(shī)人思想情感的局部呈現(xiàn),在這局部的背后是整體意蘊(yùn)的表達(dá)。“金黃的稻束”是整首詩(shī)的主要象征物,它是承載著思想與生命的思想者,它的“疲倦”是個(gè)人生命感覺的體驗(yàn),它的“沉思”是社會(huì)歷史哲思的表現(xiàn)。“秋天”在詩(shī)中不僅是季節(jié)的簡(jiǎn)單呈現(xiàn),其指向的也是廣袤無(wú)垠的空間,有宇宙之深意在其中。“意象是一個(gè)標(biāo)示藝術(shù)本體的美學(xué)范疇。”[4]詩(shī)中“滿月”“樹巔”“暮色”“遠(yuǎn)山”等意象本就意蘊(yùn)深遠(yuǎn),在詩(shī)人的獨(dú)特組合下,呈現(xiàn)在讀者眼前的是一幅幽美的水墨畫。“金黃的稻束”的靜默在這幽美的空間里顯得比靜默更靜默,在這更靜默的情緒之中,“我們”真摯的內(nèi)心被守護(hù)著。“詩(shī)歌意象都是‘情‘景交融的產(chǎn)物,‘情與‘景都是不可分離的,即所謂‘景無(wú)情不發(fā),情無(wú)景不生。”[5]這首詩(shī)中的“景”與“情”是相互融合在一起的。沒有“景”,詩(shī)中的“情”無(wú)法表達(dá);沒有“情”,詩(shī)中的“景”無(wú)法呈現(xiàn)。詩(shī)中的“景”賦予了“情”更深刻、更悠遠(yuǎn)的表達(dá),“情”實(shí)現(xiàn)了“景”更具生命力的呈現(xiàn)。
“詩(shī)歌的結(jié)構(gòu)本身就是詩(shī)歌散文的釋義,它幾乎可以是任何性質(zhì)的邏輯話語(yǔ),可以表達(dá)適合于邏輯話語(yǔ)的任何內(nèi)容。”[6]對(duì)于鄭敏這首詩(shī)的結(jié)構(gòu),我傾向于將其分為兩部分,詩(shī)人是以遞進(jìn)的方式在表達(dá)其思想內(nèi)蘊(yùn)。詩(shī)中前半部分從第一句至“沒有一個(gè)雕像能比這更靜默。”是詩(shī)人以“金黃的稻束”的堅(jiān)忍形象引發(fā)個(gè)人對(duì)自我生命感覺的體驗(yàn)與思考,在這一部分中,詩(shī)人所采用的人稱代詞是第一人稱“我”“我們”,其指向于個(gè)人內(nèi)心的世界,而“我”至“我們”的人稱轉(zhuǎn)換也是情感遞進(jìn)的表現(xiàn)。后半部分則是詩(shī)人以“金黃的稻束”的人生態(tài)度啟迪關(guān)于社會(huì)歷史的哲理思想,詩(shī)人在這一部分使用的人稱代詞是第二人稱“你們”。其意在進(jìn)行一場(chǎng)“我”“我們”與“金黃的稻束”的無(wú)聲對(duì)話,這場(chǎng)無(wú)聲的對(duì)話既建立起“我”“我們”與“金黃的稻束”之間情感及思想上的聯(lián)系,又建立起詩(shī)人、讀者與“金黃的稻束”之間情感及思想上的聯(lián)系。只有在“我”“我們”與“金黃的稻束”對(duì)話的基礎(chǔ)之上,“我”“我們”、詩(shī)人以及讀者才能理解并領(lǐng)悟到“金黃的稻束”與“秋天”的無(wú)聲對(duì)話中所傳達(dá)的形而上的精神內(nèi)涵。鄭敏擅于將多重感官體驗(yàn)融合在一起,實(shí)現(xiàn)情感表達(dá)的多重可能,“割過的秋天的田里”,“割過”是觸覺上的體驗(yàn),卻能使人獲得聽覺與視覺上的想象,而“秋天”是視覺上的認(rèn)知,卻能使人產(chǎn)生觸覺與聽覺上的體驗(yàn)。詩(shī)人通過多重感覺互通的表現(xiàn)手法,豐富詩(shī)歌情感表達(dá)的內(nèi)涵與接受者多重感官體驗(yàn)。
關(guān)于詩(shī)人的斷句與標(biāo)點(diǎn)符號(hào)的使用,其特殊之處在于其中的哲思表達(dá)。詩(shī)人在詩(shī)中一共使用了四個(gè)句號(hào),其中三個(gè)句號(hào)是置于“靜默”之后,這一呈現(xiàn)絕不是詩(shī)人偶然的行為。整首詩(shī)是以“金黃的稻束”為中心,而“金黃的稻束”最重要的表達(dá)方式就是“靜默”,詩(shī)人也是以其“靜默”來(lái)傳遞核心的思想情感。三個(gè)句號(hào)呈現(xiàn)“靜默”的狀態(tài)是與外界隔離的自我內(nèi)心的靜思與沉淀,“靜默。靜默。”表現(xiàn)的是獨(dú)立于其他個(gè)體的自我彰顯,是站在曠野之中孤獨(dú)冷靜的思想者。鄭敏在斷句上也有其獨(dú)特的安排,“金黃的稻束站在/割過的秋天的田里”,“收獲日的滿月在/高聳的樹巔上”,“遠(yuǎn)山/圍著我們的心邊”,在謂語(yǔ)前后斷句,強(qiáng)調(diào)事物呈現(xiàn)的狀態(tài),給讀者更真實(shí)、更客觀的感受。“歷史也不過是/腳下一條流去的小河”,強(qiáng)調(diào)個(gè)人生命的感受不應(yīng)以歷史為評(píng)判的標(biāo)準(zhǔn),面向內(nèi)心的真實(shí),走向思想的深處才是個(gè)人生命力迸發(fā)的關(guān)鍵。詩(shī)人在詩(shī)中追求生活美學(xué)與藝術(shù)美學(xué)結(jié)合的語(yǔ)言呈現(xiàn),是詩(shī)歌語(yǔ)言內(nèi)涵與外延內(nèi)容上的整體表現(xiàn)。“語(yǔ)言具有語(yǔ)義和語(yǔ)音雙重屬性,前一種屬性是語(yǔ)言在比較固定的常規(guī)下對(duì)語(yǔ)言外物體的指涉,它構(gòu)成語(yǔ)言的意義;后一種屬性指的是語(yǔ)言本身作為一連串客觀物理聲音的存在。”[7]在鄭敏構(gòu)建的語(yǔ)言藝術(shù)世界之中,其語(yǔ)言所指涉的精神空間是雙重的,既能表現(xiàn)出現(xiàn)實(shí)生活的真實(shí)感受,又表達(dá)了超脫于現(xiàn)實(shí)生活之上的思想情感與精神內(nèi)蘊(yùn)。詩(shī)人在聲音與色彩上的處理為“金黃的稻束”的“靜默”呈現(xiàn)提供了視聽上的感官體驗(yàn)。“暮色”“滿月”所呈現(xiàn)的朦朧色彩,為“靜默”營(yíng)構(gòu)了具有藝術(shù)美感的意境,而“割過”“流去”所傳遞的消弭的聲音,是過往傳來(lái)的空響,為“金黃的稻束”的“靜默”留下了生命的余韻。“詩(shī)歌不會(huì)斤斤于邏輯的完美,卻非常在意從格律需要中悄然產(chǎn)生的那不確定因素的積極意義,仿佛生死攸關(guān)。”[8]鄭敏在這首詩(shī)中并不刻意追求其邏輯性的表達(dá),而其恰到好處的藝術(shù)形式為思想情感的表達(dá)提供了審美空間,使整首詩(shī)具有了某些不確定性的情感因素與思想因素,將詩(shī)中的思想情感提升至超越的精神領(lǐng)域?qū)哟巍?/p>
在中國(guó)新詩(shī)的平民化與貴族化論爭(zhēng)之中,有人提出新詩(shī)創(chuàng)作的理想追求是:創(chuàng)造出既包含平民化思想內(nèi)涵與貴族式藝術(shù)形式,又能得到受眾群體的普遍接受與認(rèn)同的詩(shī)作。這不僅對(duì)詩(shī)人而言是極具挑戰(zhàn)性的目標(biāo),對(duì)接受者與社會(huì)教育也有著較高的要求。在內(nèi)在精神與思想情感的表達(dá)上,從詩(shī)人鄭敏《金黃的稻束》這首詩(shī)中似乎可以窺見平民化與貴族化之間的融合互通。這首詩(shī)既沒有回避對(duì)現(xiàn)實(shí)生活的表現(xiàn),也沒有刻意在藝術(shù)形式方面設(shè)置圈套,而是以最真實(shí)、最動(dòng)情的方式表達(dá)詩(shī)人內(nèi)心深處的思想情感,且在藝術(shù)形式上具有其獨(dú)特的美學(xué)價(jià)值。在新詩(shī)發(fā)展的過程中,鄭敏《金黃的稻束》或許也可以稱得上是對(duì)上述的詩(shī)歌創(chuàng)作理想追求的嘗試與努力。但不可否認(rèn)這首詩(shī)對(duì)于普通讀者來(lái)說(shuō),在接受與理解上有其相對(duì)應(yīng)的難度。這首詩(shī)思想情感的表達(dá)不是直接的、外露的,而是隱匿在詩(shī)句的背后,需要接受者仔細(xì)品讀、反復(fù)體味,才能領(lǐng)悟其中所蘊(yùn)含的深意,才能與詩(shī)中站在曠野中的思想者產(chǎn)生情感上的共鳴與心靈上的交流。
注 釋
[1]孫玉石,中國(guó)現(xiàn)代詩(shī)學(xué)叢論[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0:526.
[2][美]約翰·克羅·蘭色姆著,王臘寶等譯,新批評(píng)[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15.
[3]趙毅衡,“新批評(píng)”文集[M].北京: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88:357.
[4]葉郎,中國(guó)美學(xué)史大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265.
[5]葉郎,中國(guó)美學(xué)史大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297.
[6][美]約翰·克羅·蘭色姆著,王臘寶等譯,新批評(píng)[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192.
[7][美]約翰·克羅·蘭色姆著,王臘寶等譯,新批評(píng)[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203.
[8][美]約翰·克羅·蘭色姆著,王臘寶等譯,新批評(píng)[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206.
參考文獻(xiàn)
[1]孫玉石.中國(guó)現(xiàn)代詩(shī)學(xué)叢論[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0.
[2](美)約翰·克羅·蘭色姆著.王臘寶等譯,新批評(píng)[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
[3]趙毅衡.“新批評(píng)”文集[M].北京: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88.
[4]葉郎.中國(guó)美學(xué)史大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5](美)布魯克斯.精致的翁:詩(shī)歌結(jié)構(gòu)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作者單位:湖南科技大學(xué)人文學(xué)院)